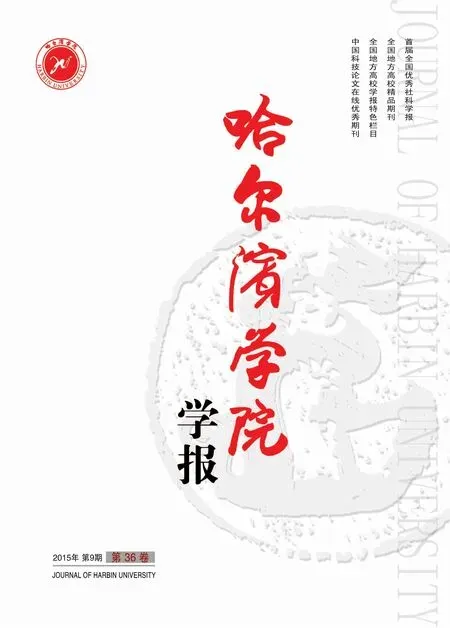王桐龄的日本观研究
霍耀林
(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吉安 3 43009)
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戴季陶、周作人等人,而对王桐龄等知之甚少。王桐龄作为京师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分别在20世纪10~30年代东渡日本留学考察,对日本有详细的考察记录,而这三个年代恰好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发展阶段。王桐龄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历史学学者,通过对他及他的日本观的研究,对全面透视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观有着重要作用。
一、王桐龄及其赴日经历
王桐龄,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字峄山,号碧梧,1878年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赵北口村,清末考取秀才,于1900年考入直隶大学堂肄业。此时,由于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陷入混乱。《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时变,于1902年1月下令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复校。责成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拟定学堂章程,章程历经多次修改于当年8月奏定颁行,即《钦定学堂章程》,章程颁布实施后,京师大学堂也马上着手招生开学事宜。经过两次招考,大学堂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
王桐龄通过两次考试于1902年底进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据《速成师范馆考选入学章程》,[1](P315)考选的方法分为八门: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数学、物理及化学、英论、日本文论。考试十分之六以上者方为合格,英、日文及代数可从宽录取。王桐龄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表明此前他接受的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科举教育,涉猎的新学应该对他帮助不小。
1903年底,张百熙等向朝廷上奏,称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乃不可缓之事,而教育乃基础,应当从培养教员入手,及早储备大学堂教习。“现就速成科学生中选得余棨昌、曾仪进、张耀曾、杜福垣、王桐龄……陈治安等共三十一人,派往日本游学,定于年内启程。”[2](P20)能够顺利入选赴日游学队伍,可见,王桐龄在京师大学堂一年的学习成绩应该是非常出色的。这批学生“志趣纯正,于中学均有根柢,外国语言文字及各种普通科学亦能通晓。大凡置之庄岳,假以岁时,决其必有成就”。可见,在出国之前,都已经学习了外语,对于各种普通科学也都已经有所了解,为出国留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批学生于1903年底顺利出发,张百熙亲自送行,由教习章宗祥护送前往日本。
1904年,《东方杂志》刊登文章,对于这批留学日本的学生的分科情况做了介绍,王桐龄被分到哲学科,以教育学为主。王桐龄随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部文科,第一高等学校被视为是东京大学的预科,修学年限为三年,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部分进入东京大学,王桐龄也于1908年顺利升入东京大学史学科,于1912年毕业。在东大留学期间,他曾受清政府之命,赴日本京都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提交给了留学生监督处,并随后以《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之名,在1910年的《中国地学杂志》和《教育杂志》上刊发。
1912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世凯任大总统,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也随之北迁。7月,蔡元培辞职,由范源濂接替教育部总长职位。范源濂曾任清末京师大学堂东文分教习、正教习服部宇之吉的翻译助教,王桐龄应该在京师大学堂时便与之相识,他也正是由范源濂电召而回到北京,并入教育部,任参事。11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课。范源濂于次年1月辞职,王桐龄也随之辞教育部之职,专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课。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学界风潮不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新增了一批教授,校园内各种思想非常活跃。1919年冬,校长陈宝泉被派赴欧洲考察教育,翌年归国后调往教育部任职。在此情况下,1921年春,由陈宝泉推荐,经教育部批准,王桐龄被再次派往日本留学,《东游杂感》正是记述了他这次赴日途中耳闻目见及到达日本后的感想。1922年7月,王桐龄从东京返回北京,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大学一年零四个月的留学生活。这一年多,他收获很大,除了《东游杂感》之外,另作成《中国历代党争史》《女真兴亡略史》《儒墨之异同》等著作。
回国后,王桐龄继续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员,此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在申请将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1923年7月,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正式成立,范源濂于11月1日出任第一任校长。王桐龄撰写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过去十二年间之回顾》,回顾了他自入校以来的点点滴滴,表现出了对学校深厚的感情。
1934年9月,中国国内纷争不断,王桐龄借机请假赴日考察,在两年的考察中,他旅行足迹遍及日本南北,对日本人文、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考察和体验,并且和自己之前两次在日经验进行对比,展示出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史。他身在日本,不忘祖国,时常将两国文化相比较,指出中日间文化上的差异。除此之外,他还于1935年5月21日至6月6日以教授的名义陪同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团体参观学校及教育机关(主要在东京市内外);1936年4月8日至4月20日陪同河北同乡康迪安参观产业组合,分别为:群马、新泻、石川、福井、滋贺、三重、爱知、静冈等。
1936年,《留东学报》第五号刊载有《本社社员王桐龄先生》简介的文字,其中说道:“前后四次渡日,在日本生活前后约十四年、对日本社会状況有明确的观察……任师范大学教授之职。”由此可见,王桐龄在日本生活应该有十四年之多。根据《东游杂感》的记述,1919年暑假,王桐龄曾应邀参加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夏季地理讲习会。由于史料原因,此次赴日详细不明。
二、20世纪10年代的日本观
1910年,王桐龄受清政府委派去日本京都视察。关于视察的目的尚不明确,但是他为留学生监督处提交的考察报告书《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后来发表在《教育杂志》1910年第12期上。从他的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日本观。
据文章载,这一时期,王桐龄一直居住在东京。1910年的京都视察也许是他第一次京都之行。他发现东京和京都完全不同,东京的建筑样式都是洋式或者和洋折衷式,而京都则都是和式。京都的裁判所、小学、古寺都是古代建筑,由此而感叹日本人善于守旧。东京的工厂机器皆由煤气运转,而京都则是由水力运转。东京属文明开化之中心,男子着洋服者多,而京都则很少。东京的女性劳动者多,而京都的女性则从事艺妓者多。东京的劳动者勤而奢,京都的劳动者俭而惰。东京的电车往返便利,而京都的电车迟滞。凡此种种,皆可看出东京之气象与京都不同,“东京处处振作长足捷步直追从西欧,而京都处处因循泄泄沓沓萎靡不振,犹有我国陈后主南唐李后主元顺帝明神宗时代之遗风”。[3]
以上是王桐龄初次在日本留学时所写,文章整体着眼于维新后东京之“新”与京都之“旧”,在他看来,东京活力四射,俨然已经成为维新的中心,成为了日本文明开化的代表,成为了现代化的都市。
从该文章的前记来看,他受政府之命利用学校假期赴京都考察。由此可以推测,他所着眼的东京与京都的“新”“旧”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决定,也有可能是政府的命令。和他后期的旅行记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日本观稍微有些主观,但是在清末,作为中国人,这应当是首次对日本东西两京进行的比较。
三、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观
1921年3月,王桐龄第二次赴日本留学,到翌年7月归国之前,他在日本实际生活一年半左右。《东游杂感》是他第二次赴日时所写的游记。据载,他是为《地学杂志》而写,发表后,被国内许多杂志转载,兴起一阵热潮。1922年,《东游杂感》的单行本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1928年再版时改为《日本视察记》。该书详细记载了王桐龄第二次赴日的经过,以及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各种经历。
1.20年代的朝鲜观
王桐龄第二次赴日经由朝鲜到达。此时距离朝鲜被日本合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朝鲜半岛对他来说是怎样的存在,他对于朝鲜人又有怎么样的认识?以此为参照,他的日本观或许会更加凸显。在他的论述中,日本作为朝鲜半岛的统治者,民族意气奋发,而朝鲜民族则相反,作为弱者,甚至每个朝鲜人身上都富于了弱者的气质。从这些看法不难看出他对日本人的感情。他并没有对作为弱者的朝鲜民族表示同情,相反对于列强日本却表示了赞赏。
鸭绿江是中国到达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那时,已经建桥,但日本人却在桥两边设置警察署,检查过往行人。对于中国人的检查并不严格,但是朝鲜人则必须获得警察署的出入许可,即使持有许可,也要进行盘问,如有任何出入,则没收许可,本人也被拘留。
当时,朝鲜三一运动已经过去两年,但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严格统治由此可见一斑。日本人满面精明气,朝鲜人满面忠厚气,日本民气发扬,朝鲜民气则相反。由此他认为征服之国与被征服之国,性格也不同。“朝鲜人富于猜疑心,阴险心,此亦弱者之恒有性也。……日本人好劳动,得钱即花。”[4](P26)王桐龄之所见或许为实,但他的日本认识却明显倾向日本,充满了对弱者朝鲜的批判。他在东京时,经过歌舞伎,看到了朝鲜艺者表演,他用刘禹锡的“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慨叹朝鲜人国土被日本侵占,却无一点救国意识。
1921年5月,王桐龄迁居到东京黑川家,其中住有两个中国人和三个朝鲜人。据他记述,中国留学生皆胸怀大志,按时上课,夜里也学习到很晚。而朝鲜人不论何时皆窝在家中,几乎不出门,白天用朝鲜语大声喧哗,晚上则与日本情妇幽会,他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批判朝鲜人不知亡国之恨。
2.日本民族特性
《东游杂感》也写到了日本人的国民性,但是在文中,并没有使用“国民性”一词,而是用了“民族之特性”,由此也可得知他是从民族这一视角出发来探索日本人特性的。他认为日本民族是由通古斯族、马来族、朝鲜族、汉民族等四大民族构成,特别是汉民族给日本带来了中国文化,对于教化日本人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最早和大和民族相融合。
实际上,日本民族特性、民族性、国民精神抑或是国民性等词均是从日本传来。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人先后渡日,派遣至日本的留学生也不断增多,关于民族性的研究也渐渐增多。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的日本民族性研究已经受到极大的关注,先后有戴季陶、王桐龄、许藻镕、谢晋青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王桐龄作为先行中的一人,其所起的作用当然不容忽视。
他首先认为民族性如同人的个性一样存在,而造成民族性产生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遗传;二是后天的环境教育。而日本本土由三个大岛组成,所谓的岛国根性当然也就会存在,但日本岛又不同于其他的岛屿:首先,地理气候不同;其次,日本自古受到中国儒家、道教和印度佛教影响;最后,日本人种由多数民族融合,其遗传性也不同。由此,三个原因导致日本民族性也非常复杂,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历史的考察和实际体验出发,认为日本民族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模仿性与没创造性;第二,服从性与妥协性;第三,敢死性与残忍性;第四,易感性与浮薄性;第五,淡泊性与孤僻性;第六,细密性与褊小性;第七,爱美性与浪漫性;第八,沉默性与现实性。[4](P38-76)
他认为日本民族所具有的这八个特性都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因为世界万物均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或许恰好就是王桐龄日本民族性研究的特征。
3.日本家族制度
王桐龄认为家族的起源始于农业时代的互助。他在承认进化论的同时,也接受了传统的夫妇是人伦之始的观念,认为家族制度是夫妇关系的开始。他认为日本的家族中也存在着男尊女卑,夫妇不平等现象。并认为日本的家庭主妇在家庭内实际上以主妇资格,兼领厨子、裁缝、打杂、买办、招待、会计、庶务及家庭教师等职。还认为日本的家族特色是离婚之容易。日本的风俗男尊女卑,家族的财产皆属于男子,离婚后男性可再婚,而女性的再婚则受社会非难。王桐龄认为日本夫妇关系不论是法律还是社会道德都是片面的。
4.关于中国和日本
在《东游杂感》中,王桐龄痛感“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命,竭全国上下之力,以调查我国国情,其所组织之社会团体:若东亚同文会,东亚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斯文会,启明会等,所处之杂志,若新支那,东洋,东洋学报,东亚研究,斯文,支那美术,东洋哲学,东亚之光,东洋学艺杂志等;凡我国之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备,交通,外交等诸要端,无不分门别类,详细研究”。[4](P222)出版之单行本堆积如山,对于我国国情了如指掌。相反,中国无知之人太多,对于世界、东亚、日本则一无所知。自称为聪明智慧之士或者以新人物自居者终日大声疾呼,痛斥日本之无礼,每天都高喊排日,而日本国情如何,如何抵制则一无所知。
确实,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向日本派遣数万留学生,但日本国情究竟如何,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个谜。王桐龄身在日本心系中国,他在强烈批判中国人的无知的同时,利用留学之机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亲自调查日本,撰写文章,介绍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桐龄的论述特别有意义。他不以日本国情调查为目的,但是却站在了日本调查的前沿。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祖国的关心。可惜的是,他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观
1934年9月,王桐龄以考察之名赴日。此时,王桐龄已经是国内知名教授,并且也已是知天命之年,和前几次渡日相比,这次赴日考察更加深入,所到区域以东京为中心,足迹也达日本关西、东北等地区,所到之处均有游记详细记录。游记的最后一部分基本上都附有自己的旅行感受。通过这些,不但可以再现30年代日本的情景,也可以反映出王桐龄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
1.交通便利、乘务员热情
王桐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游记中,几乎都写到了日本的交通工具。火车、电车、汽车的便利性、车掌的热情、处处为乘客着想的理念以及日本人的守秩序都给王桐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尾山游记》《日光游记》《东京附近观樱记》《环游伊豆半岛记》《吉野观梅记》《水户观梅记》等文章中认为日本的火车是做买卖,凡事为乘客着想,而中国的火车属于办公事,绝不为客人着想。旅游季节,铁道局也特意加开电车,迎送游人。而且车掌待客恭敬有礼,非中国车掌做梦所见。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到“火车煤烟可以搅乱市内空气,东京人口稠密,空气容易变坏,故开入东京市内之火车照例在市外卸下火车头,换上电车头,再开入市内”。[5]由此可见30年代东京的环境保护意识。日本旅客买票,上车皆按照先后顺序,不争先恐后;最大之车站,同时数处卖票,数路上车,秩序井然;赶不上第一次者,可以坐第二次、第三次;长途火车票,往返火车票可以通用两日以上,三个月以上。绝不会让乘客为难。旅客上火车是站上职员在入口处检票,下火车时在出口处收票,车掌只管维持秩序,车上并不查票,不似中国车掌带领许多武装巡警,用侦缉队捕盗形式,检察官问案之口吻,来向旅客索票。
2.女性参与社会、战争时期可在后防转用
王桐龄也注意到这一时期日本的汽车、轮船公司之卖票生、招待员皆女子,升降机之司机生亦女子,茶馆、饭馆、旅馆之堂倌也用女子,日间劳动之农人亦多女子,不似中国旧式女子,只会擦粉、带花、裹脚,也不似新式女子,只会烫头发、穿高跟鞋、听戏、看电影、逛公园。[6]由此可见他对日本女性的认识,他认为日本社会中多有女子活动,既可为社会服务,又可为家中挣钱,利人利己。事实还不仅如此,他认为汽车为战争时运输利器之一,而日本国民中能司机者多,则战争是可以收转运之效。而司机中,女司机也有不少,日本政府时时整军经武,作有备无患之预备。汽车之车掌概用女子,练习有素,一旦有战事起,男子征赴前敌,此辈女子即可在后防司转用。[7]在他看来,中国不论旧式还是新式女性,都非理想中的女性。而日本政府经略之武备,则给当时中国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可惜这些都未引起中国人的足够重视。
3.极力保护古迹、森林
日本人迷信神权,高尾山上松杉成林,概系善男善女奉献,有人保护,无人砍伐。不似中国人自私自利,全国多不毛之山,山上之树皆被砍伐。“中国社会系无秩序之社会……社会全体腐败,绝不能让一家单独生存,只好同归于尽尔。”[8]“吾侪老百姓只宜安之苦命,不必生气,且生气亦无用也。”[8]日本人保护森林,满山皆树,葱翠盎然。中国摧残森林,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树木斩伐殆尽。
4.儒教之国、礼仪之邦
王桐龄认为日本是儒教流行之国,重礼貌,崇谦让,凡火车、电车上满人时,有老人后上车,照例少壮者起而让座,妇人背负小孩子上车,也常有人让座,不似中国,先入者躺卧后入者罚站;也不似我国,老人上车,无人让座。“日本人极忙,自政府至一半劳动者全国合成一有机体,向同一方向进行。……盖公德心发达,凡事实事求是,负责任,守信用,不敷衍,不因循,不为一己个人私利,抹杀社会大家公益,不为口号,不为标语,不说虚话,不重宣传,此诚为我国民所宜取法,然亦绝非我国民短期内所能作到者也。”[9]
日本人能勤、能俭、能操作,男女老少皆能生产,无游手好闲者。日本人无架子,小车站之站长时常持帚自扫站台。不似中国站长官僚气重,大小事皆须唤人,自己之手绝不会动也。日本人又洁癖,火车到终点,电车,自动车回至车库时,即刻擦洗。女车掌忍苦耐劳之气概实不亚于男子,不似中国女子弱不禁风。日本人善于宣传,同时即为客人谋便利。“日本人好洁,故火车,电车,自动车内俱较为整洁。此非车掌维持之力与查房扫除之功,盖国民之习惯然也。日本人守秩序,凡多人聚集之地,绝不大声说话。”[10]日本人“爱国心,爱社会心之强,守秩序,重公益心之勇,非自私自利之中国国民所能梦见”。日本为儒教国,其社会习惯,亲亲,贵贵,尊贤,尚齿,平素优待老人。日本多山、多水而少平原,除去水灾,旱灾,虫灾,雹灾以外,尚加上震灾,风灾,冷灾得于天者独薄,人人奋勉,男女皆克勤克俭,有嗜好者极少,故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而且日有进步。[7]
5.反面的中国和中国人
与对日本及日本人的赞美之言相比,将王桐龄所描述的中国称之为日本的反面似乎也不为过。他认为中国人所称小鬼之日本,为历史上之日本,时至今日,已经完全不同。东京面积比北平大4倍,东京人口比北平多3倍。工业之发达,商业之繁盛,经济力之集中,亦压倒上海、广州、天津。建筑之庄严伟丽,道路之宽大整洁非中国可比,……有志者宜发奋求自强耳,勿得以一骂了之。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国民闭塞,对于外省,外府人往往含有歧视之意。而日本则开通,对于外国人与以平等待遇,不巴结,亦不欺侮,与中国从前之排外,现在只媚外迥乎不同。“九一八为日本国难纪念日,各处开会演说,到处游行,健忘之我国国民,从前之口号标语,所谓打倒……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者,何以噤若仗马寒蝉,屁都不敢放也。”[9]“九一八”之际,王桐龄所看到的日本到处都是开会演说、游行,本来是中国的国难纪念日,居然在日本成为了日本的国难纪念日,面对这讽刺性的局面,王桐龄表达了自己极大的愤慨,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认为中国人只顾自己,不顾国体公益,与此等国民谈自治,多见其不能成功也。
以上可以看出王桐龄在20世纪前三个年代所关心的焦点虽然不同,许多地方甚至也有矛盾,但其中也不乏一贯性。通过对他的赴日经历及他的日本观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他在三个不同年代的日本观的变化轨迹。透过王桐龄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变迁过程。
从20世纪10年代的稍显主观性的日本观向二、三十年代的历史的、全面的日本观发展。第一次在日期间,他利用假期去京都考察。在短暂的时间中就注意到东京与京都的“新”与“旧”,这些从建筑样式等直观的观察来看也并非不可,但是在短暂的时间中观到人的意识的“新”与“旧”恐非易事。而二、三十年代在日期间,他所关注的点不断增加,从日本人到日本的国家、生活、环境意识等各方面均有涉及,而且对于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也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
随着在日本生活时间的增长,王桐龄对日本的感情也在不断加深。从第一次京都旅行的稍微主观的、简短的、片面的论述到二、三十年代全面深入的论述;从单纯的东京生活到后来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他对日本的批判逐渐减少,相反的对于中国和中国的批评却不断增加。此时正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正在处于大正民主期和二战前夜的日本,想来并非没有批判之处,想必这些都是王桐龄有心之选。
王桐龄的日本观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深入。他在关注日本的同时,也和中国相比较,将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祖国。王桐龄的日本观随着时期不断变化的同时,其作为中国人对祖国的关心则是始终如一的。他从日本的风土人情、风俗文化、社会构造、民族特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将之介绍给中国。他强烈呼吁中国人应该将注意力投向一海之隔的邻国日本,并为中国人努力向日本学习而大声疾呼。他比普通的中国人更加深入了解日本,在指出日本和日本人的优点的同时,强烈批评中国及中国人的盲目自大。他尽可能的收集日本的相关资料,将同处东亚的日本介绍给中国;他以日本为参照,在否定中国人的劣性的同时,不惜大量笔墨反复强调日本人的优点,为中国人忽视日本而大声疾呼。
[1]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王桐龄.日本东西两京之比较[J].教育杂志,1910,(12).
[4]王桐龄.日本视察记[M].文化学社,1928(2).
[5]王桐龄.高尾山游记[J].文化与教育,1934,(39).
[6]王桐龄.日光游记[J].文化与教育,1934,(38).
[7]王桐龄.环游伊豆半岛游记[J].文化与教育,(45).
[8]王桐龄.高尾山游记[J].文化与教育,1934,(39).
[9]王桐龄.游东通讯(三)[J].文化与教育,1934,(34).
[10]王桐龄.水户观梅记[J].留东学报,19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