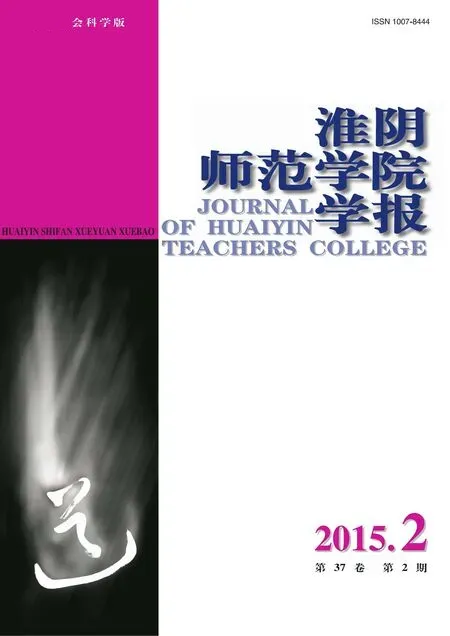限定摹状词两种用法的区分及语义学两可性
朱耀平, 钱 承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唐奈兰对限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的区分,自它产生之日起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语义学意义这个核心问题上。首先对限定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是否意味着有关语句具有语义学上的两可性提出质疑的是克里普克的《说话者指称与语义学指称》(1977年)一文。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韦茨坦(Howard k.Wettstein)与萨蒙(Nathan U.Salmon)之间展开的。前者坚持认为唐奈兰所作的区分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后者则站在格莱斯和克里普克的立场上,认为摹状词的两种用法的区分只具有语用学意义,而不具有语义学意义。这场争论虽然没有最终的定论,但却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摹状词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一、唐奈兰对限定摹状词两种不同用法的区分
罗素在以《论指称》(1905年)为代表的论著中基于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分提出的摹状词理论,标志着分析哲学的诞生,甚至被称为“哲学的典范”。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摹状词不同于专名,不起指称某个对象的作用。斯特劳森的《论指称》(1950年)一文第一次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出系统的批评。在斯特劳森看来,无论是专名还是摹状词,只有通过与它们有关的语句的具体使用才能发挥指称作用,就它们本身来说并不具有指称某个对象的作用,像罗素那样把是否指称某个对象作为划分专名与摹状词的标准是错误的。唐奈兰在《指称与限定摹状词》(1966年)一文中则认为,无论是罗素还是斯特劳森都没有对摹状词作出正确的说明,因为他们二人都不懂得根据语句的具体使用来判断其中的摹状词究竟是起指称作用还是起归属作用。
在唐奈兰看来,在某个语句的具体使用中,其中的摹状词究竟是起指称作用还是起描述作用取决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该语句。换言之,即使在语句的具体使用中,其中的摹状词也不像斯特劳森所认为的那样必定起指称作用,它完全有可能只起描述或归属的作用。唐奈兰与罗素和斯特劳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主张根据语句的具体使用场合来判断其中的限定摹状词究竟是起归属作用还是起指称作用。
根据唐奈兰的看法,摹状词的归属作用与指称作用的区别在于:“在一个论断里以归属的方式使用一个摹状词的说话者,谈论的是一切具有如此这般之性质的人和物。另一方面,一个以指称的方式使用摹状词的说话者则希望他的听众能够知道他正在谈论的是哪个人或哪个事物。”[1]451这就是说,在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中,说话者谈论的是任何符合摹状词所描述的性质的人和物;但是,在它们的指称性用法中,摹状词仅仅是引起对某个特定的人或事物注意的工具。举例来说,假设善良正直的史密斯先生被人杀害了。如果某人面对史密斯被杀的惨状在不知道凶手是谁的情况下发出感慨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谁,只要他杀害了史密斯先生,他就是疯狂的。这是对限定摹状词(“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的归属性用法。另一方面,假定琼斯因史密斯谋杀案而受审,而说话者是审判厅里的旁听者之一。了解到被告席上的被告的野蛮行为后说话者可能会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那么,他是特指琼斯这个人是疯狂的。这是对限定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
唐奈兰认为,通过考虑“不存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对摹状词的上述两种不同用法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两种用法之间的区别。无论是对“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还是指称性用法,都预设或蕴涵了那个凶手的存在。但是,如果史密斯先生实际上是自杀的,因而并不存在杀害他的凶手,那么,对于“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词的两种不同用法来说,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归属性用法来说,如果没有凶手,那么“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就成为一句无真假性可言的话。斯特劳森所说的对语句的虚假使用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指称性用法来说,即使结果证明我们正在谈论的琼斯并非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我们也仍然可以谈论他是否是一个疯狂的人。
二、克里普克对限定摹状词语义学两可性的质疑
唐奈兰对限定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的区分引起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唐奈兰所作的区分“仅仅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还是“不仅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上。
唐奈兰本人否认他所作的区分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他在谈到“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时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无论是以指称的方式还是以归属的方式使用那个摹状词,包含这个摹状词的语句都具有相同的语法结构:这也就是说,这个语句在句法上并不是两可的。假定这个语句所包含的语词的涵义具有两可性,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个语句看来在语义上并不是两可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语句在语用上是两可的,在那个摹状词所起的两种作用之间的区别是说话者的意向的功能)。当然,这些都是直觉上的看法;我并没有对这些结论作出论证。不过,进行证明的负担无疑落在另外一方。”[1]464
但是,克里普克认为唐奈兰的这段话与后者的那篇著名论文(《指称与限定摹状词》)的整体趋向“不相容”[1]489。唐奈兰一方面否认“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个陈述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同时又认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仅仅对摹状词的归属性而非指称性的使用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克里普克认为唐奈兰的这个说法是“不融贯的”,因为可以对之作出分析的并不是语句的使用,而是语句的涵义。“如果语句(在句法上或)在语义上不是两可的,那么,它就仅仅有一种分析;认为它具有两种相互区别的分析这种说法便把句法上或语义上的两可性归之于语句了。”[1]489克里普克的意思是说,虽然唐奈兰口头上否认包含限定摹状词的语句可能因为摹状词具有不同用法而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自觉地认为那样的语句确实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即那个语句的意义会根据其中的摹状词是起归属作用还是起指称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唐奈兰有意无意地设定摹状词在语义上的两可性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日常语言交流中的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即在对象与摹状词不相符合的情况下,该摹状词仍然被用来指称这个对象。例如,即使琼斯并不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摹状词来指称他。因此,这个摹状词对唐奈兰来说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是“任何一个杀害了史密斯的人”,另外一种意义是“这个被认为杀害了史密斯的人”。
与唐奈兰不同的是,对罗素来说,摹状词并不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不论是以归属方式还是以指称方式使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摹状词,“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个句子的意义都是“有且只有一个人杀害了史密斯,这个人是疯狂的”。
但是,如果要坚持罗素对摹状词的意义的上述这种单一性解释,那它就必须对摹状词或名称可以用来指称与它们不相符合的对象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作出解释。克里普克认为,包括罗素摹状词理论在内的任何一种单一性理论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一般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那种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对专名和摹状词的“语义指称”(semantic reference)与“说话者指称”(speaker's reference)加以区分。关于“语义指称”,克里普克的解释是:“如果一个说话者在个人言语中有一个指示词,那么,这种言语中的某些约定便能确定出该指示词在这个人的言语里的指称,我们称之为该指示词的‘语义指称’。”[1]492至于“说话者指称”,克里普克所下的定义是:“说话者(在某个给定的场合)想要谈论并且自认为它满足称为该指示词的语义指称而应具备的条件的那个对象。”[1]492-493例如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个例子中,在琼斯不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的情况下,琼斯虽然不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的语义所指,但在某个具体的说话场合,它却可以作为“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的说话者所指。
总之,在克里普克看来,虽然唐奈兰表面上否定摹状词在语义上的两可性,但他的实际做法却是主张摹状词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并以此反对罗素的单一性理论。克里普克认为,唐奈兰用语义上的两可性加以解释的那种似乎很令人费解的现象不难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即对指示词的“语义指称”与“说话者指称”的语言学区分得到解释。设定语义上的两可性是不必要的,而且语义上的两可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专名的使用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例如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可以用“琼斯”来指称史密斯。既然语义上的两可性作为对它试图加以解释的那种特殊现象的解释“既是不充分的又是不必要的”,那么就不应当设定这种语义上的两可性。
三、韦茨坦对限定摹状词语义学两可性的辩护
克里普克并不否认限定摹状词像唐奈兰所说的那样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但他反对用语义学上的两可性来解释摹状词的这些不同用法,或者说,他认为包括限定摹状词在内的指示词的两种用法之间的区分只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
但韦茨坦在他的《指示性指称与限定摹状词》(1981年)一文中表达了与克里普克不同的看法。根据前者的看法,“这个F是G”这样一个语句的内涵和真值条件,会根据其中的限定摹状词“这个F”是起归属作用还是起指称作用而有所不同,即“这个F是G”这个语句确实具有语义上的两可性,而不是像罗素或克里普克所认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一种涵义、一种真值条件。
在克里普克等人看来,尽管摹状词具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但只有唯一的语义内容,即能根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加以分析的内容。按照这种看法,在“这个F是G”这样一个语句中,不管其中的摹状词“这个F”是起归属作用还是起指称作用,它作出的都是下列这样一个命题:“有一个且仅有一个F,并且这个F是G。”如果使用唐奈兰的例子,那么,不管我们是以指称方式还是归属方式使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它都具有下列这样一种涵义:“有且只有一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并且他是疯狂的。”这样的话,就看不出在说话者知道凶手是琼斯或者在他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的情况下,上述这句话的涵义会有什么不同。
韦茨坦同意唐奈兰的看法,认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作的上述语义分析也许对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对于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来说则肯定是不合适的。按照罗素的说法,“这张桌子上堆满了书”的意思是,“有一张且只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堆满了书”;并且只要确实存在着一张上面堆满了书的桌子,这个句子就是真的。但这种分析显然是错误的[2]。原因在于,在上面这个句子中的“这张桌子”是以指称的方式来使用的,上面这个句子的意思仅仅是说:说话者所谈论的那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并且只要那张桌子上确实堆了很多书,那么那个句子就是真的。
在韦茨坦看来,罗素等人的看法忽视了下列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所谓的“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s)其指称往往是不确定的,严格来说,应该把它们称为“不确定的限定摹状词”(indefinite definite descriptions)或“不完全的限定摹状词”(incomplete descriptions)[2]。
韦茨坦认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无法说明我们如何能够使用“不确定的限定摹状词”作出一个具有“确定的”内涵的命题。世界上的任何一张桌子都可以被称为“这张桌子”,那么,当我们说“这张桌子上堆满了书”时,我们指的究竟是哪一张桌子呢?
当然,罗素会和韦茨坦一样认为说话的语境会告诉我们说话者指的究竟是哪张桌子,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语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过程中,语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罗素等人看来,语境的作用在于将语句中的“不完全的”“缩略的摹状词”补足为“完全的摹状词”,例如,将“这张桌子”补足为“在这栋大楼的209房间的桌子”“这张在说话者的面前的桌子”,等等。然而,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更完全的摹状词之中,哪一个是真正“捕获”了说话者的意图的摹状词呢?说在日常语言交流中的“听者”被迫在那些不同的罗素式的摹状词中进行选择,以便“捕获”说话者的意图,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韦茨坦认为,那种把“不确定的限定摹状词”看作具有唯一指称的摹状词的缩略语的看法是错误的。
从以上所述中不难看出,韦茨坦与罗素等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根据韦茨坦的看法,限定摹状词的指称通常是不确定的,并且我们无法通过对限定摹状词的罗素式的改写来达到将它的指称确定下来的目的。换言之,当我们以指称的方式使用一个限定摹状词时,这个摹状词的指称只能通过语境来确定,而无法通过代之以一个罗素式的“完全摹状词”的办法来确定;并且语境对限定摹状词的指称对象的确定是直接的,而不是通过给出罗素式的摹状词来进行的。
总之,在韦茨坦看来,当“这个F是G”中的限定摹状词“这个F”起指称作用时,它的指称对象直接由说话者的意图和说话时的语境来决定,它并不作为罗素式的完全摹状词的缩略语起作用。当然,这并没有否认当“这个F”起归属作用时,“这个F是G”这个语句的语义和真值条件能够用罗素摹状词理论提供的方法进行分析。因此,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F”这个摹状词的情况下,“这个F是G”这个语句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真值条件。这就是韦茨坦认为限定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具有语义学上的两可性的理由和根据之所在。
四、韦茨坦与萨蒙关于限定摹状词两种用法区分的语义学意义争论
自从斯特劳森《论指称》(1956年)一文发表以来,区分语言表达式本身的意义与它们在具体的使用中的意义,逐渐成为一种思想潮流,语用学大有取代语义学成为语言哲学主流的趋势。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甚至唐奈兰本人也明确声称他对摹状词的两种用法的区分只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格莱斯对“说话者意谓”(utter's meaning)与“语句意蕴”(sentence meaning)的区分,克里普克对“说话者指称”与“语义学指称”的区分,进一步扩大了上述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韦茨坦却大张旗鼓地宣扬摹状词的两种用法的区分的语义学意义,这多少有点逆思想潮流而动的味道。可以预见的是,一定会有不少人站在格莱斯和克里普克的立场上反对韦茨坦的看法。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而萨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韦茨坦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上发表《指示性指称与限定摹状词》(1981年)一文的次年,萨蒙便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断言与限定摹状词》(1982年)一文,对韦茨坦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评。
萨蒙认为,韦茨坦关于限定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的区分的语义学意义的主张实际上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那些包含摹状词语句具有语义学上的两可性,即那个语句根据其中的摹状词是起归属作用还是起指称作用而或者表达一个普遍命题,或者表达一个单称命题。”[3]这就是说,根据韦茨坦的看法,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区分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会造成无论从内容上来说还是从真值条件上来说都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就拿“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来说,如果我们以指称的方式使用这句话,把“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作为琼斯的指示词,那么,在琼斯确实杀害了史密斯并且是疯狂的情况下,上面这个命题显然是真的。而在“琼斯虽然是疯狂的,但他并没有杀害史密斯”那样一个可能世界中,“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作为对那个可能世界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如果在那样的世界中说出那样一个语句,那么,它将是一个错误的或缺乏真值的命题。尽管如此,就那个句子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说(即“琼斯是疯狂的”),它在那样一个可能世界中仍然是真的。因此,在“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个摹状词在实际世界中指示的个体是疯狂的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那个单称命题都是真的[4]。当以归属方式说出“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时,它的意义绝不是上述那个单称命题:琼斯这个人是疯狂的;而是下列这样一个普遍命题:“有且只有一个人杀害了史密斯并且那个人是疯狂的。”在琼斯杀害了史密斯并且他是疯狂的情况下,这个普遍命题将与那个单称命题一样是真的。但是,在琼斯虽然是疯狂的但并没有杀害史密斯的情况下,这两个命题的真值之间的不同就会显现出来。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只要琼斯是疯狂的,那么即使他没有杀害史密斯,“琼斯是疯狂的”这个单称命题也是真的。与此不同的是,普遍命题“有且只有一个人杀害了史密斯并且那个人是疯狂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假的(或没有真值)[4]。
那么,摹状词的不同用法是否真的会造成两个无论从内容上来说还是从真值条件上来说都完全不同的命题呢?萨蒙认为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没有人会否认,当我们以归属方式使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时,它表达的是一个普遍命题,这个命题在“有且只有一个人杀害了史密斯,并且他是疯狂的”情况下是真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以指称的方式使用该语句,那么它是不是就成为关于琼斯的单称命题?萨蒙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是否具有语义学意义的问题。
那么,不完全摹状词是否会造成有关被指称对象的单称命题呢?萨蒙认为在这里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句子包含指示代词或其他易受语境影响的词,那么它将根据使用语境的不同而表达一个不同的命题,即这个句子的语义学内容相对于使用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但就“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句子而言,其中的限定摹状词“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一个其内涵相对固定、对语境的变化“不太敏感”的指示词,因此这个句子的语义学内容也就并不完全由语境决定,而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一般来说只能用来指称被认为确实杀害了史密斯的人,在明知琼斯不是杀人凶手的情况下仍然把他称为“杀人凶手”是不妥当的,这种做法不具有语义学上的合法性,而顶多只具有语用学上的有效性。因此,萨蒙认为,韦茨坦所坚持的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只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与一个语句的语义学意义相比,它在语用学上的意义更加错综复杂、灵活多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在琼斯不是杀人凶手的情况下用“这个杀人凶手”来指称他(在语用学的意义上)。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以指称的方式使用“这个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疯狂的”这样一个语句的情况下,它表达的并不一定是某个单称命题,它完全有可能用来表达一个普遍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完全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不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而只具有语用学上的意义。韦茨坦关于“摹状词的两种不同用法会造成两个无论从内容上来说还是从真值条件上来说都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不难看出,萨蒙在这里所采取的分析方法,就是斯特劳森、格莱斯和克里普克等人所倡导的对某个语句的“说话者断言”与“语义学内容”加以区分的方法。萨蒙认为,韦茨坦关于摹状词的两种用法的区分的语义学意义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语句的“说话者断言”与“语义学内容”。他这样写道:“与唐奈兰一样,韦茨坦没有对‘说话者断言’与‘语义学内容’加以区分。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它们的具体使用中,那些语词的语义内容是什么。表明某个人通过对语句的指称性使用作出了一个相关的单称命题并不能证明指称性用法的语义学意义。因为说话者可能同时也作出了一个相关的普遍命题。在任何情况下,问题都不在于说话者想要说什么,而在于他的话表达了什么样的语义学内容。”[3]简而言之,韦茨坦的错误在于把说话者通过某个语句所作的“说话者断言”与这个语句的“语义学意义”混为一谈,萨蒙将这种错误称为“实用主义的谬误”(The Pragmatic Fallacy)。
作为对萨蒙批评的回应,韦茨坦在《指称—归属用法区分的语义学意义》(1983年)一文中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韦茨坦坚决否认在他的理论中包含萨蒙所说的“实用主义谬误”,因为他本人“并不认为由于说话者表达了一个单称命题,因而这个命题就是他可以根据语义学规则得到的命题”[4]。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把说话者通过某个语句所作出的“说话者断言”作为这个语句包含的语义学内涵来看待;他只是认为当摹状词以指称的方式使用时,它“传达”了一个与在摹状词以归属的方式使用时完全不同的命题。
韦茨坦认为,他之所以提出关于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的语义学意义的理论,不过是基于以下这个简单的想法:既然包含指示性术语的句子可以决定一个单称命题,不管这个术语是像专名一样没有任何内涵(如“这”“那”等)还是像“她”一样具有一定的描述性内涵,那么,当限定摹状词起指称作用时,它是否也能像指示词一样起作用呢?认为指称性摹状词确实能起这种作用,就为“如何通过一个在语义学上不确定的语句表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命题”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4]。韦茨坦认为,他并没有因为上述这种考虑而把通过摹状词的指称性用法表达的命题(即萨蒙所谓的“说话者断言”)看作符合包含那个摹状词的语句的语义学规则的命题,因此指责他的理论包含着“实用主义的谬误”是对他的理论的误解。
但萨蒙似乎并没有被韦茨坦所说服。在《实用主义的谬误》(1991年)一文中,他坚持认为在韦茨坦的理论中包含着下列这样一种谬误:即把说话者通过某个具体表达式的使用实现的某种言语行为上的目的,看成那个表达式在说话者所处的语境中的语义学功能,即没有把使用某个表达式实现的言语行为上的断言或指称与那个表达式的语义学规定严格区分开来[5]。
对于韦茨坦与萨蒙之间的这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虽然很难说出一个谁是谁非,但毫无疑问,它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于“限定摹状词两种用法的区分是否具有语义学意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堪称通过学术争论取得理论进步的典范。
[1] 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Howard K Wettstein.Demonstrative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J].Philosophical Studies 40,1981:241-257.
[3] Nathan U Salmon.Assertion and Incomplete Definite Descriptions[J].Philosophical Studies 42,1982:37-45.
[4] Howard K Wettstein.The Semantic Significance of the Referential-Attributive Distinction[J].Philosophical Studies 44,1983:187-196.
[5] Nathan U Salmon.The Pragmatic Fallacy[J].Philosophical Studies 63,1991:8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