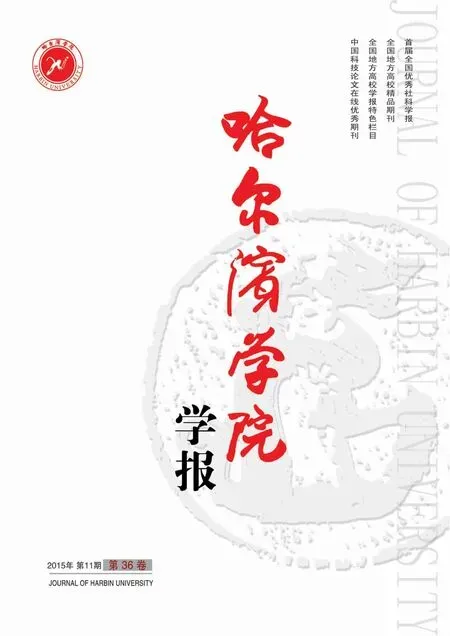藏书楼型变的传播学观照
魏秀萍
(兰州文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中国古代藏书楼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于清末型变为近代图书馆,不啻为社会文化传播发展的原始记录,也反映出中华文化传播及流变的历程。藏书楼随着历史进程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直至衰落,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与嬗变。在此变身过程中,藏书楼充当了奠基人的角色,对促进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明清时期藏书楼为典型代表,对其转型期变身近代图书馆的前因进行透视,以传播学的视域观照探析藏书楼重构的国内外历史动因及其产生的传播作用,并进行了现状考察与反思。
一、西方图书馆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时,不能忽视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他们来华创立教会大学图书馆,传播西方公共图书馆管理理念。在明清时期,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嬗变中起到了启蒙示范作用,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和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传教士译书传播西方图书馆思想
西方图书馆文化传入中国,但发端于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为传教服务的宗旨下,翻译传播了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与古代藏书楼大不同的西方新式图书馆理念。17世纪,艾儒略传教士在其中文译著《职方外纪》(1623年)中最早向我国介绍了欧洲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他说:“欧逻巴(欧洲)诸国皆尚文学”,“其诸国所读书籍,皆圣贤撰著,从古相传,而一以天主经典为宗。既后贤有作,亦必合大道,有益人心,乃许流传。国内亦专设校书官,看详群书,经详定讫,方准书肆刊行。故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卷,毋容一字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1]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有关西方图书馆最早的中文翻译介绍。伦敦的马礼逊是19世纪后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他在《外国史略》(1807年)中多处记载了西方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情况,比如,“葡萄亚国”(葡萄牙):“书院积书八万本”;[2](P25)“荷兰国”:“国内大开书院,学士云集,讲术艺,小学馆二千八百余处,大书院四处,皆聚印翻译之书”;[2](P27)“佛兰西国”(法国):“其都曰巴利(巴黎)城,……所藏古今书籍,计八十万册,此国都以内之情形也”。[2](P30)美国传教士祎理哲在《地球说略》中记述:“‘佛兰西’(法国)藏书之室极广大,所藏卷帙约计数十万本”;“以大利”(意大利):“藏书之富,是国为最著名。至其书从何而来,约系古先知辈所流传也”。[3](P14)该书还特别介绍了当时的读书风气及藏书,以及图书馆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亚利曼列国”(日耳曼国):“此国不知学习者,千人中不过一人,不能书写者,千人中不过五六十人。卖书之人,缚之背上,载之马车,周行各处以相售,城内多藏书之室,每室所藏约数十万卷。倘有愿读其书者,不拘何人,尽可入内披读。”[3](P17)美国的传教士戴德江在《地理志略》中记述:“‘欧逻巴’(欧洲)各处人民性情灵敏,知礼达义,开设学堂,不识字者甚少,著书籍,印新报,立阅书室,看画阁,俾人随意观览,以广见闻。”[4](P8)“俄罗斯”(俄国):“论大城京都名散备德伯(圣彼得堡),居民约九十万,内有皇宫阅书室,皆巍峨宏敞,修饰尽善。”[4](P9)“瑞典挪威”:“论大城京都在西兰岛上名哥笨哈根(哥本哈根),居民约二十四万,中有著名之书院,雄壮可观,又有阅书室,所藏之书籍约五十万卷。”[4](P9)“德国”:“论大城京都名伯林,居民约一百十万,……中有最著名之书院,又有阅书室,内藏之书约六十万卷。靠哀勒伯河有大城名罕伯(汉堡),巴斐利亚(巴伐利亚)之京城名门中有书院、书室、画阁,皆整洁宏丽。”[4](P10)“法郎西”(法国):“论大城京都名巴利(巴黎)”,“其内宫殿、画阁、阅书室、大书房,皆高大壮观”。[4](P12)美国传教士高理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记述:“国人于礼拜日皆不工作。故设一会所逢礼拜日教人,内藏书极多,如不在者亦可借回家自习至礼拜日复送回。”[5](P44)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城中文学最盛,书楼数所,内一楼藏书二万五千本,各楼共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官吏士子皆可就观,惟不能携归而已。”[5](P12)19世纪80年代后,传教士所撰写的著作如英国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和美国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等书,均用以传播西学及公共图书馆理念,对当时生活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无疑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且是明清藏书家们认识西方图书馆最原始、最珍贵的材料,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构建。[6](P29)
(二)“西学东渐”传播开放图书馆理念
“西学东渐”使得传教士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介,引起国人极大的读书、学习热潮,无形中对中国古代藏书楼“藏而不用”“藏而轻用”的观念产生强烈冲击。“西学东渐”是中国藏书楼衰落的原因之一。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引进大量西方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尼阁。金尼阁曾于明代两次来华,1614年,他遍游比利时、法、德等国家,募集到大批图书。除教皇所赠7 000余部图书外,从各国各界募集到的图书超过10 000部,除宗教类外,自然科学及其他文化书籍占有较大比例。金尼阁表示:无论就数量、学术门类、装帧而言,他所收集的图书,在耶稣会中还没有可与他抗衡的。就学科门类来说,除我们图书馆的哲学类、人文类、教义类、神学类及其他名著外,他所搜集的音乐类、法学、医学等图书也很多,而教学类书籍则应有尽有。这样门类齐全、数量庞大的欧洲书籍主要收藏于北京教会图书馆,因此,北京教会图书馆就成为明朝中国最大的西书图书馆。金尼阁还拟定了译书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等中外人士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后来部分西书也分散到西安、山西、杭州和嘉定等国内其他地方。1651年,汤若望从欧洲带来个人藏书3 000余卷;1720年,嘉禄主教携来包括国法、伦理、教律、教典、神学及史学等大批图书。所有这些较早传入中国的西书,经翻译产生了我国最早一批西方科技书籍的中译本,无疑为了解西方打开了窗口,为创办教会图书馆奠定了物质基础。传教士引进西方文献在晚清达到高峰。1807年,马礼逊是伦敦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1811年,他于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序幕。此后,传教士们开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办学校传播西学。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文献32种,重要的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贸易通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这些书刊成为魏源、林则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西书输入,已经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1815年,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创办了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创立的报刊越来越多。据统计,19世纪40-90年代,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170种,约占同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六合丛谈》《中外新报》《教会新报》《格致汇编》等。对我国报刊的产生、文化典籍的丰富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有一定启迪、示范意义;特别是在传播开放图书馆理念、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方面影响深远;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学、促进传统封闭的藏书楼向近代开放图书馆转型与嬗变的传播作用。[5](P30)
(三)公共图书馆模式输入——示范传播活动
19世纪,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是具有近现代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的重构与创建,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和严厉的禁教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才在中国陆续创办学校及图书馆,从而开启了中国藏书楼走向近现代图书馆的历程。1847年,藏书丰富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一度成为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藏书中心。据胡道静在20世纪30年代记载:“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是一所广敞的二层屋子,下藏中文书,上藏西文书。”[7]其中,中文书约12万册,西文书8万册。而徐家汇一带各教会组织及博物院、天文台、徐汇师范、徐汇公学等都设有专门的图书馆,合计存书计30万册左右。1849年,上海英租界的西方侨民自发组织了“书会”,1851年改名为“上海图书馆”,后由“私立”转向“公立”,到20世纪20年代末更名为“工部局公共图书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成为一所较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公共图书馆。[7]1871年,英国伟烈亚力牧师创办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收藏了东南亚和中西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艺术、宗教等各方面图书,曾被认为是“在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8]到20世纪30年代初,馆藏书总约1.6万册,虽然藏书规模不大,但采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等先进的图书馆分类管理方法,是较早的专门图书馆。1874-1901年,英国傅兰雅传教士和华人徐寿成立了“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从事翻译工作,向华人开放,“是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7]各教会大学都设立图书馆,重视馆藏建设,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新型图书馆的新观念、新模式。西方的办馆模式开放、藏书结构多样化、图书分类编目法先进,最重要的是注重为读者提供服务的职能,这一系列示范传播活动,加大了对公共图书馆办馆理念在中国的影响,开启与加速了明清封闭的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型的历史进程。[7]
总之,西方图书馆文化的传播,在中国藏书楼变身近代图书馆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译书介绍到思想理论的传播,再到真实图书馆模式建立的示范传播活动,在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演变过程中,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有相当部分理论观念和制度建设都间接或直接的与西方传教士有关,因此,影响意义深远。
二、中国清廷新政“维新派”公藏理论实践公共图书馆运动
从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来看,维新时期正是西方图书馆理念传入我国的时期,清末新政也是公共图书馆运动兴起的时期。中国近代开明士绅有关藏书公共的倡议、理论主张和实践得益于晚清国门开启后,以及对西方公共藏书制度的认识、领会和借鉴。因此,“维新派”为促使清末藏书楼型变为近代公共图书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维新派”公藏思想主张开放的图书馆藏书体制
晚清,王韬认为清嗜古力学之士虽“雅喜藏书”,但“皆私藏而非公储”,“若其一邑一里之中,群好学者输资购书、藏庋公库,俾远方异旅皆得人而搜讨,此惟欧洲诸国为然,中土向来未之有也”。[9]他曾感慨道:“夫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私家之书积自一人,公所之书积自众人。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萃于公,则日渐其多而无虞其散矣。……不佞尝见欧洲各国藏书之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于连尾充栋,怀铅椠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学之所以日盛也。”[10]李端棻上奏皇帝的《推广学校折》建议朝廷在学校设置“藏书楼”,因西方“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人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11]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各出义捐”,“择地购书”。他的《公车上书》(1895年)说:“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其太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万余册,所以开民智者广矣。”[12]基于此番认识,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公共藏书楼的设想:“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则人才不可胜用矣。”[12]维新派的集大成者郑观应认为,西方公共藏书制度与人才培养和国家富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说道:“英国近数十年来,人但诩其称雄宇内,人才辈出,而不知其培植人才之法有以致之也。此正所谓人才得而国家兴矣。然设立书院,法似平平,久而行之,其效捷于影响,诚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验亦必接踵而兴矣。”[13]他在《藏书》中对我国传统以封闭为特征的藏书积习和近代西方开放式藏书制度的优劣评判道:“我国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14]虽然乾隆开《四库》、建“七阁”以嘉惠士林之举,无奈,“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庋,寒士未由窥见”。[13]这种秘藏之风与泰西各国公共藏书院形成鲜明对比。1892年,郑氏主张设立的官办藏书机构,接近西方公共图书馆。他提出:“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15]郑观应所说的“书院”,并非指中国传统的具有讲学、考课、研修等性质的书院,而特指类似欧洲各国的藏书院,即近代公共图书馆。
维新时期,各地官员创设公共图书馆的奏折中,也多强调西方公共藏书机构在培育人才方面的先进作用。如山东巡抚袁树勋在1909年所写《奏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中称:“迩自五测交通,新理日出,无人不由其学,无学不各有其书,东西列邦,莫不竞设图书馆、博物院,高楼广场,纵入观览,称为知识之输入品,良以学堂教授既有专门,而参考之书,则必藉公家之力,广为储藏,以遗饷于学者。”[16]1908年,端方奏请建立江南公共图书馆:“窃维强国利民,其先予教育,而图书馆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奴才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而以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17]次年,清学部奏分年筹备图书馆事宜折,各省先后响应。
(二)清廷新政“维新派”公藏建设实践近代公共图书馆藏书事业
维新时期,各地纷纷成立学堂学会,并借鉴了西方公共藏书机构的做法。如京师大学堂、长沙时务学堂等设有藏书楼;南洋公学设有图书院;上海强学会、武昌质学会等筹集专款,收藏书报刊。《常德明达学会章程》:“西国都邑皆设大藏书楼,庋书数千万卷,随人纵览,故异才日出,学术日新。本会拟择中国书籍,先购其经世有用者,制造局、同文馆所译西书甚多,均采购之。然书中义理非图不明,图中用度非器不显,今并购中外各种舆图、动物、植物图,测量、艺学各器,以资试验而收实功。”[18]《两粤广仁学堂善圣学会会章》:“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庋藏至多。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19]从 1895 -1897 年,维新派设立了学会24所、学堂19所和报馆8所,而这些学会、学堂、报馆大多附设了专对内人士开放或兼对外开放的藏书机构。许多学会“尽购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20]其所藏书籍已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扩大到舆地、算学、农商、格致部类及报刊杂志,并大多订有切实可行借阅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允许办学堂,自由开设报馆、学会,为近代公共藏书思想和实践创造了条件。当年学会就增加到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所,南方各省的南学会、湘学会和粤学会等都有藏书较多、管理完善的学会藏书楼,这些成为了中国近代公共藏书事业的先声。
维新派所倡导的集资公藏思想及其公藏建设实践,对开明官吏影响较大。如:“广西近日风气大开,皆由该省大吏士绅踊跃提倡,故一切善举,次第举办。现大吏即于经古书院添设算学时务之课,近又于省中广仁善堂,开设圣学会,崇奉孔子。史中丞先拨万金以为经费。会中拟购置书籍,刊刻报刊,广设学塾,翻译西书各事。”[21]“顷闻桂中官绅,或捐书,或捐器,或捐款。布政游公智开捐廉一千元,唐中丞景崧、岑京卿春煊各捐款为时务课加奖。而欣助图书,尤以唐中丞为最。”[22]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产生的新式学堂,注意藏书建置。张之洞在广东设立广雅书院,陈宝箴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起到设学堂开图书公藏风气之先河的作用。江南储才学堂购备各种书籍给学生公用,湖南崇实学堂也“广购书籍,以备研求”。[23]京师大学堂也内设大藏书楼,“广集中文要集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24]“戊戌政变”失败后,近代公共藏书机构的倡议并未因此中止,反而出现了类似近代图书馆的公共藏书楼。此时倡议和实践公共藏书的主导力量,已由开明官吏扩展到先进士绅。
三、古代藏书楼型变为近代图书馆
明清时期,藏书楼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藏书系统和管理体制。但20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迫切需要藏书为社会所用,旧式藏书体制急需变革,必须建立适应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型藏书楼。原有的官私藏书划归到图书馆,私藏或捐献或售卖或赠与,纷纷流向图书馆,在清末民国时期,完成了藏书体制的转变,古代藏书楼型变为类似近代图书馆的公共藏书楼。几千年的旧式藏书楼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型藏书楼(图书馆)开始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古代藏书楼无论从典藏还是图书管理体制方面都进行了适时的转型嬗变和重构,从文化传播的视域观照,它都对近代新式图书馆的创建和兴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随着社会转型,古代藏书楼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打破旧有私藏体系,承担新式图书馆奠基人角色。古代藏书楼藏书生命的延续及转型造就了近代图书馆事业,为社会文化传播进一步夯实了物质基础。[25]
以作为公共图书馆萌芽的“焦山书藏”为例,清代藏书家阮元是其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筹划者,曾从扬州“文选楼”精选许多私藏捐赠。其他著名藏书家丁丙、梁鼎芬、陈庆年等也都从私藏中选书捐赠,才使“焦山书藏”成为全国第二大书藏。此后,许多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藏书也都以私家藏书楼的藏书为基础起家。比如,建国初“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幹致信浙江省图书馆,提出愿意将藏书楼及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捐献给浙江图书馆永久保存,从此,“嘉业堂”藏书楼成为浙江省图书馆的一部分。常熟翁氏家族也将自己的藏书楼中积聚了200多年的藏书,分批捐献给公共图书馆,其中国家图书馆3 779册,南京图书馆7 924册。曾国藩的“富厚堂”藏书多达30余万卷,现在大部分也都珍藏到了湖南省图书馆。广东新会梁启超“饮冰室”数千种书籍及手稿等,卒后尽捐北平图书馆。浙江吴兴蒋汝藻“密韵楼”藏宋元明清善本书2 700部,5.8万余卷,1926年转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部分珍本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几乎国内每一大型公共图书馆都或多或少从明清时期私家藏书楼中得到过藏书,这足以说明明清私家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以及社会文化传播方面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近代以后,藏书家们顺应社会转型发展,藏书服务社会意识增强,纷纷以私藏捐公藏,数以万计的私家藏书汇聚到公共图书馆,掀起了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从近代公共图书馆萌芽阶段起,私家藏书楼的无私捐赠和藏书家的精心筹划共同承担起了公共图书馆奠基人的角色,古代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近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其生命却也因此融入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延续之中。
综上所述,输入西方图书馆文化最具历史意义的结果,就是促进和实现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图书馆近代化的转型与嬗变。但是古代藏书楼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不可能仅因西方传教士几次来华就发生变化,其嬗演过程是国内外社会文化传播发展、诸多背景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即西学和公共图书馆理念的传播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与中国清廷新政、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等综合因素在不同层面上相互影响、彼此推进、共同作用汇成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的交响乐,促成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1]〔意〕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第四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英〕马礼逊.外国史略[M].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1999.
[3]〔美〕祎理哲.地球说略[M].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1999.
[4]〔美〕戴德江.地理志略[M].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1999.
[5]〔美〕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M].长沙:古微堂重刊定本,1838.
[6]王辉.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影响[D].山东大学,2008.
[7]侯集体.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馆[J].兰台世界,2007,(2).
[8]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出版社,1935.
[9]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下册)[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10]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A].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李端棻.推广学校折[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康有为.公车上书(1895年)[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3]郑观应.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则[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6]聚兴报房.京报[N].聚兴报房,1909-02-28.
[17]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从清末到抗战[M].台湾: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
[18]常德明达学会章程[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两粤广仁善圣堂学会会章[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梁启超.论学会[N].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初一日.
[21]维新派.知新报(第七、八册)[N].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十六日.
[22]维新派.知新报:第 30册[N].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十一日.
[23]维新派.中外日报(第3号)[N].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九日.
[24]何熙年.皖省绅士开办藏书楼上王中丞公呈[N].汇报,第276号.
[25]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