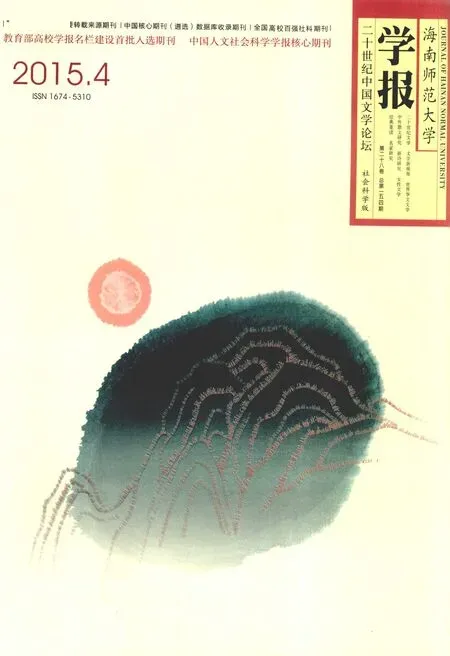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文艺神祇
于丹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中文系,广东珠海519041)
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总称。在古希腊神话中,缪斯原本是三位女神,分别司掌艺术、音乐和文学,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后来,随着神话故事的不断演进发展,缪斯逐渐成为九位女神的总称,而且每一位女神所司神职的艺术类型不同。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中所描绘的九位缪斯女神,除乌拉尼娅司天文外,其他八位女神所司神职都跟文艺有关,所以严格地说,在古希腊神话体系中,掌管文艺、科学的缪斯女神主要神职应该是侧重在文艺方面。那么,中国的民俗信仰中是否有文艺神祇呢?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梳理和论析,笔者发现在中国的民俗信仰中并无文艺神祇。相校浪漫自由的爱琴海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民俗崇拜更偏重于实用性,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含有更多的现实功利目的。
戏剧是文艺的一种,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墨尔波涅司和塔莉娅分别司掌悲剧和喜剧,给戏曲作家以创作的灵感。中国的民俗信仰中也有和戏曲相关的神祇,不过跟戏曲艺术创作的灵感无关,而是戏曲演员们供奉的保护祈福的行业保护神。
中国戏曲种类庞多,戏曲的行业神也由此呈现出极为繁杂的面貌,因时间、地域、曲种、行当不同而各异,但古代戏曲行业供奉范围广、影响大的行业神有两种:一种说二郎神是戏曲的行业神,如清代戏曲家李渔在他的传奇《比目鱼》中说:“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教的李老君。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象儒释道的教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降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在心,切不可犯他的忌讳!”李渔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大家,写有很多优秀的剧本,对戏曲行业十分熟悉,所以清代肯定有些戏班把二郎神供奉为行业神。
戏曲行又称为“梨园行’,戏曲演员也称作“梨园弟子”或“梨园子弟”。“梨园”之说又与唐玄宗有关。据《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
“梨园”是唐代训练和管理乐舞杂戏的专门机构,由唐玄宗所设,所以后世很多戏曲行供奉唐玄宗为“梨园神”,又称“老郎神”。清朝观察使刘澄斋在《老郎庙诗》中写道:“梨园十部调笙簧,路人走看赛老郎。老郎之神是何许?乃云李氏六叶天子唐明皇。”与刘同时期的钱思元亦在《吴门补乘》中写道:“(老郎)庙在抚司门前,梨园子弟祀之。其神白面少年,相传为唐明皇,因明皇兴梨园故也。”①清朝刘澄斋、钱思元二人诗文,转引自周濯街《梨园始祖与保护神》一文,发表于《寻根》1996年第5期。
让本领高强的二郎神或至尊的人间帝王来做戏曲行业的守护神,反映了在古代地位甚低的戏曲行业为了求得生存发展,努力抬高本行低贱地位的良苦用心。而二郎神或唐玄宗,只是戏曲行业的守护神或祖师神,跟艺术无关,所以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没有类似古希腊神话的戏曲艺术方面的神祇。
古代民俗信仰中的文昌神、文昌帝君、魁星受读书人的膜拜,那么他们是否是跟文学艺术有关的神祇呢?
文昌,本是六颗星的总称,《史记·天官书》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六星的职责据《史记索隐》引《春秋元命苞》释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认为文昌星主司人命运,掌管人的穷通富贵、福禄灾运。古代星象家将文昌星看作是吉星,道教将其尊为主掌功名利禄之神。所谓“文昌”有文运昌盛之意,民间俗称“文曲星”,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文人学士多虔信之。
据《明史·礼志》、《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一、《文献通考·郊社考》等文献记载,唐以前四川临潼一带信奉地方性神祇“临潼神”,后逐渐与文昌星合二为一,成为民间信仰中的主司功名利禄之神。元代仁宗延祐三年,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1]81“文昌帝君”之名自此相沿,成为文昌星的拟人化代表。
中国古代民俗信仰中的文昌帝君所掌管的文运是读书人的科名禄籍前程富贵,跟文学创作无关,不是文艺神祇。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卷十四中称文昌神“专掌注录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明代曹安《谏言长语》云:“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2]描绘出当时读书人对文昌神的崇拜热情。到清代,“文昌之祀,遍天下矣”。②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六“文昌为淫祠”条,见《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清初康熙、雍正时期,朝廷曾把文昌神崇拜定为“淫祠”而予以禁止,但屡禁不绝,到嘉庆六年不仅恢复祭祀,朝廷还拨款重建文昌帝君庙宇,嘉庆皇帝还亲谒朝拜,对文昌帝像行九叩大礼,并把文昌神列入国家祭祀大典中,③《清朝续文献通考·群祀考》载:“嘉庆六年谕:京师地安门外,旧有明成化年间所建文昌帝君庙宇,久经倾圮,碑记尚存。特命敬谨重修,见已落成,规模聿焕。朕本日虔申展谒,行九叩礼。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进一步提高了文昌神信仰的地位。
潘承玉先生在《浊秽厕神与窈窕女仙——紫姑神话文化意蕴发微》一文中,提出“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亦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女神存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厕神紫姑“还是两宋士人心目中真正的文艺女神”这一观点,用文献再对其进行分析论证。[3]
紫姑神的信仰崇拜在南朝刘宋之时已出现,自唐代起,紫姑成为民俗信仰中公认的“厕神”。但是名为厕神,却非主厕事,南朝时人就多在家事方面对其扶乩问讯。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五载:“(紫姑)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南朝宋东阳《齐谐记》云:“正月半,……其夕则迎紫姑以卜”;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一云:“其夜迎紫姑以卜”。可见紫姑信仰产生之初,是占卜预测家中诸事的功用。
唐宋以来紫姑信仰影响更加广泛,晚唐李商隐诗“羞逐乡人赛紫姑”就记载了世俗请紫姑的景况。宋代民间请紫姑占卜扶乩更为普遍,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扶乩请紫姑的情景:“尝观其下神,用两手扶一筲箕,头插一箸,画灰盘作字,加笔于箸上,则能写纸,与人应答……作文可观,著棋则无人能敌者。”可见紫姑在民俗信仰中的职能更类似于“乩仙”。
潘文中引《东坡续集》卷十二“子(紫)姑神记”条,认为苏轼在这则故事中描绘了紫姑神的诗才,赋予了她“新的美学意蕴”:
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寘箸手中,二小童扶焉,以箸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余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粗为录之,答其意焉。
在上段文字中,苏轼描绘刻画出一个能诗善文的“乩仙”紫姑形象,但是,《东坡志林》卷三中的一段文字则明显看出苏轼对紫姑的品评不高:“绍圣元年九月,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或以其托于箕帚,如世所谓‘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岂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4]
“超逸绝尘语”,“非紫姑所能至”——这是苏轼对紫姑的清晰评价。
潘文中引宋代洪迈《夷坚志》中多条紫姑降神赋诗的故事为例,以证明紫姑是两宋士人心中的文艺女神。但是,洪迈在《夷坚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条,明确谈到时人请紫姑的活动主要是为占卜问询:
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近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有以木手作黑字者,固已甚异,而衢人沈生之术,特为惊听。其法:从古者各自书心疏,仍自缄封,用印蜡亦可,沈漫不知。既至当门,焚褚镪而祷。沈居武雄营门,无厅事,只直头屋一间,逼街狭小,室仅容膝,供神九位,标曰侍御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之类。先焚疏毕,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纸于案。来者又增拈白纸成卷而实缄之,多至四十幅。沈接置于砚傍而出,虽垂疏帘,不加糊饰,了然可睹。沈同客坐伺于外,少则闻放笔声,共入视,才有数字,只是报真人名称为何神。又坐食顷,复放笔,然后取其书,上有讫字皆满,墨迹未干,凡所谒,无不报。但每问弗许过三事,钱止三百五十文,可谓奇奇怪怪矣!无用论其或中或否也。东阳陈亮同父,以杀人坐狱,鞫于衢。前者数翻成款,最后秀州一尉来,尉少年喜立事,逼取承服。其子惧甚,敬扣神,神大书曰:“无忧,当登第。然须经天狱始明。”子奔诉阙下,得移大理,讫以无罪释放。后两年廷对,魁天下。黄齐贤求占,许以奋发,至问其父,则曰:“宜保六七之年,恐有大厄,盍佩吾符,再炷香进纸。”顷之,篆符四道,笔势飞动,与世间议拟而画者绝殊。黄父生于己亥,果终于甲寅,如其大厄之语。[5]
再如洪迈《夷坚支戊》卷二“方翥招紫姑”条所载:“莆田方翥次云,绍兴丁巳秋,将赴乡举。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题目为问。神不肯告,曰:‘天机不可泄。’又炷香酌酒,祷请数四,乃书‘中和’二字。翥时方十八岁,习词赋,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极’、‘致中和天地位’、‘以礼乐致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类,凡可作题者,悉预为之。是岁以举子多,分为两场。其赋作前题曰:‘中兴日月可冀’,后题曰‘何戎国之福’,始悟所告。翥试前赋,中魁选。”
由上两则故事,可见南宋当时人请紫姑的习俗是为了占卜预测,士大夫读书人参与请紫姑的游戏,是为了占卜自己的科第前途。所以“在两宋士大夫的信仰中,紫姑确是他们钟情的诗仙,是没有文艺女神称号的真正的文艺女神”[4]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请紫姑的占卜活动是中国古代民间一种兼具神灵崇拜和巫术观念的民俗信仰,展现出虚构、附会、随意和含混等性质特征,是华夏民间俗信崇拜的一个缩影。其实,宋代很多士人对当时愈演愈烈的请紫姑占卜的“淫祀”风气是非常不满的,陆游在《箕卜》诗中就批评这种风气:“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扶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凭,对答不须臾。岂必考中否,一笔聊相娱,诗章亦间作,酒食随所须。兴阑忽辞去,谁能执其祛。持箕畀灶婢,弃笔卧墙隅。几席亦已彻,狼藉果与蔬。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6]
洪迈的《夷坚乙志》卷十七中写了一则士人险被紫姑迷惑丧命的故事:“天台士人仇铎者,被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壮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数数延紫姑求诗词,讽玩不去口,遂为所惑。晨夕缴绕之不舍,必欲见真形为夫妇,又将托于梦想。铎虽已迷,然尚畏死,犹自力拒之。鬼相随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烦运箕也。同行者知之,惧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径与入城隍庙祠,焚香代诉。始入庙,铎两齿相击,已有恐栗之状。暨还舍,即索纸为妇人对事,具述本末。……其所书凡千五百字,即日录焚之。铎后三日始醒,盖为所困几一月。”在这则故事中,紫姑成了害人性命的厉鬼,这种写法表现了洪迈对当时民间紫姑崇拜的态度和评价。所以,以《夷坚志》中紫姑作诗的故事为例来证明紫姑是两宋士人所尊奉的诗仙的说法,与《夷坚志》作者洪迈的实际看法是相悖的。两宋之时,“厕神”紫姑在民间信仰中更贴近于占卜问询的“乩仙”。
综上所述,与古希腊神话不同,中华文化民俗信仰的神谱中没有较为清晰的文艺神祇的芳踪。归其原因,这反映了两种文明起源的特点。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两种不同形态,古希腊海洋文明具有崇尚艺术审美、追求自由的浪漫性特征;而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农耕文明则重视务实性,在民俗信仰中也追求更多的实用性、功利性而非艺术性。由对中国民间信仰中文艺神祇存否这一问题的辨析,可以窥探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某些层面,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民俗文化和民俗心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1]吕宗力,栾保群.重增搜神记[M]//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曹安.谏言长语[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3]潘承玉.浊秽厕神与窈窕女仙——紫姑神话文化意蕴发微[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0(4).
[4]苏轼.东坡志林[M].上海:上海书店,1990:卷三.
[5]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86-1487.
[6]陆游.剑南诗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