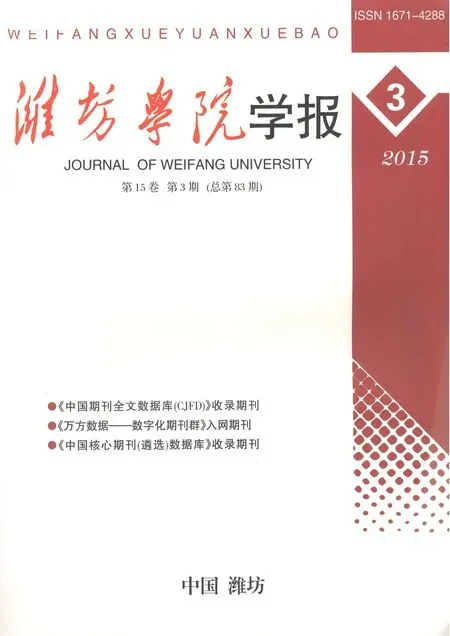巴拉丁斯基哀诗诗思浅探
——兼论十九世纪俄罗斯哀诗的流变
卢文雅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巴拉丁斯基哀诗诗思浅探
——兼论十九世纪俄罗斯哀诗的流变
卢文雅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巴拉丁斯基突破了浪漫主义哀诗的局限,为了确定哀之缘由,达到文之真实,他将“环境与个人”、“具体与普遍”等现实主义思考与浪漫主义笔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开拓了一种新的哀诗诗思。作为俄罗斯诗坛上最卓越的哀诗诗人之一,他的哀诗创作对十九世纪俄罗斯哀诗的流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巴拉丁斯基;哀诗;真实;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叶甫盖尼·阿勃拉莫维奇·巴拉丁斯基(1800—1844),这位“普希金时代诗人群”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他的诗优美清晰,哲意丰富,感情与心理刻画真切动人,其诗才连普希金本人都称赏不已,普希金甚至给他指定了一个“在茹科夫斯基的旁边,在家神和塔夫里达的歌手(指著名诗人巴丘什科夫)的上面”[1]的诗坛位置。他的哀诗尤为缪斯女神所青睐,那种无奈和愁苦彻心彻骨,句句似嗟,字字如泪。这些美妙的诗篇不仅为俄罗斯文学画卷涂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还有形无形地影响了后代诗人的创作甚至彼时文坛的整体走向。将巴拉丁斯基的哀诗放置于整个俄罗斯哀诗流变的历史语境中去考查,更能理解他的哀诗创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转折性作用,以及他作为诗国传统的延续者兼创造者的历史价值。
一
哀诗(элегия)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最为盛行的一种抒情诗体裁,顾名思义,其思必忧,其情必哀。别林斯基将哀诗定义为“内容忧伤的诗歌”[2],但哀诗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民族文学传统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俄罗斯文学受西方影响颇深,其哀诗体裁的兴起与西方哀诗的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哀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它起源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最初以表达道德政治内容为主,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爱情主题渐占上风。[3]由于不见容于扬“理性”而抑“抒情”的古典主义,在17世纪日渐衰落。但是到了18世纪,由于前浪漫主义思潮的勃兴,哀诗再度成为西方文人寄兴寓情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下,诗人们纷纷用哀诗来抒发对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忧思,对沉重现实的哀诉,以及对田园理想的向往……
在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繁盛时期,特列季亚科夫和苏马罗科夫最先为哀诗这一体裁赋予了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俄罗斯哀诗真正的黄金时代还应始于茹科夫斯基,始于他那首“为俄罗斯前浪漫主义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的《乡村墓地》(1802),以及那首被誉为“俄罗斯第一首浪漫主义哀诗”的《黄昏》(1805)。[4]茹科夫斯基一改前人重外部刻绘而轻内心描摹的作诗传统,将更多笔墨倾注于个人所思所感,再加上自然风景的巧妙渲染,使一腔幽思回肠九转,分外哀婉动人。他也因此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大地上第一个悲伤的歌手”[5]。与茹科夫斯基同时代的诗人巴丘什科夫也是一位吟唱哀诗的大师,他克服了前者的诗题局限,将历史题材和公民题材纳入自己的哀诗之中,忧郁之余更显壮丽。如果说茹科夫斯基的忧郁哀诗是俄罗斯文学踏入浪漫主义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巴丘什科夫的历史哀诗便是这扇大门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当文学发展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时,哀诗却遭遇了严酷的危机。В.К.丘赫尔别凯的《关于近十年我们的诗歌——尤其抒情诗——之动向》(1824)一文一发表便激起了一股关于哀诗体裁的争议之潮。尽管这篇文章遭到了诸如布尔加林、沃耶伊科夫、雅科夫列夫、别斯土舍夫、维亚泽姆斯基等各个派别文人的不同程度的反对[6],作者对哀诗的一些见解却不可谓不深刻。丘赫尔别凯认为,哀诗发展的瓶颈不仅在于这一体裁本身的封闭性,还在于众多哀诗作者才情的匮乏,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效仿者们的拙劣伎俩:“效仿者毫无灵感:他说的不是发自内心之言,而是强令自己复述他人的观念和感受…我们这儿尽是些‘梦想’和‘幻影’,尽是些‘似乎’、‘好像’、‘仿佛’,尽是些‘宛若’、‘犹如’、‘某种’、‘某个’……感觉在我们这儿久已不存:忧郁感吞没了其他一切…我们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怀念着自己逝去的青春……画面处处雷同:月亮自然是忧郁的、苍白的,山岩上其实从不曾有栎树丛,森林中成百次升起旭日和晚霞……”[7]在他看来,毫无来由的忧伤使哀诗变成了无病呻吟的呓语,似乎到了该将这一抒情体裁打入冷宫的时候了。
不过哀诗并没有就此退出诗人们的视野。当哀诗体裁同浪漫主义文学一道陷入困境时,正是普希金力挽狂澜,为哀诗写作寻得了新的出路,也为浪漫主义物色了新的替代者——现实主义。他所开创的政治哀诗表达了进步人士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忧愤,对自由理想的讴歌和神往,将时代精神融入字里行间。普希金挖掘出了哀诗之“哀”的社会性原因,在他和巴拉丁斯基的笔下,哀诗成了早期现实主义的“试验田”,而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哀诗则随着浪漫主义的式微越发黯淡无光。
与此同时,巴拉丁斯基也以另一种方式改变着哀诗体裁的面貌。
二
1827年是巴拉丁斯基第一部诗集面世之年,也是他的诗歌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将巴拉丁斯基的创作历程截然划为两个阶段。在巴拉丁斯基的早期创作阶段即1819至1827年这段时间的诗作中,哀诗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这一时期,俄罗斯哀诗早已树立了浪漫主义代言者的名望,并渐渐走向两难之境: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积极寻求改变,还是苟且生存在蹩脚诗人自我陶醉的诗行里、然后自行告别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舞台?
面对哀诗危机的到来,巴拉丁斯基却依然执着于他所钟爱的体裁。不同于开创政治哀诗的普希金,他决定以传统的形式向传统发起挑战,在文学发展的新条件下重写爱情哀诗。
如果说,茹科夫斯基还相信尘世之外存在永恒的幸福,巴丘什科夫还试图从宗教中寻求拯救,那么,巴拉丁斯基则对一切都绝望了:包括世界的制度,包括人被挟至的处所,包括爱情和友谊。他不信尘世的和谐,也不信天堂的和谐;他怀疑“此岸”的幸福,也怀疑“彼岸”的幸福。在他看来,人从一开始就支离破碎,而压在人肩上的沉甸甸的生活则是陪伴他一生的不可规避的痛苦。[8]这种无所不在的失望感贯穿于巴拉丁斯基几乎所有的哀诗之中,而他的爱情哀诗则无一不以“爱的失却”来展示这种失望,因此或许也可称其为“没有爱情的爱情诗”。
巴拉丁斯基早期爱情哀诗的基本母题在他的《爱情》(1824)一诗中得到了表述,诗中所描写的情感被抒情主人公看作是“危险的毒药”,它毁灭人的心灵,使人对未来的快乐失去希望[9]:
我们在爱情里啜饮甜蜜的毒药;
但我们依然在其中啜饮着,
我们为短暂的快乐而付出了
长久的不快乐。
爱情的焰火,生机勃勃的焰火!
所有人都说:可是我们会看到什么?
充满破坏力的焰火
将他的心灵包围、毁灭!就像诗人在哀诗《失望》(1821)中发出的感慨一样,“我”不相信眼下的爱情,也不相信人类的所有爱情,甚至幸福本身也不可能存在:
我已经没有信心再相信,
我已经不再相信爱情,
我不能再一次、
再一次沉湎于那变幻多端的梦景!在巴拉丁斯基最负盛名的爱情哀诗《自白》(1923)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痛入骨髓的无望的爱情。诗人运用真实而细腻的心理描绘手段,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对旧爱曾经满怀情意:“你的娇容和那旧日的幻想啊,我曾苦心铭记。”可是如今,生活的风波和长久的苦别早已熄灭了“我”的热恋之火:“但今日的回忆已无生机/旧日的誓言也力不能及”,“你的影子在我心中业已淡薄,/我很少将你召唤,违背自己的心意,/炽热的爱情逐渐冷却,/心中的火焰已自行停息。”“我”也曾向往爱情,但初恋的幻灭使“我”再难寻觅新的爱情:“我孑然一身,仍有求爱之心,/但我要将这爱情远远抛弃,/不再坠入另一个情网,/只有那初恋才使我们沉迷。”爱情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即使新婚也不能使“我”重温爱情:“也许,我会选得一个不爱的伴侣,/在精心安排的婚礼上我会向她伸手表爱。”但是,“我们不会互倾心中的秘密,/也不会纵情欢乐与狂喜,/我们结婚未结同心,/是命运将我们牵到一起。”[10]
在诗人笔下,抒情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是动态的、变化的,准确的选词和精到的分析使那种欲爱而不能的矛盾心理格外具体可感。这种分析式的心理描写作为巴拉丁斯基哀诗的重要特点,在《失望》(1821)、《吻》、(1822)《辩解》(1824)等其他爱情哀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自白》的最后四句道出了爱情破灭、幸福无望的根本原因:
诸事难从人愿,你我身不由己,
在那青年的时代
我们曾匆忙发过誓言
但在全知的命运看来可能会是荒诞滑稽。[11]
是什么造成了昔日女友的悲伤、未来娇妻的不幸?不是“我”的负情与无情,而是环境使然,命运使然。人无力抵抗命运,客观现实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这正是巴拉丁斯基在早期哀诗中竭力试图表达的思想,也是他在哀诗危机来临时作出的体裁改革的探索,即将“个人与环境”这个现实主义命题植入浪漫主义气息浓厚的哀诗体裁中去。
1821年,初露锋芒的巴拉丁斯基写下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谬误和真实》,诗人对自己的审美信念进行了论述,对自己诗中所描绘的生活现象进行了哲理性的阐释。在巴拉丁斯基的行文中渗透着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感觉机体所感知的客观现实是外在于我们的,它并不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它。我们在造就了我们的意志与观念的现实的影响下发生着改变,用不同的方式去评价同样的事物,而事物本身却依然故我,不以我们的评价为转移。经验“为我增添一些东西,或者消除我的某一部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再是之前的我,——我变了,而客观事物却没有变。”[12]巴拉丁斯基创作思想中的关键要素——经验、环境、现实——非但不由人的观念和意志而定,还对人的理智与情感、观念和意志,对人的生活的改变、个性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还在1819年时巴拉丁斯基就在他那首浪漫主义色彩十足的赠言哀诗《致克列尼岑》中隐隐透露出了人无法摆脱现实控制的悲剧性事实:
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曾经的梦想在哪里?
那童心的活力和希望的甜蜜!
冷酷的经验销毁了所有。
朋友你知道吗?——病痛和哀愁,
使他在青春华年里便老去;
你熟悉的许多弱点已消失,
他的许多梦想变得陌生不已!
理智更可靠、更坚固,
言谈举止更谦虚;
或许,他变得更谨慎、更聪明,
不过,想必如今幸福也减少了百倍。我们无法驾驭时间,甚至无法驾驭我们自己。眼睁睁看着时间将万物改换得面目全非,自己却无计可施,那是怎样一种悲哀。前文提及的《自白》一诗就是对这种悲剧意识的最完美的印证。
多年以后,现实主义声势渐起,客观事物与外界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影响之大已成为人所共识。当屠格涅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现实主义大师将客观环境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之列时,巴拉丁斯基早已在诗歌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尽管他的作品与真正的现实主义还相去甚远,他的哀诗中还充斥着浪漫主义特有的词汇手段和形象体系,但是从这些哀诗中已经可以看到未来文学发展趋势的端倪。“人与环境”问题的提出使巴拉丁斯基的哀诗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换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环节。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拉丁斯基的哀诗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三十年代反动统治的加剧,这一切都促成了巴拉丁斯基诗歌的转变。少年时节最爱吟弄的爱情悲歌逐渐让位于而立之际深沉的哲理思索,只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失望感和悲剧感却有增无减。生命与死亡、历史与永恒、诗的繁盛与衰落,这些困扰着所有哲理诗人的存在性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巴拉丁斯基。诗歌的命运、诗人的命运,终究都是悲剧性的存在。他忧伤地审视着因无人关心而渐趋没落的诗歌:
时代沿着钢铁之路迈进,
人心贪财,欲壑难填,
幻想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无耻地
专注于迫切需要的、有利可图的东西。
诗歌的幼稚幻梦
在教育的光照下消逝了,
人们不再吟风弄月,却操心办工业。[13]创作主题的嬗变、悲哀情绪的加重意味着巴拉丁斯基哀诗的思想基础的蜕变。诗人曾在其颇具纲领性的《关于谬误和真实》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力图在诗中描绘真实的愿望,而他前期的哀诗的确也在努力践行着这一目标,方法便是将客观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当作悲剧不可逃避的缘由写入诗中。在巴拉丁斯基的后期创作中,“真实”依然是一个关键性的词汇,不过此时的真实已经不再是先前那种具体可感的真实,而是另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真实,抒情主人公的个性也不再那样清晰、鲜明,而变得更加宽泛、更加难以捉摸。我们可以在巴拉丁斯基为自己的长诗《姘妇》(1831)所作的序言以及随后发表的文章《反批评》(1831)中看到诗人思想变化的轨迹。此时的诗人看到的并不是无穷无尽的真实,而是一个真实的范畴,以及与其相反的非真实的范畴。真实乃是关于事物和现象的所有真相。在艺术作品中真实的尺度只有一个,即生活和现实。文学应是“类似于其他科学”的学科,作家应“像科学家一样”能够“展现真实”。巴拉丁斯基不仅在艺术中看到了现实的反映,还解释了艺术是如何完成反映现实这一功能的。他在若干文章中都提出了——尽管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艺术典型化的问题。为了达到真实,思想应当“从总体中获取,而非从个别中获取”,而“总体”指的是那些最普遍、最典型、最常见之物。[14]正是这种对真实的理解成为了巴拉丁斯基后期哲理诗创作的思想基础。
在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世界里,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同对哲学的深切关注是不可分割的。现实蕴藏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在诗人笔下却都被赋予了哲学的涵义。物理学家牛顿从坠落的苹果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诗人巴拉丁斯基则从同样的果实中发现了“上天的律令”:
苹果果实从树上落下:
人类便理解了上天的律令!普遍的规律取代了具体的现象,整体的存在取代了个别的人与物,这就是巴拉丁斯基后期哲理哀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秋天》(1836)是这类哀诗的典型代表,诗中那“步入秋日”的“生命田野的耕者”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形象,那“怀着希望播种”、“做着关于遥远的奖赏之日的美梦”的“农夫”展现给我们的也不是某个特定之人的命运。巴拉丁斯基临终前写下的另一首哀诗《何时你的声音,噢,诗人……》(1843)则将“没有主人公”的哀诗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何时你的声音,噢,诗人,
会在高呼中被死神终止,
何时正当盛年的你
会被迫不及待的劫数捉住,——
谁会被繁华时光的夕照,
触动内心深处?
谁会为你的死,
哀叹着心扉紧缚,
拜谒你静静的棺木,
为沉默了的缪斯号哭,
向你的骨灰致敬,
真诚地祭奠亡灵?
不会有一个人!——但是不久前的佐伊尔
会为歌者编写一支赞美曲,
他已为死去的人摇炉散香,
也要让活着的人沾沾香炉。
显然这是一首献给死者的哀诗。但这位“被死神终止声音”的诗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巴拉丁斯基并没有交代,研究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不过这首诗的主角是谁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诗中体现的存在性意义。全诗有七个完成体动词表示将来时态,分别是“终止”(остановит)、“捉住”(уловит)、“触动”(тронет)、“哀叹”(восстонет)、“拜谒”(посетит)、“致敬”(почтит)、“编写”(сложится),笔者以表达未来意义的“会”字置于其前用以标记时态。这七个动词支撑起了整首诗的意义框架,诗人的死不仅仅发生在过去,还发生在现在,甚至未来。不仅仅是已成之事,也是将成之事。死,是已逝者的命运,也是在世者、甚至未生者的必然归宿。这首哀诗看似讲的是某位诗人死时的冷清之境,但实际上巴拉丁斯基是将“死”作为一种普遍的存在来书写的,身后的凄凉或许是每个人都难以逃避的宿命,存在的悲剧使这首诗更添了几分苦楚。
同早期哀诗相比,巴拉丁斯基的后期创作对“真实”的孜孜追求丝毫未减。他将艺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他把个别的真实与总体的真实区分开来,他以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律作为诗歌写作的对象。这一切都使他的诗思十分接近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他并没有像涅克拉佐夫一样成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哀诗哀叹的不是社会的现实,而是存在的现实。诗人站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十字路口,无处可归的孤独身影就像他笔下的哀诗诗句一样,既哀伤,又无畏。
四
纵观巴拉丁斯基的整个诗歌创作生涯,哀诗这一版块尤其醒目,其情之哀、其语之美、其绘之真、其思之深,共同构成了他的哀诗特色。他的哀诗艺术对同时代和后代诗人的创作具有无法忽视的影响,在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哀诗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巴拉丁斯基的一丝影子。
在巴拉丁斯基之后,莱蒙托夫的哀诗开启了俄罗斯哀诗体裁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其中也不乏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承继。他的爱情哀诗里有静静的眼泪,朦胧的愿景,以及梦似的回忆,使人想起多情善感的茹科夫斯基。他的历史哀诗则继承了巴丘什科夫的诗歌传统,借史抒怀,哀而不伤。但是莱蒙托夫的哀诗却有一套不同于浪漫主义哀诗的哲学:他不去来世、不去身外憧憬那种神赐的幸福,而是一头扎进混沌的现实,激烈地控诉,决绝地反抗。这与巴拉丁斯基不无相似,后者尽管承认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却从不曾向虚无的未来或宗教乞求幸福的可能。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巴拉丁斯基最先意识到,对现实的确证也包括对反抗现实的确证,这种反抗正是现实的一部分,叛逆的梦想有其存在的权利。[15]
莱蒙托夫进一步发展了巴拉丁斯基的“叛逆”哀诗,他对世界的悲观态度与对虚伪的人世、冷酷的上流圈的不肯妥协是紧紧相连的。
涅克拉索夫大概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哀诗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特色独具的诗人了。他的时代已同浪漫主义挥手作别,哀诗体裁的风头也不似以往,诗歌发展趋势如此,他的哀诗创作便显得尤为不同寻常。在涅克拉索夫的现实主义哀诗中,我们不仅能够体察到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诗诗风,也感受到了巴拉丁斯基早期爱情哀诗中那种对“真实”的不倦追求。Г.А.古科夫斯基这样描述涅克拉索夫的抒情主人公:“爱情诗的主人公不是作为一种规范,不是作为一个道德审美的理想模型或者合乎道德的爱情形象——最纯洁、最自由、最崇高的爱情之形象被描绘的,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具体又普通特点的活生生的人被描绘出来,这是个好人,但却为‘丑陋’的时代所毒害,他将这个病态时代的精神通病带到了自己身上、带入了人自己的爱情中。”[16]这一曾似相识的爱情主角,不正是我们在巴拉丁斯基的哀诗《自白》中所看到的那个再不肯相信爱情的主人公吗?
[1](俄)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散文选[M].谢天振,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45.
[2]В.Г.Белински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13-ти т.,Т.5 [M].М.:Наука,1954,стр.50
[3]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ерминовипонятий [M].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А.Н.Николюкин.М.:НПК《Интелвак》,2003,стр. 1227.
[4]王立业.《黄昏》:俄罗斯文学的清晨——解读茹科夫斯基的风景哀诗《黄昏》[J].国外文学,2006,(2).
[5]В.Г.Белинский.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трехтомах[M].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Ф.М.ГоловенченкоМ.:ОГИЗ,ГИХЛ,1948 ТомIII.стр.32.
[6]см.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элегияот 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60.
[7]В.К.Кюхельбекер.Онаправлениенашейпоэзий[DB/OL],http: //az.lib.ru/k/kjuhelxbeker_w_k/text_0180.shtml,2009-1-27
[8]см.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XI-XIXвв[M].Подредакцией В.И.Коровина,Н.И.Якушина.М.?Русскоеслово?2001,стр.235.
[9]С.В.Рудакова.Своеобразиежанраэлегиивраннемтворче стве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J]/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фил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2008,(20):102.
[10][11][13]译诗选自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7-169,172.
[12]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элегияот 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104
[14][15][16]см.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 элегияот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 110-111,123,111.
Research on Poetic Thoughts of Baratynsky’s Elegy——Also on and the Chang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ussian Elegy in the 19 Century
LU Wen—ya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Baratynsky overcame the limitations of Romantic elegy, and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reason of sadness and obtain the reality of poems he combined the questions of Realism such a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dividual”the specific and the general”with the Romantic style, thus opened up a new poetic thought of elegy. Baratynsky i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Russian poets, and his elegy writt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ssian Elegy in the 19 Century.
Baratynsky;elegy;real;romanticism;realism
I106.2
A
1671-4288(2015)03-0035-05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5-03-21
卢文雅(1988-),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