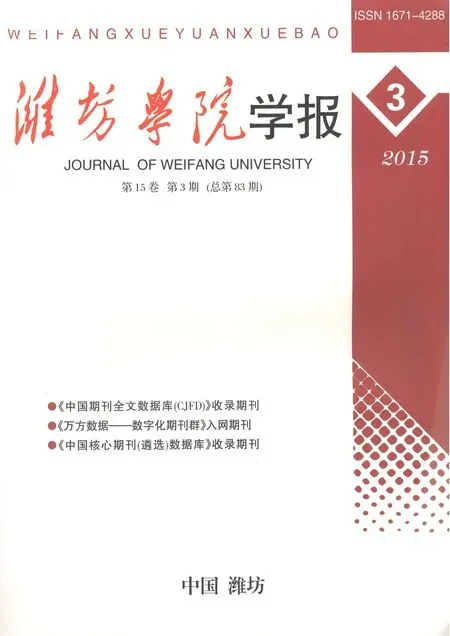小说不能承受之轻交给诗
——论雷蒙德·卡佛的诗与小说的互文性关系
王万顺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小说不能承受之轻交给诗
——论雷蒙德·卡佛的诗与小说的互文性关系
王万顺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雷蒙德·卡佛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卡佛的诗言小说所不能言,是作者最为心仪的本色表达方式,是生存状态与精神理路的真实复现,同时与他的小说在行文风格、叙事主题、深层意蕴等方面存在着互文性关系,值得重视。
卡佛;诗歌;极简主义;互文性
当我们谈论卡佛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卡佛戏谑式的貌似弯弯绕实则富有严肃意义的逼问。曾有一个年代,不读卡佛的小说就会被视为落伍,而且人们都自以为从中读懂了卡佛。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读了他的传记。在笔者看来,要理解一个完整的卡佛,不读他的诗是不可能的。诗歌才是走向卡佛腹地的门扉。但是把雷蒙德·卡佛的诗称作“流水账”即使在前面加个“特殊的”是有失公允的[1],如果公平的话,什么诗不是生活或思想的特殊的流水账呢?何况是卡佛,哪怕再穷困潦倒都不放弃写作的卡佛,以行文简约著称的卡佛。作为小说家,卡佛的名声早已从美国远播他乡异域,但这不能说他的诗歌就没有读者、毫无影响,或者与他的小说相比相形见绌,实际上他的诗至少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毫不逊色于其小说成就的认可。只活了五十岁的卡佛留下了七十多个短篇,对他推崇备至的村上春树认为至少会有六篇被当做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而卡佛创作的诗歌却有三百余首之多,有评论家认为如果他不写小说也是一个极好的诗人。事实是,在卡佛的文学道路上,诗歌和小说并驾齐驱,写小说解决生计问题,只为稻粱谋,诗歌却是让他在困顿中坚持下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像许多大作家一样,卡佛走上文学道路恐怕是从练习写诗开始的,最早出版的两本书都是诗集:《Near Klamath》(1967年)、《Winter Insomnia》(1970年)。卡佛去世以后,人们在追思会上朗读他的诗歌为他送别,他的墓碑上写着“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墓碑及石凳上还镌刻有两首诗:《Gravy》和《Later Fragment》。因此,从作家自己和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诗歌在卡佛的文学世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中国,卡佛只是以一个短篇小说家被熟知,他的短篇小说曾被认为是文学阅读的时尚,而他的诗歌则湮没无闻,无人赏识。所幸近年来卡佛的诗开始引进国内,惜乎遭受了极大的冷遇。如此以来,我们不仅不会读懂卡佛的全部,更不能深入他的内心。
一、人生履痕的写照
小说家写诗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笔者近来尤为关注。这些作者的文学身份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遗憾的是,那些靠写作小说成名并主要以此为业的作家们的诗歌与其小说相比艺术上终究无法媲美,也没有在诗坛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最终有许多人失去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卡佛似乎不同。他能够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之间“游刃有余”地交手并行创作,保持了相对一致的风格和稳定的艺术水准,非常难能可贵。就像他后来的女性伴侣、诗人苔丝·加拉格尔所说,他的诗“不是小说写作间隙的产物”,而且“正是源自诗歌的精神力量支撑他转向短篇小说的创作”[2]。诗歌是卡佛人生的力量之源,如果没有对诗歌的一腔热爱,恐怕他难以挺过困苦不幸,如果不写诗的话,很难想象他能在小说领域能有什么大作为。到底是诗歌影响了小说,还是小说反作用于诗歌,不得而知。卡佛的诗深蕴着与其小说大致相同的基因,具有相似的文风,比如追求所谓的“极简主义”,关注美国底层民众或所谓下等人特别是那些失败、不幸的人的境遇,也可以权且将其纳入“肮脏现实主义”的范畴,等等,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诗美品质。
人们对卡佛的印象是隐忍平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村上认为,“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3]这样的低调和不事张扬出于他卑微的出身和坎坷的人生经历,在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中流砥柱的美国,卡佛不过是一介草民,一个命中注定时运不济的穷小子。在前四十年,卡佛过着马足车尘、朝不保夕的生活,生存是第一要务。像亨利·米勒一样,卡佛也担心屁股底下的椅子会随时被人移走。年复一年,他和妻子所能做的便是奔波打拼,任劳任怨,努力保住自己头上的屋顶。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做兼职,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等等,但又不断失业,多次经济破产,备受折磨的是他还有酗酒恶习。尽管如此,他从未中断过写作,并且在学业上不断求取进步。小说是虚构,诗歌则是诗人的真情流露。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切身感受在小说中进行描写反映,也用诗歌形式作了最真实的记录。面对来自生活的重压,遭受着物质贫乏、经济拮据、人际关系纠结的折磨,除了被迫接受,卡佛像一个不屈的硬汉,在精神领域不断向上攀援。他是以潜伏的匍匐的姿态来忍负的,唯有如此,才表现得切肤刻骨。因此,他不是那种空喊口号的人。在诗歌中,他最大程度地呈现生活的原态,毫不遮掩地袒露自己,揭自己的伤疤。比如对于十数年戒不掉的酒瘾,相应的“酒”便成为一个关键词。他的许多诗中都提到了酒,大有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的阵势。戒酒成功是他晚年津津乐道的一大成绩。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没有死于酗酒,而是死于吸烟过度而导致的肺癌。除了酒,还有女人,包括钓鱼的嗜好,是他以追忆前期生活为基调的诗歌中的重要构成。
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度,诗人的车是什么样子的呢?“那辆挡风玻璃破裂的车。/那辆手柄脱落的车。/那辆没有刹车的车。/那辆U型联合器有缺陷的车。/那辆散热器上有个洞的车。//”(《那辆车》)那辆车真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转向失灵、电机麻烦、费油、软管腐烂、轮胎磨光、水泵破裂、计时器老掉牙、一氧化碳泄露、恒温器堵塞、没有前灯、雨刷失效、离合器踏板断裂、小孩子在里面呕吐、撞了狗却继续奔驰,等等。他幻想有一辆新车,却无力偿付。一辆车就像一个缩影,揭开了悲催生活的一角。他把自己破产的情景写下来:“二十八岁,毛茸茸的肚子/从汗衫(被豁免)下露出来,/我侧身躺在/长沙发(被豁免)上,/听着我妻子那美好的嗓音(也被豁免)/发出奇怪的声音。//(《破产》)他也写我们熟悉名字的人,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马克·吐温、海明威,从他们身上寻找精神支撑。卡佛对生活保持着足够的敏感,这可以让他不致于趴下再也爬不起来。他经常写睡眠和梦境,对于一个困顿而又坚韧的人来说再好理解不过。“这个黄昏五点到七点之间,/我躺在睡眠的河床里。/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仅仅是希望,/我拐进一串黑暗的梦里。/正是在这段时间,天气/经受了彻底的改变。/变得疯狂。从前那些/卑微、破败但尚可理解的东西,/变得膨胀,无法识别。/一些彻底堕落的东西。//(《片刻》)表面上看诗人的境况和意志在下坠下坠下坠……,然却饱含着对生活及命运的质询,试图做出挽回、拯救与超越的努力。假如有人能够把卡佛的诗按照时间顺序排好,一定能够从中找到诗人生活的线索,还原他的日常生活场景,发现他的精神或思想起伏的轨迹。
二、小说不能承受之轻交给诗
论者说:“卡佛自己曾坦言,尽管他的小说名气更大一些,但他更珍视自己的诗歌。只读过卡佛小说的人,或许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卡佛的文字冷峻、节制、撕裂了太多生活的痛,难免以为卡佛的冷漠疏离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卡佛的诗歌具有与小说气质同中存异的复杂的气场。”[4]卡佛的小说是把悲剧性的人生撕裂给人看,诗歌则是捶扁揉碎了给人看。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愤怒、无奈和妥协。卡佛的写作不仅接地气,而且接人气。如同他的小说,卡佛的诗歌向社会底层冷眉扫射。但在极端穷困的生存状态下,失望、无奈、绝望成为基调,冷酷的人际关系往往承载着这些难以言喻的主题内容。比如《大象》这篇小说,写的是“我”因为亲人理所当然地向他借钱或要钱而陷入了经济危机,四面楚歌。编出各种理由借钱的兄弟,等着每月汇款的母亲,法庭判决必须每月付生活费的前妻,还有一个拥有无赖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儿,一个在外上大学经常威胁说要去吸毒或抢银行的儿子。念及母子、夫妻、兄弟、父子感情,他责无旁贷,拼命干活,整天辛苦工作,每天回到家“扑嗵一声坐椅子里,动也不动”,想解鞋带都很费力,累得连站起来开电视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借贷维持周边的人际关系。他一再缩减开支,告诫自己不出去吃饭,不看电影,不买新衣服和新鞋,牙齿坏了,汽车散架,都不敢破费。不堪负重的他想过解脱,要去澳大利亚一走了之,亲人们对此不以为然,他感觉自己已被牢牢地控制。最后,为了省油,他不得不带着饭盒步行去上班。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无耻之尤的吸血社会,亲人之间变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卡佛的诗许多都是以此为主题重复抒写,践行着他的小说一样的叙事风格。比如《我能做的事》写一个破产的父亲受困于这种被“家人”吸血的窘境:在意大利的儿子威胁说要结束生命,老母亲一旦跟他通话就是要钱,而自己却无法向他人求援。《邮件》这首诗几乎是上述这篇小说的翻版,共有五节:第一节是儿子从法国寄来明信片,说自己处境不佳,急需用钱;第二节是女儿来信,说她的老男人那个瘾君子正在拆卸摩托车,她和孩子们靠燕麦粥糊口,需要帮助;第三节是母亲的来信,说她病了,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要做最后一次迁移,希望儿子替她付钱建一个家;第四节是他极度郁闷,出去散心;在第五节他碰到了送信的邮递员,“他的手伸向身后——好像要袭击!/那是邮件。//”置身于被群虻啃噬的境遇中,恐惧成了自然反应。《钱》、《秋天》、《食物去哪儿了》等莫不如是。诗人的希望和理想,比如去钓钓鲑鱼,出去吃饭可以随意点餐,买身衣服买辆车,跟女孩调调情,都化为了云烟,仅止于想象。没有希望是可怕的,得过且过无异于行尸走肉或死亡。“那些比我们好的人舒服。/他们住在粉刷过的有抽水马桶的房子里。/开着年份和品牌清晰可辨的车。/而那些穷人可怜,没有工作。/他们怪异的车停在尘垢满目的院子里的石块上。//”(《得过且过》)诗人不是为了控诉、鞭挞贫富不公的社会怪相,而是关心像他一样的穷人的精神病变,他们除了工作之外的无所事事只是空空地消耗时光。他们“从没喜欢过工作”,只能是“得过且过”。在这样的生命状态里,他们对未来失去了想象的能力,消糜了渴望,对小孩子打招呼不是说“长大了你想当什么?”而是“我不认识你吗?”成人这一代是如此,后人也可想而知。当然,诗人尚葆有青少年时代的温馨回忆带来些许慰藉,就像小说《大象》中描写的一样,“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稳稳当当,高高兴兴,感觉父亲就像一头大象。大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比喻,自己就是一头负重前行的大象。在这一时刻,我想,卡佛也理解了作为酒鬼的父亲。生活的困境进而导致人陷入无边的孤独,孤独之极便会产生弃世解脱的想往,在《我的乌鸦》、《舞会》、《血》、《明天》、《悲伤》等诗歌中,诗人把死视为终结之地,一再欣赏玩味自己想象的死去的场景。
一个作家的小说与诗歌往往体现出这样复杂的联系:“文学就是一符号文本对另一符号文本的模仿。……一文本借另一文本而存在,新文本永远被某一旧文本的幽灵所困扰,或被嫁接在某旧文本上。”[5]文学的本质即是它的文本性(textuality)或互文性。卡佛的诗善于使用简练朴素的文字瞬间营造一种真实的生活场景,它们是片段式的,比如走神时的胡思乱想(《驾车时饮酒》)。像他的小说一样,卡佛的诗也善于使用省略和空缺的技术手法,对所书写事件的起因、情节和结局进行省略和空缺处理。他不去交代背景,也不凸显紧张的冲突,结尾戛然而止,造成所谓的开放式结构。他的诗还充满了对话以及戏剧性的独白。诗人有时候不是以自己的面目出现,但总有一个“我”在,是卡佛面对残酷现实的吐槽。另外,卡佛的诗,包括小说,一下就击中了美国人的内心,原因在于他所书写的是一部分美国人的真实生活。诗歌中频频出现的“钱”、“鲑鱼”、“酒”等字眼,实际上是现实、理想、毁灭的指代。因为卡佛感同身受,所以对底层美国民众的失败、破产与绝望进行了触目惊心的点画描写。有人批评卡佛只看到了美国的阴暗面,批评人士似乎不懂得美国,不知道美国梦的背后是无穷的梦魇。谁是不幸的始作俑者?让我拿什么拯救你?我们仿佛看到卡佛在掏心挖肺地思考,并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喊。
三、无功利的诗歌观
与国内作家不同的是,虽然卡佛更加珍视诗歌,但没有把诗歌看作是更高一级的文学形式。诗歌在国内作家手中,态度是仰视的,高不可攀。[6]他们中的许多大都写过诗,但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因而转向了小说创作,主要是长篇创作。他们的小说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诗化色彩。国内作家早期的诗歌创作往往被后来的小说所遮掩,因不能引领诗潮或者影响甚微,这也是自然的事情。而卡佛的诗歌却散射出熠熠光华,与小说相比丝毫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这乃是卡佛的文学观使然。卡佛对文学的期望值很低,文学能不能改变人生的境遇,对他来说没有明确的答案,是怀疑的,而现实告诉他还是别那么奢望了吧。其实在开始写作之初,卡佛已经做好了坐十年冷板凳的心理准备,不指望依靠写作发迹,来改变糟糕的生活状态,谁想他这样憋着气一写就写了二十年。在美国,人们有着短篇小说的良好阅读习惯,诗歌生存的空间狭窄。同时因为卡佛生活窘困,家庭人口众多,时间琐碎,只能选择写越短越好的短篇小说,在他逐渐优裕起来的最后十年,一万字以上的小说明显增多。诗歌这种短平快的文体特别适合卡佛对文学的单纯诉求。而他的诗歌又不像小说那样必须面对读者,更多的是写给自己。正因为此,他才能够毫无功利地写作,不去趋炎附势,追逐时风,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卡佛的创作态度是要求真诚面对自己和读者,最起码的是不让读者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卡佛是认真的,诗歌内容也是真实的。作为艰难时世的亲历者、观察者与表达者,这种生吞活剥、罄竹难书的真实,即面对生活重压和冷酷的人际关系纠缠的挣扎,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发自内心的吁叫,反倒让诗歌具有了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特点。基本上卡佛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中想象的成分也是真实的,符合当事人所处的现状和思想情绪。在中产阶级之外,卡佛成为了美国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正是沿着简单朴素、真诚无欺的创作道路,卡佛才在美国文学史上彰显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和价值,卡佛才成其为卡佛。
总结一下的话,卡佛的诗歌是卡佛一生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影子文本或者是姊妹文本。早年的卡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用文字道尽了小人物的悲哀。“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现在就想要。”[7]卡佛的诗歌就是充满了这种无法走出困顿人生的痛苦煎熬的焦灼感觉。卡佛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紧张,而是割不断理还乱的胶着,毕竟他的诗歌里面注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以及个人经历。这是其一。其二,有人说,在文学语言方面,卡佛非常明白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他将自己的语言刀砍斧削,删除心理活动,剔除形容词,用陈述句和对话敷衍小说。但是他所删除的那部分语言并没有扔掉,都跑到诗歌中去了。[8]他自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小说家,表明他是非常重视被小说遮蔽的另外一部分文字,它们以诗的形式呈示出来,洞穿小说语言皮肤之下的深意。小说作为虚构文体,有其无能为力之处,并不能达到言说的最大自由度。追求言外之意,是卡佛出于对新小说的别样追求,简单说是由于技术上的需要,而诗歌则为卡佛提供了一个尽情表达的空间,以自我为书写对象、揭示自己、锤炼自己的场域。如果说所有的文学都是诗,那首先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他的诗。如果只读他的小说,我们只能读懂半个卡佛,甚至根本无法触摸到卡佛的内心。
卡佛的一生一如他诗歌中所叙写的那样是穷困潦倒的一生。在前四十年里,他从来没有一份超过十八个月的固定工作,也没有依靠写作成为专职作家赚到足够的钱。他的孩子们也仅仅靠手工劳动挣来的钱勉强糊口。直到他的最后十年,命运之神垂青,这种境况才有所改善。卡佛去世时,留下了三座房子,两辆还算新的汽车,还有一艘十年的船,以及二十一点五万美金的储蓄。卡佛的一生令人唏嘘万分,也为他那些夫子自道般的诗歌画上了一个还算完美的休止符。
[1]胡雁然.特殊的流水账——品卡佛的诗[J].诗歌月刊,2010,(10).
[2](美)卡佛.苔丝·加拉格尔.序言[M]//舒丹丹,译.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15.
[3](日)村上春树.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M]//(美)卡佛,著,肖铁,译.大教堂.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3.
[4]舒丹丹.被小说遮蔽的卡佛的诗[N].文艺报,2013-06-12(05).
[5]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
[6]王万顺.作为小说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当代小说家诗歌创作现象简析[J].诗探索,2012,(3).
[7](美)Carol Sklenicka[M].Raymond Carver:A W riter's Life,Scribner,2009:389.
[8]泛凫.卡佛: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J/OL].http://article.hongxiu. com/a/2009-6-7/3211163.shtm l.
责任编辑:陈冬梅
I106
A
1671-4288(2015)03-0027-04
2015-04-24
王万顺(1976-),男,山东青州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