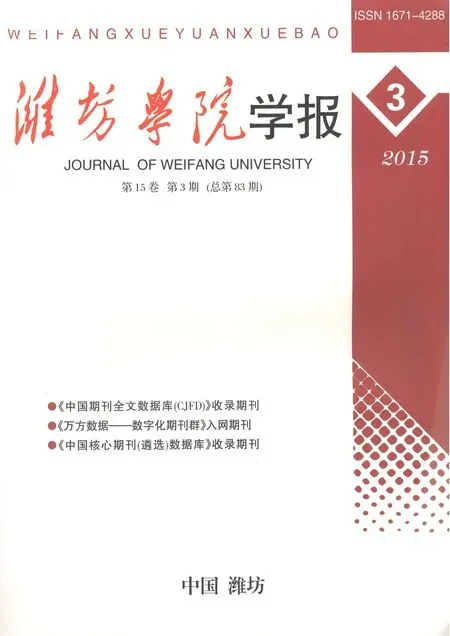纯真与经验之歌
——《潜水鸟》与《故乡》的比较研究
王建伟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纯真与经验之歌
——《潜水鸟》与《故乡》的比较研究
王建伟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潜水鸟》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短篇小说集《屋中的小鸟》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借草原潜水鸟的销声匿迹、自然环境的改变来暗喻梅第女孩皮格特·坦那瑞人生轨迹的变化以及梅第人社会生活边缘化问题。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刻画了与皮格特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人物闰土,借农村生活的凋敝以及闰土的沧桑变化来反映农民在民国乱世间的艰难处境。这两部作品有着许多卓然可比的文学现象,他们对自然美好乡村的怀念、人文社会对自然的破坏、特定社会环境下处于底层人物的遭遇方面都有着相似的探讨,共同唱响了一首纯真与经验之歌。这两个文本所具有的能够引发共鸣的内在一致性为他们的平行对比提供了可能性,彰显了文学跨域国别、跨域文化和语言所具有的普遍而永久的魅力。
边缘化;纯真;《潜水鸟》;《故乡》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一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久负盛名的加拿大女作家,她以虚构的草原小镇马纳瓦卡为背景创作的五部小说——《石头天使》(1964)、《一个上帝的玩笑》(1966)、《火中人》(1969)、《屋中的小鸟》(1970)和《占卜者》(1973),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加拿大特色的全景式画卷,让人“不由得驻足凝望”。马纳瓦卡系列作品奠定了劳伦斯在加拿大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她赢得了极高的世界声誉。《屋中的小鸟》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她不同时期写的八个故事。其中《潜水鸟》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皮格特·坦那瑞的梅第(法裔和印第安人的后裔)少女的故事。皮格特年少时热切渴望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最终未能与命运成功角逐而变得心灰意冷,麻木度日。小说借草原潜水鸟的销声匿迹、自然环境的改变来暗喻主人公人生轨迹的变化以及梅第人社会生活边缘化的问题。
这个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192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乡》以及小说中与皮格特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人物形象闰土。闰土亦曾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年,但最终被社会和岁月打磨成一个麻木懦弱的沧桑中年人。小说借农村生活的凋敝以及闰土的沧桑变化来反映农民在民国乱世间的艰难处境。
笔者从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传记及其诸多作品中未发现她与鲁迅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联系,杨周翰、乐黛云、李春林等编写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著述中也未曾提到玛格丽特·劳伦斯,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亲缘关系”或“因果联系”。虽是如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作品之间不存在平行研究的可能性,相反,笔者经过文本细读认为鲁迅的《故乡》和劳伦斯的《潜水鸟》两部作品中有着许多“卓然可比的文学现象”,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研究价值。本论文试从主题学角度对两部作品做平行对比分析,以期挖掘出两部优秀作品所共同拥有的超越国界、超越文化的文学内蕴。
一
《潜水鸟》故事发生在马纳瓦卡草原钻石湖旁的乡间别墅、“我”(叙述者——温妮莎)家的避暑老屋——“麦克里奥”。“碧绿的湖面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云杉树枝叶茂密,周围长满了凤尾草、悬钩子藤、野草莓,灰色的小松鼠也是这里的常客。“我”在冰凉的湖中游泳,树林里探险,玩过家家,还有在夜间去钻石湖听潜水鸟的叫声。这儿是原始的大自然,是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童年记忆的快乐王国。父亲让孩子们好好听听并记住潜水鸟的叫声,因为过不了几年,随着来这儿的人多起来,它们就会离开钻石湖。潜水鸟在夜间会“像幽灵般地从岸边的窝巢中腾起,飞往平静幽暗的湖面上”。它们的叫声“悲凉凄厉,任何人都无法形容,任何人听后也难以忘怀”。
数年之后从大学回家,“我”又一次来到钻石湖,这时父亲已经过世,“麦克里奥”老屋已卖与别家。“从此我再也没去看它一眼,因为我不想看见自己昔日的王国如今为别的陌生人所有。”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去了湖边,父亲筑起的小栈桥如今已被政府出资修筑的大栈桥代替,钻石湖也改成一个颇具印第安风情的名字。湖边已经有了几十家商店,加上舞厅、宾馆、咖啡馆,四处弥漫着炸土豆片和热狗的香味。而那些让人惦记的潜水鸟终于没有出现,“我”到底还是没有听到“尾音拖得长长的、凄厉而带有冷嘲意味的叫声”。
《故乡》中的“老屋”在“我”(叙述者——迅哥)阔别二十余年后也是人去楼空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这全然不是“我”记得的故乡。“我”的故乡好得多。当“我”到家时,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当母亲提起儿时的玩伴“闰土”这一名字时,儿时的记忆全部闪电般苏醒过来。对于“闰土”的记忆全然离不开美好的自然和天真的童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少年的闰土会扑鸟,什么鸟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海边日里拾贝壳,红的绿的,鬼见怕,观音手。晚上跟爹管西瓜,月亮底下拿着胡叉刺獾猪、刺猬、猹。这就是我对家乡的美好记忆,这儿有淳朴的游戏,大自然的新奇探秘和孩子们纯真的情意。但最终有着美好童年记忆的“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
两篇小说均以“回乡”、“老屋易主”为故事线索,共同交织出对家乡的怀念和对美好童年的留恋,同时展示了时代带给家乡面貌的巨大变化。《潜水鸟》中我“家”的别墅与自然合二为一,鲁迅对于老屋的最美好的回忆也是那个在深蓝的天空下自然纯朴的少年。乡村原本是自然的、健康的、充满生机的,但多年之后两个“我”均发现今日之故乡已非昨日,自然遭到破坏,童真亦被泯灭,乡村因被社会物质化抑或是贫瘠化而失去原来的自然本质。
二
与环境改变同时发生的是主人公人生轨迹的改变。“皮格特”和“闰土”一开始都是作为“玩伴”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潜水鸟》中皮格特与“我”是同班同学,一个梅第人——法裔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家住在丛林中搭建的简陋棚屋里。她患有骨结核,经常缺课,我们之间没有多少交集。一年暑假作为主治医生的父亲建议带她一起去钻石湖度假,方便对她腿的治疗。这个建议一开始遭到母亲和外婆的反对,但最终她还是去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陪“我”玩耍。《故乡》中,“我”正是一个少爷,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家大祭祀值年缺人手,闰土的父亲便把闰土叫来帮忙。这样,他成了“我”的玩伴。
皮格特说话声音沙哑,由于骨结核的缘故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她皮肤粗糙,脸庞平宽,又黑又直的长发垂到肩上,具有典型的印第安人的面貌特征。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有着农村乡土特色的装扮。
皮格特来自森林,闰土来自乡村,他们均来自充满着万千奥秘的大自然,一个“我”所陌生的世界,让年少的“我”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幻想。闰土不到半日便跟“我”熟识起来,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和朋友往常所不知道的。
虽说皮格特一直没有跟我熟识起来,却也是一个让“我”着迷的人。皮格特印第安人的血统以及印第安人祖先的历史使她在“我”的眼中产生了无穷魅力。皮格特的祖先是“大熊”和“庞德梅克”的族人,是那些吃过布雷博夫神父心脏的易洛魁人,“我”想她一定熟知许多大自然的奥秘——夜鹰在哪里做窝,猎狼是如何育雏,还有《海华沙之歌》中提到的所有事情。在“我”的眼里,她就是森林的女儿,蛮荒世界的女先知。
毕竟他们仅仅是作为“玩伴”短时间出现在“我”的身边,当年少不再,当各自忙于学业、生计时,“玩伴”渐渐退出“我”的生活。数年后再次相见,他们都有了惊人的变化。
乡村别墅一别后,“我”只与皮格特打过一次照面,那是多年后在咖啡馆的一次偶遇。她大概是十七岁,以前呆板的面孔“现在却带有一种有几分狂欢的活力”,她涂着鲜亮的洋红色唇膏,头发烫成弯弯曲曲的小卷,而且“一条紧身裙和一件桔黄色毛衣将她那柔软、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恰到好处”。在钻石湖的那个夏天她整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从不与“我”多说一句话,而今变得十分健谈,絮絮叨叨地向“我”诉说对小镇的不满和几年来的经历,最后还向“我”透露,她就要跟一个白人小伙子结婚了。此刻“她那揭下面具和保护罩的脸上露出的是一副坚强不屈、敢于挑战一切的神色,她的眼神里也透出一种强烈得令人害怕的渴望”。这一次其实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真正认清她的面目,充满渴望憧憬的真面目。如果说那年夏天闷闷不乐、敏感多疑的女孩并非我所真正认识的,这次才是她未加伪饰的原本的面目。
之后再没见到她。大学一年级放假回家跟母亲拉起家常,母亲面带难色地说出皮格特的情况,“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最后几年里,没有人确切了解她的情况,只听说她跟那个小伙子结了婚,可后来又分了手,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家乡。她从不跟人说话,愈发变得不像样,衣衫邋遢,肥胖不堪,整日酗酒。一个寒冷冬日的夜晚,醉酒的她带着孩子在窝棚里,窝棚起了火,他们没有逃出来。
《故乡》中,三十年后“我”回乡卖房时再次见到闰土。三十年的艰辛生活把这个颈戴银项圈、健康活泼的少年打磨成了满脸沧桑的中年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见到我,他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比起闰土,皮格特更早地体察到了等级地位和种族之间的歧视与不平,因而在原本少不更事的年纪就过早地变得敏感。对于“我”的每次邀请都视为不怀好意,她一方面抗阻着来自白人的帮助和友善,而另一方面则在内心渴望着能够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能够被白人接纳。她争取过,但是现实打碎了梦想,最终她放弃了追求而麻木地生活,以至于麻木地不再把生死放在心上,像潜水鸟一样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地方而自生自灭了。
闰土也许自小就习惯了旧时封建礼教的约束,未曾企望能够过上与迅哥一样的生活,他现在所谓的希望就是烧香点烛供奉着神明偶像,相安无事地生活。然而,忍辱负重、辛苦麻木的闰土何尝不像潜水鸟,“把生死也不再放在心上,就这样自生自灭了”呢?
三
皮格特和闰土的人生巨变对应着家乡的巨变,是动荡社会的生动体现。加拿大建国之前,印第安人和梅第人一直以来就居住在北美大陆茂密的森林里,以狩猎为生。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建国的过程中向西扩张,与印第安人和梅第人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冲突,梅第人领袖里尔在1885年的反抗中被捕并施以绞刑,梅第人起义遭到彻底失败。《潜水鸟》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尔起义失败的50年后。皮格特的祖父曾跟随里尔参加过战斗,失利后便在马纳瓦卡山下的空地上建起了简陋的棚屋定居下来。《潜水鸟》反映了梅第人的土地被政府进一步蚕食,他们被迫放弃原有的土地,放弃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没有了森林和土地,无猎可狩,无牧可放,他们只得四处打零工,无所事事。家乡已面貌全非,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与潜水鸟一样随之消失匿迹,这便是加拿大原居住人生存的状况。
鲁迅1919年回乡接母亲去北平,目睹了辛亥革命前后几十年间乡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生活的困苦。辛亥革命时期,农民遭受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剥削和压迫,终身侍弄着小块田地,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多子,饥饿,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人民“像一个木偶人了”。同时中国农民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忠孝思想的影响,养成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性格。闰土未曾尝试着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未曾反抗过,但试想如果他也曾像皮格特那样争取过,恐怕也难免皮格特的结局而更加麻木不仁了。
闰土和皮格特在文学中属于与时代密切关联的典型形象,反映着时代社会特征,具有时代意义。闰土的变化、对命运的态度和人生结局符合民国时期具有旧封建思想的农民现实境况。鲁迅先生抨击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农村生活的衰败以及社会对农民的盘剥。而皮格特的变化和命运悲剧反映了梅第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加拿大社会尴尬的边缘化地位,即便有过抗争也无法逃脱族裔命运的安排。他们都未曾走出希望、希望幻灭而后变得麻木的怪圈,未曾走出时代社会的命运。
“我”与他们最终未能达成一种长久而平等的关系。他们终究是以“下等人”的身份来到“我”身旁的玩伴,无论年少时如何无拘无束,等级和种族身份的差异最终未能消融他们之间无形的藩篱,玩伴终归是玩伴,不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是并肩作战的革命者,也不是亲密无间的家人,他们之间的鸿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终难逾越。对心怀良知的上等人“我”来说,面对他们穷困潦倒的生活除了同情无助之外,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两部作品中除了“我”在故事叙述中流露出来的善意和同情,还有来自父辈人的些许期望。“母亲”多年一直对闰土照顾有加,搬家时不能搬走的家具留给闰土补贴家用,而对那些如杨二嫂一般的偷营之人不屑一顾。“父亲”是皮格特的医生,像亲人一样地照顾着皮格特,皮格特自己也坦承“父亲”是镇上唯一一个对她好的白人。也许这就是一息尚存的希望,在寒冷的冬天,在主人公悲惨的生活境地里,让人还依稀感到一点温暖。
乐黛云认为“和而不同”是研究比较文学的重要原则,某些“不同”所以能构成“和”,是因为其中具有某些“和”的“因素”,也就是具有某些相似的,可以引起共鸣、可以一以贯之、可以找到某种共同历史渊源的层面。比较文学研究的其中一方面就是在不同文化的文学里,从诸多差别中,寻求其内在的一致,也就是“和”。劳伦斯和鲁迅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在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文学内部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对于自然乡村的留恋、人文社会对自然的破坏、特定社会环境下处于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都有着相似的探讨,正是这些“和”的因素为两个故事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也反映了文学跨越国别、跨越文化和语言而显示出的普遍而永久的魅力。
[1]King,James.The Life of M argaret Laurence[M].Toronto:Vintage Canada,1998.
[2]Laurence,Margaret.A Bird in the House[M].Toronto:M 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74.
[3]Page,Norman.Speech in the English Novel[M].London:Long man,1973.
[4]Selected Storiesof Lu Hsun.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Gladys Yang[Z].http://www.ibiblio.org/eldritch/hsun/hsun.htm#Home.
[5]陈淳,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李春林.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玛格丽特·劳伦斯.占卜者[M].邱艺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9]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杨周翰,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1]张汉熙,王立礼.高级英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12]张鑫友.高级英语学习指南:第一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3]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A Song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oons and My Old Home
WANG Jiang-wei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 The Loons”is one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A Bird in the House written by Margaret Laurence, a woman Canadian writer. The story expos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etis people in Canada by relating the changes of Piquette Tonnerre, a Metis girl and also employing the symbols of loons’disappearance and nature’s changes.“My Old Home”by Lu Xun depicts a Chinese peasant Jun-tu, who has a similar life course as Piquette and reflects the intense sufferings of the peasants during the turbulent ye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changes of countryside and also the changes of Jun-tu. Within the two texts are lots of comparable literary elements, like yearning for the beautiful rustic life, damage to the nature by the human society and blights of the lower class, woven with a song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The resonating unity within the two text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also shows the universal and everlasting charm of literature acros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marginalization;innocence;The Loons;My Old Home
I106
A
1671-4288(2015)03-0031-04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5-03-21
王建伟(1970—),女,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加拿大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