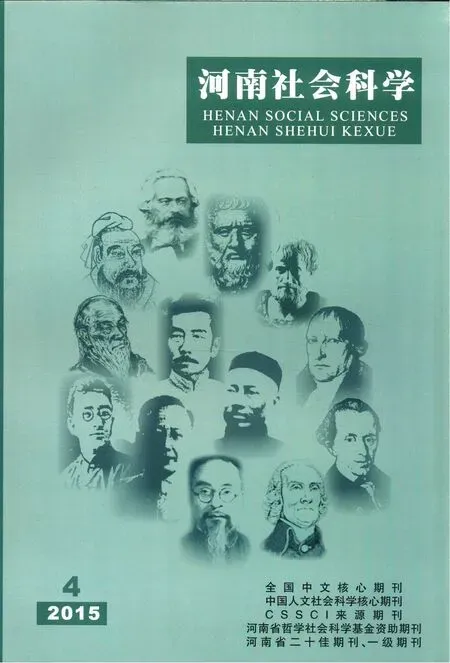元代科举制与延祐以后南北文风的混一
杨 亮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元代科举制与文风的关系是什么?元人文风的趋同混一是否和科举制的实行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元代诗文风貌趋同混一是后人常常引用并习以为常的结论,但形成这种风貌的原因却没有一个圆满的回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文学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在元代,其中是否有内在特殊性?从元代科举制实行前后文士的态度和文风的转变入手,或许能对这一重要问题有所解答。
一、词赋的存与废——元代科举背后的角逐
自元世祖立国伊始,便屡有志士建言必复科举,然而对词赋科试的存废之争,以及元代早期统治者对科举的轻视,使得重开科举一直延宕到近半个世纪后的延祐初年。其间,纠正程文之弊是词赋论争焦点之一,主张古赋取代律赋成为科举条目,复古文风开始在文坛取得主导地位。
世祖立国之初,大臣宋子贞、史天泽即进言开科取士,至元四年(1267),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又上奏忽必烈请开科举,然而均为有司所阻[1]。至元七年(1270),朝廷复议行科举之事,当时文臣中分成了两派,并围绕科目展开了辩论:一派以出身金代科举的礼部、翰林院的金莲川幕府文臣为主,如王鹗、王磐、徒单公履等,他们沿袭金代旧制,拟以经义、词赋取人。另一派则是尚书省的许衡、董文忠等北方新理学派,他们秉承词赋害理的理念,竭力反对将词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对宋代科举弊端的承袭。这便是当时的词赋派与理学派,也叫“文章派与德行派”[2]。关于词赋要不要列入科举中的论争,显示了两派背后的宋、金二朝文士在学术思想、治学路径上的差异。当时蒙元政府正忙于讨伐南宋的军事斗争,行科举并非头等重要的大事,两派的论争使科举更加难以恢复。
这场争论中,同在翰林国史院任职的北方文士王恽写了重要的《论科举事宜》《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议贡举》等一系列奏章,他既反对沿袭金制的词赋取士,又不赞成理学派的激进主张。他基于“实用”和“得人材”的目的,依据现实情况并参考唐宋取士的特点,提出切实的建议,特别强调朝廷的引导。因为“诗赋立科既久,习之者众,不宜骤停”[3],但是针对词赋取士的弊端,他提出在廷试中着重试经史的方法,以革学风尚虚文之弊端,经史、词赋两科则“转经出题”,“先为布告中外,使学者明知所向”[3],即朝廷引导士子学习的方向。王恽的方案显然更加务实而有针对性,他能将蒙古人务实的民族心理、朝廷取士的现实需求,以及词赋文章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结合在一起,针对词赋大有人习的社会事实,反对骤然罢黜词赋一科,而是建议朝廷引导士子学习的方向,以规避泛滥无端、专以虚文为务等词赋科的历史弊端。
造成元代科举久废的原因有很多[4],其中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文人,均认为科举有很大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科举考试中词赋科空疏不切实用,不利于选拔人才。宋金亡国,遗民多以国家之坏归罪于科举。如戴表元在文集中就多次提到“科举之弊”,赵文在宋亡科举不行之后曾说:“四海一,科举毕。庸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丸而使之浮游尘埃之耶?”[5]在北方儒士中,“金以儒亡”的观念也很流行。宋金诗文之弊,时人也以为是由科举程文所引起的。这样的观念也为元代南北文人普遍所接受,吴澄、许有壬、胡祇遹等也多批评科举程文的空疏无用。胡祇遹言:“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也,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万言,愈博而愈不知其要,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何功之有?”[6]蒙古统治者一向注重实用,对于汉族的诗赋文章,颇为轻视。一言可以兴废的忽必烈,对于科举并不感兴趣。忽必烈对于儒生“日为诗赋空文”十分不满,他曾问许衡:“科举何如?”许答道:“不能。”忽必烈很满意许衡的答复:“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7]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了解不深,认为词赋空虚无实用,科举所取人才只能舞文弄墨,没有其他能力。这也是有元一代进入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文士只治文事,不能参与实际政治的原因,这实际上成了元朝治国方略的一部分。
科举制度在易代之际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其弊端被无限放大,加之舆论普遍对科举评价不高,议言科举者在当时很难找到共鸣。张之翰《议科举》云:“自国家混一以来,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8]
延祐前期关于词赋的这些争论,直接影响到了科举恢复时科目的设置。词赋在后来虽没有被废置,但废去了易于流于外在形式、讲求华丽辞藻的律赋,而仅考古赋,蒙古、色目人则可以不考古赋。另一方面,经义以朱子“四书”为尊,理学等策略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的,不可避免地成为元代统治思想的主流。
元代科举只考古赋,加之理学标准的特点,形成了元代学术质朴无华的风气,同时也影响了文风的走向,浮华艳丽的文风在元代受到了排斥,这也是“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能够风靡延祐文坛的原因之一。
二、从对峙到混同——科举恢复前诗文丕变
(一)承宋金之弊、诗风歧异的南北文坛
元初南北统一之后,在地域上有南、北之分隔,而诗文创作也是承宋、金之旧,各有特点。欧阳玄对此总结道:“宋、金之季,诗之高者不必论,其众人之作,宋之习近骫骳,金之习尚号呼。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9]虽有元人的成见在其中,不过大体上还是符合元初南北诗歌创作的特点。龚肃在为袁易《静春堂诗集》作序时说:“一自士去科举之业,例不为诗,北音伤于壮,南音失之浮。”[10]欧阳玄与龚肃对元初诗歌特点的批评可谓不谋而合,这也代表了元人对于元初诗歌的看法。
元代统一之前,南方诗风流于浮艳,北方诗风限于粗豪,这是对一统之前南北文坛的一般认识。然而在这样的特点之下,南北文风的具体情况亦各有所侧重。宋亡之后,元初南方诗歌创作呈现一派繁荣之象,这与宋亡之后科举废止有关。由于宋代科举不考诗歌,故而读书人专习程文,无复用力于诗歌。举凡诗歌者,要么是已入仕途而在公务余暇时所作,要么是不求仕进的江湖文人所作。“宋人尚进士业,诗道廖落”便是宋代文坛的面貌[11]。直到宋亡,科举之业废,士子们开始竞相创作诗歌,诗学大兴。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学者多有描述,“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成为当时共识[12]。黄庚便是其中的代表:“仆自龆齔时,读父书承师训,惟知习举子业,何暇为推敲之诗,作闲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13]从黄庚的自身经历来看,科举对宋朝士子的牢笼束缚不可谓不深,“平生豪气”尽被压抑,所以当时宋亡以后文人士大夫对科举的痛切批评不可谓无因,“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成为元人对南宋文坛的主要观感[11]。科举废止后,程文无用,士子们无所施其才志,“呻吟憔悴无聊,而诗生焉”[14],诗歌恢复到吟咏情性的本位。
一种习惯性的制度虽然被废除,然而其潜在影响不可能骤然消失。科举程文由于篇章结构、起承转合等都有固定的模式,易于模仿。科举废除后,士子弃文作诗,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这些诗歌大都难脱时文习气,科举程文的固定模式自然而然地又被带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去了[15]。故而元人批评宋末元初诗歌:“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12]便是据此种情况而发。虞集所谓的“事科举者以程文为诗”亦源于此[16]。
就诗歌风气而言,元初南方诗歌主要有三派续有影响,均为继承南宋而来,分别是四灵、江湖、江西,其中尤以江西诗派对元初诗人影响最大。在元初诗坛颇为有名的江浙诗人如戴表元、赵孟 、仇远、白珽等人的诗学渊源,大多自四灵而来,只是他们的诗歌注入了时代特征、人生感慨、故国之思等的抒写,使得他们的内容更加深厚,意境有所扩大。
总的来看,虽然元初南方诗歌受南宋众多流派的影响,复杂多变,却也给了学者转益多师的机会,尤其在时代之变的历史大环境之下,个人遭际与家国之感都融入到了诗歌中,借助多样化的诗法表现出来,遂使得元初南方诗歌创作蔚为大观。
同时期,北方的诗文风尚与南方大不同。北方诗歌承金代诗歌之余绪,燕赵之地多豪杰之士,诗风亦粗豪,欧阳玄所说的“呼号”便是北方诗歌豪放阔大特征的别样说法。对于北方诗歌,固有的看法是学习苏轼,这与清人所谓“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17]有关。金代后期,学苏之外,亦学黄庭坚之诗、韩愈之文。于是便导致学苏的平易与学黄、韩奇崛之间的矛盾,由此影响到了元初诗文家,他们之间也分为两派。
关于元初北方诗文风格流派,今天学者多有论述,查洪德以为:“在元初代表诗文家中,郝经、刘因、姚燧为一派,他们承金末奇崛之脉,诗学李贺,文学韩愈;卢挚、王恽为一派,他们接金末平易淡泊一脉,诗学唐代元、白,由元、白更上追魏晋,文宗宋代欧、苏。”[18]可以说涵括了元代北方诗歌的总体特征。
在元初诸流派之外,理学诗风尤须引起重视。理学诗在南宋以说理为主而文采次之,以至“理学兴而文艺绝”[19],为当世所批评。然而南宋末期在理学家诗人中间,已经开始反拨前期重理学宣扬、轻视诗歌美学特征的弊端。尤其以叶适为盟主的浙东学派,更加注重文辞的功用,能够不以理害文,浙东学派的学者,多有以文章名世者。到了元初浙东学派的戴表元、袁桷则对理学害诗痛加批评。而吴澄所学为朱子理学一派,亦辩驳朱子之学“未尝不力于文也”[20]。可以说元代初期学者都已不再拘守理学的森严门户,“作文害道”的观念已不被认同,文道调和观念渐成主流。是以元代理学继续发展,并由南方传至北方,最终程朱之学成为元代官学,但理学“流而为文”,治理学者如吴澄、许衡、虞集以及金华学派诸人都是学者而兼文人身份[21]。这些代表者中,他们的诗歌还表现出与文章截然不同的审美趋向。
(二)元代南人北游与混一文风的肇端
随着蒙元灭宋,南北一统,元初南北诗文风气的不同出现改变。其间的节点是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诏南方求贤,此后江南俊彦大量进入北方,南北文风由此开始融合,新的诗文观念被提出,渐渐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领导南北文风融合潮流的,首当赵孟 无疑。程钜夫所求江南诸贤中,赵孟 为第一人,可见赵孟的影响力。赵孟 至大都后,与当时北方文坛名宿往来唱和,主导着当时文坛风向。当时北方卢挚、刘因等在文坛倡导复古,学习唐人诗法。赵孟 结而和之,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宗唐复古”遂成为一时潮流。“静修刘公复倡古作,一变浮靡之习。子昂赵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视唐无愧。”[22]在世祖时期,大都文坛以北方文人为主。直到成宗大德年间,吴澄、袁桷、虞集、贡奎等南方文人均赴大都,并先后进入翰林国史院,开始在文坛上展露他们的声音。这一时期,北方文坛名宿相继去世,主盟文坛的已是北方文坛领袖卢挚和姚燧,且二人都以文章称名当世,诗歌方面的才华则不及南方文人。故而袁桷、虞集、吴澄等与赵孟 等一起,高举“宗唐复古”的大旗,共倡建立诗文新风尚。袁桷论诗推崇赵孟 ,亦以唐诗为宗。他认为:“然则诗果何自哉?唐诗之完,成于文敏,诗由文敏兴矣。诗盛于唐,终唐盛衰,其律体尢为最精。各得所长,而音节流畅,情致深浅,不越乎律吕。后之言诗者,不能也。”[19]在《书闵思齐诗卷》《书余国圃诗后》等文章中,充分表达了取法《诗经》“风”“雅”之义,务求表现出“舂容怡愉”的气度,“将以鸣太平之盛”[19]。和袁桷同时的虞集也倡导元诗和平雅正,成为治世之音,其影响也最大。
虞集关于诗风最著名的论断是:“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11]他认为诗歌情感应该中正不迫、雍容典雅:“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务,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11]这是虞集诗论的核心论断。而虞集这些诗学理念之所以能够风行天下,为文人士大夫所尊从,实与虞集喜奖掖后进,交游广泛有关。延祐以后四方文士游京都求仕者甚多,而“道德文章重海内”的虞集平易近人,多举荐后进之士,是以“四方来见之士,道路相望,坐上常满”[23]。当时名士如苏天爵、王守成、陈旅等都是由虞集所提携。是以虞集倡导诗体复古革新,能够为当时文士所响应。欧阳玄《梅南诗序》言:“京师近年诗体一变趋古,奎章虞先生实为诸贤倡。”[12]虞集在元代文风的融合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大力提倡雅正的文风,致力于元代盛世文风的构建,对元代及明代文风影响深远。
今天所谓的元代文坛南北文风的融合、“复古宗唐”的风气在元初并不鲜明。直到大德年间,这种理念才被赵孟 、袁桷、虞集等宣传强调,作为一种诗学追求而被普遍接受,遂成为元代文坛的一代文风。可以看出,北方文人关于新的诗学风尚的倡导作用不是很明显,而南方文人在其间居于主导地位。到延祐初年,北方文坛宗将卢挚、姚燧相继辞世,文坛遂由南方文士所驰骋,北方文士中稍有名声者,只有元明善一人,与虞集并称于世。然而元明善以文章见称于世,诗名不显,元代后期很多文人对其已多不知晓。
元初的复古风气并没有形成潮流,虽然南北文人对各自文风的衰弊都有认识,南北双方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南方文人袁桷、虞集、吴澄等倡导的“宗唐复古”、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在延祐之前,只是稍开其端,延祐恢复科举,南北文人交流的频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的诗文风尚有了更广大的受众,从馆阁之士到民间文人,无不为建立符合元朝盛世局面的文风努力。王理《元文类序》对元朝一代文风发展进行概括:“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车书大同,风气为一。至元、大德之间庠序兴,礼乐成,迄于延祐以来极盛矣。大凡国朝文类,合金人江左以考国初这作,述至元、大德以观其成,定延祐以来以彰其盛。”[24]可以看出元代文风变化的脉络,即国初祖承宋金之弊,至元、大德是新文风形成之时,延祐为文风兴盛之时,这里面都有科举制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关注是,元代虽有四等人之分,但是身份较低的南人在科举制和文坛上却成为主流,这大概是蒙古统治者并没有认识(料想)到的,凭借科举制度的国家意志,南方文人事实上成为元代文学思潮的主导,其文学品评标准占据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
三、混一文风的流衍——以科举中的师生网络为中心
元初南北不同的文风,在大德间开始混一趋同,形成平易雅正的盛世文风。而混一文风的流衍于世,成为文坛普遍的追求,则是在延祐时期,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科举制。
“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灵亦寂然者四十年余。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断,明诏天下以科举取士,而蜀人稍复治文昌之祠焉。”[11]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在科举制废除后没了实际的用处,其庙宇倾废,而元仁宗延祐时恢复科举,文昌君的祭祀也恢复并又逐渐兴盛,可见中国古人在祭祀神灵上也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元代科举制实行之后对文人诗文风气的引导不可忽视,揭傒斯说:“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去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也。”[25]而科举“利诱”作用的实现,则有赖于科举中座主、门生、同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元代科举的实行,使得座主、门生与同年之间形成一个社会关系网络[26],这种网络可以看作是一种人际关系和派系,它们保证了延祐之后科举之士意见的一致性和趋同性。具体来说,表现在延祐盛世文风在元代这一社会网络中得到快速传播和接受。
在这个传播网络中,元代考官也即座主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考官的文风追求,往往通过衡文选士的权力影响士子,为士子们所接受。历史上亦不乏此例,如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举考试,任主考官,他黜落了一大批写“太学体”文章的考生,选取了苏轼、苏辙、张载、曾巩等文风平易朴实之辈,这些人被录取后进入文坛,并进一步主盟文坛、主持科举,继续推行平易典实的古文创作,与欧阳修等前辈共同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从中可见考官在推行文风革新中的关键作用。
元代新文风的推行,考官在其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前代不同,元代考官多出自翰林国史院及各地名士宿儒,名望是选考官的一个重要考量,并且一人往往多次担任考官,并不忌讳座主、门生之间形成朋党。元代新文风的倡导者都不止一次担任乡试、会试的考官。譬如袁桷曾“为读卷官二,会试考官一,乡试考官二”[27],“自设科取士,桷未尝不预议焉”[19]。其中一次是担任了十分关键的大都路乡试考官。
多次任乡试或者会试的考官,甚至任廷试的读卷官,使得同一考官往往门生众多,另一方面本朝进士往往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担任考官,这种情况从延祐开科之后的第二科即开始出现。考察相关文献记载,本朝进士担任考官的情况非常突出,欧阳玄、黄溍、干文传、许有壬、马祖常、王沂、张士元、李祁、吴师道、杨惟祯、郑复初、黄清老、俞镇、宋本、宋褧、余阙、林泉生、吴暾、夏日孜、卢琦等是进士出身而担任考官。元代科举考试的这两种特点,使得座主、门生之间的关系网络非常庞大,同时消除了南北地域上的分别,这保证了诗文风尚能够稳定有序地传承并被发扬。虞集、袁桷、邓文原等盛世文风的倡导者通过担任考官,他们的文风对其门生自然而然产生影响,而门生复又担任考官,文风如脉络一样传承有序。这是延祐以后,单一的诗文风尚能够占据文坛的原因。
具体而言,座主的文学理念通过批卷选士的权力影响门生,合乎考官文学理念的考生文章容易胜出。元代科举考试的设计更容易使应试文士走向复古之路,比如延祐五年袁桷主考,所出试题《试进士策问》:“夫礼以防民,乐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19]这就要求应试文士熟读经史,从古代典籍中找到理论依据。袁桷在泰定元年的《试进士策问》中说:“时有古今,制宜损益……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于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纲领,当今未尽举行者,何事?”[19]客观地说,袁桷所出试题难度很大,要求熟读经史,其目的是必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必须从历史中找到根源与依据。科考的目的是录取那些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的文士。苏天爵与袁桷又同在翰林院任职,苏天爵虽是北方文士,但与袁桷、虞集关系交厚,到了他主持进士考试时,所出试题为《廷试汉人南人策问》:“今天下治平百年,制礼作乐,维其时矣。子大夫明古今之制,通礼乐之原,其详陈之。”[27]这一试题居然与袁桷早年所出试题十分相似,至少说明考官的观点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认识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有相同之处。元代大儒黄溍是继袁桷、虞集之后的文坛代表人物,他是延祐二年进士,之后在翰林院任职,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其《金华黄先生文集》中收有各类策问51篇,涉及领域广泛,所出试题的难度比袁桷所出要浅显明了,如其《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十八首》其二:“学者将以行之也,所学何道欤?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学……愿试陈之,无以让为也。”[28]总体而言,元代科举所出试题,突出讲求实用的色彩,其要求从古代经史中寻找治国之依据。而且元代科举考官往往是长期担任,上文中所说的袁桷、黄溍都是如此,而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师承关系,这些被录取的文士大多充任到翰林院中,这就构成了一种师生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师友网络,使他们的理念更为趋同,故而元代的雅正风气、宗唐理念和科举的试题是有密切关系的。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元代通过科举考试建立的师友网络关系,并没有所谓的民族之间的界限,其蒙古、色目进士汉文化修养甚深,成为元代文坛追求雅正的重要力量之一。元仁宗延祐元年首开科举,延祐二年三月廷试,李孟、张养浩、元明善、袁桷都曾任考官,马祖常中二甲第一,他是色目人。此年录取的张翔、哈八石、马祖孝是色目人;许有壬、王沂是汉人;黄溍、欧阳玄、干文传、杨载是南人,这些人有很多都成了日后文坛的重要领军人物。其中马祖常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任职,与袁桷、虞集等人交好,日相唱和,成为提倡元代雅正诗风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元代科举考赋,最能体现出考官的影响。元代刘仁初所辑科举文献《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收录了元代科举中的考赋资料,里面辑录了许多考官的批语,从这些批语可见考官所认同的优秀古赋的特点[29]:
卷一湖广乡试第十二名陈泰的《天马赋》中考官批云:“气骨苍古,音节悠然,是熟于楚辞者,然不免悲叹意,疑必山林淹滞之士。天门洞开,天马可以自见矣。”所谓“气骨苍古”,其实意思还是说赋文有古风,又说是“熟于楚辞”,可见赋文摹拟楚辞是比较受考官欢迎的。卷二江西乡试第十八名冯福可《云梦赋》[30],考官批云:“此赋虽简,绰有楚声。”第四名周尚之的《科斗文字赋》,考官批其试卷云:“诸卷形容科斗,殊使人闷,然此篇词气老□,有感慨怀古之意。”卷四江西乡试第五名彭士奇《泰堦六符赋》,考官李将仕批云:“赋雍容典雅,善于铺叙,非苟作者。”卷五湖广乡试第二名周镗《大别山赋》,考官掦徯斯批云:“笔力高古,远追作者,六用江汉,愈用而情愈深,有三百篇之遗音焉。”卷六湖广乡试第二名曹师孔《灵台赋》,考官刘岳申批云:“此赋音韵铿然,造语下字殊有楚声,发明文王不忍劳民之意,又非雕虫篆刻者比。”
从这些批语可以看出,考官们认同的佳作,大都是能够复古,有楚声,以楚辞为师法对象。这就给举子们点出了习文的方向,即复古典雅风格的文章才能中选。举子认真揣摩已中进士习作,又通过《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这一类科举范文选集等形式促使中举习作在士子中传播。这便是科举将“宗唐得古”、平易雅正的诗文风尚广泛传播的具体途径。
刘仁初在《庚集》目录之后题曰:“圣朝科举,中场用古赋,而赋者辄能一洗近代声律之弊,复继古人浑雄之作,猗欤休哉!”[31]科举改变文风的显著效果之一是带来了元代诗文风气的一致性:“近循习多用赋,则赋当日盛,上不追骚,下亦不失为汉、魏矣。而世反有今不逮昔之叹,何哉?……后之人无学可充,而惟式是拟也。”[32]显然,许有壬严厉批评了科举考试之后举子应试时卷子的雷同。反过来说,科举考官在其中起到的倡导作用不可忽视,师友网络的建立使观念的一致性有了可能。
四、元代科举中文风传播的多样性——书序与雅集
元代科举考试促使了平和雅正诗风的传播,这种传播在文士的游历过程中得以构建。元代大一统格局的出现使元代文士的游历成为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潮流。“视前代分裂隔乱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岂不快哉!”[11]元代的科举考试促使南方文士大量北上大都,他们客观上虽为了求仕,博取功名,取得人生出路,但最明显的效果,一是扩大了视野,“观乎四方”,“观乎会通”[11];二是使平易雅正的诗风通过门生、座主、同年的社会关系网络传播。这其中,书序与雅集是最具效力的传播方式。通过书序,往往可以直接宣传作序者的诗文理念。而科举制又促进了南北文人的交流融合,推动了文人士大夫间雅集聚会的盛行,参与雅集者同韵唱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元代诗风的趋同,也在这过程中实现。
元代文人游历非常普遍。宋末元初,南北方文士到大都求仕是常见方式,到了元仁宗延祐恢复科举之后,游历更为普遍,以诗文游历干谒成为一种风尚,还有一些游历天下与文人相交的文人,他们都推动了混一文风的传播。如袁桷说:“(干谒人士人)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率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迄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19]从袁桷记载来看,元代科考录取非常困难[33],尽管朝廷没有拔擢一人,但游历之风依然兴盛。程钜夫身为南人,但一生仕宦通达,官至一品,举荐人才颇多,曾代表朝廷写有《科举诏》,表明了他的科举立场。程氏早在至元年间便到江南罗致人才,他罗致的都是声名赫赫之辈,后世评价颇高。但如果读他的《送王谦道远游序》可知元代很多籍籍无名之士,在大都求仕不得,困顿终生,不得不远游,“行无可聚之粮,居无可托之友”[34],这些游历之士大多生活困难,最后都是无奈南归。元代这些文士的赠序,从程钜夫到袁桷、虞集,一直到元末的欧阳玄、危素,都表达了对来大都游历文士的深切同情。可以说正是这些游士才促进了赠序的发达,往来酬赠,是元代诗歌的主要生产方式之一。而他们的游历干谒也将大都文坛领袖倡导的盛世文风的理念传衍至南北。
同时,北方文士的游历风气也很兴盛,其中有些人科举入仕之后,到各地任职,视野扩大,诗歌水平大进。延祐二年许有壬中进士,他的同年张雄飞是西北唐兀人,许氏为张所作《张雄飞诗集序》:“唐元氏张君雄飞,首科右榜有闻者也。不以一得为足,益砺其学,尤工于诗,往往脍炙人口,佳章奇句,不可悉举。拜御史西台,按巴蜀,越隽,足迹殆尽西南,履少陵之躅,默有契焉。移南台,行岭海,穷极幽险。佥浙东宪,过钱塘,登会稽,探禹穴、天台、雁荡之胜,举在心目,得江山之助,故其诗益昌而多也。”[32]张雄飞和许有壬同属一个阶层,爱好志趣相同,从许有壬的评价中可以知道,张雄飞的宦游生涯使他的诗歌境界扩大,得江山之助为多。
在游历的过程中,以诗文结交文坛名宿,为他人诗集作序是诗文理论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主动传播方式。请人作序,往往要请当时文坛名宿、声名显扬之辈,元代文坛名家如袁桷、虞集、邓文源、欧阳玄、黄溍等常常替人作序。他们的知名度使求序者的诗文集能够拥有足够多的读者,同时,这些主持科举的文坛领袖的诗文理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与传播。元代汪泽民是著名的忠义之士,他在延祐五年登进士第,向考官袁桷求序,袁桷写《赠宣城汪泽民登第归里序》说“必能以复古”[19],期许很高。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是文风革新的推动者,故而他们的诗文理论能够借助序言这种形式在士子中迅速而广泛传播,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书序文字的创作。借助赠序可以迅速让文坛领袖的理念得到传播,而求序者也获得了承认,自然对元代的诗文雅正风气更加认同。虞集为谢坚白写序言:“近世学诗者,好言长吉。言长吉者,造语多不可解。又言山谷,言山谷者,即必故为不谐。又言简斋,言简斋者,意浅气短。又言诚斋者,率易鹵莽,文类俳优。好言道理者,最近似之矣。”[35]虞集批评宋末元初南方诗坛的风气,其中模仿李贺、黄庭坚、陈与义、杨万里等人的诗风,主要是因为学养不够,所以所学浅薄,诗风萎靡,境界狭窄。他批评北方诗坛诗学风气时说:“中原之人,又宗遗山而祖东坡,浩浩一律,亦未知溯其原者。”[35]说明金末元初北方文坛流行的以苏轼为源头,以元好问为师法对象的诗风,这样北方诗风常常表现出粗豪而学养不足的一面。虞集对南北诗坛的批评表明了他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诗风。
虞集所说的雅正诗风是什么呢?虞集这种观念来源于他的“赫然鸣其治平之音”的需求[36]。其文集中最多的是对元朝盛世之音的赞颂,“天运在国朝,元气磅礴于龙朔,人物有宏大雄浑之禀,万方莫及焉。是以武功经营,无敌于天下;简策所传,有不可胜赞者矣”[35]。雅正要和国家强盛相符合,所谓盛世之音,就是赞颂元朝前所未有的功业。袁桷云:“雅也者,朝廷宗庙之所宜用。仪文日兴,弦歌金石,迭奏合响。”[19]“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庙,宾客军旅,学校稼樯,田猎宴享,更唱迭和,以鸣太平之盛,则谓之雅。”[11]虞集为我们解释了元代科举制实行之后,什么是雅正的概念。
元代科举实行以后,考官们为举子们的诗集作序是一种常见的文坛形式。吴澄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其《吴文正集》中,仅书序就有8卷,其中为诗文集作的序文有96篇之多,如果计算送行诗序,这个数量将会更多。而吴澄的诗歌仅有10卷,足见吴澄对书序的重视。再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李仲源,他有《仲源集》一卷,与赵孟 、程钜夫、吴澄、虞集、袁桷、邓文原等都有诗歌唱和。李仲源曾自录其五言诗,题曰《宗雅》,虞集作序称:“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则其人有大过人而不系于时者也。……《宗雅》可以观德于当世矣夫!”[11]可知李仲源的诗也是辞平意和,属于“盛世之音”。吴澄序其诗曰:“仲渊心易直而气劲健,其为诗也肖其人,古体五言如生在魏、晋,略不涉齐、梁以下光景。七言杂言,翩翩乎钟山丞相,雪堂学士之间而无留难。约之而为近体也亦然。”[20]由此可见,通过序言这种形式,虞集、吴澄等人的诗学观念能够在普通士子中间传播接受,进而成为主流规范,这便是新诗风的向下传播。
诗文雅集酬唱是最常见的文人活动,而文风可由这种文人活动在与会者之间传播接受。在元代,科举考试犹如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将五湖四海的文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座主、门生、同年聚会等方式交流情感,当然也免不了诗歌才艺的切磋。这使得不同参与者的诗文风格得到碰撞、融合,最终走向趋同。南北诗风的混一,雅集聚会中的诗歌唱和是其实现方式之一。
元代由科举产生的进士,一般都在翰林国史院任职。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生活清闲,这在翰林文士的许多诗歌中多有描写,王恽曾在《题雪堂雅集图》中说“扰扰黄尘若个闲”[3],虞集在《玉堂燕集图》中说“朝廷多暇日,别馆又青春”[11]。他们只能投身于诗文雅集聚会等传统文人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他们消遣时光的最好选择。翰林国史院文士在这些雅集聚会中所创作的诗歌,表现出了浑厚的文人雅致情怀:“官清无事足优游,下马长楸作胜游。济济衣冠唐盛世,诸贤不减晋风流。”[20]翰林的悠闲生活,使他们普遍寄情山水,追慕晋人名士风流。而雅集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使得他们的诗歌普遍表现出不怨不丽、平易雅正的风貌。
元代文坛的这种风气也波及了文学修养较高的僧道群体,特别是黄冠释子爱好文艺者很多,他们也与当时诸名士如虞、杨、范、揭、赵孟 、袁桷、黄溍等游历往还,和平雅正的盛世文风也传入到了黄冠释子中去。黄冠道士,在元代以张雨最为知名。张雨诗书画皆佳,年二十时便抽簪入道,好游历南北,喜与文人、士大夫交游。张雨曾将他与当时文坛名流交往的诗歌汇为一编,名为《师友集》,黄溍在序其集言:“当文明之代一时,鸿生硕望文学侍从之臣,方相与镕金铸辞,著为训典,播为颂歌,以铺张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间,又皆与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埙鸣而篪应也。”[28]张雨相交的“文学侍从之臣”,都是平易雅正诗风的倡导者,他们创作盛世之音,使其深受影响。明初藏书家徐达左在为张雨诗集所作序中说:“当元盛时,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钱塘来句曲,负逸才英气,以诗著名,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也。”[9]他的诗“格调清丽,句语新奇”,清丽与平易雅正的诗风并不违背,虞集、赵孟诸人诗歌也有清丽的特点。这说明张雨作为道士,在与当时文坛巨擘交往时,诗风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玄教宗师吴全节也是元代十分著名的道士,他与张雨类似,多才艺,且乐与朝中文学侍从之臣来往,诗歌也具有“盛世文风”的特点。这从当时与其交往的好友对其诗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吴澄序其诗集云:“其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盖其少也,尝从硕师,博综群籍,蚤已窥闯唐宋二三大诗人之门户。况又遭逢圣时,涵咏变化,其气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垒之民大穰,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声诗特余事耳。”[20]李存《和吴宗师滦京寄诗序》云:“咸以为是作也,和而庄,丰而安,婉而不曲,陈而不肆,其正始之遗音乎。”[37]佛教中也多有如张雨、吴全节辈者,譬如著名的“诗坛三隐”便是其中代表,他们的诗风,也受到盛世文风的濡染。许有壬总结科举实行之后的文坛风气说:“我元诗气,近岁号盛,是体大行,每见于赠别。”[32]这是同僚苏天爵由大都南下任职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大夫士又分题赋诗以饯”[32]后,许有壬应苏天爵之请而写,许有壬总结出了元代这种风气之盛,这也是实行科举之后带来的最明显的结果。
五、结语
元初科举制的取消使士人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感。虽然说宋末元初很多文人评论科举制取消使士人得以致力于诗,但这多是无奈之举。元人敏锐地认识到这不是科举的制度问题,而是科举的内容与标准的问题,所以有关元人科举制的争论实际上了反映了以何种方式为国家选才的问题。从宋末元初的文人为科举制的取消而欢呼,到最后为何时恢复科举制的焦灼等待这一变化,我们看到,科举制毕竟是保证士人通过读书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也说明了为何元仁宗恢复科举制时,士人参与的踊跃程度超乎想象,对元朝的认同也空前高涨。文人不惮于在诗文中表达对元朝的认同,这种急切颂圣之情,在科举制恢复时达到了高潮。可以说,科举制使文人的诗文混同风气得到了快速传播,因科考而产生的士人流动也造成了士人之间题赠文学的发达。
元诗的发展脉络与元代科举制由废到兴的发展过程,在阶段上具有一致性。元仁宗延祐(1314—1320)时,诗文风气丕变,以“宗唐复古”为尚,倡导平易雅正、舂容和雅,这种风气是元初南北各承宋金之弊文风混一趋同的结果。正如欧阳玄所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12]在南北文风混一的同时,科举制也由久废而重兴,重新激励了元代学者压抑百年的经世理想。
科举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种权力暗含了一种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命题,士子们如果想入仕,必须按照国家权力意志来进行。因而,他们和考官的兴趣一致也是一种必然,所以科举制无疑是元代盛世文风流行的外在推动力量。早在元成宗大德(1297—1307)年间,平易雅正、颂赞盛世的诗文风气已经出现,而科举制的实行,在延祐年间又将这种诗文风气扩大化。“延祐设科取士,而得人之盛”[38],科场中的考官、举子都是这种诗风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元代延祐时期以复古为尚、以平易雅正为旨归的诗文风气,之所以在文坛被普遍接受,成为后世认同的盛世文风,科举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虞集、袁桷、吴澄等学者在大德年间提出融合南北的诗文理念之后,科举制则适时地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和途径。作为文学清望之士,他们的诗文理念很快借助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同年结成关系网,从而在整个文坛迅速流衍。在具体的传播方式上,书序、雅集、游历等多种文人活动方式,保证了诗风以多样性的方式在文人中间传播和接受,使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风靡天下,元代文坛的典型风尚由此定型。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M].索介然,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3]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J].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6):26—59.
[5]赵文.青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胡祇遹.紫山先生大全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陈高华,孟繁清.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张之翰.西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清光绪万卷楼藏本.
[10]袁易.静春堂诗集[M].知不足斋丛书本.
[11]虞集.道园学古录[M].四部丛刊影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12]欧阳玄.圭斋文集[M].四部丛刊影明成化本.
[13]黄庚.月屋漫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戴表元.剡源集[M].四部丛刊影明本.
[15]史伟.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6]李修生.全元文[M].凤凰出版社,2004.
[17]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18]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J],殷都学刊,2000,(3):61—71.
[19]杨亮.袁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吴澄.吴文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查洪德.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两相浸润[J],文学评论,2002,(5):35—39.
[22]张翥.蜕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赵汸.东山存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苏天爵.元文类[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揭傒斯.文安集[M].四部丛刊影旧钞本.
[26]萧启庆.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J].中华文史论丛,2010,(1):35—58.
[27]陈高华,孟繁清.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8]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29]李超.元代科举文献考官批语辑录及其价值[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3):138—144.
[30]陆元龙辑.历代赋汇[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黄仁生.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J].文献,2003,(1):95—105.
[32]傅英,等.许有壬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3]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34]张文澍.程钜夫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35]虞集.道园类稿[M].台北:台湾新文丰文化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36]傅与砺.傅与砺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李存.俟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王祎.王文忠公文集[M].嘉靖元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