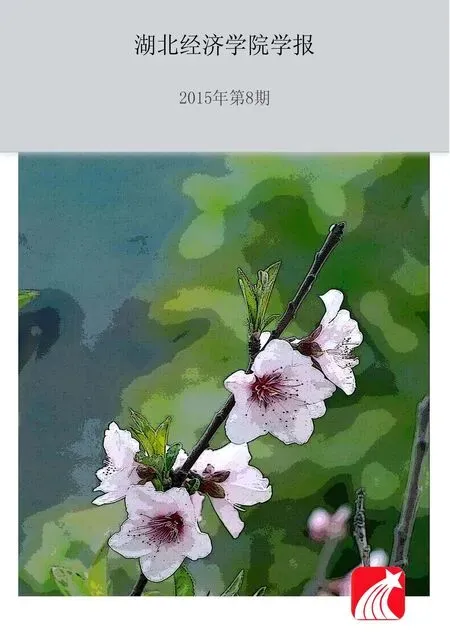种族主义消除的理想期待:解读《宠儿》作家的写作动机
一、前言
托妮·莫里森本人就是一位有着强烈种族意识的作家。黑人女性的特殊身份使莫里森对非裔美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了较多的体验和认识,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倾注了作家本人对黑人同胞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对于以白人文化占主流的非裔美国人民的生存和前途更令她忧虑。黑人种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始终是莫里森作品的主题。
《宠儿》是托妮·莫里森经历了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才问世的长篇小说代表,该作品讲述了美国蓄奴制的规训和惩罚逼迫黑奴塞丝弑婴罪行导致她精神分裂、人性扭曲、自我身份的丧失和文化之根的追寻。该小说于1993年使莫里森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至此,全世界学者对它的研究热情持久不衰。作家并没有用犀利的语言赤裸裸地攻击惨无人道的美国奴隶制,而是运用高超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富有诗意的语言讲述黑奴多舛的命运,凸显了美国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细读文本,不难看出该小说通过几位特殊身份的白人与黑奴之间的故事更加深层地体现了作家宽宏的人文情怀,表达了作家珍爱生命、消除种族主义和共建人类和平的愿望。
二、白人种族主义者眼中的黑人形象
“种族主义通常指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与迫害。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种族主义(Racism)是一种认为一个种族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某一种特定的品质或者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群及种族间优劣的信仰或者观念。在法律上,联合国并没有定义“种族主义”。根据英国法律,种族(Racial group)指“根据人种(Race)、肤色、国籍和族群或民族分类的某一类人”。 [1]种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年代。当时非洲的资源被大量掳掠到欧美各国,包括人力资源,无数黑人被当作奴隶在市场上公开售卖。
在美国,“美国人”就是特指白人。美国文学一方面热衷于表现白色特征,另一方面又制造被束缚受压迫的黑人形象。从一开始美国文学就受到种族主义的污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化的全过程就是把黑人变为奴隶的过程。长期以来,黑人在美国文学界不是被肆意歪曲或误读,就是保持沉默或逃避。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正是借助文学作品的形式向世人讲述美国奴隶制时期无数黑人尤其是黑奴难以言说的历史故事。
《宠儿》就是作为美国白色人种的臣属民族之一的非裔民族遭受白人奴隶主蹂躏和管制的真实写照。黑奴们在白人监视下压抑地生活,经历非常坎坷。在白人的价值观念中,黑人是劣等人种。新奴隶主“学校老师”认为农庄五个黑奴“就是人种中的渣滓。是没有牙的看门狗;是没有角的公牛;是阉割的辕马,嘶叫声不能翻译成一种重任在肩的人使用的语言。” [2]在文学想象力的作用下,黑人妇女的外貌从最初就人为地被丑陋化、男性化、工具化,女黑奴被描写成性力超强、缺乏道德、人格卑贱的女人或被塑造成粗壮如牛似男非女的老佣。从本质上来讲,蓄奴制是一场违背上帝愿望和人类良知的罪恶,美国的种族歧视恰恰是它的恶果。 [3]
三、蓄奴制背景下黑白种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北美白人契约奴的历史和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同样长远。17世纪时,契约奴成为北美殖民地最常见的奴隶,他们约占全部移民人口的一半。在蓄奴制时期,无论是无力偿还负债只好和债主签约的白人契约佣工,还是混有少量黑人血统的白皮肤美国人,他们都像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美国”的黑人一样遭受过美国奴隶主的歧视和奴隶制的戕害。白奴人数有限,反抗也激烈,致使美国又大力贩卖“黑奴”以满足劳动力的要求。众多黑奴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不乏善良的白人的救助。
(一)白人契约女佣与黑人逃亡奴隶塞丝
在美国文学尤其是南方文学中黑人妇女总是被妖魔化—他们肥胖的身躯、超强的生育力总是用来象征野性和低贱,被剥夺了最起码的尊严和自我。 [3]在“甜蜜之家”庄园,塞丝是唯一一个成年女性黑奴。第一任奴隶主白人加纳用温婉的管理手段奴役着他的黑奴。年轻的女黑奴塞丝“做得一手好墨水,熬得一手好烫,按他喜欢的方式给他熨衣领,而且还剩十年能繁殖。” [2]黑奴黑尔和塞丝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俩的“洞房之夜”是在其他黑奴兄弟能看得到的玉米地过的;黑尔为赎回母亲贝比·萨格斯的自由却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塞丝也并非是专属于黑尔的妻子,常常受到白人的侵犯。
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为种族主义提供“科学”依据的思潮。“甜蜜之家”的新任奴隶主“学校老师”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冷酷的行为将黑奴的人性扭曲和摧残。表面文质彬彬的“学校老师”却在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在塞丝的身上进行测量,甚至塞丝遭到侄子学生吸奶侮辱时,“老师”还在一边做记录,收集相关的数据研究奴隶的动物属性。这些都给塞丝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丈夫黑尔不经意间亲眼目睹妻子受辱却不能挺身相救最终疯掉。塞丝的告状无济于事反遭鞭笞毒打,在肉体和精神双重被虐待的情况下毅然出逃。
塞丝身负重伤、身怀六甲,在投奔婆婆贝比·萨格斯的途中,遇到了散发跣足的白人契约女佣爱弥·丹芙。她的主人和亲生父亲巴迪先生也让爱弥受过鞭打之苦,可是她从来没见过塞丝后背像开满小白花的“樱桃树”一样的伤疤。“这个姑娘说起话来像下暴雨,可是她嘴周围没有残忍。她把太太带到那间披屋,还帮他揉脚。” [2]“可别给我死在夜里,听见没有?我可不想看见你这张又丑又黑的脸勾我的魂儿。” [2]爱弥说话直率甚至有点尖刻,语气中充斥着明显的“种族优越论”的观点,但是她心地善良,且积极精心地照料塞丝。如果爱弥交出一个逃跑的黑奴,她就可以领到一笔赏金。事实上爱弥用实际行动足以让塞丝信服她并坚定信念活下去:为了赶到婆婆那里,她什么苦都吃过。作为一名契约女佣,黑奴的遭遇她感同身受:她同情塞丝被主人欺压,也能想象塞丝追求自由和天鹅绒般幸福生活的向往,所以她不顾自己的身份处境带来潜在的危险而竭尽全力地拯救塞丝母子。为了报答爱弥·丹芙,塞丝给新出生的孩子取名叫丹芙并讲述她死里逃生的故事,以示让孩子永远记住救命恩人,另一方面肯定丹芙的功劳,并告戒孩子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是冷酷邪恶的。
(二)混血人种教师与黑奴孩子丹芙
种族主义者白人不仅暴戾、残忍、血腥,而且对驯服、历来顺受的奴隶还不信任,充满恐惧。在大多数白人眼里,黑人充满了动物性和野蛮性,是种族分子时刻提防的对象。黑奴被剥夺了话语权、身体权和受教育权,丧失了自由、尊严和自我,摧毁了肉体和灵魂,成为沉默的迷失的羔羊。
加纳是奴隶制时代打着文明的旗号实则对黑奴进行残酷剥削和压制的白人奴隶主。新奴隶主“学校老师”也看到了年轻的塞丝将会给他们创造有用的价值,发现塞丝逃跑后就赶紧猎捕她。“那些白鬼夺走了我拥有和梦想的一切,”“还扯断了我的心弦。这个世界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 [2]塞丝早已受够白人的蹂躏而对白种人痛恨至极。塞丝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宠儿长大后再受到白人的凌辱而生下自己厌恶的混血后代。贝比·萨格斯跟六个不同的男人生了八个孩子,有的孩子她不能爱,有的孩子她根本不去爱。不能爱的不是被卖掉就是被带走,根本不爱的是她和白人生下的孩子在海上奴隶贸易船上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抛入大海,唯一留在身边的是给了她那时一文不值的自由的孩子黑尔。
“肤色论是种族主义者让奴役永远成为经济剥削的一种政治手段。” [3]只要是活着的黑人,无论老少都是奴隶主手中待估的有价动产。按照美国的《黑人法典》,黑人母亲是奴隶,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奴隶身份。丹芙有幸在白人爱弥的帮助下顺利地诞生,但是因为鬼魂宠儿的出现,母亲塞丝精神分裂导致丹芙从孤独封闭到走出家门寻求帮助,尤其是受到混血家庭教师琼斯女士的教诲。美国的法律规定,黑人是没有受教育权的。但是琼斯在家里给如饥似渴了解世界的黑人孩子们提供了上学的机会。“每月收费五分钱,琼斯做了让白人们认为即便合法也毫无必要的事情:让她的小客厅里挤满那些有时间也有兴趣读书的黑孩子。” [2]丹芙跟那些同肤色的孩子一起学习拼写、算术和读《圣经》。渐渐地,丹芙开始成长,母亲也在社区同胞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心魔而觉醒。
四、结论
塞丝逃亡弑婴事件不仅震撼了白人奴隶主,而且博得了部分白人的怜悯和帮助。苏格兰鲍德温兄妹是开明的白人废奴主义者,“为黑奴斯坦普·沛德、艾拉和约翰提供了逃犯们用的衣服、物品和工具,因为他们比恨奴隶更恨奴隶制。” [2]《宠儿》的行文中提到不少白人比如还算温和的加纳夫妇、为贝比奶奶灵魂祈祷的牧师等人让黑奴深信:奴隶制殃及的不光是黑人还有白人自己的同胞;那些遭受欺压的白人与黑奴同病相怜,他们同样希望早日解除奴隶制,得到上帝的宠爱。“没有人能单靠自己成功。”“你可能永远会迷失,如果没有人给你带路的话。” [2]塞丝的觉醒和丹芙的成长离不开那些善良白人的帮助,但是黑人要想有尊严地生存下来还得团结本族的力量并延续祖先的文化以及联合其他民族共建和谐的社会才会有幸福的生活。由于历史的局限,黑人的反抗没有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但是莫里森在《宠儿》中鲜明地反映出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强烈愿望,作家试图通过文学的传播让更多的人关注黑人种族的发展和未来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