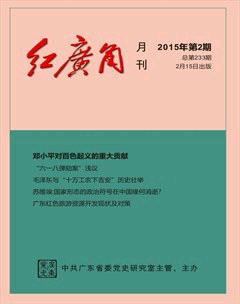苏维埃:国家形态的政治符号在中国缘何消逝?
李晨升
【摘 要】“苏维埃”符号在中国建构过程中受苏联影响严重,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与政权对抗,战争环境下拘泥于国家形态,局限了斗争基础和斗争策略,导致“苏维埃”符号因中共中央及红军撤离苏区而受到削弱;来自共产国际“统战”政策的调整,再加上中国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中共最终放弃了作为国家形态的“苏维埃”政治符号。“苏维埃”符号的运用体现着中共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思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关键词】苏维埃;政治符号;国家形态
“苏维埃”作为一个外来词,在中国近代史中,并不仅仅代表一场运动、一种道路和制度的选择,它对于1931-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同时还是一个国家形态的政治符号。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苏维埃”符号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将着重探讨作为国家形态政治符号“苏维埃”的消逝,以期相关研究的增益。
一、建构与传播过程中的隐患
较早直接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派。大革命失败前,托派多次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要求“立即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但遭到斯大林等人的反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要求立即以“苏维埃”的政权形式与国民政府决裂,无疑是不适宜的。宁汉合流后,中国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斯大林在1927年8月8日给罗明纳兹等人去电:“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
维埃。”①
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共的指示中,也基本持类似意见。1927年5月,虽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共产国际仍然右倾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反对建构“苏维埃”符号,认为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等于“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意味着要在中国“建立双重政权”,在当前形势下是“欠妥当的”。此时共产国际仍然基于其对国民党的左右派别的成分划分,寄希望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认为他们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②随着国内形势的急遽变化,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建构“苏维埃”政权符号的态度和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1928年2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认为,虽然“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存在走向革命新高潮的各种征兆,因此,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组织苏维埃”,推翻现存政
权。①1929年来自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中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中共“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②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到“一苏大”,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督促下完成的。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共的信中为中共列出了“三位一体的任务”,其中明确要求中共“建立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制度”,并催促中共“赶快把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的建立在最安全的区域”。③甚至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已经为其急于在中国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起草了《土地法令草案》等文。
可见,“苏维埃”作为国家形态政权符号的建构中“苏化”十分严重,就连“苏维埃”一词都是从俄语中直译过来的。“苏维埃”符号不仅在“符号化”的过程中被赋予较为强烈的苏联色彩,而且在“符号解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误会。中共中央在1932年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信中就提到,“工会与苏维埃对立的现象”是突出存在的,群众的观念中片面地认为“工会是工人的,苏维埃是农民的”,并且要求工会来监督苏维埃。④这种对“苏维埃”符号的误读,与中共的宣传工作不无关系。张闻天1932年底曾反思道:“‘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统治中国这类简单的道理”都需要“许多事实的证明与细心的解释”,然而“我们党八股的宣传鼓动工作却完全不注意这些事”,自然无法向群众完整地解读“苏维埃”符号。⑤杨尚昆也指出,“‘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虽然在苏区各地墙壁上写了许多,但是,一直到现在,有许多群众还不晓得‘什么是苏联。是一间店子,一个人名,或者是苏维埃区域的大联合呢?”⑥。
共产国际主导下建构的“苏维埃”符号直接移植自苏俄革命,对于年轻的中共来说具有权威色彩,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这无可厚非,但过度的“苏化”使得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政权形态的中国特色,道路、制度的“非本土化”也增加了民众对“苏维埃”的认同困难,以致出现了如“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别号”等猜测,为“苏维埃”符号的消逝埋下伏笔。
二、抽象政治概念的局限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一部分持革命的失败情绪,一部分则坚信革命必将迅速“重新高涨”。从各省的武装暴动中,中共中央似乎看到,“革命的潮流普遍的高涨”,实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国家形态的“苏维埃”似乎势在必行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使立三中央的头脑更加发热,决心“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⑦在这种革命高潮论调下,立三中央忽视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与政权对立,对形势做出了“过分的不正确的估量”。⑧1930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全国政治总的形势:一方面是反动统治日益动摇削弱而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是群众斗争日益逼近新的革命高潮”,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全体大会,“以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用苏维埃的政权“与国民党反动的政权对抗”。①在1931年8月30日给苏区中央局及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中共中央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但仍然坚持要“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显示出两个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要求一致抗日的舆论声中,国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对抗仍不降温,国民党继续把“围剿”作为“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中共也针锋相对地坚持“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②1931年11月起,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新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基本目标,这一方面诱发了军事上寻求决战的激进心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剿”,不可避免会导致两个政权之间更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3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训令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激进的倾向:“红军的有利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③这一点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得到了更为直接的体现。1932年11月,面对国民党的第四次重兵“进剿”,中共中央批评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为“纯粹防御路线”,认为“积极运动的路线,是最有利的防御方法”。激进的心理导致对形势发展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过“左”的估计,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已经受到削弱,“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现在主要的危险,其结果则会导致苏区“土地之丧失”。④1934年中共更是直接以“不让敌人占领我们的一寸苏区”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口号,上升到“死亡或者胜利”的高度,⑤动员苏区民众“坚决地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每寸领土”而斗争。⑥可见,中共把两个“政权之尖锐对立”,作为“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⑦已经不能单纯从军事的角度看待反“围剿”,而不得不考虑“一城一地之丧失”,这也把红军束缚在苏维埃的“国土”上,无法打到外线去,失去了很多主动权。在此时的中共看来,“苏维埃”符号已然上升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政权象征,苏区则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可侵犯的领土,之前灵活的军事方针似乎与这种“国家形态”的思维方式相矛盾,人们不免把军事上的进退与政治上的主权得失联系在一起,局限于“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endprint
念”,⑧使“苏维埃”符号的政治认同感随着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而受到削弱。
三、统一战线政策的变动
早在1933年,中共就不断倡导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立即武装民众”⑨等特定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但由于受共产国际和党内“关门主义”倾向的影响,再加上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中共一度过分强调对下层群众的动员和争取,忽视了统一战线的民族性。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逐渐发生变化,允许开展一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逐渐突破了以抗日军队为主要联合对象的局限,主张“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⑩
1935年沙窝会议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在少数民族中的政策时,考虑到“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以及少数民族“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主张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①这是中共较早独立自主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思想灵活地处理民族关系。随着1935年11月下旬林育英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刚与失联许久的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就面临着统战政策的重大调整。随后,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既贯彻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又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其中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表明“苏维埃”符号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人民”一词的增加,是对作为国家形态“苏维埃”政权符号的突破。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②瓦窑堡会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6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共产国际除支持中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特别建议中共“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以此联合中国“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③1936年9月1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又改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中共显然已经注意到“苏维埃”符号下阶级斗争的局限性,逐渐从中华民族存亡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也意味着“苏维埃”符号不再仅仅等同于工农民主专政,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扩大了政权的群众基础,更“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但内涵与外延的扩大也加速了“苏维埃”符号的更替。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作为国家形态的“苏维埃”符号正式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余论
“苏维埃”作为国家形态的政治符号,标志着中共的初次执政尝试,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探索。然而,符号的消逝并不意味着断裂,而是继承与更替。在“苏维埃”的符号体系中,既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符号,也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符号,这些仍带有苏联色彩的政治符号随着“苏维埃”符号的消逝,从名称到内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也是符号的时代性使然。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实行苏维埃:“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④从“苏维埃”到“人民代表会议”的更替,不仅意味着中共摆脱了苏联式的话语符号,也是中共话语范式的转型。中共在“苏维埃”符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等属于自己的政治符号,体现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积极探索。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