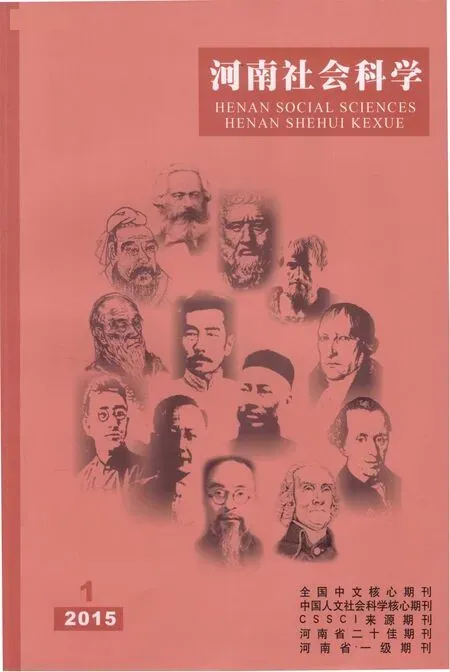“令”体考辨
李飞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词之“令”体,又称小令、歌令、令曲、令章、令词等。“令”的常见解释有四种:其一,“令”的原义是命令或法令,故冒广生《疚斋词论》云:“酒曰酒令,词曰词令也。”[1]一般认为,令“盖出于唐人宴席所行之酒令而得名”[2]。其二,“令”又称“曲”,施蛰存先生《词学名词释义》云:“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字代曲字。”“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3]马兴荣先生《中国词学大词典》云:“一般称字句不多的小调短曲为令词,又称小令、令曲。”[4]其三,以“令”指舞,朱熹《经世大训》云:“唐人俗舞,谓之打令。”敦煌舞谱中有令舞,“是一种动作化的酒令,有比较确定的舞蹈程式”[5]。其四,以“令”为词牌通称,王力《汉语诗律学》云:“‘令’是词牌的通称。因此,许多词牌都可以随便加上一个‘令’字。”[6]以上关于“令”体的解释,分别从词调来源、体式特征、表演方式等方面揭示了令体字句不多、曲短调小、节奏明快、与酒令关系密切等特点。在各种定义中,以“令”为短曲小调或急曲子,以“令曲”同于歌令,以“小令”属小唱,以“小品”为令体,影响较为广泛,却有诸多似是而非之处,须作进一步辨析。
一、“令”与短曲小调
通常认为,无论是从乐曲还是文本篇幅上而言,“短小”都是“令”的核心定义或突出特征,如“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令”[3],“令”一般都指短调之辞,“小令,又叫‘令曲’。词的短小者之称。唐宋文人于酒宴上即席填词,利用短篇小调,当做酒令,遂称小令”(林焕文《词学词典》)。唐五代时期的令词一般篇幅短小,节奏急促,以短曲小调之辞来界定“令”体,似有道理,其实不尽然。
第一,“令”的篇幅、字数并不一定较“引、近、慢”短小。不是所有令词都是短曲小调,如柳永《甘州令》有七十八字,《采莲令》有九十一字,欧阳修《梁州令》有一百零五字,就字数篇幅而言,在词体中皆可归之于长调。《高丽史·乐志》中《献天寿令》的字数反而多于《献天寿慢》。字数篇幅并不能将词调完整划分开,故万树《词律》云:“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调乎?”
第二,唐宋时期词曲的篇章单位不同。唐五代词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联章,同调的多首词连串一起演绎一个主题。《云谣集杂曲子》《花间集》《尊前集》等唐五代词集在作者系词之下,多是按词调排列,同调作品不少是联章。据任半塘《敦煌曲初探》统计,仅唐五代词中就有一千多首联章词。这只是根据后世有据可依的文献统计,此外又有多少只曲单调曾是联章,已难以计算。
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云:“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3]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统计,令体在唐五代时期的创作,以“子”命名的词调就有三十三调。“子”即“曲子”之意,是一首曲的次级单位。多首“曲子”共同构成了一首曲,一首曲也可包含多首“曲子”,就像后来的一首慢词分为两阕、三阕一样。虽然每阕的乐曲、歌法、格律相近或相同,但一阕不足以称之为一调。同样,联章词亦应以整体视之,即将令词还原其本来面貌,而非碎拆成一首首独立的小词。有些令词根据编辑需要而被后人打散重新编排,在当时并非以一调一阕一片来计算,而是以组曲、套曲或大曲形式存在,因而不能视之为短曲小调。
第三,叠唱是唐五代令词的通行唱法。张炎《词源·讴曲旨要》云:“慢近曲子顿不叠,歌飒连珠叠顿声。”[7]叠和顿是唱曲的通用歌法,“慢、近”等曲子通常只顿不叠,而小词令曲通常可以叠唱,如《阳关曲》又名《阳关三叠》,其中一句叠唱三次。一首字数较少的词,通过叠唱就可以对应较长曲调。以此而言,不能说令词对应的曲调就是短曲小调。
第四,令体曲度不一定短于慢体。据王灼《碧鸡漫志》载:“近世有《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又有大石调《兰陵王慢》,殊非旧曲。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一则为令,一则为慢,都是十六拍,“从而又可证‘令’之曲度未必比‘慢’为短。一般人囿于小令、中调、长调之说,多以令为短曲小调,以慢为长调,观此可知,非但令之字数未必比慢少,并令之曲度亦未必比慢为短也”[8]。
将短曲小调等同于令,始于宋人编集而确立于明人的词调分类。故朱彝尊《词综·发凡》云:“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为牵率。”
二、“令”与“急曲子”
针对以篇幅长短来界定“令”体之说,龙榆生《词曲概论》曾反驳道:“一般讲词的人都‘以长调为慢,短调为令’,却是错的。就音乐上讲,曲调只有急、慢之分,所以《唐书》和《宋史》的《乐志》中,都常说‘急、慢诸曲’,把急曲子和慢曲子对举,并不以歌词的篇幅长短来决定。这长期的误解,是由于后世填词家不懂音乐,也不肯用心去研究所造成的。”[9]因而主张不以短、长而以“急、慢”来界定“令、慢”。张高宽《宋词大辞典》亦云:“多数令词字少调短、节奏较快。”[2]那么,是否“慢”就对应慢曲子,“令”就对应急曲子呢?事实上并非如此。
第一,唐五代“令”词配合的乐曲不都是“急曲子”。如唐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琵琶抄谱一卷,写在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即《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变文》)的背面,计录《品弄》《倾杯乐》《西江月》《心事子》《伊州》《水鼓子》《急胡相问》《长沙女引》《撒金砂》《营富》等急、慢曲子二十五首,其中被后人划为令曲者多数是慢曲子而非急曲子。标明“急曲子”仅有四调,分别是《急曲子》(第六首)、《急曲子》(第九首)、《又急曲子》(第十七首)、《急胡相问》(第十九首)。标明“慢曲子”者,除了四首《又慢曲子》(第四、八、十、十四首),还有《又慢曲子西江月》(第十三首)、《慢曲子心事子》《又慢曲子伊州》等。《倾杯乐》(第三、十二首)和《伊州》(第二十四首)则是“急曲子”“慢曲子”交互使用。可见,敦煌乐谱中令曲配合慢曲子的情况反而比急曲子还要多。此外,敦煌乐谱中的“急曲子”多为器乐小品,很少配词歌唱。
第二,令曲在曲拍节奏上不都是急曲子。杨荫浏认为,令“其狭义可能是专指曲破部分所用的节奏比较快的曲调而言;其广义则是泛指一切较短的曲调而言”。今存以“令”字题名之曲,有长有短,有快有慢,但短而较快的曲调占大多数[10]。大部分令曲短而较快,符合急曲子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着长而较慢的曲调。这主要是界定急、慢曲子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敦煌曲谱中的“急”“慢”是节奏概念,主要从速度、节奏和节拍等方面进行区分,而非用韵多少。因此,“慢曲子”不都比“急曲子”长,“急曲子”也不一定比“慢曲子”短。与唐五代以乐曲节拍来界定曲子的急慢不同,宋人则以用韵多少来界定曲子的急慢。清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五云:“声之悠扬相应处,即用韵之处也。故宋人用韵少之词,谓之急曲子;韵多者,谓之慢曲子,义盖如此。”一般情况下,韵少则词促,韵多则词缓。但是对于拗调而言,韵多之词可用于急曲子,韵少之词也可用于慢曲子。
第三,词调的长短与曲子的急慢,可通过改变唱法来调整。张炎《词源》云:“慢近曲子顿不叠,歌飒连珠叠顿声。”[7]任半塘先生解释说:“引、近音谱中亦有顿声,顿而不叠,与慢曲同。”“又所顿与住者,乃一句之中,唱至某字而顿住,但延长其音,一时不连接吐出下字也;字虽顿住,而音实延长。”[11]采用了顿的唱法,配合的乐曲自然曲度延长,进展缓慢。
事实上,慢、引、近等曲子并非只顿不叠。“慢曲子”也有叠唱。宋人毛幵《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依之节歌者,其谱传自赵忠简家。”[12]张炎《词源》亦云:“慢曲有大头曲、叠头曲。”[7]同样,令词演唱不仅有叠唱,还有顿唱,不仅有四均拍,还有六均、八均之拍。叠唱为曼声,便于应对慢曲子,故沈雄《古今词话》云:“两句一样为叠句,一促拍,一曼声。《潇湘神》、《法驾导引》,一气流注者,促拍也。《东坡引》,‘雄心消一半,雄心消一半’,不为申明上意,而两意全该者,曼声也。体如是也。”[12]
以急、慢曲子划分词调,是根据早期词的乐曲形态来划分的。随着词体的嬗变,尤其犯调、转调等手法的应用,已不能简单地用急、慢曲子来对词调进行分类。宋代慢词兴起以后,已很少出现以急、慢曲子来标注词调的情形。北宋以后,令、慢逐渐取代急、慢曲子,成了划分词体的标识。根据篇幅长短,以令、慢对应短调、长调来划分词体,是明清之时才出现的。因此,“急、慢曲子”与“令、慢”词体是两个不同概念,不具有对等性。
三、“歌曲令曲”与“歌令”之曲
张炎《词源·讴曲旨要》云:“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7]此处历来有两种断句之法。一是“歌曲、令曲四掯匀”,将歌曲与令曲并列。冒广生《疚斋词论》云:“歌曲令曲,四字对举。歌如《子夜歌》之类是也。令如《调笑令》之类是也。”“歌曲令曲,多为四句,故用四掯。”[1]赵尊岳《玉田生〈讴曲旨要〉八首解笺》云:“凡曲,长调之属为‘歌曲’,小令之属为‘令曲’。‘破’、‘近’自小令衍出,其调体视小令略多。‘慢’为长调。”[13]将歌曲、令曲作为两个并列且对立的概念来理解,并以“歌曲”指慢,“令曲”指小令、破、近等。一是“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令曲与破、近、慢并列,同属歌曲的一个种类。蔡桢《词源疏证》云:“令曲即令,歌曲令曲者,谓歌曲中一体之令曲。”[7]王易《词曲史》云:“‘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盖篇首先将诸小唱均数揭出,其下始分述各种唱法。”[14]洛地《词体构成》亦云:“‘讴曲旨要’开头几句若由我来作标点、句读,大约会是这样: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官拍、艳拍分轻重,七敲八掯靸中清。”[15]以歌曲指所有词调,包括令、破、近、慢等。
断句方法不同,对“令”的含义及其与“破”“近”“慢”等关系的理解也不同。第一种断句,以令曲指小令(包括令、近、破等),以歌曲指慢,显属牵强。宋代并无歌曲指慢,令曲指破、近之说。以“歌曲”命名的词集,如《白石道人歌曲》,不但包括慢,还包括令、引、近、序、中腔等体。郑孟津《词源解笺》考察了大量有关“歌曲”“曲”的文献记载,认为“‘歌曲’或‘曲’在两宋文献里,往往指词调而言”。第二种断法,以“令”“破”“近”“慢”归属歌曲,在诗体句式上亦有不通。既然讲“令曲四掯匀”,为什么又赘余一个“歌曲”呢?
歌曲、令曲既不是并列概念,也不是从属概念,乃是同一概念,即指“歌令”之曲。唐孙棨《北里志》载有歌伎习歌令之事:“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天水仙哥,字绛真,住于南曲中。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王团儿曾被贩卖至京师,“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在唐代,歌令是一种曲艺类型。北里歌伎之习歌令,正与宋代歌伎之习小唱、嘌唱等情形相似。五代亦有关于歌令的记载。《旧五代史·符存审传》载:“迁延之际,主将拥妓而饮,思得歌者以助欢。妓曰:‘俘囚有符存审者,妾之旧识,每令击节,以赞歌令。’”苏轼《洞仙歌》序记载眉山老尼曾述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据其首两句寻味,疑即《洞仙歌令》。《洞仙歌》全称应为《洞仙歌令》,欧阳修和康与之的《洞仙歌》都题作《洞仙歌令》。
林玫仪《令引近慢考》云:“‘歌令’乃唐人习称。唯‘歌令’究系一词或分指二事,又其意义为何,皆不无疑问。”[8]根据以上记载,歌令无论作为曲艺类型还是词调种类,都是一事。《云谣集》中《内家娇(〇二三)》词云:“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李义山《杂篡》“时人渐颠狂”条内,亦有“孝子说歌令”一项。因此,任半塘认为:“‘歌令’二字,应视作一件事,谓酒令之托于歌唱者,对其他酒令之仅托于言词者而言,并非指歌与令之两事也。(苏莫遮《一〇八》:‘善能歌,打难令’,分指二事,与此义别。)至于‘打令’之令,与‘歌令’之令,意义正同,谓酒令中所应用之小舞与小唱;仍指酒令,并非舞势。(宋人沿用此类酒令所用较短之调,乃谓之‘小令’,作为一种文体,并用以概括词中所有一切之短调。南宋耐得翁《古杭梦游录》曰:‘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讴’,犹是此意。)”[16]由此可见,“歌曲令曲”乃为“歌令之曲”,即令曲。如此理解,则“歌曲令曲四措匀,破近六均慢八均”的意思已明,前句指令曲小词之演唱,即嘌唱;后句指破、近、慢之演唱,即小唱。
四、“令”与“小唱”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据《靖康稗史》之二《瓮中人语》载,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虏尽索……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出城”。张炎《词源》卷下云:“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7]杨荫浏解释说,小唱“是从已有的大型歌舞大曲中,选取其慢曲、引、近、曲破等歌唱部分,进行清唱,唱时用板打着拍子。歌唱中充分运用强弱的变化,来加强抒情的效果。所以,在小唱中所选用的,已是艺术性相当高的一些传统形式的歌曲”[10]。王洪《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将小唱归为“表演形式”部分:“唐宋时代的一种音乐表演形式。即从已有的歌舞大曲中,选取其中慢曲、引、近、曲破等歌唱部分,进行清唱。歌唱时用拍板伴奏。”
以上关于“小唱”的记载与解释,包括“慢曲、引、近、曲破”等歌唱部分,却唯独不含“令”,看来“令”好像不属于小唱。但一些论著关于小唱的界定,则多包含“令”。王易《词曲史》云:“令,引,近,慢,在宋时名曰小唱,惟以哑簪篥合之,不必备众乐器,故当时便于通行。”“《词源》讴曲旨要首二句云:‘歌曲:令曲,四掯匀;破,近,六均;慢八均。’盖篇首先将诸小唱均数揭出,其下始分述各种唱法。”[14]张高宽《宋词大辞典》亦将小唱归属于“杂曲子”:“宋代因其演奏、歌舞方式与大曲不同,又称之为小唱。……宋词的大量词调是以杂曲小唱转化来的。引其音乐上或体段上的不同,可分为令、引、近、慢诸体。”[2]以小唱与大曲相对而言,则小唱明确包括“令”。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云:“在宋时称为小曲或小唱,以与大曲相对而言。”[17]以规模小、人数少、乐器简单的演唱为小唱。小唱与大曲相对而言,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进一步解释说,“大曲以外的单支的曲子,统称为曲子或杂曲子……又称之为小唱”,“分为令、引、近、慢诸体”。大曲与杂曲或曲子演唱之不同在于,“搬演大曲须动用大乐,先后用十多种乐器合奏。小唱则称为‘清音’、‘细乐’,只用普通丝竹小乐器,有时甚至光用手打拍清唱”[18]。王兆鹏先生认为小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演唱形式,主要演唱小令和慢曲”[19],廖奔认为小唱是“妙龄女郎清唱令曲小词、慢曲、曲破以侑觞助欢”[20],皆认为小令或令曲小词属于小唱。张鸣师云:“‘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那么,作为词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令”,如果不属于“小唱”,就称不上“最普遍的演唱形式”。“如果从形式上看,宋代词的演唱,比较常见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小唱、群唱(群讴、合唱)、歌舞演唱等几种情形”[21]。亦以“小唱”指规模较小、形式简单的演唱,与群唱、歌舞演唱等相对而言。
但是,在宋代文献记载中,“令曲”并不属于“小唱”。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云:“更有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正谓之‘浅斟低唱’。若舞四十大曲,皆为一体。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二者的区别在于,引、近、慢、破等属于小唱,而令曲通常用作“嘌唱”。如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调,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亦明确指出,嘌唱是“唱令曲小调”,不包括慢曲、引、近、破等。于天池指出吴自牧已将“小唱”与唱“令曲小词”作了区分:“从演员看,小唱的演员有男有女,而唱令曲小词,一般为年轻女性,往往与色相联系,如《梦粱录》卷二十历数唱令曲小词的演员……没有男性。”强调“主要唱慢曲的小唱与唱令曲小词的是有区别的”[22]。赵义山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宋代的令曲小词,是‘小唱’和‘嘌唱’的歌唱对象,尤其是‘嘌唱’所歌唱的主要对象,只不过小唱唱‘令曲小词’时,要求用雅调,嘌唱则多用俗腔”,“‘小唱’在当时主要唱传统雅曲,‘嘌唱’便主要唱流行俗曲,即‘令曲小词’”[23]。吴自牧《梦粱录》所说的小唱,唱的是包含小令在内的词调,“这些歌曲有的可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雅的;有的已是纯粹的新声,是当时被认为的俗曲了”[24]。
然此“小唱”已非彼“小唱”,以雅俗分别界定“小唱”与“嘌唱”,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载灌口二郎生日百姓献送之事:“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民间有“小唱”艺人活动,不可谓之不俗;皇家也蓄有“嘌唱”艺人,不可谓之不雅。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灭北宋时曾搜取宋朝宫廷和达官贵人之家的歌舞伎艺人才,其种类计有“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弹筝、琵琶、吹笙等一百五十余家”。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记载乾道三年(1167)三月初十日圣驾春游,“亦有小舟数十只,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蔬果,与湖中一般”。可见,小唱、嘌唱并不能以雅俗强分,它们都是比较通行的表演艺术。
作为演唱方式的“嘌唱”与“小唱”互不混淆,泾渭分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延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燕南芝庵《唱论》云:“凡唱曲之门户,有:小唱,寸唱,慢唱,坛唱,步虚,道情,撒炼,带烦,瓢叫。”陈多、叶长海认为,“瓢叫”疑即“嘌唱”[25]。与嘌唱相提并论者,还有“叫声”,则“瓢叫”应为“嘌唱、叫声”。据周密《癸辛杂识》载,南宋时华文阁学士高文虎侍妾银花“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可见,“小唱”与“嘌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唱类型。在宋词的表演中,有用于慢曲、引、近、破的“小唱”,也有用于令曲小调的“嘌唱”,为专门曲艺。
饶宗颐《词集考》“乐府混成集”条云:“今止存‘林钟商’一类之娋声谱、小品谱三段于《曲律》中,不满五十字。娋字,《说文·女部》云:‘小小侵也。’娋声或即《芝庵唱论》所言之小唱。”[26]此语若确,则“小唱”自应是专业唱法之名称。后世论词,对此也有区分,如冒广生“论小令”云:“后来或嫌其繁重,则仅仅嘌唱,而令之名不属于酒而属于词矣。”[1]陈匪石《声执》曾云:“(《尊前集》)名之尊前,且就词注调,殆专供嘌唱之用者。”“(《金奁集》)并因菩萨蛮原注之五首,已见《尊前集》,亦颇合符,断为宋人杂取《花间集》词,各分宫调,以供嘌唱,为尊前之续。其说是也。”[12]《尊前集》《金奁集》所载多是唐五代小令,指其演唱为“嘌唱”,是十分准确的。
要之,小唱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界定。就演唱类型而言,以清唱或轻歌舞来界定小唱,则“令”可称为小唱;就演唱规模而言,如吴熊和、王兆鹏、张鸣等以演唱规模、人数多少来界定小唱,则“令”可称为小唱;就演唱的受众而言,如赵义山、程宇昂等以雅、俗之别来界定小唱,则“令”可称为小唱;就演唱的歌舞形式而言,如陈能群《论大曲与小唱之不同》一文以歌、舞之别来界定小唱,认为“大曲歌舞相合,而小唱则歌而不舞”,则“令”或可属于小唱。这些界定都是后人根据小唱的表演特点、形式、环境及功能归纳总结出来的,一方面考察与揭示了小唱的某些艺术特点,另一方面却以“小唱”的某些特征来替代宋人曲艺中的“小唱”。但无论从演唱规模、人数、方式、雅俗、歌舞等任何一个方面来界定,都无法将宋人曲艺品种中的“嘌唱”“叫声”等与“小唱”区分开来。到了元代,令曲亦可用于小唱。根据元人夏庭芝《青楼集》所载之小唱与宋代小唱的对勘比较,赵义山认为元代小唱已不同于宋代的小唱,“元人夏庭芝所言之‘小唱’,恰同于宋人所言之‘嘌唱’,二者也是名异而实同的”[27]。
五、“小令”与“小品”
“小品”一词源自佛教经典《释氏辩空经》:“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佛经有全本和节本之分,全本为大品,节本为小品。如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等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二十七卷本和十卷本之分,前者为《大品般若经》,后者称《小品般若经》。在词体中,“小品”有以下几种含义。
其一,以小品指单乐段小词。郑孟津《宋词音乐研究》云,“宋人继唐、五代单叠体令曲之后,仍流传着单用一个乐段的作品,叫‘小令’或‘小品’”,其中“一韵合词腔一个乐段”。郑先生列举了张元干《长相思令》、康与之《长相思令》(游西湖)、莫将《独脚令》、史达道《独脚令》等四首小令,认为:“四例令词如予分片,则每片都属单乐段作品,如不予分片,则诚唐五代单片小词。又明王骥德《曲律·卷第四·杂论第三十九·下》引宋《乐府混成集》林钟商目(歇指调)后,载小品二则,观其型式,亦属单乐段小品。”[28]因将一贯视为一体的《娋声谱》小品谱拆分为《苦吟》小品谱与《灊酒》小品谱。在郑孟津看来,“小品”相当于单片令词的二分之一,或者双片令词的四分之一,后用以代指简单的诗文作品。明卓发之《卓云传》云:“公于学为汗漫游,凡方术技艺,能单体小品以上者,皆与之嫟;稗官小说、支离覆逆之术,皆所该览。”何乔远《卓光禄北游诗序》云:“征父之交,上自嘉、隆之间,世所称大方巨匠。其所及见者,自酒下人拘徒,能单体小品以下,其耳所极闻者,莫不寻声望景,投意委志而与之游。”“能单体小品”,应指简单的文艺创作技能。
其二,以篇幅短小者为小品。张高宽《宋词大辞典》释“品”云:“有大品、小品之别。大品类似法曲中‘散序’,无拍。多未被用作词调。小品短于大品,可用作词调,如姜夔《醉吟商小品》。”[2]以词曲分为大、小品,最早见于明王骥德《曲律》卷四《林钟商目》“品”注云:“有大品、小品。”[25]大品应是篇幅较长之令词,而篇幅较短的则为“小品”。在唐宋词调中,有《品弄》《品令》《品字令》等。唐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琵琶抄谱写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中录《品弄》等急、慢曲子二十五首。后世知名作家,如欧阳修、周邦彦等人,亦有《品令》《品字令》等作品传世。
其三,“小品”或是一种别致的歌舞词调。宋杨无咎《解连环》词云:“援琴试弹贺若。尽清于别鹤,悲甚霜角。怎似得、斜拥檀槽,看《小品吟商》,玉纤推却。”明毕自严《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筠苍王公墓志铭》云:“尤善为小品歌曲,兴至辄命家僮歌以侑酒,奋袖低昂,蹋足为节,不自知其拓落不偶也。”既然可以“看《小品吟商》”“奋袖低昂,蹋足为节”,则小品应系歌舞之曲。在表演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动作,或载歌载舞,或歌舞相间。姜夔《醉吟商小品》云:“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29]应是歌唱结束,转入琵琶演奏(器乐演奏常与舞蹈相伴)的一种过渡,描写了醉酒之后且歌且舞的情形。
其四,姜夔《醉吟商小品》之“小品”应指乐曲技法。姜夔《醉吟商小品》序云:“石湖老人(范成大)谓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传矣,曰濩索(一曰濩弦)、梁州、转关绿腰、醉吟商胡渭州、历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谒杨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实双声耳。”[29]王奕清解释说:“按《胡渭州》,唐教坊曲名。醉吟商,其宫调也。姜夔自度,乃夹钟商曲,盖借旧曲名,另依新腔耳。”[30]《醉吟商》之曲在五代时已出现,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载,黔南节度使王保义女善弹琵琶,梦美人授曲,中有《醉吟商》一调[29]。宋人吴埛《五总志》云:“余先友田为不乏,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应圣羽》,其声清越,不可名状。不伐死矣,恨此曲不传。”田不伐即田为,曾任大晟府制撰官,则北宋末年此曲尚有人知。唐教坊曲及宋大晟曲皆作《醉吟商》,无“小品”二字。
冒广生和夏承焘认为“小品”是相对于大曲而言的,《白石词乐说笺证》引冒广生校词曰:“此词当题‘醉吟商胡渭州’,‘商’者声也,‘醉吟’与‘濩索’、‘转关’、‘历弦’,形容其声与指法,曰‘小品’者,对大曲而言。‘小品’二字当作注,不当标题。若径以‘胡渭州’三字标题,‘醉吟商小品’五字作注,尤惬意。”夏承焘认为冒说甚是,“《五总志》以醉吟商为凤鸣羽,应圣羽诸名并列,后二者或亦宫调非曲调名”[31]。“醉吟”是指法还是宫调,尚未明确。
据姜夔之序,从《醉吟商》到《醉吟商小品》,系“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则“品”调应是得名自“调弦法”,即“品弦法”。也就是说,“品”起初应是一种音乐术语或演奏技法,之后将这种类型的词调称为品弄、品令、品字令,或分为大品、小品。“商”是宫调,“醉吟”是曲名,而“醉吟商”应系一种曲调名。至于“小品”,或应是演奏技法,即一种“品弦法”。关于“品弦法”,姜夔琴曲《古怨》序云:
琴七弦,散声具宫商角徵羽者为正弄,慢角、清商、宫调,慢宫、黄钟调是也;加变宫、变徵为散声者曰侧弄,侧楚、侧蜀、侧商是也。侧商之调久亡。唐人诗云:“侧商里唱伊州。”予以此语寻之:伊州大食调黄钟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转弦,取变宫、变徵散声,此调甚流美也。盖慢角乃黄钟之正,侧商乃黄钟之侧,它言侧者同此;然非三代之声,乃汉燕乐尔。予既得此调,因制品弦法,并《古怨》。[29]
杨荫浏、阴法鲁合著之《宋·姜白石制作歌曲》书中对琴曲《古怨》序中提及的“品弦法”未作明确解释,而将《醉吟商小品》序中提及的“品弦法”一词解作“弹奏的方法”[32]。《汉语大词典》中“品弦法”一词也以姜白石《醉吟商小品》序为据,释为“指弦乐曲调的弹奏技法”。关于“品弦法”的确切所指,张林以“制品弦法”为“没有学到节奏,自己制造节奏的方法”[33],而李勤认为“品弦法”作为一个专门的音乐术语,其确切的含义应是“调弦法”或“定弦法”[34]。以此而解,从《胡渭州》到《醉吟商小品》,系改变了调弦之法。
姜夔《醉吟商小品》序中有“因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实双声耳”之说,欲知品弦法对于词体之影响,需结合“双声”来考察。清陈澧《声律通考》卷十云:“姜氏词所注宫调皆在二十八调之内……惟《醉吟商小品》云实双声,不知何调。或即双调欤?然每字不注律吕而注当时俗字。”怀疑“双声”为“双调”。而“双声”又有两解,如戴长庚《律话》中卷论及《醉吟商小品》云:“此词原序注双声,按双声有二:如词有两段,前后同音曰双声;又双调亦曰双声。双调者,乃夹钟一字为宫,仲吕上字为商,林钟尺字为角,南吕工字为变徵,无射凡字为徵,黄钟合六字为羽,太簇四五字为变宫收,仲吕上字名双调,乃商音也,故曰《醉吟商》也。”《醉吟商小品》及后来以“小品”命名的词调,都是单体短调,不可能是“词有两段,前后同音”。“双声”之意,或应为“双调”。“曲终底拍词句断处皆无拍”,无拍则不可歌,应为合舞之曲,这也与前文所言之小品为歌舞曲之推测相合。
后来,人们又将才力稍逊的作品称为“小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云:“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镜台’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让和凝、李珣辈,惟骨韵不高,可称小品。”卷三又云:“吴薗次词,调和音雅,情态亦浓,词中小品也。”[35]一是“才力不逮”“骨韵不高”;一是“情态亦浓”,失之自然,故称小品。
此外,曲中也有小令一体。词、曲中的小令含义虽然不同,但界定方式相似。曲之小令作为散曲的一种形式,由一只独立的曲子构成,相对于“套数”而言,是一种不成套的曲。曲中的小令篇幅一般更为短小,相当于词之一阕。小令除由单个曲牌构成外,还有重头、带过曲、换头、集曲等特殊形式。曲中的小令不论长短,只要是单独一曲,不合成套数,即使是超过60字,也称为小令。
作为一种词调类型和词体形式,令体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已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不同的形态特征与文体功能。在使用令体概念之时,我们应全面理解令体的丰富内涵与形态特征,准确把握不同文献中“令”的具体含义,避免因概念混乱而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
[1]冒广生.疚斋词论[J].同声月刊,1942,(5-7).
[2]张高宽.宋词大辞典[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3]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马兴荣.中国词学大词典[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5]王小盾.唐代酒令艺术[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
[6]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蔡祯.词源疏证[M].北京:中国书店,1985.
[8]林玫仪.词学考诠·令引近慢考[M].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9]龙榆生.词曲概论[M].北京出版社,2004.
[10]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11]王小盾.词典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2]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词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4]王易.词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5]洛地.词体构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6]任半塘.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17]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19]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J].文学遗产,2004,(6):51—64.
[20]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1]张鸣.宋代词的演唱形式考述[J].文学遗产,2010,(2):16—27.
[22]于天池.宋元说唱伎艺脞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2):15—21.
[23]赵义山.“嘌唱”考论[J].文学遗产,2004,(4):131—133.
[24]程宇昂.《梦粱录》所指宋代“小唱”辨析[J].韶关学院学报,2007,(4):18—21.
[25]王骥德.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6]饶宗颐.词集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7]赵义山.宋元“小唱”名实辨[J].文艺研究,2008,(1):103—106.
[28]郑孟津.宋词音乐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29]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王奕清.钦定词谱[M].北京:中国书店,2010.
[31]夏承焘.白石词乐说笺证[J].浙江学报,1948,(2):25.
[32]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制作歌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
[33]张林.论《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的节拍节奏[J].中国音乐,1998,(3):28—30.
[34]李勤.“品弦法”释义考辨[J].中国音乐,2000,(1):29—30.
[35]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