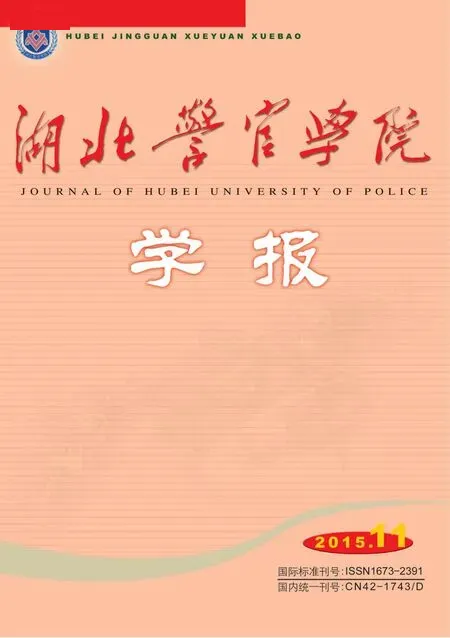我国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理论探析
韩继领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不能犯,根据国外刑法理论,是指行为人陷入错误认识,导致行为不成立犯罪,不具有可罚性。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不能犯的研究未形成系统理论,以至于在肯定不能犯的可罚性基础上,将不能未遂犯(或称不能犯未遂)作为不能犯的同义替代,即认为不能犯(或不能未遂犯)是未遂犯中不可能既遂的情形。对不能未遂犯的处罚依据的研究,除在于寻求不能未遂可罚的伦理,更在于通过对处罚依据的科学性、合理性的完善,划清可罚的不能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的界限,更好地实现刑法兼顾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的功能。
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不能犯大致分为三类:(1)规定不能犯不为罪,严格区分不能犯和未遂犯;(2)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犯的一种,即区分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在可罚性方面分为可罚的不能犯和不可罚的不能犯;(3)不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规定处罚未遂犯(包括不能犯)的一般原则,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犯的下位概念。我国立法基本遵循第三种立法模式,虽将迷信犯排除在未遂犯之外,但并未将不能犯从未遂犯中剥离,因此不具有任何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犯罪未遂,由此带来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因而备受诟病。我国理论界对不能未遂犯的处罚依据如何界定?不能未遂犯的立法是否兼顾了权利保障和社会防卫功能?本文拟在介绍国外未遂犯处罚依据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未遂犯处罚依据存在的问题,以期完善我国的不能未遂犯理论。
一、国外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的理论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刑法观都认识到危险是不能未遂犯应受处罚的依据,但在如何界定危险方面,主观危险说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中心,侧重于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考察;客观危险说则立足于行为的基础性地位,从行为危险性的角度分析。随着现代主观主义与现代客观主义的出现,主观危险说与客观危险说从针锋相对发展到相互借鉴、修正。
(一)主观危险说
主观危险说包括主观未遂论和现代主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强调处罚不能未遂的根本依据在于行为人主观的刑事违法性,行为系行为人意思或性格危险性之外部表现,行为人反社会的性格本身即敌对法的意思已构成处罚必要之危险。在未遂犯的场合,行为人因与自己意志无关的事实才无法既遂,其主观恶性与既遂犯没有差别。
现代主观未遂论修正了主观未遂论过于强调主观犯意的问题,认为作为可罚未遂的行为应同时符合表征行为人犯罪意思的确定性和取消不可能性,强调行为自身的表征作用和意思的客观化操作。现代主观未遂论建立在新派实证主义哲学构建的目的刑和行为人刑罚理论体系下,重视特殊预防,认为出于法秩序维持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在行为人以犯罪意图着手行为时,刑罚应适时提前介入以防止对法秩序造成侵害。
主观危险说之下,又分为以下学说:
1.犯意说。该说认为只要行为人在行为中反映出内心犯意,就应受到刑事制裁,它强调犯意的支配地位。不同学者对犯意在认定未遂行为中的作用及对不能未遂犯的处罚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未遂犯应与既遂犯同等处罚,处罚未遂的充要条件是故意的外部表明,只要在接近既遂结果发生前的行为中充分表明了犯罪意思,就可以将之与既遂犯同等处罚。有学者主张迷信犯具有犯罪性,如法比安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外部行为中表现出犯罪意图,就具有可罚性,“处罚迷信犯虽然是一种非常严厉的结论,但绝不是不正确的结论。”[1]
2.表征犯意说。该说认为处罚未遂犯的依据在于行为人通过其行为表征出其内心犯意,它强调表征行为的地位。德国学者考勒尔认为,“对于法秩序的危殆化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某种计划因可能的手段而被实现,而是在自然法则上能够引起结果的计划已经表现于外部。”[2]德国学者凯斯特林以错误是否使客观行为丧失行为性为标准区分未遂行为是否可罚,认为当行为人表象中所设定的因果关系完全不具有现实性时,活动就欠缺行为性。
主观危险说认为,因果关系法则是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并不存在客观的可能性或客观的危险性。如果将客观的犯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危险性作为行为可罚性的判断依据,所有的未遂犯均不可罚。
(二)客观危险说
传统客观未遂理论创立者费尔巴哈认为,可罚的未遂成立条件有两点:一是行为因外在障碍而未达既遂;二是行为依其外部特征,与行为人所欲实施的犯罪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客观的危险性。费氏认为未遂间接地破坏了法的状态,达到既遂的盖然性程度决定着未遂犯的可罚性程度。
与传统客观未遂理论坚持未遂犯的处罚依据在于盖然性危险不同,现代客观未遂理论认为该危险是指向法益侵害的危险,根据坚持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立场的不同,该理论又分为以下两种。
1.行为危险说。行为危险说“着眼于行为之反伦理性而作否定性之价值判断”[3]。该说源自德国学者威尔兹尔的行为无价值论和人格不法论,主张不法是与行为人相关的人的行为不法,违法性通常是对与行为人相关联的行为的否定。行为危险说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不法,体现出的是行为的意志性、目的性或人格性,带有浓厚的目的论和人格论的色彩,未能跳出主观危险说的藩篱。
2.结果危险说。结果危险说着眼于行为引起法益损害或危险的结果,对此所作的否定性价值判断。结果危险说认为侵害法益危险性的有无,应通过行为是否具有引起结果发生的具体的、现实的危险来判断,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李斯特、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等。有学者指出,结果危险性的判断固然重要,行为的基础性地位亦不可抹杀。如日本学者名和铁郎认为,“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别在于‘行为’有无实行行为性……但具有实行行为性时并不直接成立可罚的未遂犯,只有同时具有‘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时,才成立可罚的未遂犯。”[4]
二、我国不能犯的处罚依据
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不能犯的处罚依据分为形式依据——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和实质依据——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通说在判断不能犯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根据抽象危险说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其次,从事后的立场,以科学的观点,判断行为是否可能实现犯罪结果,从而区分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5]
(一)形式依据
“未遂犯之所以要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是因为它具备了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而是因为它符合修正的构成要件。”[6]通说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认为不能未遂犯虽因工具、手段或对象方面的原因而不可能致使既遂结果出现,但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故意与既遂犯的主观恶性是同等的,它决定了不能犯的罪质;客观层面上,行为人在主观恶意下实施了通说认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该行为虽因错误而无法致使既遂结果出现,但只属罪量上的考量。我国犯罪构成要件间是一损俱损的耦合关系,任一构成要件欠缺便会导致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下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本身进行修正。然而“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7],把基本的犯罪构成(既遂犯的犯罪构成)与符合未遂犯的修正犯罪构成之间的区别理解为行为在事实上是否齐备了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又承认“无论是基本的犯罪构成还是修正的犯罪构成,都只能作为一个诸要件完备的统一体而存在”[8],将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作为区分基本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的根据,逻辑上自相矛盾。在未遂犯的问题上,传统理论无法妥当解释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一论断。
(二)实质依据
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严格意义上只是解决了不能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并未解决对某一行为动用刑罚权的实质原因。传统理论并未深入探析危险这一核心理论,而是将犯罪的实质解释为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社会危害性是一个主观色彩浓重、抽象而难以量化的概念,对其大小及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甚至对其有无的判断,不同主体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抛开刑事违法性,一个普通的违德行为或违反治安规范的行为,与触犯刑律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方面可能无法区分,对其的评判完全被吸纳在违法性评价中。因此,未遂犯处罚的实质依据并未作为问题在个罪中予以论证,仅在出罪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才予以考虑。与证明式的危险客观存在相比,这种推定式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认定方式有过多入罪之嫌。
三、我国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理论的完善
在认识我国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理论弊端的基础上,需斟酌国外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在力求将国外理论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寻求这些理论的本土资源。
(一)以法益侵害性代替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李海东教授认为社会危害性并非刑事规范,而是政治与道义上的否定评价,在刑事司法中起不到任何规范与限定的作用。[9]陈兴良教授提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转换成法益这一规范的概念。”[10]张明楷教授认为,是人们未充分揭示社会危害性一词的规范质量,而非该词本身不具备规范质量。[11]在区分不能犯和未遂犯的问题上,关键是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12]应充分揭示社会危害性的规范质量,发掘(或赋予)其法益侵害性的内涵,将客观危险作为评价要素融入到社会危害性有无的评价标准中,引导社会危害性评价向客观方面倾斜。
(二)坚持结果危险说
传统的危险判断停留在表征犯意说,本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在与主观相结合后容易被认定为是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忽视了刑法保护法益的价值。因此,在判断危险是否存在时,应结合行为是否具有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具体、现实危险。
(三)以实行性限定对实行行为的认定
实行行为须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的类型化行为[13],对实行性的判断可借鉴该当构成要件行为理论,即结合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客观表现形式,将行为置于具体犯罪构成中,从客观因果关系的角度界定行为是否具有实行性。
(四)修正犯罪构成理论内在矛盾冲突的解决
三阶层理论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与否判断构成要件是否齐备,犯罪结果并非在所有的罪名中都是必要的构成要件要素。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犯罪构成可从构成要件要素方面区分。传统理论没有厘清犯罪构成的不同层次,混淆了构成要件理论在区分既、未遂和在犯罪成立意义上的地位。构成要件要素应作为构成要件之下位概念,如主观方面存在犯意、动机、目的,客观方面存在行为要素、结果要素,应从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情况区分既遂与未遂。
四、结语
在不能未遂犯处罚依据的问题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是必然趋势。纯粹的客观主义强调不能犯未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故而主张不处罚不能未遂犯。这种观点虽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但不利于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其结论亦难被信服。[14]主观主义的绝对化可能走向惩罚思想犯、迷信犯的境地。处罚不能未遂犯是基于预防主义的立场,行为的基础性地位虽然不能漠视,但无疑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界定该行为的性质与客观危险性。
[1][2][日]宗冈嗣郎.客观未遂论的基本构造[M].东京:成文堂,1996:100,20.
[3]余振华.刑法违法性理论[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82.
[4]张明楷.未遂犯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东京:成文堂,1997:275.
[5]陈家林.为我国现行不能犯理论辩护[J].法律科学,2008(4):12.
[6][7]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461,87.
[8]赵秉志,吴振兴.刑法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85-186.
[9]李海东.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中、德、日刑法学的一个比较[A].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4 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6-47.
[10]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J].法学研究,2000(1):13.
[11]张明楷.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A].陈明华等.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4.
[12]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
[1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47.
[14]余向阳,梁博文.不能犯的可罚性研究[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