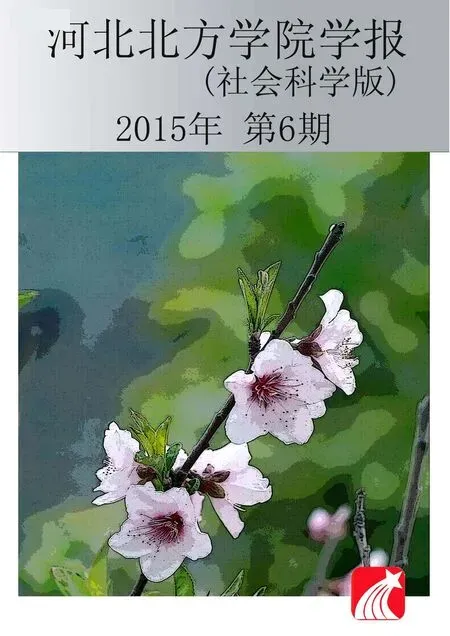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
陈 晓 俭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
陈 晓 俭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宋哲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登基后,分别于该年五月五日及六月二十五日两次下诏求言,由于两次诏求直言前后都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特别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波助澜,借求言聚集旧党力量,这使得宋哲宗登基求言成为北宋历史上独特的政治风景,为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清算,即元祐更化进行了舆论准备。
关键词:宋哲宗;诏求直言;司马光;元祐更化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130.1123.07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30 11:23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宋神宗驾崩,六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宋哲宗履行新皇帝即位后诏求直言的政治惯例,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五日下诏求言。在这之前,司马光早因对熙丰变法和新党人士的不满屡次上书,乞开言路,废罢新法,攻讦新党。但五月份的这份求言诏书并不合司马光等旧党人士的心意,他们认为不应该对上书直言者设置限制,更不应该让敢于直言者以言获罪,即要为旧党畅所欲言地抨击新法和反对新党制造舆论,为废罢新法进一步扫清障碍。由于得到垂帘听政之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在朝廷迅速壮大,在旧党人物的推动下,六月二十五日宋哲宗不得不重新颁发求言诏书。此次诏书颁布后,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更为露骨,全面而系统地抨击新法,攻击新党,要求控制台谏。在旧党铺天盖地的直言攻击下,“元祐更化”终以旧党的胜利而告终。宋哲宗登基求言的全过程掺杂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是反映两党势力此消彼长的一面镜子。
目前学界对唐代的求言和上书制度研究较多,而对宋代以及宋哲宗一朝的求言还没有专门的论著。从哲宗登基后诏求直言的背景入手,并对求言的整个运作过程加以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北宋中期新旧党争的理解。
一、宋哲宗登基求言的背景
发生于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曾经在北宋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朝臣反对的呼声高涨,但王安石仍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原则,坚持要将变法进行到底。漆侠将变法斗争分为两个浪潮,在第二次反变法的浪潮下,王安石曾被两次罢相[1]。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本就对变法产生动摇的宋神宗“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2]10 547,加之慈圣和宣仁两太后认为王安石乱天下,遂罢安石。在王安石被解除宰执期间,变法派内部不断分化,宋神宗陆续任用了部分旧党大臣,但此时的政权仍掌握在变法派手中。王安石复相之后,受到了以吕惠卿为首的分裂集团的沉重打击,宋神宗又“益厌之”且“事多不从”[3]10 549,王安石此时已力不从心,于熙宁九年(1076年) 春向宋神宗请求辞去相位。
王安石的离开削弱了本就分化的新党势力,尽管此时的新党仍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但在旧党成员的参与下,由宋神宗主持的新法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向着有利于以豪强地主为中心的守旧派的方向转化。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王珪三见神宗,希望早建东宫,定立储一事,并请高太后权同听政。宋神宗深知立储之事一日不定就会多增一日猜忌和党争,但他每次都是“微肯首而已”[3]8 409。此时,蔡确和职方员外郎邢恕密谋拥立雍王颢或曹王頵,由邢恕联络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两人。这两人知道邢恕来意后惊惧道:“君欲祸我家!”[1]8 410蔡、邢两人见谋立不成,便反咬高太后欲立雍王颢。
同年二月癸巳,即二月二十九日,神宗弥留之际建储之事已迫在眉睫。赵煦是神宗的第六子,而他的5个兄长早殇,故立赵煦为皇太子本是不争事实,于是宰相王珪道:“上自有子,复何议!”[1]8 411这就使蔡确与章惇等人另立太子的企图失败。次日,赵煦被立为皇太子。三月五日,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哲宗即位,“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1]8 456。随着宋哲宗的登基,垂帘掌政的高太后更是加大了党同伐异的势头,变法派的许多成员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排挤,大部分新法也废除殆尽。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有直接关系。
二、宋哲宗登基后的第一次诏求直言
宋哲宗登基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五日下诏求言:“盍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朕私闻谠言,虚己以听,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厚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而不逞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偏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政缺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廷。”[1]8 508这次求言,一方面是宋哲宗例行新皇即位求言之故事,另一方面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欲将求言作为抨击新法和攻讦新党的舆论工具。
(一)司马光连篇累牍地上疏活动
关于此次诏书的颁布,司马光的频频上疏发挥了关键作用。
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1]8 465。道路两旁的数千百姓也一齐欢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1]8 465可见,司马光在朝廷内外可谓深孚众望,也足以想见他在日后对新党及新法的打击中的作用之大。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自然也不会错过向天下人表示其顺应民心的机会,遂问计于司马光所当先者为何,司马光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三十日上《乞开言路札子》道:“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缺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封实状,尽情极言。”[4]335并且详细地讲述了求言的具体实施过程,以期达到“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4]335的效果。表面看来,司马光的这一道札子是遵循了新皇即位例行诏求直言的故事,但实际上则为废新法与罢新党做了舆论准备。
随后,司马光又于四月二十一日上《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除再次请求下诏书开言路外,进一步指出古代贤君历来都是求贤者,去不贤者,以此要求皇帝“博访选举,拔其殊尤”[1]8 482,选出能为君主所用的贤臣,言外之意是在暗示皇帝罢去身边的新党等不贤不肖者,而招用神宗朝被罢废的旧党人物。数日后,司马光又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明确指出:先王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1]8 490。这一奏疏明确指出新法不合古理以及新党人物的自以为是。接着批评王安石,“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之异者摈弃沉沟壑……不顾国家大体”[1]8 490,又批评他“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1]8 490,“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1]8 493。司马光为罢黜新法早有准备,又连上三状,力陈废罢保甲、免役与将官诸法并附对策,要求恢复旧制,以顺民心。5日之后,他又上《乞开言路状》,再一次将矛头对准新党。这一次,他指责道:“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聪明,专威福,行私意……甚于盗贼。”[1]8 509对王安石的攻击进一步升级,王安石成了比“盗贼”更甚的敌人。他认为王安石一派当道,使“百姓愁苦无聊,靡所控告”。因此,“首乞下诏开言路,以通下情”[1]8 509。
司马光费尽心思上了如此多道札子,非但未闻下达开言路之诏书,反而听得太府少卿宋彭年及水部员外郎王谔因言事获罪。这就意味着旧党成员肆意攻击新法的进言之路不够畅通无阻。所以,司马光一再建议有官无官,当职或不当职之人皆可言事。表面看来司马光是要广开言路,但其言外之意却是希望旧党人士能借诏求直言的机会自由地上书抨击新党及新法,而又不会获罪,为进一步聚集旧党力量和打击新党扫清障碍。
(二)围绕五月五日诏书的博弈
哲宗即位,高氏垂帘,但凡事须经由蔡确等人办理。因此,该诏书的颁布也必然维护新党利益。若言及新法之人能论理得当并利于社稷民生,就会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反之,若阿谀奉承,心怀不轨,则会受到黜罚。这本是稳定当时主少国疑政局的良策,但在司马光看来,此诏是新党向旧党的一次严正挑战,将会阻碍其发表反新法的进言之路。于是,他立即上疏并指责道:“上言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也;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然则天下之事,无復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4]352。并随之提出删去“若乃阴有所怀……是亦不得已也”一节,欲使天下人各尽所怀,实际上是让旧党极言新党及新法的不是。司马光除了在言语上回击此诏外,还以辞去门下侍郞的行动警示高氏必须按他的意愿修改诏书。凭借司马光能够“活百姓”的号召力,高太后不得不积极回应,让梁惟简赐其手诏,谕令供职,表示日后仍要共处政事,且会“再降诏开言路”,司马光这才受命。
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韩维和司马光相继对五月五日诏书展开抨击。韩维的上疏首先对此大赞一番:今开言路实乃天下之大幸也!之后,便直言道:宜刊去“若乃阴有所怀……是亦不得已也”这一段,“别撰诏文,遍颁天下”[1]8 535,以使天下人知陛下的好谏之心。虽然,宋廷之前对司马光要求删去诏书中的中间一节的上疏已作出回应,但无实质性行动。于是,在韩维上奏同一天,司马光又上了类似的一道札子,仍就五月五日诏书“多设防禁”,使天下人多有所惧而不得尽言一事,详细介绍诏书如何为天下所知,“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示”[1]8 536。另外,还考虑到如何帮助皇帝处理繁多的奏状,“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或乞降付有司施行”[4]356-357。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废新法,罢新党。
吕公著于六月二十一日陈述明主应做的10件事,同时又响应韩维及司马光,希望皇上能“所言无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终不以言罪人”[1]8 547。3人的连连上疏终于迫使高太后于六月二十五日颁布新的求言诏书。不难看出,此时的旧党势力呈上升趋势。同时,旧党人士在中央的任职情况也证明了旧党集团渐渐渗入到中央重要部门并有压倒新党之势。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旧党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吕公著和刘挚分别知陈州,兼侍读,任吏部郎中;五月间,旧党势力再上一层。司马光代章惇为门下侍郞,同时旧党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被任用;六月,王岩叟升为监察御史。双方即将为争夺台谏控制权而展开斗争。尽管如此,此时的新党仍是朝廷的主导力量。
三、宋哲宗登基后的第二次诏求直言
基于旧党压力,宋廷于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二十五日,颁布如司马光等旧党所愿的诏书:“朕绍乘燕谋,获奉宗庙,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宁,惧无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达听,以防壅蔽,敷求谠言,从辅不逮,然后物情遍以上闻,利则得以下究,诗不云乎:‘访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其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鼓、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1]8 548
与五月五日诏书相较,此诏书并未言及上疏臣民会因言获罪之事,这正符合旧党心意,也是司马光等人自五月五日诏书颁布后频频上疏的目的所在。因此,此诏书可以看作是新党对旧党作出的让步,是适应当时新、旧党势力此消彼长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反应。诏书颁布后,司马光与刘挚等旧党人物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罢废新法和攻击新党的活动,最重要的一步即是控制台谏系统。其实,早在六月二十一日,吕公著就指出:“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臣,正直敢言之士,通置左右,使掌谏诤,无空要职,广益言路。”[1]8 546六月二十五日诏书颁布之后,他又于二十八日连上两奏,其中一折尽言新法致民不聊生,“恐当一切罢去”[1]8 551;另一折则引荐孙觉、范纯仁、刘挚及苏轼等众多旧党成员,并将他们日后的具体职务也一并列出。可见,旧党为在宋廷占有一席之地费尽心思。高氏封吕公著所上札子并交予司马光,此两人同为旧党,其言论同出一辙,彼此相符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随后,司马光复上一折,又罗列了近30个可被委以重任的旧党成员呈予高氏。九月,宋廷对吕公著和司马光两人所推荐的人作出回应:朝奉郎、秘书少监刘挚除为侍御史,吕公著、司马光与刘挚3人,凝聚并加强了旧党力量。
七月十四日,司马光上《乞降臣民奏状札子》,不满皇帝虽下诏求言却不施行的行为。他又如1个月之前的六月十四日所说:如何处理这繁冗的札子——“降付三省……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前后相隔1个月,内容完全一致,但惟少了一个“乞”字。六月十四日司马光仍言“或乞留……”“或乞降……”,而七月十四日的札子却无“乞”字。在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时代,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说话口吻。“乞”字的有无说明此时司马光已拥有这样的实力:朝廷若对他再三强调之事若不及时实行,他可省去敬语表示不满。事实证明,高氏不想也没有违背司马光的心意。关于处理的成果,司马光道:“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卷,臣仅与诸执政选择,其中除无取及冗长之辞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1]8 589司马光作为反变法派的主导者参加了筛选直言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一批新法派言论已被淘汰,而呈现在皇帝面前的大多数札子则是如何罢废新法和打击新党。司马光的这一举动为旧党势力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作了铺垫。
同年九月,刘挚任侍御史之后,立即提出增置谏官一事。十月,高太后即诏仿《唐六典》置谏官,谏官由皇帝亲自除受,掌握台谏就意味着有了先发制人的权力。宋廷在听了司马光五月之前的上疏后,下诏开言路;又从吕公著和司马光之议,除刘挚为侍御史;此次,又从刘意增置谏官。旧党的要求一步步加深,而宋廷也鉴于新旧两党势力消长而一点点接受。紧接着宋廷便对可充任谏官的5人作了具体安排:“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朝请郎、知虔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正字范祖禹为右正言,令三省、枢密院同进呈。”[1]8 606选谏官一事是旧党在新党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高太后秘密进行的,当高太后问“此五人何如”时,章惇给予了有力回击:“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浸启。”[1]8 606高太后言非左右也,皆由大臣所荐,章惇又反问道,就算是由大臣举荐,“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1]8 607,结果高太后等旧党并未对其作出正面回答。之后,旧党便将注意力转移到罢去章惇等重要新党人物的势力上。但围绕置谏官一事,新旧两党的斗争并未结束,章惇以旧党荐谏官之方式不依故事进行反击后,受到了王岩叟因其“不循所守,越职肆言”的弹劾[1]8 628。无独有偶,宰相蔡确又以祭奠神宗之际夜不赴宿,“慢废典礼”与“殊不尽恭”的罪名受到刘挚的弹劾[1]8 629。更有甚者,左正言朱光庭又将蔡确、章惇及邢恕等人以“共谋诬罔太皇太后”的罪名弹劾,旧党弹劾新党代表人物的罪名越来越严重,新旧两党的暗斗已逐渐升级为了毫无遮掩的明争。
元祐元年(1086年),刘挚和王岩叟又对免役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批判,要求依旧制改用差役法。而左正言朱光庭数次上疏怒斥新党,以蔡确不恭、章惇不忠和韩缜不耻罗列罪名,要求去奸邪之新党,选忠贤之旧党,并为3者罢去后安排了备选之人,“蔡确既去,乞以司马光补其缺;韩缜既去,乞以范纯仁补其缺;章惇既去,以韩维补其缺”[1]8 726。此时,新党在旧党猛攻之下已处于劣势,但旧党对新党的攻击言论仍在铺天盖地地袭来。刘挚以天下大旱为借口,陈蔡确10罪,连上10疏乞罢其相位,声称罢确是顺天意,召和气,慰公议。同时,王岩叟除陈废新法外,也极力要求罢去蔡确和章惇这样的佞人之杰。在旧党肆无忌惮的攻击下,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宋廷罢蔡确宰相,外放知陈州;罢章惇知枢密院,外放知汝州;蔡、章两人被贬离朝廷,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至此门下侍郞范纯仁等大批旧党控制了朝廷。而熙丰变法的内容也被废除殆尽,这就意味着元祐更化以新党的失败告终。
宋哲宗的诏求直言是旧党借机废罢新法和攻击新党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为新旧两党斗争的牺牲品。神宗去世后的数月之内,旧党人士陆续入朝,接二连三上奏废罢新法,要求皇帝清除身边的奸佞小人,安排旧党人士进入朝廷,最后发展到整治台谏。台谏一事的介入,使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与激化。这一程中,双方争相控制台谏系统,并将其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这一关键环节中,旧党受到新党的阻碍,于是罢黜新党核心人物成了他们进一步的目标。双方的政治斗争活动均通过上疏形式进行,不得不说,哲宗的诏求直言是旧党排挤新党,废罢新法的渠道和有力工具。经过元祐更化,旧党成功登上政治舞台。但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死后,旧党内部又在废罢新法的程度、范围和如何对待新党朝臣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按地域分成了3派: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虞云国认为:“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5]251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本身也有局限性。尽管元祐更化是新旧两党围绕废新法和罢新党引发的一场政治运动,但它确实针砭时弊地指出部分新法伤国病民的弊端。不得不说,哲宗的求言和旧党争罢新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端。新法实行之初,神宗曾抱怨道:“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3]10 547-10 548元丰年间又有大批旧党不断抨击新法之弊,由最初的“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1]8 493,到后来认为新法一无是处,司马光称其“尽改熙宁、元丰法度”[3]10 286,以至在他行将就木之际看到“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便叹“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3]10 768。废罢新法一事夹杂着新旧两党的私人恩怨,牵扯着两党的政治利益,但从大臣屡屡上疏言新法致民不聊生和伤民害国的情形看,尽管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认新法确实存在着诸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1]8 522以及“宽富而困贫”[1]8 523等弊端。姑且不论神宗及王安石欲富国强兵的本心,新法在自上而下的实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歪曲了其实施的初衷,再加上用人不当也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从这一方面讲,宋哲宗的求言虽成为旧党向皇帝进言罢废新法的渠道,但部分新法如保甲、保马和将官法的废除,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压力,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总之,宋哲宗登基求言的整个政治活动贯穿着新旧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是反映两党势力此消彼长和斗争日趋激烈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参见李军的《论唐代帝王的因灾求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谢元鲁的《唐代的求言和上书制度》,《天府新论》1998年第6期等。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漆侠.王安石变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根林.司马光奏议[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5]虞云国.细说宋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薛志清)

Two Seeking-Advices after Emperor
Zhezong’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in Song Dynasty
CHEN Xiao-jian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After he ascended the throne in lunar March,1085,Emperor Zhe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ought advice from court officials on lunar May 5 and June 25.Along with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arties,especially with the help of the old party headed by Sima Guang,he resumed the power of the old party,which made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become a unique political landscape at that time.All this paved the way for the later Yuanyou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public opinions.
Key words:Emperor Zhezong;seeking advice from court officials;Sima Guang;Yuanyou political transition
中图分类号:K 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6-0020-05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