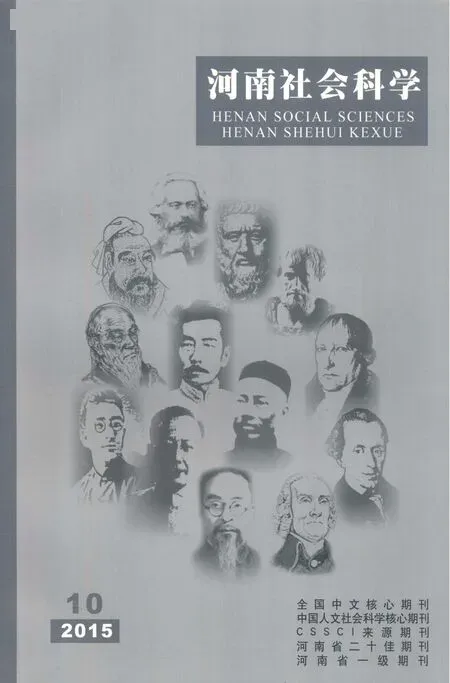复合联邦主义:效用与缺憾
周 顺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701)
现代联邦主义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在于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目的:各次级共同体拒绝合并成为单一制国家;却又不愿分头独立、自成一国。它们既要享受联合的强大,又想保留分治的自由。在18世纪的西方政治视野中,这一要求远远超出了既存制度的能力范围,甚至显得蛮横与任性:人们一面从单一主权国家的角度指责邦联散漫无能、施政乏力,一面从邦联的角度控诉全国政府傲慢专制、野心勃勃。
作为联邦主义探索与推进过程中的范例之一,美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弹力在权力延伸、危机修复方面展现出特定的效用与优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复合联邦主义”之路。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言,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这场“政府原则与实践的革命”将联邦主义内涵从政治体之间的联盟关系扩展到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层级政府或部门间的自治/共治关系的同时,也让现代人见证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复合政治体的诞生——形似邦联、实则民族国家,更准确地说,是两者的混合。同时,复合联邦主义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展露出其内部制度的界限、发展困境及失衡趋势。
一、联邦主义的历史与实践
从词源意义上讲,联邦主义(Federalism)源自拉丁语Foederatus,指“受约法约束(的状态)”。在前现代政治理论中,联邦主义多指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间的同盟关系。它历经三阶段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的面貌[1]。
第一阶段为“希伯来圣约”模式。这是一种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上帝不仅仅是契约见证人,也是契约参与者。上帝通过契约来自我限定,降低自身以成为人的平等伙伴;同样,人通过契约来自我扩展,提升自己以成为神的平等伙伴。在后来的契约关系中,神逐渐隐退,但契约的神圣性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圣约关系中所体现出的诸多要素,成了后来联邦主义的重要特性,如平等的契约各方,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同意的基础上交换誓言等。值得一提的是,圣约对于共同体采用何种政体形式并无单一要求,圣约所构建的联邦主义也并非单纯的宪法或制度框架,它更是一种文化与宗教共同体,一种基于某种特定信仰的普遍的关系网络。
第二阶段为“古希腊罗马实践”模式。虽然当时的理论家(如亚里士多德)并不欣赏这一“无益于政治最高目的(正义与自由)”的组织形式,人们仍出于以下两种需求而以联盟的方式践行联邦主义:一种是出于战争需要而缔结同盟;一种是出于宗教目的而联合起来敬奉神灵。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联盟规模有多么庞大、盟邦间力量如何不均,各个成员邦仍然是独立的邦国,在联盟形式中能够保持各邦的政治独立与宗教自由,这为后世联邦主义实践确立了基本的规范。
第三阶段为“中世纪理论与实践”模式。为了保持独立的商业城市地位,人们纷纷从经济联盟转向政治联盟,中世纪的联邦主义概念从瑞士到法国,再到德国与荷兰,后由英国人输往美国,最终又以美国模式重新回到欧洲,塑造了现代联邦主义的瑞士与德国。其中有三位思想家决定性地推动了圣约观念下的联邦主义的近现代历程: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迪普莱西·莫耐(Duplessis-Mornay)与约翰尼斯·阿尔秀斯(Johannes Althusius)。他们主张的“共生体”之间通过圣约方式形成联合的联邦主义模式也成为中世纪政治理论的核心与基础。
进入现代后,联邦主义作为一个与主权国家观相对的理念,引发了许多重要思想家的浓厚兴趣。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两派——“目的派”与“手段派”。“目的派”理论家蒲鲁东(P.J.Prodhon)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将联邦主义视为自由的终极形式,在关于民族国家或整个未来世界的构想中,联邦主义被赋予了极高的理论地位。蒲鲁东认为,大型政治体对于自由的根本威胁在于它败坏公民德行。唯有通过分散的权力关系——如“生产者自治联合会”,方能将自由较好地保存于联邦内部,使人获得自由。而布伯则强调,联邦主义的出路不在于政治权力的进一步分割与制衡,而在于以“对话”(Dialogue)的方式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目的派”学者反对政治科学家工具性、实验性、阶段性地滥用联邦主义这一概念。因为联邦主义是人类最基本、最完善的生存方式,它是目的本身,而非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手段派”理论家如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麦迪逊、约翰·卡尔洪、托克维尔等则仅仅把联邦主义作为某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运作手段,通过加强区域自治、促进政治整合的方式,来达到政治体外环境永久和平、内环境享有共和自由的目的。孟德斯鸠笔下的“联邦共和国”或“小共和的联邦主义”(Smallrepublic-federalism)旨在克服国家因太小而亡于外敌,因太大而亡于内乱的现实缺陷。卢梭所主张的联邦主义,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性同盟”,他思考的重点并不是保护同盟内小国免受外敌侵犯,而是如何保持小型共和国的自在与道德,施以统一的政治教育。康德的联邦主义旨在消除国际间的自然状态,建立永久和平,他所倡导的国际联盟的功能仅限于促成和平、结束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联邦主义不过是一种积极的“世界共和国”观念的消极替代品。麦迪逊与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分别从“联邦维护中央统一”与“联邦维护州主权”的角度实验性地运用联邦原则,但两人都没有成功破解双重主权所带来的问题,只是无限期地推延了这一冲突。托克维尔则仅仅将联邦视为美国实践共和制的阶段性工具,甚至已预言了其死亡:联邦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只要环境有利于它,它就能存在下去……联邦主要依靠组建联邦的法律而存在,只要爆发一场革命,或舆论一有改变,就可使联邦不复存在。
二、分离与改制:美国联邦主义的早期尝试
在美国正式确立联邦体制前,“联邦”(Federal)一词多指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邦联”概念。《联邦论》(又译《联邦党人文集》)中,“联邦”(Federation)与“邦联”(Confederation)为麦迪逊等人交替使用,并无严格差异。中文译文从现代政治结构出发所作的区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美国建国初期“联邦主义”概念的模糊性质。从1781年3月1日《邦联条例》正式生效,大陆会议更名为合众国国会,一直到1788年11月21日批准联邦宪法,美利坚合众国的体制在这7年中不断被诟病。主要的指责是邦联国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协调各州一致对外时也缺乏足够的权威,整个国家已到了“寸步难行、摇摇欲坠”的危急关头。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说服民众改制时援引了希腊近邻同盟、亚该亚同盟及德意志、波兰、瑞士与荷兰等联盟失败的例证,并认为这些例子昭示着毫不含糊的重要真理:一个主权居于若干主权之上……理论上,是一种谬误;实践中,破坏公民政治体的秩序和目的;结果,是用暴力取代法治。
麦迪逊式的指责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观念对邦联有效性所提出的质疑与挑战。“主权至上”是个年轻的理论,比起美国式联邦主义仅仅早了一百多年。但它的出现立刻以利维坦式的绝对服从征服了整个世界。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论特性有三:一是“绝对性”,完全不受法律约束;二是“永恒性”,亦不受时间限制;三是“不可分割性”,最高权力不可转让不可剥夺,更不可能存在两个最高权力。博丹将国家视为“绝对和永久权力”的拥有者不仅为法国君主制铺设了理论地基,也为国家这一独立而抽象的行动体高效、任性甚至专断行事创造了条件。
除百年殖民地自治经验所带来的地方主权认知外,美国在与英国的决裂过程中确立起了整体性的主权实体观念。美国人最早用以限制英国议会权力的宪法语言是一对普通的反义词:内部事务(Things Internal)与外部事务(Things External)。“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我们的外部政府,我们必须服从英国议会的权威,毫无例外”,因此,美国甘愿接受英国的商业管制与垄断,并以关税或港口税的间接方式(可称为“外部税”或“间接税”)来支付;但“就我们的内部政体而言,通过英国议会法案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税收都将是专断的”[2],所以当英国试图以“内部税”“直接税”的方式(哪怕所征税收很少,在爱德蒙·伯克看来几乎微不足道)向美国民众征收时,立即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美国人拒绝一切内部税、只承认商业管制的做法直指英美主权问题的核心。美国人究竟是臣服于英国国会还是臣服于英国国王?如果臣服于英国国会,那么美国人就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如果臣服于英国国王,那么《邦联条例》的起草者约翰·迪金森所说的“殖民地依赖于大不列颠,正如一个自由民族依赖于另一个自由民族”就不无道理。塞缪尔·亚当斯称殖民地“次于(Subordinate)而不是臣服于(Subject)英国议会”更是为“单一君主制下,建立起由两个主权实体联合起来的帝国联邦”作出善意的理论铺垫。虽说英美冲突从简单的税收问题上升至原则问题、主权问题,议会难辞其咎,但英国议会始终不愿承认已到了“非要在政治制度上有所突破不可”的时候,并依然坚持,“主权之内的主权”是最为严重的政治语病,“‘两个主权’的做法根本上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
英美无法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和平且合理地分割主权,这直接影响到美国建国时的政制选择。向后看,是腐败专断的英国;向前看,找不到可借鉴的发展模式;环顾四周,又是全球暗淡的政治前景——专制统治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因此,就美国历史经验而言,它在建国之初以“邦联”的方式保障各邦自由不受侵噬,是一种最自然、最直接也是最为稳妥的反应。刚刚从专制与腐败中挣脱出来,怎么能又轻易地让自己套上枷锁跳舞呢?与其让美利坚合众国因集权之力向内坍塌(Implosion),还不如让它徘徊在向外散裂(Explosion)的边缘,至少还能保留一份自由。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一直将“主权之内的主权”或“主权可分”的信念保持到立宪,并完整体现在1787年的制宪过程中。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主权在广义上统一而不可分(人民主权不可分),在狭义上是可以分割的(绝对权力可以在政府职能间进行分配)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然而,当邦联出现内部危机时,美国人又自然而然地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视角,批评其弱点及缺陷。由于缺乏统一的中央立法、执行及司法机构,邦联政府施政乏力,难以维系。财政上,邦联政府因无权直接征税,导致国库空虚、经济萧条、国际及邦际贸易混乱。对于邦联失败的原因,有学者从主权角度总结得极为巧妙:它试图“调和联盟所拥有的部分主权和各州所拥有的完全主权,试图减去一部分而仍然保留总数,从而违背了数学公理”[3]。
客观而论,邦联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失败的,而作为邦联,美利坚合众国(该名称始于《邦联条款》)是成功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在大陆会议的领导下,以邦联的组织形式战胜母国军队,无疑已达到联盟之目的。邦联体制在现代的黯然失效,并非邦联自身产生危机,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政治体制的要求与现有制度间产生了落差。各邦仅仅作为独立的主权体已经不够了,它被要求重新成为“臣民”,这一次是整个美利坚联邦的臣民。既想“由一而多”,又想“由多而一”;既要保持自由,又想强大而高效,出于这样两种相反的目的,一种新的制度在邦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三、复合联邦主义:新模式的争论
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对现代“联邦主义”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其“复合共和制”的构想重塑了人们对联邦的传统认识,将联邦理论从一种松散的共同体契约关系上升为一国之内同时达致区域自由与国家强盛的制度屏障。在当时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立宪之争中,只存在两种已知的政府模式:联邦/邦联(Federal/Confederal)与单一制/民族国家(Unitary/National)。其中,作为松散联盟的代名词,联邦与邦联可互换使用。美国立宪之后,世界上多了一种新模式:“联邦”。在全新的“邦联—联邦—单一制国家”三者关系中,邦联与单一制国家作为两种传统形态分处两个极端,“联邦”不再表示联盟或邦联,而是成为“兼有联邦性质(Federal)与国家性质(National)之复合体”的专有名词。《联邦论》[4]第39篇中这样描述其“复合”特性:
制宪会议提出的这部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国家宪法,又不是联邦宪法,而是二者的结合。就其构建基础而言,它是联邦宪法,不是国家宪法;从政府常规权力的来源看,它部分是联邦性质,部分具国家性质;从行使这些权力的方式看,它是国家性质,不是联邦性质;就权力的延伸范围,它又回到联邦性质,不是国家性质。最后,在宪法修正权方面,它既不全是联邦性质,也不全是国家性质。[5]
可见,当时尚不存在一个能够真正涵盖美国政治特性的新词语。美国立宪者在使用Federal一词时,与18世纪的普通公民一样,都表示“邦联”。当他在说“既不是国家宪法,又不是联邦宪法”时,意思却是“既不是国家宪法,又不是邦联宪法”。而对于如何描述这部既像邦联与单一制国家,又不是邦联或单一制国家的宪法,立宪者却找不到相应的名词,只能称之为“复合体”(Composition)。
联邦主义的复合性质是导致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分歧的直接原因。争执焦点在于:联邦性质与国家性质,哪个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联邦主义者认为,传统小邦国(州)容易滋生党派斗争,纯粹的直接民主制无法有效克服多数党的肆虐,在激情与利益的驱动下,政府极有可能沦为多数选民的工具。唯有在一个大型、异质、难以形成压倒性多数党派的“复合式联邦”中才能拯救共和危机,“根据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提出一种共和制的矫正办法,克服共和政府易于产生的弊病”。而反联邦主义者则认为,联邦主义者主张“将联邦直接建立在公民个体之上”的做法正是国家走向集权与腐败的危险信号。联邦的目的是保存个人的自由,自由最温馨的摇篮、最坚实的堡垒并非单一制国家,而是作为自然共同体的乡镇与州。因此,小邦国间的简单联合,而非复合式联邦才是国家的基本构成单位。换言之,州的自由与权利应永远优先于联邦的光荣与伟大。
关于复合联邦主义的争论并没有因宪法的确立而消弭,相反,却以制度化党争的形态保留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模式的关键性特征。从1787年9月《联邦宪法》制定完毕,各州制宪会议陆续批准,至1789年3月宪法正式生效,这群支持联邦宪法,自称为“联邦派”或“联邦主义者的”国父们尚未建立政党的意识,他们甚至认为“党争”将直接导致国家分裂,应在未来的政府实践中予以警惕。而之后的历史证明,观念与利益终将在政治格局上有所反映。除了从“制度论”(选举制度决定派别联合)、“冲突论”(极化政策,无中间立场)、“政治文化论”(实用主义者善妥协)、“社会意见一致论”(个人主义价值观决定基本政治共识)、“自我修复论”(维系现存制度的中庸之道)等角度[5]解释美国两党制的成因外,联邦性质与国家性质的争论应是政党制度背后最为根本的推力。
复合联邦主义也是现代人理解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关键锁钥。在当代美国人看来,美国宪法是一部不民主的宪法。其中遭受诟病最多的“选举人团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还险遭废除的命运。唯有从复合性质的角度,我们才能体会制宪者深思熟虑的精妙所在。以选举人团制度为例。首先,选举人团制度是大/小州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性质与国家性质间复合作用的结果。制宪会议初期许多联邦主义者(如麦迪逊、詹姆斯·威尔逊、莫里斯等)都支持全国直选总统,后来在州权捍卫者的不懈努力下,才引入间接选举的元素。可以说,选举人团制度是一个“反国家权力的设计”,它无意于将选举权从人民手中夺走,相反,它将选举的控制权从政治家那边拿回来,重新交给人民大众。其次,选举人团制度并不是畏惧民主本身,而是畏惧在当时环境下,全国直选无法在一个边域如此广阔的国度里顺利进行。特别是对于许多来自小州的代表,由于信息的缺乏,一般民众都会选举自己州的代表,相形之下大州的优势显露无遗。宪法中要求每位选举人在所投的两张总统票中,必须有一张是选外州候选人的规定,其实就是希望一张票体现州原则,另一张票体现国家原则,以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在遵循大众意愿的前提下找到那位超越地域限制的总统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人团制度才是真正保障大众选民利益的选举方式[6]。
四、复合联邦主义的两种分析视角
美国联邦主义的复合性质有两种理解角度,一为联邦性质(Federal)与国家性质(National)的复合,二为大共和国与小共和国的复合。这看似与普布里乌斯(Publius)(该书作者汉密尔顿、麦迪逊与杰伊所使用的笔名)《联邦论》一书的两大主题——联邦与共和体制——正相吻合[7],实则相差甚远。
第一种复合性质的视角是美国立宪者的视角。它在论述联邦新宪法的可行性、邦联的缺陷以及何种政体能够实现联邦目的的同时,强调了新宪法与共和政体原则高度相符的特性。在联邦主义者眼中,创建一个“复合的新联邦”意味着以联邦的形式拯救共和危机,“根据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提出一种共和制的矫正办法,克服共和政府易于产生的弊病”[4],使之在民主时代焕发自由之光彩。这一几乎被忘却的视角于20世纪中叶“新联邦主义革命”的大讨论中重新得到关注。
联邦主义研究者马丁·戴尔蒙德(Martin Diamond)①认为,所谓“联邦性质”与“国家性质”的复合,在制度安排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与分权问题相关。包括:统治同一的土地和人民的两级政府;各级政府至少有一个自主行为的领域;以宪法形式对各级政府所属领域内的自主行为做出保障[8];以及三权分立与制衡;等等。其二,与中央政府中的联邦性质相关。即在联邦层面,大小州之间平等无差。这包括“既有联邦的底气,又有单一制国家的视野”且施行一州一票的参议院,“每州至少保证一票”的众议院,及作为全国直选总统之“绊脚石”的选举人团[6]。复合性质的精妙与复杂体现着立宪者在驾驭、平衡“联邦”与“国家”这对不确定关系过程中的智慧与魄力。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当代人对于复合联邦主义的理解仅剩下了“州—联邦”分权关系,这一理解的缺失注定现代研究的视野必将是片面而局限的。
第二种复合性质的视角是当代“简化者”的视角。称其为简化者,是因为它将“联邦性质”与“国家性质”理解为小共和与大共和的复合,进而缩减成“作为同一批人民的不同代理者与受委托者,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分工与竞争关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把联邦主义概括为“宪法规则下运行的多政府单位体制”,它是“某种可以反复应用于每个单位都受可实施的宪法性法律约束,这种约束基于政府体制中各个不同政府单位的立宪选择而来”②。在奥斯特罗姆看来,所谓复合性质即是“复合共和制”的理论问题:一国之内同时存在两个或多层级的共和国,只要每个共和国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人们就能够在提供不同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共和国之间进行选择;或者说,只要存在相互交叠的市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购买者就可以从竞争的诸多共和国中收获实惠。这种对复合性质的删减收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锐化了问题,反映出当代联邦主义的矛盾及困境,但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复合性质原有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事实上,这种“简化”的过程从美国立宪之前就开始了。如果说孟德斯鸠将联邦共和国的目的从“好的生活”下降到“共和主义的自由”,从而完成了“简化”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缩减工作的第二步则是美国立宪者自己完成的。首先,麦迪逊舍弃了孟德斯鸠关于“唯有小型共和国方能培养公民德行与爱国情操”的论述,强调“大型帝国产生专制,不利于共和自由”,并向人们暗示,只要新宪法有助于遏制专制,就成功捍卫了共和自由,至于培养德行的问题,可作为“题外话”暂时搁置起来。这样一来,得以克服共和国常见弊病的“大共和”方案就少了更多限制。
其次,汉密尔顿努力模糊新宪法的独特性,将其与孟德斯鸠的“联邦共和国”相提并论:“联邦共和国的定义……是‘一些社会的集合体’,或者,两个或更多的邦,结成一个国家……拟议中的宪法,并不要求废除各邦政府,而是把它们变成全国主权的构成部分,允许它们在参议院内有直接代表权,允许它们保持若干独享权力,保持非常重要比例的主权。就这些词的合理含义而言,这与联邦政府的观念,完全符合。”他似乎毫不理会孟德斯鸠的原意,哪怕联邦共和国在法文原稿中是“由诸多共同体构成的共同体”(Unesociétédesociétés)③。换言之,孟德斯鸠不但不支持联邦主义者的复合联邦主义,还站在反联邦主义者同一战线上反对将权力伸向每位公民。那么,汉密尔顿为何还要一次次固执地援引《论法的精神》中关于小共和国的论述呢?原因只有一个:缩减联邦的定义,即便在背离联邦原则的情况下,拟议中的宪法也能作为联邦的一种新模式为大众所接受,并使之得以保存与延续。当代人对于复合联邦主义的“简化”理解与立宪者一脉相承。这样的简化对于联邦主义的原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降低目标是为了更容易实现目标,缩小人们的视野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甚至,我们说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精简原则、不断降低门槛,从而轻松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也毫不为过。
五、复合联邦主义的效用与危机
立宪者期盼“联邦”与“国家”的复合能囊括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部优势,而不带有它们的任何缺陷。如果这一“复合体”既有高效的执行力,又保留区域自治所带来的自由,岂不皆大欢喜?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复合体或折中做法,比起所要仿效的两个“极端”,显得不够稳定。单纯也罢,复合也罢,都伴随着瑕玷,以至所有的抉择,可以说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9]。在享受复合所带来的好处时,同样也要承受它的劣势。
复合联邦主义相较于之前的邦联,其优势体现在强大的行政权与执行力上。一美元背面白头海雕嘴中的绶带上写着拉丁文格言“EPluribusUnum”(合众为一),海雕头顶上象征13州的13颗五角星对此作出的释义是“合众州为一国”。事实上,该工作在《邦联条例》通过时已经完成,新宪法所要真正推进的是“合众人为一国”。此中的差别如此鲜明,难怪反联邦主义者从宪法“序言”的开头——“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中就嗅到了单一制的气息:
含铅较高的铜锍在后续冶炼工序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会带来阳极板电解过程钝化、阴极铜中含铅超标及阳极泥产率大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业内均普遍认为铜闪速吹炼对杂质铅的脱除能力很有限[10],但学术上缺乏对铁酸钙渣型铅脱除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能有效指导高铅铜锍闪速吹炼的实际生产。
他们有什么权力说,我们,人民?我对公共利益的热切渴望,还有我的政治疑惑都让我不得不问一句,谁授权他们用我们人民的名义,而不是我们各州的名义来说话呢?各州是邦联主义的特征与灵魂。如果各州不是他们订立契约所成邦联的一部分,他们就只能是由所有州人民构成的单一制政府的构成部分。[10]
联邦主义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联邦政府不能将自己的立法直接贯彻到公民个人,各州政府就可轻易中断贯彻立法的进程,最后整个联邦会因缺少强制力与执行力而全面崩溃。所以联邦政府必须像州政府那样,拥有同样的手段及权力,采纳所有的办法,直接应对公民个人的希望与担心[4]。立宪者不仅要延伸权力,更要说服反对者“权力是安全的”:如果说有力的执行权(Energeticexecutive)不总是好的,那至少软弱无力肯定是不好的;强大的行政权并不像反联邦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都属“君主制的遗迹”,它可以在保持强劲有力的同时亦忠于共和政府的原则;也就是说,拟定中的宪法所具备的执行能力是可以“共和化”的,它既有积极的效力又符合共和自由原则[11]。即使立宪者真切地希望能“通过反思和选择,而不是机遇与暴力,来建立良好的政府”,他们也不得不在必然性(Necessity)面前学会优雅地低头。在某些关乎国家存亡、制度兴衰的极端状况下,人们的行动往往并非由于特定的道德目的或对某项制度设计的偏爱,而是当务之急下不得不为之,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就是“出于饥馑而非野心”[12]。更为重要的是,立宪者为获得有效的执行力而在共和允许的范围内向必然性屈膝,这一过程让他们学会了如何运用“主动选择”以无愧于“共和国公民”的称号④。简言之,新联邦的建立因事出必然而成就其事业之伟大,因把握“主动选择”而享有其行动之高贵。
复合联邦主义相较于之前的单一制国家,其优势在于保留了次级共同体的自治权力,从而为共和国公民的成长创造自由空间。塞缪尔·比尔在《创建国家》一书中提到了宪法范围内保持州政府活力的三大理由[13]:一是共同体的需求。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中的人们会产生一种对政府的自然的亲近感以及对法律的自愿服从。更重要的是,一个积极运转的州政府能使选民在政府组建的过程中真实感受到自身的参与。代议制也因此变得切实可行起来,代表们不仅代表“理性”,也可以代表民众的“习俗、情感与利益”。如果布鲁图(Brutus)⑤看到新联邦以传统“联邦”的方式成功解决民主共和国所遭遇的困境,他或许会反过来说,“人类自由与幸福的朋友们啊,请赞成这一宪法吧!”⑥
二是实用的要求。联邦主义者很清楚,无论是客观条件的便利或是情感的需要,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州政府永远优先于联邦政府:州政府与人民的依赖关系更为直接;州政府对个人影响力更强;州政府拥有更多可施行的权力;人民更偏爱与支持州政府;州政府的措施更少失败或遭受抵制[4]。对于联邦而言,只要州充满活力,联邦就洋溢出健康的色彩;只要分权关系(无论是地方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上下两院或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在次级共同体中运行良好,就意味着整个联邦的复合性质已得到了最充分的贯彻与体现。
三是因自由之名。反联邦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曾说过:“我牢记于心的第一件事是美国的自由,第二件事才是各州合众。”另一位反联邦主义者梅兰克顿·史密斯甚至愿意为合众而牺牲掉除国家自由之外的一切事物,因为对他而言,没有比牺牲国家自由更大的不幸了[10]。自由是政府的目的,保护国家自由即是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这一目的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已经深深烙印在美国立国精神当中。可以说,自由的实现仰赖于州的自治与教育功能:作为联邦大共和的缩影,州不仅是一种政制,也是一所公民学校。在这里,年轻人学会谦卑、学会虔诚;学会友爱,学会包容;也学会努力,学会成功。共和政府与自由宪法的支柱、生命与灵魂在这里奠定。复合联邦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借助小共和国的力量,不断提升美国公民的品位及能力,最终形成优良的习惯,为共同体注入健康的公共精神[14]。
我们在关注复合联邦主义优势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复合性质所存在的缺陷。如卢梭所说,“使社会制度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社会制度的滥用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些缺点”。美国复合制度的缺陷正是联邦主义自身悖论所在:强大抑或自由;制约抑或平衡。
首先,州—联邦的共治框架中,州的自治地位正受到侵蚀。虽然宪法第十修正案明确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但在执行中,联邦的列举权往往因下列两种原因而发生僭越:某些州内部的事务,如果在国家层面处理效率更高,就应该由联邦政府接管办理;如果州的政策不能关照弱者,同情大多数民众,那么这个责任就应该由联邦来统一负责。事实上,这种趋势所否定的不仅是宪法的权威,更否定了美国政制得以自由,并成功保存联邦性质(Federal)的权力基础——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由各个州让渡的,无论从经验上或是逻辑上来说,州永远是联邦政府的前提。就“效率”而言,各州可通过区域合作等方式予以改善;就“同情”而言,这本身就不属于政制范围的问题,联邦权力并不能因为受宪法列举权保障就随意将触角伸向任何一个挑起民众正义感、同情心的领域。对弱者的同情更是无法换算为宪法权威之来源的[14]。
再次,司法审查权表现得过于积极与能动。汉密尔顿在评论“三权分立”时并不认为司法权或最高法院有能力干涉其他部门,美国宪法对联邦法官任命的特别规定(由总统任命,而非人民选举,法官终身任职),也表明了将司法从立法、行政等政治过程中隔绝开来的决心。而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提高联邦司法部门与另外两个政府部门相抗衡实力的同时,逐步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地位:对国会立法是否合宪拥有最终审查权,即司法审查权。该判决结果在此后的高院审判中被频繁引用,达数百次之多。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对司法僭越立法权再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会议席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一个由国会自行解决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司法问题。首席大法官沃伦以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一款“法律的平等保护”来论证最高法院受理该类诉讼案件的正当性,打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司法能动的第一枪。作为一种曾经以至高道德约束力来赢得公众信任的权威,最高法院不再恪守“政治问题回避原则”⑦,那扇通向“政治棘丛(Political Thicket)”的大门[17]被打开了。已有的法律规则及其推理形式已经无法为司法部门提供行动的正当性,它更乐于“沉浸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以政治家的判断替代自己的判断。
作为同一事物的两种面相,强大的行政权与执行力一旦滥用,共和国的自由便岌岌可危。同样,分立的权力一旦陷入彼此无法制约的失衡窘境,整个联邦便寸步难行,甚至面临内部崩塌的危险。
六、结语
美国人以复合的方式,重塑了联邦主义的内涵。从当时的理解来看,立宪者称得上是“国家主义者”,反对派才是真正的“联邦主义者”。而历史的戏谑之处则在于,“欺世盗名”的立宪者因其变通转换、审时度势终获胜出。复合性质使联邦主义既诙谐散漫,又冷峻严酷,仿佛集两个不同人格于一身,而这恰恰就是自然之道。它扩大了“共和国的半径”,赋予其自我延伸、自我修复的神奇能力。在此后美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僭越”事件(三权间的僭越、联邦权对州权的僭越)中,联邦主义一次次回到“主动选择”的原点:“为什么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方妥当适宜,方恰如其分?”[4]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追问美国政制的“原始意涵”,试图从中找到值得现代效仿的精神价值时,我们必须牢记:历史不提供范式,它只赋予建制者灵感;最佳的政体构制并不存在,唯有多加审慎,治国者才能在驾驭不确定的紧张关系中,避免无意间推进与建国精神相反的目的。
注释:
①马丁·戴尔蒙德,师承列奥·施特劳斯,其作品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过世后由其学生编辑整理出版,命名为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 Will Admit。但其联邦主义研究“切实恢复了美国建国先父们,尤其是麦迪逊及《联邦论》其他作者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丹尼尔·伊拉扎语),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之前,他是联邦主义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
②[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原文翻译为:“反复应用于每个单位都受可实施的宪法性法律约束的政府体制中各个不同政府单位的立宪选择。”
③关于联邦共和国的定义,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原文如下:Cette forme de gouvernement est une convention par laquelle plusieurs Corps politiques consentent à devenir citoyens d’un Etat plus grand qu’ils veulent former.C’est une société de sociétés,qui en font une nouvelle,qui peut s’agrandir par de nouveaux associés qui se sont unis.对该原文的阐释,详见Martin Diamond,The Federalist’s View of Federalism,in Essaysin Fedralism,pp.30—31.
④ Saving the Revolution,pp.173—174.,Paul Peterson,Federalism at the American Founding:In Defense of the Diamond Theses,Publius,Vol.15,No.1.(Winter,1985),pp.30.
⑤反联邦主义者也常常以古罗马名人作为笔名,如布鲁斯(Brutus)、加图(Cato)等。
⑥Brutus I,New York Journal,18 October 1787,in Kaminski and Leffler eds.,Federalists and Antifederalists,Madison:1989,pp.13.
⑦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4页。“政治问题回避原则”指在司法实践中,某些案件虽然可以由法院管辖,但是这种司法介入可能会与立法或行政机构发生冲突。因此,法院就可以认定它们是“非司法性”案件,予以回避。
[1]周顺.前现代联邦主义传统:圣约与联盟[A].比较视野中的现代国家建设[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2.
[2][美]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论[C].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5]张立平.美国政治与选举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Martin Diamond.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the American Idea of Democracy[A].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WillAdmit[C].VA:OIEAHC,1993.188—189.
[7][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8]William Riker.Federalism:Origin,Operation,Significance[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4.
[9][美]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0][美]赫伯特·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Charles R.Keslered.Saving the Revolution:The Federalist Papers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M].Michigan:The Free Press,1987.
[1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3]Samuel Beer.To Makea N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Press,1993.
[14]Martin Diamond.As Far as Republican PrincipleswillAdmit[M].WashingtonD.C.:TheAEI Press,1992.
[15]邹平学.美国总统立法否决权述评[J].外国法学研究,1988,(2):17—23.
[16]王希.原则与妥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Bernard Schwartz,Stephan Lesher.Inside the Warren Court[M].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