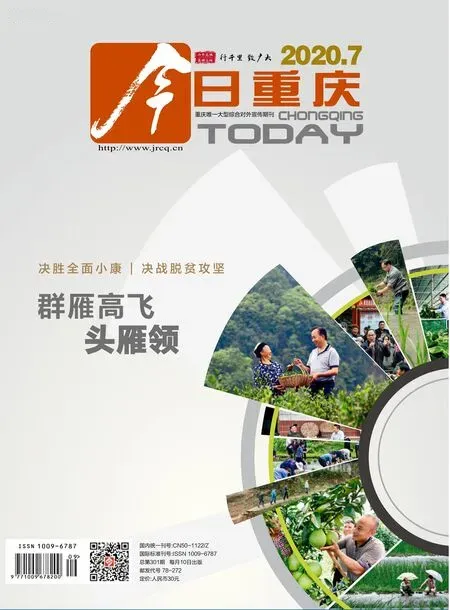李一凡:隐藏在业余状态
◇ 文 / 本刊记者 周瑞丰 ◇ 图/ 受 访者提供
◇ 文 / 本刊记者 周瑞丰 ◇ 图/ 受 访者提供
他原本是不喜欢拍电影的。
“那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很多设备又要拉赞助,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1986年,原本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习画的李一凡,阴差阳错迈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
在北京、在中戏的日子,让他眼界大开。
似乎顺理成章,毕业就到了广东省群众艺术馆。可四年后,他选择了回到家乡重庆。
不喜欢,但却再一次阴差阳错与电影结缘,这缘于2001年与导演施润玖的一次交谈,后者曾拍摄《走到底》等影片。“在那次交谈中我得知,现在数码技术已解决了很多问题。”
李一凡和朋友合资买了台索尼150p的小摄影机,开始了纪录片之路。
2002年,李一凡和朋友鄢雨前往奉节拍摄纪录片《淹没》。片子的拍摄和剪辑,各自花了一年时间。他试图通过拍摄搬迁的过程,揭示人性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被淹没的过程。

《淹没》的剪辑过程,深受安东尼奥的纪录片《中国》的影响。“拍摄纪录片时,很多人会容易情绪化,但是安东尼奥的克制以及理性、客观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片子一点都不滥情。”
影片很快获得了各个国外电影节的青睐。去柏林电影节领奖的那天,快40岁的李一凡一点也不激动,“我只是解决了自己想去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实现了什么电影梦想。”
纪录片没有剧本,拍摄过程中,需要导演有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表达我自己对现今世界的一个看法,拍纪录片是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我的好奇心引导我去了解和发现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奇心把我引入了一个黑洞,可以不停地去了解以前不懂的东西,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对于我来说有更大的意义。”
虽然拍摄很辛苦,但李一凡却一点不觉得累,甚至感觉是在玩耍。“学艺术的人有一个优势,他们也许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哪天是在玩,哪天是在工作。因为喜欢,所以就有不断去探索的欲望。”
《淹没》之后,李一凡再次回到奉节,拍摄《乡村档案》,流水般记录奉节乡村的多样生活。“乡村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就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没有复杂的语言,画面单纯、坦率。
在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李一凡有了区别于纪录片导演的另一个身份:大学讲师。
他教授录像艺术。他说自己一直以一种业余的心态生活,不管是做纪录片,还是当讲师。“我喜欢保持一个业余的状态,认真做事,跟着自己的心去做。其实艺术到了现在,技术已经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的看法。所有的艺术都不是艺术,是人生。”
李一凡“稳坐”重庆。“我没有去外地拍摄的打算,就像《百年孤独》里的村庄也可以诉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与文化一样。在重庆,我也可以拍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剪辑《乡村档案》时,李一凡的助手对拍摄出来的农村没有“土”的感觉大惑不解。“当有了国际视野和当代视野时,电影又怎么会土?电影和小说不一样,电影是具体的,做视觉艺术一定是落地的,落地在一个点上。这个点的选择就在于你的修为了,如果你有国际化的视野,那这个点就是一个世界。”
李一凡,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生活、工作于重庆。与鄢雨合作纪录片《淹没》,2005年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掏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作家协会大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大奖、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大奖“青铜奖”等多项国内外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