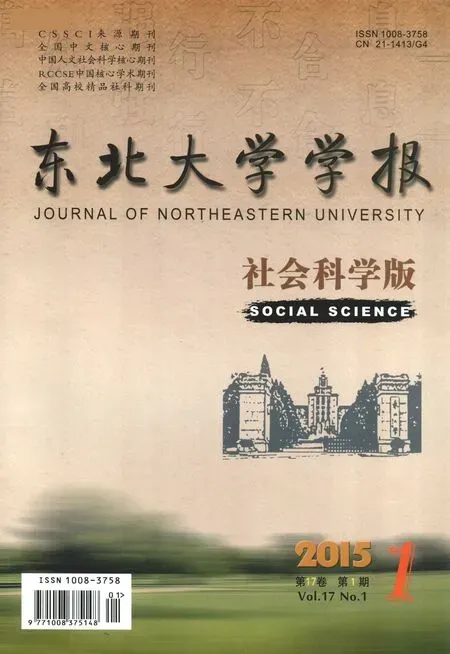从抽象理性到生存理性----试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从抽象理性到生存理性----试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李海峰1,宋成1,王现伟2
(1.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2.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摘要: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不是偶然的,而是和西方人对理性的追求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以孤独个体为特征的理性形象。这种形象随着科学的产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存在论基础。生存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要告别理性,而是意味着追问理性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理性产生和衰落过程的追溯表明,理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追求一种可以解释的合理性生活。生存论的出现表明,西方人开始认识到现实存在对人的理性存在的在先性,从而企图从现实出发重构一条走向理性生活的道路。
关键词:上帝; 理念; 实在; 理性; 确定性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1.003
收稿日期:2014-06-28
作者简介:李海峰(1964-),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宋成(1982-),男,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王现伟(1973-),男,河南洛阳人,洛阳师范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1-0014-05
AbstractFrom Ration to Existential Ration The existential turning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s not accidental bu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sterners’ pursuit of ration. From the ancient Greece, the westerners set up the rational image of the lonely, which lost its original existential founda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The appearance of existentialism does not mean the loss of ration in the western society;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way of inquiring into rational life has changed. Looking back on the occurrence and decline of 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veloping ration is to pursue a rational life which can be explain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existentialism, the westerners began to realize the pre-existence of real existence to rational existence and strove to reconstruct the path to rational life from reality.
---- On the Existential Tur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LIHai-feng1,SONGCheng1,WANGXian-wei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022, China)
Key words:God; idea; substance; ration; certainty
自柏拉图以后,西方哲学一直把理念当做真正的实在。当柏拉图的理念演变成为上帝形象的时候,上帝就取代理念充当了解释一切的终极因,满足了人们对事物的确定性解释的内在渴望。然而,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当上帝形象逐渐变得模糊之后,西方人就不得不从人自身的生存去重新理解世界的确定性,以对人类的现实生活给出有意义的安排。所以,从生存论出发,重新寻求对客观性的解释就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努力方向。
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如何建构一种公共理性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要谈论陌生的他者、谈论交互主体性理论?要明了这一点,就需要对西方人形成这种观念的背景进行一番梳理,以此去理解“上帝死了”到底对西方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也试图去理解现代西方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确定性的需要。
一、 观念论:抽象理性的起源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的历史开始于柏拉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就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而是说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影响了几千年的大哲学家,他个人的思想几乎奠定了西方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思维模式。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为柏拉图的思想做注脚。”[1]在柏拉图的哲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应该是观念论。根据这个理论,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现实世界以外,我们生存的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不可见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真、善、美的完美世界,即理念世界。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称做“圆”的事物中就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在一个类似于天国的理念世界中“圆”却无疑是完美的。这样一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后人对“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存在”、“什么事物是完美的存在”等此类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不仅中世纪的哲学家们进行了认真讨论,而且后来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也把这些问题作为关键性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柏拉图哲学的另一大影响来自于“洞喻说”。在柏拉图所设置的“洞穴情景”中,被缚了双手的坐在椅子上的人看见的是什么?是墙壁上的影子还是真实的人呢?也许我们会说,他看见的当然是影子,并且影子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真实人的存在。但是,柏拉图引导我们做进一步的设想:如果走进来的人只是一个小孩,假装成年人手里举着一个“面具”走过, 那么坐在前面的人能否发现他所看见的原来并不是“人”的影子, 而只是“面具”形成的影子? 很明显,那些坐着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所看见的影子到底是否是“真实人的影子”; 相反, 他们只能凭着被给予的“回忆”, 通过查看记忆中的影像来作出判断, 但是这个可见的影像到底代表了什么却是未知的。 换句话说, 实在本身是否就是观察主体所看见的样子, 人本身是无法决定的, 他只能尽力按照他所看见的来说话。
在这里,柏拉图的隐喻展现出的主体本质上是一个“孤独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类的成员孤独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同伴可以交流,只能依靠自己的可见物和回忆来判断。即使可以交流,每个同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比其他的人说出更多。所以,在那些远离这个场景之外的人们看来,他们之间任何激烈的争论都只能是一些意见。从这个地方开始,柏拉图设置的“孤独个人”的理性形象,就塑造了西方人面对自然的一切沉思者的经典形象。合乎这种要求和规范的沉思者,在思维方式上都像离开了人群的鲁滨逊一样,面对问题只能独立思考并凭借自己个体的理性来解决,没有任何向陌生他人求助的可能性。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比如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较近的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梅洛-庞蒂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等,我们都可以从中看见一个孤独个体在沉思世界的形象。
从思维方式上说,柏拉图的观念论对人们生存的世界进行了区分,使人们形成了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实际上也是现象界与实在界相区分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对世界的判断,我们就会很合理地认为,任何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都必然对应一个本真的存在,因此人应该追求真理。柏拉图的“洞喻说”则进一步表明,人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只能以一个“孤独者”的身份进行,而孤独者的形象,也就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经典形象,这种形象的设置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二、 从神学到科学:抽象理性的普遍影响
尽管在西方哲学的开始之处,曾经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历史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这就是“神学”统治的中世纪。据我们今天可见的资料,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为什么会倏忽之间跌落入一个神学的境地,以致在我们看来西方世界竟然不过是被假设的“上帝”统治了千年时间?科学史的研究表明,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和逻辑也没有发展到超过亚里士多德的水平[2]。事实上,如果认真地比较基督教的“上帝”和柏拉图的“理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神学的发生和柏拉图所展现的思维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在柏拉图看来,现实的世界没有真实的东西,只有在理念的王国中才有“绝对的”的真相。显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这种理念世界的景象和原因,则理念所要求的至善和完美就必然会引导自身进入神学的领域。就此而言,西方神学的出现本质上也是西方人的理性主义倾向的产物。
其实,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更早的一些哲学家已经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偏向,比如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概念就表明了这一点。“存在”一词不仅仅作为对可见物的谓词而提出,而且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终极因而提出,这样的“存在”作为“终极因”的代名词,其实也就是上帝的代名词。这些概念表明,抽象理性主义追求的“对象”往往都是抽象物,是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难以找到的东西[3]。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对存在的终极因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寻求,以及对可见物的不信赖,就很容易导致对作为“至善”的神的信仰。总之,一旦“上帝”在人们的心中被制造出来,他就可以从精神上控制和引导人们的生活。对于上帝,如果我们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们也许将会被中世纪基督徒的真诚所感动。关于“上帝”的本性,奥古斯丁这样说,“你是永远地生活着,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死亡,在世纪之前,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你所创造的万物的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原,一切变和不变的权舆,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4]。从哲学的角度看,这里的上帝其实就是永恒的存在,是一切东西存在之为存在的终极原因。如果联系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规定,我们也许会发现,除了语言形式上的“上帝”名词之外,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和他们的先辈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
对西方人来说,上帝的存在不仅充当着解释世界的方便方法,而且赋予了生命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心理上的寄托和依赖。赖欣巴哈在解释传统哲学不断犯下错误却总达不到科学的程度的时候说,哲学家“过于喜欢牺牲真理去迎合作出答案的欲望,牺牲明确性而屈服于用图像来说话的诱惑;他的语言缺乏精密性,而这正是科学家避免犯错误的罗盘”[5]4。为什么这样?因为人们的生活需要确定性和安全感,而一个不真实的转瞬即逝的世界却不能够给予人们所需的永恒的依赖。所以,赖欣巴哈得出结论说,“当科学解释由于当时的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概括而失败时,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5]11。可见,正是为了这种确定性和普遍性,人们在匆忙中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根据他的说法,只有等到现代逻辑出现之后,哲学通过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学转向才真正进化为科学。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对于不少普通的人类个体来说,宗教神学的积极功能可能就在于,能够通过解释世界给予人们的心灵以安宁;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物质上贫困的人们来说,通过上帝也可以获得一种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平等和满足。因为,借着对上帝的信仰,一切自然事物和社会事件都可以给予合理性的解释,尽管现在看来,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虚假的东西。
对于“上帝”在存在问题上的解释性作用,我们还可以例举笛卡儿来说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哲学思维的新方向,自此以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对世界进行解释。在笛卡儿看来,没有经过理性论证的一切事物都不能被确认为“真”,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笛卡儿通过沉思,得到的第一个确认无疑的事实就是“我思”,就是说思想本身这件事情不能再怀疑。因为,即使我怀疑“我”在思想,我也无法怀疑“怀疑本身”是一个思想上的事实,所以思想本身是不可怀疑的。接下来,笛卡儿说,在他的思想中清楚明白地看到了上帝的存在,而上帝则可以作为担保人保证其他万物的存在。这样,笛卡儿就由“我思”推导出“我在”,并把曾经被他怀疑过的东西又通过理性还原回来。在笛卡儿的哲学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权威性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了,因为他并没有以上帝存在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而是以“我思”作为出发点,但是显然,笛卡儿还得借助于上帝的存在才能完成他的论证。这说明,在从中世纪到近代转换的时代背景下,笛卡儿的思想中还保留着对上帝的某种隐蔽的依赖。
理性主义思维除了对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外,在现代科学的产生中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像笛卡儿、伽利略、牛顿,以及莱布尼兹、爱因斯坦等这些大科学家,在深入研究自然现象的同时,他们的心中依然保留着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比如,培根在《新工具》中曾经写道:“按照上帝的话说,自然哲学实在既是医治迷信的最有把握的好药,同时又是对于信仰的最堪称许的养品,因为宗教是表现上帝的意志的,后者却是表现上帝的权力的”[6]。伽利略也认为,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去理解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敢擅自去揣测上帝的圣意[7]。爱因斯坦在和玻尔争论量子力学问题的时候,曾经以“上帝决不会掷骰子”这样的理由来为他的观点辩护。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第一,上帝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植根于西方人的血液中;第二,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心中的上帝实际上就是“存在”本身,或者说就是“大自然”本身。因为大自然的奇妙所显示出来的“先定的和谐”通过人类的理性能力很难给出完整的解释,所以保持对大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敬畏,是所有这些理性人的一个很深的情结。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一次引用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8]。
以上分析表明,从漫长的中世纪开始至近代社会,无论是基督教神学对上帝与理性关系的反思,还是后来启蒙理性之后现代科学的萌芽,抽象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 生存的现实性:重建人类理性的基石
19世纪后半叶,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明确宣布“上帝死了”,要求“要重估一切价值”。自此之后,“重估一切价值”这一令人振聋发聩的语言就经常被人们提起,并深刻影响了现代哲学的发展。这是因为,西方哲学一直把上帝等同于无所不包的“存在”来理解,那么,当作为存在根基的“上帝”如同偶像一般坍塌的时候,“存在”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必真的意义。“存在”既然已经不在,那么人们的“生存”当然也就失去了其必然的目标和行动指南[9]。
我们知道,西方的中世纪甚至包括近代社会,长期笼罩在基督教统治之下,西方人对基督上帝的信仰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实生活的变换,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精神信仰的影响。根据马克思关于宗教起源的说法,大部分宗教的产生都是源于人们在现实中产生的需要,生活中苦难的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来缓解肉体的痛苦。因此,如果现实中的人们能够找到某种替代品可以缓解人们的痛苦,那么上帝信仰的衰微就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现实的情况是,当人们一步步走过漫长的中世纪,伴随着科学的诞生、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就可能希望和上帝平起平坐,甚至取代上帝而给自己加冕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实际上,从笛卡儿时代到康德时代,虽然人们依然还保留着对上帝信仰的依赖,但是“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后来,尼采明确宣布了“上帝已经死了”这一思想史上的事实,“上帝”一千多年的精神统治终于在理性的强攻下倒塌。当然,尼采哲学并不仅仅是作出了这样一个宣告,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充分发现并强化自己的意志,摆脱对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渴望,能够从现实的生存出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说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转向现代生存论哲学已经成为一种明显趋势,由形而上学实体观所打造的抽象理性已经逐渐被现代哲学所开创的生存理性所取代,而无论这种转向是通过关注现实还是通过为个人的生命体验辩护来实现[10]。
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理论相互交锋,最终在20世纪现代哲学精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黑格尔一般被称为是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近代的哲学精神在他的体系中体现得最为完美与精致,但是对近代哲学精神进行最后一次挽救尝试的人是胡塞尔。胡塞尔试图通过对科学认识的基础进行重新审视而达到对确定性的寻求,使得人们相信理性还是可以信赖的,理性依然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支撑。因此,胡塞尔对意识的内部构成,对陌生他者的存在合理性,对交互主体性理论进行了艰苦思索。胡塞尔虽然是生活在20世纪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哲学路线还是延续着笛卡儿、康德所代表的近代路线,因为他想通过“本质直观”与“先验还原”达到对整个世界的本质认识,进而能够为现代科学理论提供坚实的理性基础。当然,这只是胡塞尔的一厢情愿,最早起来反对他这种努力的人就是他的学生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所揭示的意识领域并不是理性的坚实基础,意识只能以此在的生存为前提并受人们的存在方式的规定,所以存在才是理性的最终基地。海德格尔与尼采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尼采呼吁人们强化自己的意志勇敢面对生活,海德格尔则指出抽象理性根本无法为人提供生活的最后根据,鼓励人们要敢于作出“决断”,不要沦为“常人”,不要被“常人”拖着走。海德格尔说人要“去存在”,通过“去存在”去实现自己的存在方式。这实际上是说,人在本质上是未完成的存在者,人如何存在取决于自己的存在方式本身,人的命运不是由某种抽象的力量来安排的。可见,正是在海德格尔这里,哲学完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到现代生存论哲学的转向。
总之,无论是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还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它们都是以理性所认定的某种抽象物作为标准来要求人们的现实生活。这种传统理性虽然最终促进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也曾经在其他一些时期(比如中世纪)严重地限制了人类的自由。这一事实并不说明人类追求理性生活的目标设定是错误的,而是说当时人们的理性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中。形而上学追求的是人的本能倾向,人本能地就想找到一种普遍性标准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根据。就此而言,现代西方哲学通过生存论转向,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人类的现实生活,从生存本身来安排人类的理性,标志着人类理性正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64.
[2] 理查德·奥尔森. 科学与宗教[M]. 徐彬,吴林,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19.
[3] 王天成. 哲学理性的范型转换----从认知理性到后认知理性[J]. 社会科学战线, 2001(1):59.
[4]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812.
[5] 赖欣巴哈. 科学哲学的兴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4-11.
[6] 弗兰西斯·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63.
[7] 伊安·巴伯. 科学与宗教[M]. 阮炜,曾传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32.
[8]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220.
[9] 孙正聿. “生存论转向”的哲学内涵[J]. 哲学研究, 2001(12):8.
[10] 邹诗鹏. 生存论转向与当代哲学转型[J]. 哲学研究, 2001(12):20.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