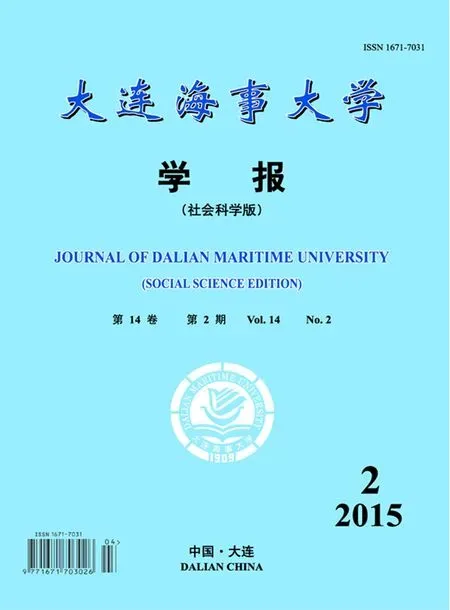从发现到遗忘
——文学风景的产生与遗失
王卫平,陈广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从发现到遗忘
——文学风景的产生与遗失
王卫平,陈广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风景描绘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它却越来越少。通过对于风景的探讨,探讨什么样的风景才算是文学意义上的风景,以及文学中的风景到底是如何产生。首先它必须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风景,然后经过作家的审美观照,并以细微的感觉体味出它的深层意蕴,最后要经过一番哲理提升方成文学风景。在钢筋水泥日渐锁闭人类期求远望的双眼的今天,将风景在文学史、文化史中记录在案是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指出新世纪文学中风景的遗忘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同时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大计的现实问题。
风景;文学风景;发现;遗忘
风景,顾名思义,就是风物和景色,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风物和景色才算是文学意义上的风景呢?显然,不能把风景与大自然画等号,这是肯定的。但说风景是大自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大自然包容万物,当然也包括风景。但是,并不是所有自然景物都可以称为“风景”,只有经过了作家的欣赏和感受过的风物和景致才是文学意义上的风景(有人会问了,那旅行观光时看的不就是风景吗?没错。不过,从文学意义来说,把它叫做“原风景”)。它包含了审美主体的主观映像,或者说是主体意志的投射,这里面承载着作家独特的情绪感悟。凡美都是“抒情的表现”,都起于“形象的直觉”,并“不在事物本身”[1]。文学是对于美的创造,如果没有美的表现,文学也将失去意义。人们喜欢看风景是因为它美,它不美,就会对它不屑一顾。风景使人愉悦,让人体悟,它总会包含一些实物之外的东西,让人感慨,甚至得到哲理性的启示、精神上的升华。对风景直观感悟,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主客体间的神圣交融。
从一般意义上说,风景一词的指称范围小于大自然,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它的反面,即风景不仅可以包含自然景物,同时它也包含人和其他事物。风景是人与物、物与物的一种奇妙组合。它是一个空间,是立体的、多维的。所以本文所论述的风景不仅仅指自然风景,同时也把一些与人物活动相关的场景物事也包括在内。
如题所示,文学中的风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首先它必须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风景,然后经过作家的审美观照,并以细微的感觉体味出它的深层意蕴,最后要经过一番哲理提升方能成为文学风景。
一、现实世界中的风景
文学中的“风景”到底源自于哪里?这看起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风景当然首先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文学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的事实,那么文学中的风景当然也来源于客观存在的大自然。“自然美是客观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因此,艺术作品描绘自然美,也必须符合客观存在的自然美的真实,只有以客观存在的自然美的真实为基础,才能产生世态美的真实性。”[2]346从文学产生的那一天起风景就已经开始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中国文学中从来就不缺乏风景描绘的传统,如果有人稍加留意,就会很轻易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对于风景的言说几乎可以构成一部文学风景发展史了。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风景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也是得到广泛认同的。法国诗人里尔克就认为,相对于“人”的发现,“风景的发现恰恰是更重要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紫式部),不写风景就似乎无法运作文字”[3]。风景之所以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风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并且是人与自然接近的最直接方式。原始人类生于自然中、长于自然中,自然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作为“主观力量对象化”的文学的建构当然也就少不了自然风景的参与。中国古代文人们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然不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人事方面的经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遍游名山大川,寻求与自然的契合。他们从来都是漫游天下,饱览山河,绝少博尔赫斯式的闭门造车。日本俳句诗人们也大都喜欢远足,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的大半生就都是在旅途中漂泊度过的。他们观朝阳,看落日,走泥途,行山路,听闻鸟语,遍嗅花香,赏万般风景,并从中探求到了生命的奥秘。
就中国新文学来说,那些以描写风景见长的作家也大都是长期与大自然亲近的人。沈从文的少年时期就一直生活在湘西那片神秘又清新的大自然中,拥抱大自然是他童年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成年以后,他也反复申明是自然长养了他,而且自然中的生活让他学到了比书本上更多的知识,给了他书本上学不到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另有很多新文学作家也都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比如早期乡土派的王鲁彦、许杰、蹇先艾、彭家煌等人,他们各自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故乡风景。上世纪30年代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见出东北地方的地域色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并把童年风景深深印在了脑海。丁帆把“风景画”作为形成地域色彩的首要因素是有道理的。[4]虽然“风景画”不等于风景,但没有风景必定不会有“风景画”,作为“自然形象”存在的风景是作为审美形态的“风景画”存在的物质前提。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虽然风景来自于客观现实,但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孤立存在。文学中的风景描写是要与现实社会发生一定关系的,这一点从意识形态色彩极端浓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见得最为清楚。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例,“对于《山乡巨变》来说,重要的不是‘环境’,也不是主观化的风景,而是风景与新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5]。周立波是通过风景的描写把“新世界”与“旧世界”的不同,以及新旧转变中那些不能言传的中间状态暗示出来。这就使风景不仅仅作为表现个人意志、抒发个人情感的载体,而且承担了更为重大的社会功用。这时的风景就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实景”,而是经过作家主观过滤后的、与现实社会发生一定关联的并打上一定时代色彩的风景。
二、心中的风景
人们之所以能够从自然风景中探求到生命的奥秘,是因为风景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同时,每个人的心中也各有自己的那片“风景”。这里所说的内心的风景当然指的是人的内在固有的随天性而来的那份胸臆,这份胸臆可以是英雄的豪气,也可以是美人的忧愁,也可以是才子的风雅……文学是“表象世界的表象”,它根本不可能完全再现现实,一切企图再现的努力都将以失败告终,所以对风景的描摹也必然是浸透了主体对于世界的独特体验与感悟。当这种体验和感悟与风景相遇时就会产生“移情”作用,从而使自然的风景幻化为内心的风景,所谓意境者就是以此种方式产生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古诗中最为显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清幽、玄远的境界的产生必以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为前提。所以“艺术境界的显现,绝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为高’。(米芾语)尤其是山川景物,烟云变灭,不可脑摹,须凭胸臆的创构,才能把握全景”[6]。心有境界,方能见诸笔端。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过风景写内心境界的佼佼者,这是《长河》最后一章社戏收锣后的一段风景描写:
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
这片景色当然不是纯客观再现,我们仿佛在社戏散去的场地边缘发现了抬头远望的作者。他就那么一个人静静地举目凝望,眼光到了天末远山,是一种凝重和苍凉,对于美好事物行将逝去的惋叹鼓荡在心胸。似乎每一个心有境界的作家都有一片自己内心深处的风景,这片风景独属于他一个人,几乎形成了他给予读者的标志性印象。比如废名的竹林流水、张爱玲的“绣在屏风上的鸟”,曹禺的神秘不可知的原始森林……这些心中的风景昭示着作家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独特理解与体味,有的甚至带有了些许哲学意味。
正是作家内心的情感、意绪使得作为自然存在的风景具有了美的素质,这是主体对于客观存在进行审美观照的结果。如果没有主体心胸的投射,自然风景也将是一片僵死的草木山石。人们常常说风景“美如画”(这里涉及什么才是“美”的问题,对此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谈美》等书中有专门探讨,可资参考)。“自然景物的形象美观既要‘如画’,就是说要像画里头的景物一样美观。根据这个看法,那画里的景物是比自然界的景物形象和其局面来得美来得好看,因此人们欣赏自然时美的量度,是要符合图画里头的艺术美的标准才算美。”[2]289(引文说的是绘画,但是用在文学上也依然成立)那么画里的风景到底比自然界的风景美在哪里?这是一个让很多人费解的问题。笔者认为,美在神韵,在主体之“意”。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写景者都追求“情景交融”的境界,以使自然美与内在之“意”水乳交融,这样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语言是一种表现能力有限的交流工具,有时候语言并不能尽意,所以借助风景所达到的“含蓄蕴藉”的意境是文学作者们的普遍追求。
人分“美感的人”、“科学的人”、“伦理的人”……每个人都是美感、科学、伦理等多方面的统一体,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即使再理性的人也有感性的一面,所以,自然的风景化为审美的风景才有了可能。感性使人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心胸,在面对自然风景的时候才会与之互相交流,这种交流用的是各自的直觉,所以才有了千差万别的“内心的风景”。
三、细微精妙的感觉
“美感经验”始于直觉,但并不是说人有了感性的一面就可以成为艺术家,因为风景的发现需要一颗敏锐多感的心灵,特别是细微精妙的感觉力。曹文轩对艺术感觉做了看似极端却又相当合理的强调:“没有感觉就没有思维,没有感觉就没有任何科学和艺术。”[7]特别是在艺术活动中,没有感觉是创造不出感人至深的作品的。而风景更是需要创作者和欣赏者来感觉,没有感觉将发现不到它的美,更体会不到无尽的情韵。艾青就是一个相当有感觉的诗人,他可以通过各种色彩给风景以象征暗示的意义。他以灰、土黄等暗淡的颜色来象征旧世界的黑暗与苦难,以红、金黄等明亮的颜色来暗示明天光明的生活。甚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感觉已经成为一种结构的方式。他的《旷野》就是一首完全用色彩搭建起来的感觉结构的诗,而且全部诗意都浓缩在那一派迷蒙的风景中。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创作动机来自于对迷蒙暗淡的色彩的感觉,然后又通过土黄、灰白各种色彩造出了一个迷茫深广的旷野,这个旷野凝聚着诗人对时代、国家的感喟与思索。与艾青同样有诗意感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们,但与艾青偏重于色彩的感觉和印象不同,他们是把生活中的琐细事物作为自己诗歌意象的主要来源,以自己内心的情绪感觉把这些琐细事物收拢到一起,造出一个个精致又有深厚情感蕴含量的小场景。《深闭的园子》通过园子里长了苔藓的小路、门上的锈锁来暗示一个凄清、荒芜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作者那孤独、凄怆的心绪。同样是这种风格的还有废名的《街头》《理发店》、徐迟《都会的满月》等作品。
要发挥风景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光有感觉是不够的,而且这感觉还要精微细腻。有细腻的感觉才能把风景写活,写得灵动起来,才能更好地为整篇服务。世界文坛上有很多写景高手都在细腻上下工夫,如托尔斯泰、川端康成。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也常常见到需要读者用心体会的精微的风景描写。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以细腻的风景描写见长的女作家,比如茹志鹃,她时常能从生活小细节中挖掘出深刻的意义,对于风景的细微感觉当然也使她的作品增色不少。《静静的产院》里给彩弟接生的那个晚上刮起了大风,作者在写风的时候不仅能听到呜呜的风声,同时也感觉到了“汽车声,人声,广播里的鼓动口号声,忽而被风送进产院,忽而被风带得远远的”。正是这些微妙变动的声音让人感到了条件的恶劣,同时也衬出了当事人的镇定与自信。同样对风景有细腻感觉的新文学作家还有沈从文、茅盾、周作人、冰心、贾平凹、莫言等。
对于风景有了精细微妙感觉的艺术效果远远不止以上所说,它不仅仅能够使作品增色,同时可以使风景自身具备某些审美个性,有的甚至能从这个性中见出哲学意味来。曹文轩曾经在百家讲坛说过一句夫子自道式的话“精微之处,深藏奥义”,并在《细米》《天瓢》等作品中实践了这一美学主张。《天瓢》以十几场不同的雨结构全篇,主要故事都发生在雨中。作家通过细腻的感觉将雨与人、雨与现实社会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结合起来,让读者体验出了至情、至爱与至恨。
四、哲学境界的提升
创造境界是很多作家对于风景描写的终极追求。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很多诗都是景与人与情结合在一起,诗人追求的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然而,人们往往有一种误区,认为“情景交融”就是意境,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没错,意境必须要“情景交融”,但是“情景交融”的作品并不一定有意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意境是一个物、情、意三位一体的立体的、多维的审美空间,说“情景交融”是意境的人们往往是只注意到了物和情而忽略了“意”。“意”是什么呢?它就是审美主体的意念、意志,是对于天地宇宙人生的哲学性思考与体悟。“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为作家的“兴趣”和“妙悟”,而在西方文学中它有时候已经形成了体系,比如萨特、席勒等人的创作。
上文说到曹文轩的“精微之处,深藏奥义”,似乎只说了一半,就是前面的“精微”,现在要说的是“奥义”。“奥义”当然是一种对于文学的哲学把握,就风景的描写来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作品可以称为优秀之作,但还不是极品,真正的登峰造极之作是能通过风景的描摹达到对于哲学境界的建构。对于风景,如果“无视它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表达内涵,这样的‘风景描写’也只能是一种平面化的‘风景’书写”[8]。这样的“风景描写”在中国新文学中俯拾皆是,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以及后来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虽然其中仍有不少比较成功的风景描写,像《创业史》《红旗谱》等,但也还只是停留在“平面化的‘风景’书写”阶段,它们没有真正达到文学对于客观世界的哲学表现。真正对风景有了哲学表现的反而是在这之前的“五四”时期的鲁迅等人。“鲁迅先生却与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不同,他注意到了‘风景’在小说中所起着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也是透着一份哲学深度的表达,这才是鲁迅小说与众多乡土题材作家的殊异之处——不忽视‘风景’在整个作品中所起的对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定调作用。”[8]比如他的《狂人日记》《故乡》《在酒楼上》都属于这类创作。“新时期”之后能把风景的描写提升到哲学高度的作家是阿城,他在风景中所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道”。“‘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亦经过老庄提升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两千年来历代哲学家莫不依循着‘道’这一中坚思想进行思考。”[9]而在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把风景作为人与自然合一的最直接方式,阿城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树王》。大火烧山后,肖疙瘩已然身心崩溃,他“在搀扶下,进到屋里,慢慢躺在床上,外面大火的红光透过竹笆的缝隙,抖动着在肖疙瘩的身上爬来爬去”,很有些悲哀。屋内红红火光覆盖下的肖疙瘩已然与外面“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一起“离开大地”。
五、结语:风景的遗忘
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在一步步挤占着乡村的土地,风景也在一幕幕地消失。青年人迁往了城市,留下一些老年人固守着残缺的自然风景。甚至很多青年父母们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不惜一切代价把幼小的孩子也带离了乡村,使他们还在未谙世事的时候就离开了自然的怀抱。在拥挤喧嚣的城市里成长,或许成年后他们会学得一身人际交往的好本领,像他们的父母们当年一样,早早地“成熟”起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然而,当人完全脱离了大自然之后,他就已经很难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五四”时期人们就高喊着“立人”,但是如果都离开了大地,满目尽是疮痍的风景,那么这个“人”该立于哪里?
在钢筋水泥日渐锁闭人类期求远望的双眼的今天,将风景在文学史、文化史中记录在案是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但是“新世纪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为什么在一天天地消失?”[8]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大计的现实问题。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11.
[2]伍蠡甫.山水与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3]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74-275.
[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5]朱羽.“社会主义风景”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意味——从《山乡巨变》谈起[J].文学评论,2014(6):163.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96.
[7]曹文轩.第二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0.
[8]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3):16-18.
[9]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8.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参考文献标注方法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参考文献标注方法采取顺序编码制,各篇文献要按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参考文献的页码一般置于参考文献表中,如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则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文献的序号,并在序号的右上标“[ ]”外注明引文页码。
文后参考文献的书写顺序、标点符号等如下。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期):起止页码.
图书:作者.书名[M].版本(1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年份:起止页码.
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版次).
会议录:作者.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年份:起止页码.
专著中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作者.析出文献题名[C(会议录)或M(图书)或G(汇编)或S(标准)]//专著作者.专著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起止页码.
报告:作者.题名[R].出版地:出版者,年份: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起止页码.
电子文献:作者.题名[EB/OL].(更新/修改日期)[引用日期].http://…….
标准:编者.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年份.
另外,文献作者3个及以下的全部列出,4个及以上的只列前3个,后加“,等”或“,et al”;外文作者姓前名后,姓全部字母大写,名用缩写,不加缩写点。
2015-01-29
王卫平(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angwp57@vip.163.com
1671-7031(2015)02-0097-05
I207.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