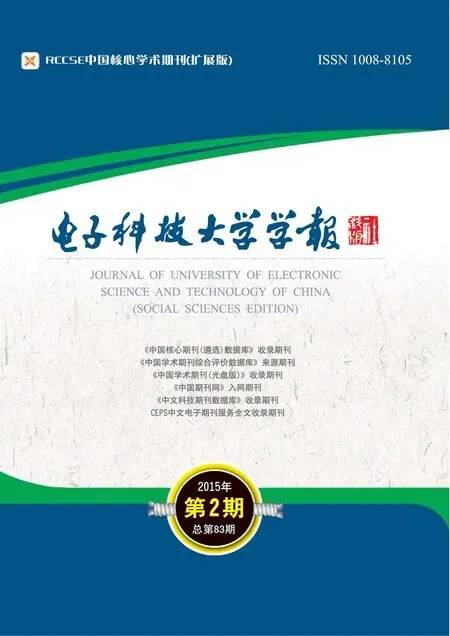七苏木案与暴力性生存竞争方式
□张 彧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08]
比利时天主教修会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在1865年进入中国,主要在内蒙古、河北、宁夏、甘肃、辽宁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土地对于传教活动有很大促进作用,于是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地区大量租赁、购买土地,以信教就可以租种教会土地为条件吸引贫苦农民入教,结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对于晚清时期天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获得土地的过程,教会人士和一些史学工作者做过简单的介绍,但大都言之不详。本文拟以《教务教案档》为基本史料,结合所搜集的一些资料,以教会在内蒙古地区较为典型的购地活动——七苏木案作一较为系统、详细的梳理,以期对该修会在内蒙古地区的购地活动有一清晰的认识,并对这一区域的暴力性竞争生存方式有所了解。
一
七苏木在察哈尔正黄旗(主要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一带)境内。光绪九年(1885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圣母圣心会两次在七苏木购买土地,历经波折终获成功。
教会第一次在七苏木购买土地是通过信教的地商韩大成进行的。从光绪九年起,教会先后共付给韩大成购地款7000多两白银,从署理七苏木佐领印务的亲军校昂晦手中购买了七苏木花桃勒盖52号土地。教会尚未组织教民前往七苏木垦种,与昂晦不和的七苏木护军校达尔玛济尔弟呈控昂晦私卖牧地,经多次审理未能结案。其后教民多次向韩大成索要土地。至光绪十五年,在昂晦同意下,教民到花桃勒盖修盖房屋、垦种土地。光绪十六年八月,七苏木护军校达尔玛济尔弟带领蒙兵100多人至花桃勒盖,将教民房屋、财物、收割的庄稼抢掠、焚毁。[1]505该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官员称之为“察哈尔正黄旗游牧私垦烧粮一案”),山西丰镇厅官员与正黄旗官员共同审理了该案。办案官员要求韩大成、昂晦向教堂退还收取的银两,由七苏木官兵赔补教民损失,教民则被要求从垦种的土地迁出。此判决并未完全执行。光绪十七年,经七苏木蒙官同意,教民迁至七苏木其伦温古茶一带垦种。光绪二十年,教会向达尔玛济尔弟支付了购地款4000多两白银。因山西丰镇厅官员拒绝给教会办理土地契据,达尔玛济尔弟等蒙古官兵又反复纠缠教会,索取银钱。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法国公使施阿兰(Gerard Auguste)出面要求清政府为教会办理土地契据,此后施阿兰又多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相同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山西丰镇厅官员与正黄旗官员再次会审七苏木购地案。在会审过程中,蒙教双方对谁对教民到其伦温古茶垦种负责上相互推诿。关于教会是否曾向达尔玛济尔弟交付过买地银,蒙教双方都坚决否认,称为教会光绪十八九年间赈济受灾所用。会审中教民杨世旺态度强硬,坚决要求划清地界,办理地契。七苏木蒙官完全倾向教民一方,并要求驱逐在七苏木垦种的三成局民人吴殿奎、孟仕仁等两伙民人。会审官员以“此案关系中外交涉,数年之久未能妥办。现据两造均恳了结,自应即照两造供词,将奇伦温果察空闲地十里宽十里长,即与教民划清界限,以杜讼端”。会审官员还定于六、七间月赴七苏木指划地界、刨挖壕沟。至于“霸种”教民地亩的孟仕仁、吴殿魁,会审官员商定,在给教民划清地界后,再行驱逐。其实这次会审不过是蒙教双方共同上演的一出戏而已。传教士刘拯(Rubbens Edmond)给察哈尔都统祥麟的禀呈中泄露了这场戏的内幕:“今蒙大宪派委会同旗厅审讯明白,果有十里长宽有结存案。断令敝堂静候清界,所有该佐领朦胧敝堂之处,姑从宽免。至若该佐领弁兵索取银四千余两,相商为隐蒙愆作为赈济草地蒙民,嗣后再不究撤。”[1]622在地方官员为教民划界后,法国署公使吕班(Dubail Constantin)致函总理衙门称,传教士刘拯灵向他反映,“地方官等尤系察哈尔都统,相助保护,甚为欣颂,该地方官精明强干。”对此他非常满意。
同年十一月地商孟仕仁在派人赴北京递交呈文,控诉丰镇厅、正黄旗地方官接受贿赂,袒护洋教,抢夺民田,请求予以办理。在呈文中孟仕仁叙述了他办理放垦手续、遭教民霸种、带领民户垦种的经过:光绪八年,他与300多民户报垦正黄旗七、八苏木的一块空闲荒地。十一月间他与七苏木蒙官谈妥,蒙官发给他报垦土地(长约30多里,宽约20多里)的印据、地图。光绪九年,他将该报垦土地印据交丰镇押荒局,由其转交丰镇厅备案。之后,他又与山西人赵业、王华楠赴户部办理相应手续。光绪十四年,户部向山西巡抚、察哈尔都统发文,要求丰镇、宁远二厅,如有空闲荒地,迅速申报核办。光绪十六年,“察哈尔正黄旗游牧私垦烧粮一案”发生后,察哈尔都统奎斌将教民垦种土地封禁。受该案影响,他也不敢前去垦种。光绪二十年教民杨世旺等霸种他报垦的土地。他多次禀请旗厅官员驱逐霸种教民,但都没有结果。眼看报垦土地的被教民霸种殆尽,他带领民户前去垦种,多次遭到教民侵扰。二十三年他的佃户刘世功因土地被霸种,自刎身亡。地方官对此置之不理。同年八月间孟仕仁连同其民户被山西丰镇厅官员从垦种的土地驱逐。在呈文中,孟仕仁哭诉道:“法即不及于洋人,而教民之抢夺逼命,官长之贪虐害民,岂俱无法乎?生等生死含冤,哭诉无路,若不据法惩治,必起祸端。”[1]645刘拯灵也向察哈尔都统呈控孟仕仁等侵害教民。法国公使吕班也照会总理衙门称,孟仕仁等在教堂地界内霸种,要求地方官员予以驱逐。总理衙门不得不要求山西、察哈尔地方官员进行调查。
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官员向总理衙门汇报了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旗厅官员在七苏木给教民指划地界的情形:经过40多天的争执,才为教民划定地界。因地是蒙地,全由蒙官指划。划地时因“在洋人意在索地,在蒙古情愿多与”,故此蒙官指划给教民的土地不止十里宽。其后七苏木蒙官又把教民地界外的3块土地划给教民。因此教民所挖壕堑内的土地更是不止十里长宽。在报告中,山西官员暗示可能存在着蒙官收受教会贿赂的情况。同年闰三月山西、察哈尔官员会审孟仕仁京控一案。在会审时孟仕仁已不如京控时那样理直气壮[1]703。教民杨世旺等则非常强硬,不肯退出七苏木蒙官划给的土地。在会审期间,三成局地户乔旺等人赴察哈尔都统衙门控告教会抢夺他们的土地、烧毁他们的房屋,要求查办。三成局地户呈控案被并入孟仕仁京控案审理。办案官员在讯问民教双方后认为:光绪九年,三一教堂、教民通过地商韩大成,向署七苏木佐领昂晦购买了52号土地,共计260顷。后遭察哈尔都统奎斌查办,昂晦被革职,教民也被迫令领银退地。教民并未遵断,反与七苏木蒙官达成另换给教民十里长宽土地垦种的协议,使教民获得的土地有70号,比教民原先购买的土地多出将近一半。去年秋季旗厅官员划入教民地界内的土地已不止十里长宽,教民原来支付的购地款也被还给教民,“是洋堂白得之地又较价买之地多增一倍矣。”当年冬,署正黄旗总管巴图德勒格尔指派的蒙官在监督教民刨挖壕沟时,又擅自把孟仕仁地户开垦出的熟地全部圈入教民地界内,使教民获得的土地“二十里长宽而犹不止,是蒙续给之地更较原买之地又多逾数倍矣”。对于巴图德勒格尔等蒙官的做法,文保等人表示不解:“该蒙员巴总管等将地指给洋堂,若亦惟恐其不多,必照原买号数而倍蓯之,并夺他人熟地以附益之,是诚何心?”办案官员担心,“在洋堂则银地两得,并且地加数倍;而孟仕仁众地户则钱地两空”,若将孟仕仁及其地户驱逐了事,孟仕仁等人岂能甘心?”“若办理太不持平,诚民教相仇,后患滋钜”。因教民不肯将多占土地退出,只有另外拨地安置孟仕仁及其地户,“则教堂可无须退地,民人亦不至流离失所。从此民教便可相安,而案内种种弊端,亦可概免深究,诚为幸甚。”孟仕仁向办案官员称,与七苏木毗连的八苏木尚有空闲荒地,八苏木官员也愿把地拨给他垦种。四月,八苏木佐领将20多里长、2-4里宽、共计150多顷地划给孟仕仁耕种。二、六苏木佐领也以“恐复日后教民影射霸种”为由,想把与八苏木毗邻的空闲荒地划给孟仕仁开垦。办案官员皆无异议,但与孟仕仁结怨的巴图德勒格尔“忿然不从”。孟仕仁又向察哈尔都统提出请求,祥麟以孟仕仁“任意要挟,形同无赖”,要求地方官员将孟仕仁押解回原籍,严加管束。不安分的佃户,也一并驱逐[1]723。
二
七苏木购地案主要反映了蒙古官兵、地商、教民团体这三个利益群体之间围绕土地展开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和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的封禁政策、蒙汉分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清一代,察哈尔蒙古的游牧区域大约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境内。总管制下的察哈尔蒙旗,其土地所有权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私有性质,即王公牧场地。另一种形式为国有性质,即官地,或称为公共游牧之地、官荒空闲地,为清政府指定给察哈尔各蒙旗放牧的区域。
自顺治朝起,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多次宣布实施禁垦,但都流于形式,在察哈尔地区即是如此。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私自放垦对蒙旗官员是一件极为有利的事情。察哈尔各旗自实施总管制以来,各蒙旗蒙官、兵丁主要依靠领取一定的俸饷和从事放牧来维持生活。事实上单靠俸饷和放牧所得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他们便把名义上属于官地的牧地私自放垦、私自收租,以维持生活。私自放垦和私自收租,就成为察哈尔蒙古人,尤其是总管、参领、佐领等官员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除此之外,清政府为解决军粮供应、安置流民所组织的官垦也使封禁政策大打折扣。在光绪八年清政府还在察哈尔右翼四旗(包括七苏木所在的正黄旗)设立丰(镇)、宁(远)荒务局,专门经办开垦无碍游牧的空闲荒地和征收押荒银两事宜。该荒务局于光绪十一年关闭。
由于私租私放的不合法,一些蒙古官兵便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的做法常常是一地两卖,或者索要更多的银两,当购地者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就以有碍游牧为借口到厅县衙门要求予以驱逐;他们也会形成一些为出租、出售土地为目的的小团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售地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以苏木为单位,有时又不局限在某一个苏木内,有时一个苏木内会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售地团体。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团体竞相出租、出售同一块土地或者相邻的土地;有时得势的团体拒不承认失势团体的出售行为而重新出售。如在七苏木购地案中,在七苏木就存在着两个售地团体:昂晦团体和达尔玛济尔弟团体,昂晦团体以七苏木部分官兵为主体,也包括三、五、十五苏木的一些兵丁;达尔玛济尔弟团体的成员主要是七苏木的另一部分官兵,并得到了长期掌握正黄旗实权的巴图德勒格尔的支持。在教会第一次购地时,昂晦团体掌握着七苏木的支配权,七苏木的出租出售活动主要都由他们控制(如售地给教会和孟仕仁)。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达尔玛济尔弟团体便想尽办法破坏昂晦团体的售地活动,在巴图德勒格尔的支持下,制造了“察哈尔正黄旗游牧私垦烧粮一案”,致使昂晦被撤职。昂晦团体失势后,达尔玛济尔弟团体拒绝承认昂晦出售土地行为的有效性,在向教民团体索要了四千两白银后,把教民安排到其伦温古茶一带垦种,这里的一些土地和孟仕仁从昂晦那里购买的土地(花桃勒盖以东的荒地)相重合。此后达尔玛济尔弟又不断向教民索要白银,在教民未能满足其欲望时,就到丰镇厅衙门以有碍游牧为由要求驱逐教民。还有个别蒙官专以土地为诱饵骗取钱财,如三苏木的笔帖式图鲁巴图,刘拯灵曾指控他“长扬言旗下放地,非过吾手,永不能成,故诓哄民财亦复不少”。[1]668
比起蒙古官兵的私租私放,清政府组织的放垦或者清理私垦也好不到哪去,要申请到无碍游牧的空闲荒地需要打通各个关节和经历繁琐的手续,[2]清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常常给购地者带来麻烦,吏治的败坏又使许多购地者无法完成购地手续。在七苏木购地案中,孟仕仁好不容易才完成他的大部分购地手续:与昂晦商谈,领取印据、地图,到丰镇押荒局备案,到户部办理有关手续,批准后再到丰镇厅核办,只差招募农民前去垦种了。“察哈尔正黄旗游牧私垦烧粮一案”发生后,察哈尔都统奎斌封禁了七苏木的所有土地,致使孟仕仁前功尽弃。在其伦温古茶邻近地带垦种的三成局地户自光绪十七年就在办理相应的土地手续,由于厅县官员的拖延,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也未完成,致使他们的土地被教民霸占。
由于私租私放不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购地者(主要是地商团体和教民团体)更多的选择和蒙古官兵私下交易。为了对抗蒙古官兵一地数卖、持续不断的滋扰,厅县衙门的驱逐,购地者也会组织武装,使用暴力保卫自己购得的土地。为了抵消蒙古官兵的一地数卖,他们也私自扩大垦种范围。蒙古官兵的一地数卖、所购土地四至的不明确,以及都试图扩大垦种范围,使得购地者之间也常常发生冲突。在七苏木购地案中,发生冲突的三股购地者孟仕仁、三成局、教民团体冲突的根源正是如此:七苏木官兵的一地数卖,购置土地四至的模糊与重合(孟仕仁购买的土地是花桃勒盖以东的荒地,教民是其伦温古茶一带十里长宽的土地,三成局地户的则是玛泥脑包至其伦温古一带的土地),购地者的竞相扩大垦种范围。
清政府施行的蒙汉分治政策使土地纠纷很难得到有效、公正的处理。在察哈尔地区,各蒙旗官员由察哈尔都统节制,具体负责蒙古人丁、土地的管理,各厅县官员(口外七厅)则归山西巡抚管辖,管理在察哈尔各旗垦种的汉族农民。这种同一地区的居民分属于不同行政机构管理的制度,必然会产生许多麻烦和不便。再加上蒙旗官员总是由蒙古族担任,厅县官员则往往由汉族或满族官员所担任,在他们会审蒙、汉间的土地纠纷时,偏向本民族的倾向难以避免,由民族差异所引起的猜忌、互不信任也时有发生。由于察哈尔各旗的蒙官大都或明或暗的参与了租放土地的活动,由他们参与会审,在指划地界时也必须由蒙旗官员进行,厅县官员不能干预,这使得蒙、汉间的土地纠纷很难得到真正公平、彻底的解决。
购地者之间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就是使用暴力。我们从孟仕仁、刘拯灵、三成局地户的呈文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浓厚的暴力色彩。还有一些人纯粹是以暴力为生。张琦就是这样的典型,刘拯灵在禀呈中称之为“草地王”,并对张琦的事迹做了简短的描述:“兄弟三人约私霸蒙地,并平民地数百顷,每年每人吃租二三千石”。在破坏教民界壕遭教民阻拦时,“怒气冲天,我就如此,听尔自便,喝令众党下手乱劈乱打”。忻州知州许涵度对察哈尔地区充满暴力色彩的土地流转过程的概括是颇为准确的:“查丰宁各厅蒙地自光绪十一年办理押荒之后,将经奏明严禁私垦。而奸民设立地局,勾串蒙员私租私放者仍复不少。其初蒙古皆经得价指放地段,有给予文据者,有未给予文据者,有文据系指此地而予以彼地者,迨耕垦成熟,其未经得钱与曾经得钱而又转租他人之蒙员,则又以有碍游牧为辞,与承种者为难,其或率众驱逐,焚毁房舍,劫夺牲畜。弱者饮泣吞声,强者不能甘服,则与后来承种之人互相呈控,或纠众械斗,每每攘争觏衅,缠讼不休,大为边疆之患。”[1]668
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团体中,教民团体无疑占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可以得到较多的捐款,教会的经济实力常常要比竞争对手强,在七苏木购地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支付的银两有:教会、教民付给韩大成7000两,其中昂晦团体得到3450两;达尔玛济尔弟团体得到4000多两。孟仕仁仅向昂晦支付了一定数量的款项。这正是巴图德勒格尔、达尔玛济尔弟倾向于教民的原因之一。在冲突中,教民团体可以得到法国使节的支持,这使得清政府官员在处理纠纷时不得不倾向于他们。这种支持又常常使得教民团体变得有恃无恐,异常的贪婪、凶暴。不过,教民团体在获取较多利益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多的仇恨。这种仇恨在1900年的反洋教风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事实上,围绕土地展开博弈的各方很少有真正的赢家:竞相出售土地不仅加剧了察哈尔蒙古人内部的争斗,而且使过多的土地甚至包括他们的公共游牧之地被出售、开垦,这使得他们的游牧区域不断缩小,大大的影响了他们的生存。购得土地的不合法、不确定,以及争相扩大垦种范围使得购地者彼此之间、购地者与蒙古人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习惯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又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相互争夺土地的地商和传教士有着某种相似性:都使穷苦农民获得土地,都组织农民进行生产,都为农民提供安全保护,都向农民提供救济、兴办公益事业。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教授狄德满(Gary Tiedmann)在《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一文中指出,晚清时期,华北地区由于人口密集,社会动乱,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上层士绅相对较少,助长了社会不法行为的产生,造就了暴力性的生存竞争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在国家权力相对虚弱的各省交界更为明显。传教士通过介入地方性的资源争夺,为传教事业赢得了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传教士的介入也使得这种群体性的暴力冲突进一步恶化。狄德满举了山东、河南、直隶、江苏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狄德满认为内蒙古的情况和华北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对内蒙古民教冲突的相关研究不够深入,他只是附带介绍了1900年内蒙古教民武装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2]。
狄德满的观点对于认识内蒙古的蒙、民、教冲突极具启发意义。晚清时期,由于清朝统治的薄弱、特殊的蒙汉分治体制、地域的辽阔、大量的外来人口与相对稀少的土著人口、官僚机构的腐败低效、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有教养的士绅阶层的缺乏,在内蒙古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暴力性的生存竞争方式。如在河套地区,地商们为了争夺对土地和水渠的控制权,多组织私人武装进行械斗。大地商王同春与另一地商陈锦绣因争夺水渠,王同春就招募杀手,先将陈锦绣剜掉双眼,后又将其杀害。对于此种情形,学者张维华评论道:“套内既为官家势力所不及,人民咸视国法若未睹,强横者可以肆为不法,狡黠者可以助人为虐。处此环境,非畜武士以自卫,亦未可以图生存。积渐而械斗起,则至杀人流血,强者田土渐辟,日臻富豪,弱者奔走流徙,终至灭亡,此为套内之通情。”[3]
在察哈尔,则是蒙官和地商相互角力的舞台。蒙官把土地私自出租、出售给汉族农民、地商私垦,之后又以“有碍游牧”为借口,焚毁租种者的房舍,抢夺其牲畜,实行武力驱逐。地商则拥有武器,豢养打手,强行扩大私垦范围,甚至与官府对抗。如大地商崔维贤,清末督办垦务大臣贻谷曾指控他“暴戾恣睢,专以强霸侵夺为事,更于界务未定之际,复行焚掠”,他所强占的土地“广轮百十余里”。即便遭官府通缉,崔维贤“近复内外贿通,出没于京城、张家口之间,非徒法外逍遥,仍复暗中把持,地虽被撤,犹在地所聚集凶徒,持械扰阻,不许他人承领”。[4]在热河一带,民间宗教、秘密社会极为活跃。自道光、咸丰以来,热河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动荡,到了光绪年间更是如此,“穷人受富人的欺凌压迫,而无业游民则聚而为匪,横行不法,无恶不作。”
晚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蒙、民、教冲突不过是该地区暴力性生存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教会一方具有其竞争对手所没有的优势:他们能够得到法国外交官员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他们战胜竞争对手关键所在。在冲突中获胜不仅使教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也为教会赢得了政治上的声望,促使更多的人加入教会。清政府官员贻谷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强争越占,有恃不恐,不入教不足以得地,一入教并可以制人。至受制于人而藉入教以保其身家者,更不知凡几矣。”法国人的支持,也大大助长了教民的贪欲,使他们成为压迫者和剥夺者。这就如同一位耶稣会教士所说的“至为重要的是,对于正义的渴求驱使贫穷的中国人走向我们。但这种自由,或者说是对于压迫的摆脱,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2]。
传教士、教民在冲突中往往获得胜利,赢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汉族农民失去家园、耕地,蒙古牧民游牧范围缩小,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的权力也遭到侵蚀。传教士对土地纠纷之类的利益冲突的干预,使本已恶化的社会秩序更加恶化。狄德满指出:“侵入的基督教不是乡村社会秩序长期恶化的始作俑者,但它却从许多重要的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这一看法在内蒙古地区同样适用。
[1]吕实强.教务教案档(第6辑)[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1981:505,622,645,703,723,668.
[2]狄德满.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J].历史研究,2002(2):79-93.
[3]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J].禹贡半月刊,1936(5):119-137.
[4]朱金甫.清末教案(第3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8:635.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96.
[6]彭嵩寿.闵玉清传[M].胡儒汉,王学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刻印本,196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