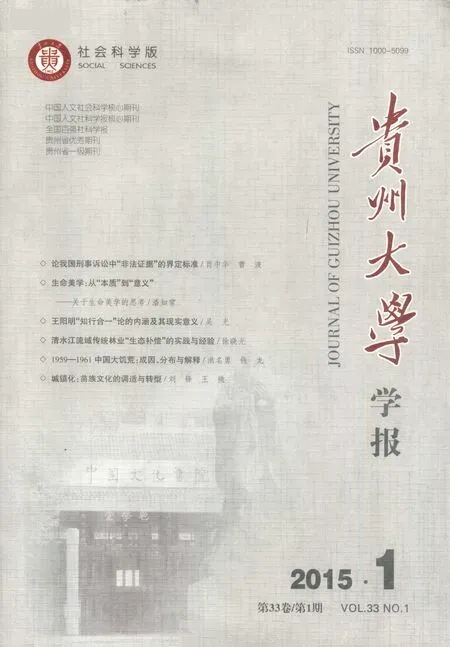论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及其完善
宁立标,高 方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我们处在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时代。“过去四十年间,一系列的地震、干旱、洪水和火山爆发在生命丧失和经济及社会基础结构遭受破坏方面带来巨大损失。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所发生的灾害成指数地增长。仅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一年内,自然灾害引起的灾难共有394次,受害人数超过2.03亿人,夺走了238,000人的生命,并造成77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正是由于自然灾害破坏力的加剧以及灾害防治国际化和区域化趋势的增强,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主权国家对自然灾害领域的国际合作日益重视,作为自然灾害高发国的中国也频频展开了灾害防治国际合作的实践。尽管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需求激增,中国参与的自然灾害防治国际合作实践也日益增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本文将以中国—东盟灾害防治法律机制为中心,讨论构建中国—东盟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梳理中国—东盟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规范以及加强中国—东盟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而且能够进一步改善中国—东盟的外交关系,并为中国灾害防治国际合作的合理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中国—东盟自然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的现实基础
(一) 现实需求:中国—东盟国家救灾合作的兴起
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大多属于灾害多发国家。根据东盟相关报告,从2001年到2009年东盟国家发生洪灾213次,风暴132次,地震42次,火山爆发15次,旱灾12次,塌方42次,灾害次数占同期全世界灾害数的14%,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 610亿美元[2],其中20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地震和海啸已造成超过29.2万人罹难。与东盟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自然灾害高发国家,中国自然灾害存在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和造成损失重四大特征,1990-2008年19年间,平均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约3亿人次受灾,倒塌房屋300多万间,紧急转移安置人口90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人民币[3]。
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除了对本国的自身影响之外,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要么领土接壤,要么隔海相望,地理位置的近邻关系使其常常共同遭受某些自然灾害的磨难。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使十几个国家受灾,2009年的台风莫拉克和台风凯萨娜使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受灾,2011年的泰国洪灾造成的水稻减产对中国大米的市场供给与市场价格造成直接影响[4],2013年的台风海燕袭击了中国以及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东盟国家,给受灾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带来巨大影响。正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以及跨国灾害的恶劣影响,开展灾害管理的国际合作成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重要任务。由于各国政府有时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也由于自然灾害影响的跨国性,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睦邻友好的外交战略,还是为了切实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保护本国公民人权的义务,中国与东盟国家都非常重视彼此间的灾害管理合作。比如,中国政府2004年9月建立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应急机制,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中国不仅提供了紧急救援,还提供了7亿多元人民币的援助[5]。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中一些东盟国家也向中国提供了救援物资,在2008年,缅甸发生“纳尔吉斯”热带风暴时,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提供价值1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物资,并派出医疗救援队救治伤员。[6]正是由于中国—东盟国家抗灾救灾的国际合作的兴起,建立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也日益凸显。
(二) 法律环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普遍建立
“救灾援助国际合作虽然不一定是新近的现象,但在当代已越来越盛行。”[7]正是由于灾害防治国际合作的日益兴起,通过法律规范以及促进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日趋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从1927年的《建立国际救济联合会公约和规约》,到1991年的《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高级特别委员会纽约宣言》和1998年联合国的《关于向减灾和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再到2005年《兵库宣言》和《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培养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的全球性法律机制日趋完善。
在区域层面,1991年的《美洲便利灾害救助公约》开启了美洲国家灾害防治区域性立法的先河。此后,1999年《加勒比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准成员国促进自然灾害方面的区域合作协定》以及2003年《建立中美洲预防自然灾害协调中心的新公约》,进一步强化了美洲国家自然灾害联合防治国际法律机制。在欧洲,欧盟尽管没有专门的灾害防治法律文书,但是其1992年发布的有关与环境保护的第2078/92号条例中,要求为保护环境、防治自然灾难或者火灾而养护废弃的耕地和林地。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东盟国家制定了《东盟灾害管理和应急反应协定》。该协定从灾害发生的过程入手,直接具体地规定了各缔约国在灾害预警、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不同阶段的权利与义务。该协定打破了国际法传统上的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入手的固有模式,对于国际和区域联合灾害防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创新启迪。
除了上述全球性以及区域性国际法律文件外,当前还存在着大量国家之间的双边灾害防治协定。根据国际法委员会2008年的统计,全世界已经签订了150多个双边条约及谅解备忘录[8]。这些双边条约与联合国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相关法律一道,构成了当前灾害防治合作的国际法律框架。
二、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合作的软法之治
(一) 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合作的现有法律机制
正是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饱受自然灾害的折磨以及自然灾害防治国际合作机制的普遍建立,也随着东盟国家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东盟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深入展开,中国与东盟国家也逐步建立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机制。当前来看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框架不仅包括二者之间的双边法律文件,也包括二者共同参与的多边法律文件。
1.中国—东盟之间的双边法律文件
中国与东盟自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签订了大大量双边法律文件。尽管早期的诸多文件只强调国际和平、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但是2002年的《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将双方合作领域拓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该文件不仅认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也指出中国与东盟各国互为邻邦,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该文件规定,中国与东盟现阶段的合作重点为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具体合作途径是加强信息建设、人员培训、能力建设以及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尽管该文件没有明确提及自然灾害防治合作,但是由于海啸、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也一直被人民视为非传统安全范畴[9],因此该宣言也可视为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规范性文件。
除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国—东盟间签署的多份合作法律文件明确提及了灾害防治领域的合作。比如,2006年发布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指出,中国—东盟在农业等10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合作,这些合作促进了双方在应对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新挑战以及更多人员交流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在该文件拟定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目标中,要求“中国支持以东盟为主导,加强灾害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地区合作,包括灾后重建和恢复。”[10]2010年的《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也要求在《东盟灾害管理与紧急应对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对减少灾害风险、救灾和重建等信息分享、经验知识交流,增强灾害管理合作,支持建立东盟人道主义援助中心。”[11]2012 年,《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将灾害管理合作作为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该文件不仅要求“探讨建立中国—东盟灾害管理领域高官磋商机制的可能性,加强减灾、救灾和重建信息与经验共享”,还要求“加强减灾、救灾和重建培训,通过项目和专家交流,提高灾害管理工作软硬件设施”,“通过信息共享、经验知识交流、举办紧急医疗服务管理和支持研讨会和培训班等措施,促进紧急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该文件还规定,“结合《东盟灾害管理和紧急救灾协议》,适时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减灾救灾合作协议》的可行性。”
此外,2013年发表的《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也指出,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防灾救灾合作,中国愿与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拓展交流与合作。
2014年,中国与东盟的防灾救灾合作有了最新的进展。10月6号,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东盟秘书长郑中强调其重要性并称其为“东盟对华灾害管理合作领域的里程碑”,并希望在为进一步加强对话和互动,全面落实该谅解备忘录[12]。尽管谅解备忘录(MoU)作为一种较非正式的国际文件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强制性的拘束力①根据《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的解释,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是一种较非正式的国际文件,往往是依据一个正式协定而规定该协定的具体安排或处理技术性细节事项的协议。谅解备忘录可能是一个单一文件,由有关国家签署,载明它们对于安排或事项的了解,并表明它们的未来行为,但无意订立法律上有拘束力的设定。,但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中国—东盟自然灾害防治合作的重大进步。
2.中国与东盟参与的多边法律文件
除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法律文件,中国与东盟共同参与的多边法律文件中也不乏关于灾害防治的规定,这些文件主要是在东盟地区论坛、“10+3”会议以及东亚峰会上发布的。
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当前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对救灾问题一直高度重视。自1997年以来该论坛就开始举行救灾会间会,商讨防灾救灾减灾事宜,为了协调论坛成员国在救灾领域的合作,论坛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比如《ARF地区论坛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战略指导文件》、《ARF减灾工作计划》和《ARF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声明》。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皆为论坛成员国,因此论坛签署的上述文件对中国与东盟国家抗灾救灾合作无疑具有一定拘束力。
除了东盟地区论坛之外,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3国共同参与的“10+3”机制也非常重视灾害防治合作。比如,2007年“10+3”会议发表的《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明确将减轻自然灾害作为社会方面问题之一,并在东亚地区鼓励建设更大规模的合作框架,促进机制建设,将减灾救灾作为整个东亚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和重要部分;《2007年—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中将灾害管理和应急作为该阶段10+3合作的重要领域,明确要求加强在洪水、山崩、地震和其他灾害领域的合作,协助支持国家和地区海啸和其他灾害的早期预警体系网,提供援助并实施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应急的协议,并增进在减灾方面的军民合作。
东亚峰会发布的关于灾害合作的法律文件主要有2009年的《东亚峰会灾害管理帕塔亚声明》。作为东盟以及中日韩等六国共同发布的以灾害合作为主题的国际文件,该声明对于中国和东盟的灾害合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该声明指出国家在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作用以及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在灾害防治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应在降低灾害风险和灾害管理方面采取一套一体化、多灾种的对策,并将灾害风险管理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该声明以加强防灾救灾能力建设为基本目标,要求成员国加强政策、计划、程序、体制到位、人员培训和机制协同方面的能力,合作开发早期预警系统和加强预警信息交流,合作开展灾后管理与恢复,合作开展应急模拟演练。此外,该声明还要求开展合作各方积极帮助其它成员国制定相关法律并加强执法能力,这一规定表明中国、东盟以及东亚峰会的其他成员国对于灾害防治合作已经从实践层面拓展到法律层面。
(二) 软法之治:现有法律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软法问题是一个长期被边沿化但是现在困扰着国际法学者的问题[13]。西方国际法学者有的将软法视为条约中笼统规定的、口气很弱的义务,有的将其视为以非约束性方式缔结的非条约性协议,如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决定、宣言和建议等。尽管学者们对软法的概念存在一定认识分歧,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共识:“软法总的来说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14]根据软法硬法的这一界分方式,我们发现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机制是软法治理机制。之所以称之为软法治理机制,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表现形式多为宣言声明。从法律表现形式来看,中国—东盟有关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文件多为宣言、声明以及行动计划等等,没有一个文件是公约或协议。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正是由于其表现形式为宣言声明,而不是正式的协议、协定或者条约,其法律效力比起协定等硬法而言无疑也弱得多。
第二,义务责任不清晰,义务没有法律约束力。作为规范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文件,无论是中国—东盟间的双边文件,还是二者共同参与的多边文件,除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以及《东亚峰会灾害管理帕塔亚声明》规定了防灾减灾工作国际合作的一些具体细节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文件对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的规定只是停留在一种口号式的倡导性层面。并且,这些文件不仅对第一性义务设置不清晰,对违背第一性义务引发的第二性义务更加没有规定。并且,由于文件中关于义务的规定,大多采用的是倡导性规范形式,则为实现所合作目标倡导缔约方为某一行为,对于没有积极履行倡导行为的缔约方没有责任规定。比如,《2007—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尽管规定在灾害管理与应急方面的合作,但是,对于合作双方的具体义务与相关权利以及不履行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缺陷不仅使整个法律文件缺乏可操作性,也可能导致行动不力和争端的产生,并且,还会促使缔约方为规避法律文件给本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规避执行或停留于口头承认层面[15]。
第三,工作机制不完善,缺乏争端解决机构。当前来看,中国—东盟联合灾害防治缺乏常设性机构,主管机关也不明确。中国与东盟目前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灾害联合防治的常设性机构,中国—东盟中心作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的政府间常设国际组织,其职能并没有涵盖减灾救灾领域①中国—东盟中心目前其职能只能覆盖中国和东盟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对于减灾救灾合作未做提及。来源于中国—东盟中心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因此,当前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工作机制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的领导人会议、外长会议等会议制度,而且上述会议多为综合性会议,灾害防治仅是会议的一个议题。除了缺少常设灾害防治合作常设机构以及工作机制不完善之外,中国—东盟之间在灾害防治合作法律机制上还缺乏争端解决机制,二者之间不仅还没有建立争端解决机构,更没有设立争端解决的具体程序。这一缺陷不仅无法有效应对不履行义务的情形,甚至会消极助长不履行义务的现象发生。
三、硬法之治: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法律机制发展的两条路径
由于中国—东盟现行灾害防治合作的软法之治存在的局限性,实行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的硬法之治无疑是其未来发展方向。当前来看,实现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的硬法之治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签订《中国—东盟减灾救灾合作协议》,第二条路径是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
(一) 第一条路径:《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条约》的签订
根据国际合作的惯有思路和国际法理论,国际合作的法律保障机制的最佳路径应该是签订硬法性的国际条约。正因如此,从理论上看,中国—东盟灾害防治合作法律机制的发展的最佳道路就是签订《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条约》。为了有效保障双方合作,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应明确以下事项:
第一,基本目标与基本原则的确立。
基本目标与基本原则乃是法律的灵魂所在,它不仅是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对法律制定也具有指导作用。正因如此,完善中国—东盟联合灾害防治法律机制,首先要确立双方合作的基本目标与基本原则。在基本目标方面,应该明确签订本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提升缔约国防灾救灾能力,最大程度保障缔约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自然灾害的侵蚀。在基本原则方面,应该将国家主权原则、人道主义原则以及不歧视原则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
其中,国家主权原则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6/182号决议,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必须在受灾国同意的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6]该原则不仅意味着进入受灾国应征得受灾国的同意,也要求施行援助时要充分尊重国家主权,遵守受灾国的法律,不得以救灾名义违背受灾国法律和侵害受灾国主权,更不得以救灾作为干涉他国主权的筹码。但是,尽管国家主权原则赋予了受灾国是否请求援助和接受援助的决定权,但是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来看,在必要时请求人道主义援助已经被视为受灾国的国家义务。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声称由于它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履行义务,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寻求国际援助但是没有成功[17]。由此看来,为保障灾民人权请求国际援助乃是国家当然义务,这一义务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
与国家主权原则一样,人道主义原则也是灾害合作的基本原则,因为灾害援助本身乃是人道主义援助。该原则要求在开展灾害合作时,将拯救生命、舒缓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作为基本任务,将人道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充分保障灾民的生存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方面的权益,尤其重视残疾人、老人、儿童和妇女等脆弱性较强的弱势灾民群体的权益。
不歧视原则乃是国际人权法中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已经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承认。在灾害合作中,该原则要求平等对待灾民,不因种族、财产、性别和社会地位等原因加以歧视。当然,正如人权法的反歧视原则允许临时特别措施一样,灾害援助中的反歧视原则与对弱者特别关怀并不矛盾,因为为了关注弱者乃是人道主义行动的基本要求。
第二,义务与责任的明确化。
根据自然灾害应对的阶段划分,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可以从灾前预防、紧急救援以及灾后重建三个阶段展开。在灾前预防阶段,应明确各方在灾害预警方面的合作义务,尤其是灾害预警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义务。在灾害应对阶段,应该规定受灾国请求支援时,其他缔约国应当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受灾国则应当尽最大努力为救援国的救援行动提供便利,保障救援人员和救援货物的进入。在灾后重建阶段,应受灾国的请求,其他缔约国可以在重建计划的制定、重建所需设施等方面提供援助。
第三,协调决策机构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
协调决策机构是实施灾害防治国际合作的关键,因此中国—东盟联合灾害防治法律机制的完善离不开专门的协调决策机构的建立。考虑机构设置的成本,笔者以为,这一机构可以考虑设置在中国—东盟中心之内。具体做法是在现有的综合协调部、贸易投资部、教育文化旅游部和新闻公关部之外增设防灾减灾部,负责与中国民政部救灾司和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直接对接,统一协调中国—东盟的灾害防治工作,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减灾防灾合作提供便利。在缔约国没有履行条约义务时,该中心可以通知其他成员国对其实行约定的制裁。对于双方在灾害防治合作方面发生的争议,应当设立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首先采用友好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18]。如果通过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由中国—东盟中心防灾减灾部予以斡旋和调停,并再次就双方争议进行协调以期达成一致。如果争端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并继续寻求解决该争端,则可以提交中国—东盟中心决策部门——中国—东盟中心联合理事会进行裁决,由所有缔约国协商一致通过的结果来进行裁决[19]。
(二) 第二条路径: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
尽管签订《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条约》乃是加强二者灾害合作的重要路径,但是该路径仍然面临一定问题。首先,东盟本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由于成员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从其成立至今,东盟的凝聚力以及执行力远不如欧盟实在,正因如此,东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也很难以条约形式签订,大多只是一些宣言或者行动计划。其次,从条约双方的主体来看,一方为中国,另一方为东盟这一国际组织,主体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在这种主体不对称性的情况下,制定软法性法律文件可能性较大。如果要形成硬法,主体不对称性可能导致东盟国家微妙的抵制心理,影响该条约的制定以及通过。其次,立法虽然能解决现实问题,但是当今时代随着立法程序的日益复杂,立法的成本日益增加,国际条约的制定也概莫能外。正因如此,中国—东盟之间要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无疑面临着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的压力。
正是由于第一条道路面临的复杂问题,完善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可能还需要寻找第二条路径。在笔者看来,这一路径就是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从理论和惯有实践上看,加入国际条约乃是成为条约之缔约国的一种普遍方式。尽管如此,这一路径仍然面临一个较大障碍。因为,《东盟灾害管理应急协定》乃是东盟国家之间的协定,东盟乃是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国尽管与东盟具有近邻关系,但是本质上而言,中国不仅在地域上不属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法层面也不属于该协定成员国。
尽管上述障碍可能有一定正当性,但是从东盟国家国际合作的实践来看,非东盟国家加入东盟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已经具有先例,《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盟国家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的国际条约,其宗旨是“促进地区各国人民之间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团结和密切关系”。尽管该条约第18条规定条约向所有东南亚国家开放,但是此后东盟国家通过了多个修改议定书,以便解决东南亚以外国家加入该条约的程序问题。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改议定书,中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欧盟都加入了该条约。正因如此,《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做法为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第二条路径,即东盟国家可以通过修改议定书方式,允许中国加入《东盟灾害管理协定》。这一道路的最大益处不仅可以避免制定新条约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消除东盟国家因主体地位的不对称性而产生的不满。正因如此,这一路径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比第一条道路似乎更具可操作性。一旦中国加入该协定,中国便享有该条约规定之权利,并担负该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
四、结语
完善中国与东盟灾害防治合作的法律机制的不仅符合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特点,符合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需求,也符合中国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情况下,加强灾害领域的互助合作,充分有效地为东盟国家提供灾害援助,不仅有利于贯彻人道主义原则,也能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维护中国地缘外交利益。正因如此,尽管中国—东盟灾害管理法律机制完善的两条路径都面临着一定困难,但是迈向灾害防治合作硬法治理模式无疑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必然选择。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应本着人道主义以及平等互利的精神,为灾害管理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付诸最大努力。
[1]联合国与减灾[EB/OL].http://www.un.org/zh/humanitarian/disaster/.
[2]ASEAN Agreement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AADMER):Work Programme for,2010 - 2015:4.
[3]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减灾行动[R].2009.
[4]龙土有.泰国洪灾牵动澳门人神经,市场担心泰米涨价[EB/OL].http://www.weather.com.cn/index/gjtq/11/1530102.shtml.
[5]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R].2011.
[6]洪凯,魏祖志.浅析中国参与东盟减灾合作问题[J].东南亚纵横.2012.
[7]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590.para.3.
[8]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590.para.4.
[9]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M].时事出版社,2003:12.
[10]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EB/OL].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7925.htm.
[11]〈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EB/O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765199.shtml.
[12]ASEAN and China Sign Agreement on Disaster Management[EB/OL].http://www.asean.org/news/asean - secretariat- news/item/asean-and-china-sign-agreement-on-disaster-management?category_id=27.
[13]GuzmanMeyer.International Soft Law[J].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Vol.2.No.1.2010:p.180.
[14]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63.
[15]杨刚勇,等.走向一体化的东盟[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0:56.
[16] Strengthening of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emergency assist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A/RES/46/182.para.3.
[17]第12号一般性意见:食物权(第17段)[R].E/C.12/1999/5号.
[18]高健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4.
[19]何新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以〈中国与东盟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对象[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