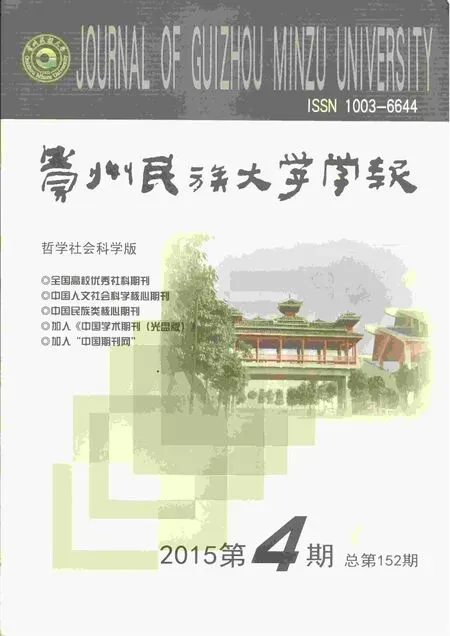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及其对刘勰的影响①
汪文学,刘苏晓
(1、2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古代文论之诸种观点中,受到近现代学者诟病最深且重者,莫过于“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说,或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或命之曰客观唯心主义,总之几乎是众口一辞地批评它是中国封建时代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性质的唯心论观点。大体而言,以“明道”为中心的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论,起源于孔孟,发展于扬雄,定型于刘勰,而流变于唐宋古文家和道学家。扬雄和刘勰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前者对后者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近现代学者对“文以载道”说的批评,其矛头多指向宋代理学家,而于扬雄和刘勰的“明道”论亦多有误解,且于前者对后者之影响亦多是语焉不详,或者略而不论。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扬雄思想体系中“道”的内涵,以明其征圣、宗经之真正意图,并进一步辨析扬雄论文与刘勰《文心雕龙》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
一、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
讨论扬雄论文以“明道”为核心的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为宗旨的文学思想,首先应该探讨的,是扬雄之所谓“道”,到底何指?有何特点?
作为一个关键词,“道”在扬雄《法言》、《太玄》中频繁使用,如:
(1)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法言·学行》)①
(2)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法言·学行》)
(3)舍《五经》而济夫道者,末矣。(《法言·吾子》)
(4)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法言·问道》)
(5)或问:道?曰:道若涂若川,车航混混,不舍昼夜。(《法言·问道》)
(6)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法言·问道》)
(7)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法言·问道》)
(8)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法言·问神》)
(9)浑浑乎圣人之道,群心之用也。(《法言·五百》)
从以上诸例看,扬雄并未对“道”作具体的界定,或言“道”之传承,如(1)条;或言其载体,如(3)条;或言学之目的是为体“道”,如(2)条;或言“道”之性质,如(4)(5)(7)(8)条;或言“道”之作用,如(6)(9)条,唯独未说“道”是什么?“道”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体道者圣,明道者曰经。那末看看扬雄对圣人之言、书、辞的界定和论说,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扬雄所谓“道”的理解。
(1)大哉!圣人言之至也。开之,廓然见四海;闭之,閛然不睹墙之里。圣人之言似水火。或问:水火。曰:水,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壮。(《法言·问道》)
(2)或问:大声。曰:非雷非霆,隐隐耾耾,久而愈盈,尸诸圣。(《法言·问道》)
(3)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法言·问神》)
(4)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法言·问神》)
(5)言天、地、人,经,德也;否,衍也。(《法言·问神》)
(6)敢问大聪明。曰:眩眩乎!惟天为聪,惟天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法言·问明》)
(7)或谓:仲尼弥其年,盖天劳诸?病矣夫?曰:天非独劳仲尼,亦自劳也。天病乎哉!天乐天,圣乐圣。(《法言·问明》)
(8)圣人有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法言·五百》)
(9)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法言·修身》)
(10)圣人之言,天也。(《法言·五百》)
(11)天地简易,而圣人法之。(《法言·五百》)
(12)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法言·五百》)
(13)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玲珑其声者,其质玉乎?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法言·五百》)
(14)圣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鸟兽草木也。(《法言·五百》)
(15)或曰:圣人之道若天,天则有常矣。奚圣人之多变也?曰:……圣人之书、言、行,天也,天其少变乎?(《法言·君子》)
(16)天道劳功。或问:劳功。曰:日一曰劳,考载曰功。或曰:君逸臣劳,何天之劳?曰:于事则逸,于道则劳。(《法言·孝至》)
圣人是道的践行者,故圣人之言、书、行,皆是道的具体而微的呈现。考察扬雄对圣人之言、书、行的评论,则可大体推知其所谓之“道”到底何指?以上列举之材料,(1)至(3)条是说圣人言辞的特征,或喻为“水火”,或比为“川”,或以“大声”拟之,与前述所谓“道”之质性近似,亦不是关于“圣人之言”或“道”的具体界定。值得注意的是,从(4)至(16)条,虽然仍不全是关于“圣人之言”或“道”的界定,但有一个核心词即“天地”或“天”反复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基于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扬雄之所谓“道”,是“天道”或者“天地之道”。其显明可证者,如(9)条“观乎天地则见圣人”,(10)条“圣人之言天也”,(13)条“圣人之言远如天’,(14)条“圣人之材天地也”,(15)条“圣人之道若干天”、“圣人之书、言、行,天也”。或直接称圣人之道为“天之道”,如前引《法言·学行》所谓“天之道不在仲尼乎”,李轨注云:“不在,在也。”或以圣人之道拟天道,如(8)条“圣人有以拟天地”,(11)条“天地简易而圣人法之”,(12)条“圣人占天地”。其以“天”或“天地”与圣人相比附者,实际上就是暗示圣人之道即“天道”或“天地之道”,如(4)(5)(6)(7)(16)条。
综上,笔者认为,扬雄所谓之“道”,是“天道”或“天地之道”。其特征,或“若涂若川”之“不舍昼夜”,或如水如火之“测之而益深”、“用之而弥明”,或如“大声”之“久而愈盈”。其“应时而造”,可因可革,可损可益,因敝求新。简言之,就是“神”或者“神明”。“道”之特征是“神”或者“神明”,《法言》于《问道》之后,另立《问神》、《问明》二篇,其谋篇布局大有深意。关于“道”、“神”、“明”三者之关系,扬雄认为:其一,圣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和“圣人”皆有“神明”之特点,故云“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天神天明,照知四方”,“仲尼,神明也”。其二,“道可道,非常道”,“神”不是“道”,“神”是“道”的特点之一。《孟子·尽心下》载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作为具有“神”性之“道”,不可知,不易知,惟圣人能知之,能测之。圣人之所以能知能测具有“神”性之“道”,是因为圣人“聪明”,圣人“尚智”。“由于独智,入自圣门”,圣人如“天地”,有“大聪明”,“能高其目而下其耳”。圣人与天同有“大聪明”,故能“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潜入“天地之道”。其三,“道”既是“天地之道”,亦是人心之道。或者说,“道”既存于天地之间,亦在于人之心中。“道”与“心”关系密切,义近旨通。《法言·孝至》云:“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为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德,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道”与“心”互文见义,实可相通。按照扬雄的观点,“道”和“心”皆有“神”的特点,故曰“人心其神矣乎”。故体道之手段是“潜心”,圣人“潜心”于天地而体察天地之道,众人“潜心”于圣而体察圣人之道。“潜心”以体察“神明”之道,并非易事,即便是颜渊“潜心”于仲尼,亦是“未达一间”。唯圣人能“潜心”,惟圣人能“存神索至”。因为圣人有“大聪明”,能“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故能“潜心”于天地之间而通达“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幽远难测,颜渊尚且“未达一间”,常人更是等而下之。能以“大聪明”之资质“潜心”于天地之间而通达“天地之道”者,惟有圣人。故学者欲“明道”,则必须“征圣”。在汉代知识群体中,扬雄之“征圣”,最为突出。据统计,在《法言》一书中,“圣人”一词凡五十八见,单称“圣”者有十五例,另有“圣门”、“圣行”、“圣言”、“圣道”等复合词,共有八十四例[1]P42,其“征圣”之言论亦屡见不鲜。但是扬雄之“征圣”,与今文学者以孔子为“素王”之观点不同,亦与汉代一般学者因“征圣”而神化孔子的取向迥异。他之“征圣”,主要还是侧重于将孔子理解为真理之掌握者或者道之传承者,强调的是孔子的智慧德性和理性精神。所以,他说:“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圣人之异于常人,就在于“独智”。因此,他说:“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圣人之所以能够“继天测灵”,取得“冠乎群伦”之影响,就在于他的“聪明渊懿”。所以,他之论道与“征圣”,皆富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今文经学繁琐和迷信之现实文化背景上,确有卓尔不群的“异端”特质。
抽象隐秘的“天地之道”,经过圣人之体察而得以呈现,经过圣人之言说而得以彰显。圣人言说道之方式有二:一是聚徒以言传身教之,二是撰为著述以传承之。无论是对道的言说,还是书写,惟有圣人方能担当。《法言·问神》云:“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心”有“神”性,所以问“神”扬雄即以“心”作答。圣人体察“天地之道”而存于心中,故心即道,道即心,皆有“神”性,故而难测难言。于常人言,“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惟有圣人,因其“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故能“潜心”于道,而成为道之体察者和传承者。圣之言说和书写,即著为经典。学者“明道”,必然“征圣”,必需“宗经”。作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之经典,不仅是言说、书写之准绳,亦是日常生活之依据。在他看来,《五经》为“济道”之途径,为众说中最富于“辩”者,故为“众说郛”。“言天地人”而与“经”相符,则称有“德”。所以,扬雄宣称“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人类的一切言说和书写,皆当以“经”为准绳,此之谓“宗经”。
总之,在扬雄的思想中,明道、征圣、宗经是三位一体的,“明道”是人生之终极追求,在人类群体中,于“道”之体察与把握最深且透,并能付诸于生活以践行之者,无过于圣人。故学者“明道”必需“征圣”。圣人于道,或言说之,或书写之,或践行之,著为言辞,则称为“经”。故“征圣”必要“宗经”。
二、扬雄文学“明道”论对刘勰的影响
扬雄以“明道”为核心内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之意义。较早提出“明道”思想,可称为明道、征圣、宗经文学观念之先驱者,是荀子。他以为,“天下之道”在圣人,故云“圣人者,道之管也”。所以学习“天下之道”,首先要学圣人,故云“学之义,始乎为圣,终乎为圣人”。此为“征圣”之义。“天下之道”在圣人,而圣人于道之体察,体现在《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中,故天地之间的各种规律,如“事”、“行”、“和”、“微”等等,皆展现在经典中。圣人远逝,圣人之道体现在经典中,故学习圣人,当研习经典,以经典为人生行事之准则,此为“宗经”之义。“道”为天地间之根本原理,它孕育苍生万物,苍生万物亦以“明道”为旨归,故国风“取是而节之”,大雅“取是而光之”,小雅“取是而文之”,颂“取是而通之”,此为“明道”之义。总之,荀子虽未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和“宗经”这几个概念,但其思想已基本具备了这种意义。所以,学者以为:“对儒家圣人与经典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在先秦时代始见于《荀子》,为汉以后文学理论批评中宗经、征圣、明道等说的先声。”[2]P128
扬雄“明道”文学思想显然是在上述荀子思想之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比之更深入具体、更具理论色彩和系统特征。真正完备周详、旗帜鲜明地提出“明道”、“征圣”和“宗经”之文学理论,并以之为论文之枢纽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书首列《原道》、《征圣》、《宗经》、《辨骚》和《正纬》五篇,以为“《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3]P727。虽说五篇皆为“文之枢纽”,但五篇中又以前三篇为主,后两篇实有补充说明之附录的性质,即“辨骚”、“正纬”之目的,是为“原道”、“征圣”和“宗经”,是为突显经典和圣人的核心地位。刘勰之“原道”文学思想与扬雄之“明道”,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或者说,前者是对后者的理论提升和系统表述。唐宋以来之古文家和理学家,又在刘、扬论说之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分别提出“载道”说“贯道”论,虽然其观点已经逐渐远离扬雄、刘勰之本意。[4]
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在“明道”问题上,刘勰与扬雄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自二人外在的学术渊源观之,有两项事例值得注意:
一是二人皆高度重视孔子,以孔子学说为依据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扬雄推崇孔子,以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万物淆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法言·吾子》),实际上,他之创说就是以孔子学说为依据,以“孔氏之门为户”。刘勰亦是如此,他撰写《文心》之动机,据《序志》说,是他夜梦“随仲尼而南行”,鉴于注经而“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其以孔圣学说为论文之准绳,昭然可见。故邓国光说:“刘勰追随孔子,衷心而生;颂美孔子,具见全书。”“《文心雕龙》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永存人间,正因为深得孔子精神。”[5]P16而刘勰之重视孔子,可能就是受到扬雄的影响。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征圣》就认为扬雄是刘勰尊圣的原型[6]P17。日本学者兴膳宏亦认为“刘勰在尊孔的态度上效学孟轲、扬雄”,“从《法言》各篇中可知扬雄在尊孔方面也是可与孟子比美的。……同时刘勰引用扬雄之言处甚多,可以说他把扬雄视为具有卓越见识的前辈,表示了充分的敬意”。[7]P102-103
二是刘勰论文,于扬雄之文学思想,有深度的契合。刘勰论文以孔圣为依归,于“近代之论文者”多有批评,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8]P725-726近代以来之论文者,虽各有所得,而缺失亦多,或者“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者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皆有或此或彼、或轻或重之缺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评述“近代论文者”之缺陷而及于两汉之际的桓谭,却于与桓谭同时且关系密切之扬雄,只字不提。并非扬雄之论文可以忽略不计,刘勰甚重扬雄文论,并于《文心》中多次引述扬雄之文论以证成己说。唯一的可能是,刘勰推崇扬雄,以扬雄为论文之知音,虽然他对扬雄亦偶有批评,但大体上以扬雄文论为论文之依据。据统计,《文心》一书论及扬雄者有二十篇四十余处,常常以扬雄作品作为“选文定篇”之典范,往往引用扬雄文论作为自己立论之依据。故徐复观说:“扬雄的文学活动,给刘彦和以莫大的影响,……扬雄有关文学的言论,皆成为彦和论文的准绳。扬雄与文学生活的有关片断,彦和生活中皆为文坛的掌故。扬雄的各种作品,《文心雕龙》无不论列。我以为最能了解扬雄文学的,古今无如彦和。”[9]P289
扬雄和刘勰的文论,皆依孔圣立言,而刘勰又常以扬雄为准绳,故二人在文学思想上实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在“明道”论上有明显体现。刘勰《文心》之作,开篇即以“原道”为题。其“道”为何?学界有不同说法,如黄侃以为是“自然之道”,其云:“《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择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10]P3马宏山以为是佛道,认为《文心雕龙》中“自然”和“神理”同是“道”的名称,是“佛道”;刘勰把“神理”和“自然”都按照“佛性”的意义来使用[11]P4-5。虽然刘勰曾入寺为僧,于佛道有深入探究,佛道思想亦渗透于《文心》一书,但遽然断定刘勰“原道”之“道”即为“佛道”,学者少有认同,故可置而勿论。争论之焦点聚集在“自然之道”、“天地之道”和“儒家之道”上。笔者认为,这些争论,往往有拘泥于概念和胶着于文字之嫌疑,实际上三者之间不无相通之处,或者说根本上就是一义三名。于此,郭绍虞的观点最为中肯,他说:刘勰论文,“一方面由流以溯源,而主张宗经”,故有《宗经》篇;“一方面又从末返本,而主张原道”,故有《原道》篇;“《原道》篇所说的道,是指自然之道,所以说‘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宗经》篇所说的道,是指儒家之道,所以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之所谓道,不妨有此二种意义,因为这二种意义,在刘勰讲来是并不冲突的”,“他因论文而推到为文之本,认识到文学是从观察现实得来的,……照这样讲来,刘勰之所谓道,确是指自然之道,确是指万物之情”,“然而他推到为文之源,又不能不承认圣人在中间所起的作用,……也就必然以经典为宗主,而所谓道,也只成为儒家一家之道了”。再进一步说,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并不冲突,“道是根据人生行为来的,所以是自然之道;可是,反过来,道又可以指示人生行为,起教育作用的,所以在封建社会也就不妨说是儒家一家之道”[12]P35-36。与郭绍虞之观点略为相近的,是徐复观。他力驳黄侃“自然之道”说,认为刘勰所谓的“道”,不是《老子》“先天地生”之“道”,而指的是“天道”,或者“天地之道”。此“天道”之内容就是刘勰所谓“盖道之文也”的“文”,故有“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之说。“彦和以六经为文学的总根源,六经是圣人的‘文’。更由圣人之‘文’上推,而认为天道的内容即是‘文’,天道直接所表现的是‘文’,由天所生的人当然也具有‘文’的本性。由是而说文乃‘与天地并生’,有天地即有文”[13]P175-176。但是,徐复观进一步指出:“‘道之文’在内容上并不止于是儒家之‘文’,因为它把自然界的‘文’也包括在内。但道之文向人文落实,便成为儒家的周孔之文。于是道的更落实、更具体的内容性格,没有办法不承认是孔子‘熔钧六经’之道,亦即是儒家之道。”[14]P177即刘勰之道,既是“天地之道”,亦是“儒家之道”,二者一义而二名,并无实质性的冲突。
综上,刘勰《原道》之“道”,既是“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亦是“儒家之道”。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刘勰之“道”与扬雄之“道”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如前所述,扬雄所谓之“道”,即“天道”或“天地之道”;儒家之圣人最明此道,将此道之体察述作于经典之中,故而“天地之道”亦就成了“儒家之道”。在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之道、天地之道、自然之道三者完全可以互通互释。鉴于刘勰和扬雄共同尊奉孔子,以孔圣之说为立论准则;刘勰又特别推崇扬雄,以扬雄之作品为“选文定篇”之范本,以扬雄之言论为证据立说论文。故刘勰于“道”理解与扬雄之“道”的显著相似,绝非巧合,乃刘勰有意学习效仿之结果。
三、余论:扬雄文学“明道”论之意义与价值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明道”论,发端于荀子,发展于扬雄,定型于刘勰,而流变于唐宋古文家和道学家,扬雄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刘勰以“原道”为核心的“文之枢纽”说的构建。
大体而言,扬雄、刘勰的“明道”论,是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之前的创建,故其所谓“道”,既是“儒家之道”,亦是“自然之道”或“天地之道”,三者三名而一义。唐宋以来的古文家特别是道学家,在“明道”论之基础上发展成“载道”说,则是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后的构建,故其所谓“道”,则是专指“儒家之道”。如果说唐宋以后之古文家特别是道学家提倡的“载道”说,必然导致重道轻文,以道为本,以文为末,文仅仅成为“载道”之工具或手段。而扬雄、刘勰的“明道”论,则是“从哲学上穷究文学的根源,而其内心实系以六经根于天道,文学出于六经,以尊圣、尊经者尊文学,并端正文学的方向”[15]P176。如果说前者(古文家、道学家)是为道,后者(扬雄、刘勰)则是为文。后者趋向于“哲学性的文学起源”的阐释,实际上体现的是他们在文学本体论建构上的努力,这与六朝时期的思想家热衷于思想本体建构的时代风尚是吻合的。虽然如徐复观所说,此种“为了提倡文应宗经,因而将经推向形而上之道,认为文乃本于形而上之道,这种哲学性的文学起源说,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意义。今日研究文学史的结论,大概都可以承认文学起于集体创作的歌谣、舞蹈,远在文字出现之前”[16]P179。但是,在文学发展之早期,其对于彰显文学之意义,提升文学之价值,高扬文学之地位,其正面价值和积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邓国光所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与‘道’的问题,不是某一位作者或论者一时意兴的梦呓。这一对于文明史进程相参照的观念,是中国文学的核心意识,讨论中国文学思想,根本不能绕过。严肃的文学研究,必须要正视‘文’与‘道’的问题,从而开敞文学本体的义理。”[17]P6文学本体意义或形上属性之建构,实际上是恢复或彰显文学书写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对过分突出“抒情语体”创作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之矫正,有重要促进。因为文学创作过度倾向于“抒情”一面,“势必陷入矫情虚饰,标奇立异,逞强一时”,“结果是诗、文、小说、戏曲之外,大量古代累积下来的文章,皆遭割弃不顾。另一方面,闲适性与才子气泛滥,突出各抒己见。闲言闲语把弄文学的严肃性,弃斥于不同的生活与学术层面,甚至把文学世界推向直觉、平面、单调的文字组装的可怜状态之中,殗殜于轻松的话头”[18]P5-6。所以,对于矫正文学的低俗化和过分地闲适性发展,扬雄、刘勰提出的具有本体论特点和形上论特质的“明道”论,仍有相当重要的现实价值。
注 释:
①本文所引《法言》,皆引自汪荣宝. 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以下不再重注。
[1]郭君铭.扬雄〈法言〉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2]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17][18]邓国光.〈文心雕龙〉文理研究——以孔子、屈原为枢纽轴心的要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日]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M].彭恩华编译.济南:齐鲁书社,1984.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1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道”的问题[A].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14][15][16]徐复观.〈文心雕龙〉浅论之二——〈原道〉篇通释[A].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