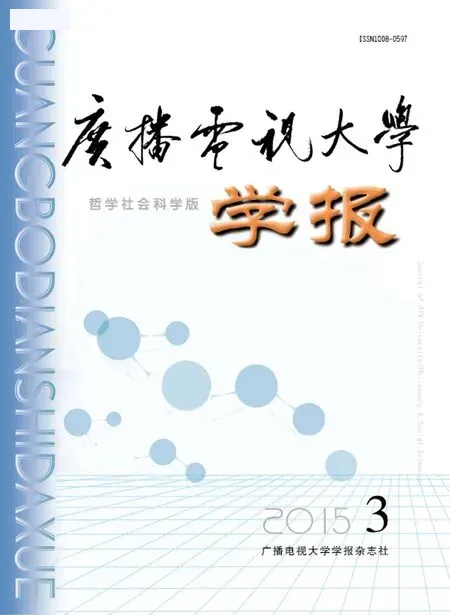唐代小说叙事的时间维度——以仙道小说为核心的考察
李春辉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时间是人类经验的最基本的一种范畴,时间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古代中国人就将时间和空间一同言说,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时空观,也即宇宙意识。《淮南子·齐俗训》就说:“往古来今曰宙,上下四方曰宇”,这里宇是上下四方,代表空间;宙就是往古来今,代表时间。《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将中国人对生命意识觉醒的感喟,对生命易逝,世事无常的悲悯或旷达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中华民族滚滚东去的历史江河之中。时间的本质意味着变化。生命来自于时间,时间的流逝使生命体衰老、消亡。在人类对时间的认识中,确立了自我的法度和文化的坐标,人类的历史就成为了时间的历史,时间成为人类舞台的主角,支配着自然宇宙和我们的价值观念。[1]“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2]唐代小说在我国的叙事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阶段。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唐代小说高度艺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小说作者对叙事的时间维度的自觉关注,而仙道小说神异玄幻的特异时空,其叙事的时间维度更有着奇异神秘的色彩,文章以时间的维度考查唐代仙道小说的独特意蕴。
一、六朝至唐以来仙道小说中时间流逝节拍的非等速性呈现及其意蕴
在六朝以来仙乡故事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常常在仙乡的半日或数日,通常就是人间的几十年或几百年。仙乡时间经过的速度不同于人间,仙人之所以不死是能够摆脱凡人世间的时间控制而超脱于衰老和死亡的威胁,因此仙乡成为人们憧憬和向往的乐土和无限的自由世界。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王质烂柯的故事: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4]P606
王质所遇童子当属仙人之流,王质在山中经历时间只是一局棋之间,而“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说明其已经历了一段非常久远的岁月,仙境刹那就是人间数世。
《幽明录》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中,刘阮“汉明帝永平五年”迷路误入仙乡,回到人间已经是“晋太元八年”,期间经历三百多年。人间已几度沧桑,而仙乡中的刘阮只是滞留半年而已。“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4]P486
现实世界深深的孤独和不能回到仙乡的惆怅与失望耐人寻味。故事以人仙时速的反差,折射出魏晋六朝中人们在朝不保夕、篡乱相继的乱世中的希冀和迷惘。
唐代小说中,仙界的时间意义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张荐《灵怪集》中的《郭翰》(《太平广记》卷六十八)[5](第二册P420)说太原郭翰,一天于盛暑乘月卧庭中。一少女自空中冉冉而下。自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之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随着叙事时间的推移,寂寞的欲求已转变为情爱的升华。“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织女的数日不来,对郭翰无疑是如隔三秋的痛苦煎熬,这里以故事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反差,显示出郭翰已经深深依恋并爱上了织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郭翰的盘问写出他少许的责怪和怀疑,是热恋中男子的口吻,织女的回答则打消了他的疑团,(郭翰)“问曰:‘卿来何迟?’(织女)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织女的回答体现了仙界的神秘和仙凡的时差,合理性的回答了“来迟”的缘由。
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 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5](第二册P420)
故事最终也还是以悲剧结局收场,郭翰在和织女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力——即所谓的“帝命有程”的干扰下,不得不永诀的最后一夕,写的是那样凄怆悲凉,人间真爱的短暂时光令人惋惜。离别后,二人赠诗互问,写出了精神之恋。“自此而绝。”是故事叙事时间的终结。但又补叙了“时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突出小说的神异色彩;“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则写郭翰难忘旧情,虽对织女的思念,甚至影响到日后婚姻的和睦,实际是故事叙事时间的某种延续。
这个故事中透露出的信息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织女说“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天上时速和人间时速是一比五的关系,虽有速差,但较王质、刘阮故事人仙时差已大大缩小;二是,织女形象虽蕴仙形,但大胆主动追求爱情,无疑曲折反映了唐代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两性关系相对开放的时代特色;三是,天上“佳期阻旷”,甚至“天上哪比人间?”看来神仙求取幸福,还得到人间来。正如钱钟书云:“六朝以来常写神仙‘思凡’,一若脱去人间,长生不老即成虚度岁月。”[6]因此,仙界的超越和自由的象征意义已大大的淡化,而人间的生活和世俗的幸福竟成为故事的核心价值,仙界的时间和人间的时间差异在缩小,其价值甚至发生了翻转,究其原因,由于唐代道教趋于世俗化,故唐代仙道小说中,描写人神人仙相恋的作品往往表现出道教肯定人欲的世俗意蕴和追求现实幸福的叙事倾向。
二、“谪世”“转世”模式:唐代小说叙事时间的丰富和人生情味的加强
《杨通幽》(《太平广记》卷二 O,出《仙传拾遗》)中,杨贵妃死后,玄宗思念不已,方士杨通幽为唐玄宗搜求贵妃精魂,遍寻天地终于在群仙所居的蓬莱之顶发现贵妃原来是上元女仙太真,自称“我太上侍女,隶于天宫,……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5](第一册P139)这就借助谪仙的模式将玄宗和贵妃的爱情故事赋予了前世夙缘的神秘色彩。《赵旭》(《太平广记》卷六五,《出通幽记》)[5](第一册P404下同)中,仙女降临天水赵旭家,自称:“吾天上青童,处居幽禁,幽怀阻旷,仙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幽居天宫的仙女青童渴望爱情生活,谪降人间。之后青童隔数夕复来,欢娱日洽。不意后岁余,赵旭奴仆盗琉璃珠鬻于市,被胡人识破送官逼问,奴仆就把秘密泄露了。其夜女至,怆然诀别。这个故事叙述婉转,描写细腻,情节丰富,颇有意趣,女仙之开放大胆,也颇有唐代风习,青童为赵旭带来美好爱情的同时,又同时带来仙肴美食、珍宝奇玩及帘帷器具一应设施等丰饶的物质享乐、甚至致以仙乐、传以长生之道予以精神慰藉,这无疑是贫穷士人长久匮乏之后所能想象的心理补偿了。《刘导》(《太平广记》卷三二六,《出穷怪录》)[5](第七册P3587)中,仙女西施、夷光不满“久旷深幽”的仙宫生活,结伴下凡,与儒生刘导、李士炯幽会。这两对仙凡情侣,还互相嘲谑,充满生活气息。体现出谪世小说在唐代世俗化增强,宗教性减弱的特点。
《崔少玄》(太平广记卷六十七)[5](第二册P414)“崔少玄,母梦神人而孕,生少玄。生时异香袭人,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十八年后,少玄果然嫁给了卢陲。陲小字自列。一次二人从武夷山经过,神人来迎,少玄对卢陲自述本为无欲天玉皇左侍书,号玉华君。“尝贬落,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这个故事与神仙谪降人世,从空中而来,又腾空而去有所不同,这里似乎揉合了佛教转世说,演变为上界仙人重新托生人世的模式。
唐代仙道小说中采用的“谪世”“转世”的结构模式,使其叙事具有了一定的时空自由,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受史传影响,唐代小说叙事时间上往往采取连贯叙述,叙事结构主要以情节为中心,而作为一种时间和叙事的艺术,为了将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和尽可能多的情节内容熔铸在有限的篇幅内,采用佛道“谪世”“转世”模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谪世”“转世”叙述的都是两世以上的生命历程,可以在叙事时间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并进而带来叙事空间的变化,叙事一旦超越了生死大限,人物的活动时空也随之扩展到上界、人世与幽冥三界。即便同是人世,其时空的自由度也变得相当大了。[7]
三、虚构和渲染:叙事中对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合理安排
厘清叙事与时间的关系,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小说批评重视对事件序列和因果关系的关注,叙事学则主要从“故事“和“话语”关系入手进行叙事和时间的研究。“故事时间指所述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话语时间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后者常用文本所用篇幅或阅读所用时间来衡量。”[8]借用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唐人小说的许多优秀篇章合理安排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突破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原始面貌。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9]P29直到唐代,小说艺术才真正进入自觉的艺术创作阶段。以唐李朝威《柳毅传》为例,小说写柳毅投书义救龙女的传奇故事。全文5000 多字,时间跨度为唐高宗仪凤年间(676年十一月—679年六月)至唐玄宗开元(713年十二月—741年十二月)末年后的几年,大约七十多年。故事曲折跌宕,主要人物形象如柳毅、龙女、钱塘君、洞庭君等都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细节刻画、场面渲染也令人印象深刻,体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而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作者对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合理安排。
小说详细地写了柳毅和龙女初次相遇的场景,故事时间应是很短的时间,只是邂逅相遇,请求传书的情节,文本时间却颇具长度。柳毅第一次见到龙女在路边牧羊,愁眉苦脸,衣衫破旧。当柳毅问她身世时,自称是洞庭龙君小女,父母配嫁泾川龙君次子。受到丈夫虐待又得罪舅姑,被贬牧羊。因得知柳毅要回吴地,请求柳毅代为传寄家书。柳毅听了龙女的身世,义愤填膺:“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10]P74毫不犹豫就承担起投书的重任,柳毅在答应帮她传书之后半开玩笑地说:“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龙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10]P75笔墨花费颇多,但生动地描写了龙女所处的困境和苦难,表现了柳毅对龙女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身上那种急公好义、勇于承当的义士性格,同时也不露痕迹的写出了龙女和柳毅彼此的好感。
柳毅在龙宫水府的故事,小说共写了洞庭君与柳毅的四次会面场景,均比较详细,故事时间只是在几天里发生的,而文本时间却占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究其原因在于这四次会面都是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甚至有的会面是在宴会的酣饮和乐舞中将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推上高潮。
如,第一次见于灵虚殿,通过柳毅的视角展示了龙宫的豪奢、神秘和奇异,又通过柳毅的视角写出洞庭君家人及宫中得知龙女受辱消息的悲痛,以及钱塘君出场的惊心动魄:“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10]P76表现了他的性格暴烈、嫉恶如仇。洞庭君和钱塘君的问答:
“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10]P77
对话简洁,节奏急促,而钱塘君的形象已然跃跃纸上。因此,这次会面对于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向高潮的一步步推动都起到很大作用。文中所用时间词,如“俄”“须臾”“俄而”“有顷”“是夕”,使故事叙事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畅达和张力。故事时间虽然时长不超过一日,但文本时间却1500 多字,接近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
后三次的会面都以宴会的形式出现。“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从时间跨度来说,这只是三天里发生事情,却占了全文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宴会中,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席间钱塘君提亲、柳毅拒婚、洞庭君夫人饯行等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一一展开,通过矛盾冲突,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柳毅当初路见不平担负传书重任,本无私心,这时更不会迫于钱塘君的威逼,因此坚决拒婚。但当龙女到宴会与他拜谢话别,他又表现出他侠骨柔情的另一面,就在读者为这一对年轻人失之交臂的美好姻缘惆怅惋惜的同时,也为日后柳毅和龙女终成眷属的情节突转埋下伏笔。此外,钱塘君性格的复杂性也表现得颇有特点,在柳毅大义凛然的一番说辞面前,他虽粗暴刚强但又知错能改,表面蛮横实则讲理,对不畏强暴具有君子之风的柳毅由衷敬佩,最终和柳毅还结为知心好友。这就使得钱塘君的人物形象趋于丰满,成为中国文学画廊里非常独特的一个典型形象。
离开龙宫后的叙事时间安排也颇具匠心。故事时间虽则虚实相生,但两次姻缘的较长时段,却只是一笔带过,叙事相当简洁,文本时间远远小于故事时间。柳毅继而续娶了龙女幻化的卢氏女。居月余,柳毅觉得妻子很像龙女,试图询问旧事,但妻子却予以否认,直到一年多龙女才对柳毅道破实情。又通过龙女之口补叙了她被柳毅救后一心求报,在被拒婚后,又坚决拒绝父母包办的配嫁“濯锦小儿某”的婚事,一直等到柳毅先后娶妻张、韩二氏去世,才终于幻化为卢氏女得以终成眷属。这段叙事极其曲折,表层的故事时间(龙女的对话)的展示,大约等同于文本时间,但深层的故事时间却跨度很大,叙述了龙女在和柳毅分别后的很长时段的经历,并通过她的讲述将柳毅的两次婚姻和龙女的坚守誓言这两条线索交融起来。最后通过二人对话,龙女对柳毅一述衷肠,并将叙述转回到传书之时,“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与前文叙事时间遥相呼应,又向柳毅询问拒婚之事。作为女子,龙女对柳毅既有报恩的一面,更有着因钦慕其高尚人品而产生的真挚热烈的爱情,柳毅对她的态度是她此刻最为关心的。毅曰:“……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壻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10]P81这一段话确实把柳毅的内心真实的表达出来了。而深层的故事时间又遥遥呼应之前的拒婚、宴别的情节。叙事的摇曳多姿,曲折委婉,形成了正如宋洪迈《容斋随笔附录》所言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9]P13的独特艺术魅力。
[7]孙 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84.
[8]申 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和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2.
[9]程国赋编.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徐 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5.
[2]杨 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0
[3]鲁 迅.鲁迅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8.
[4]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