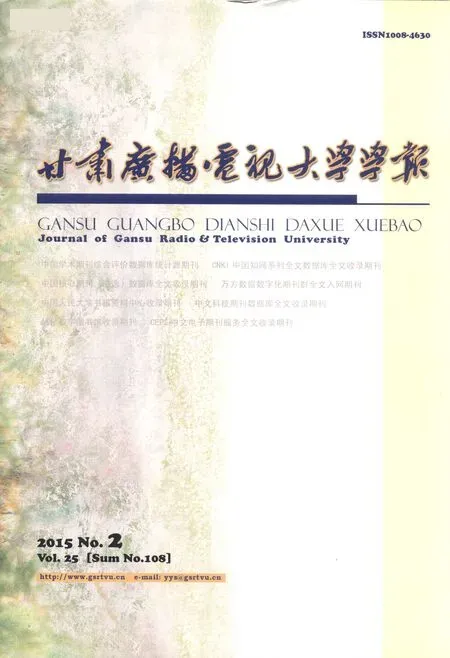论明季小说中节烈妇女形象的社会影响
汪垠涛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论明季小说中节烈妇女形象的社会影响
汪垠涛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古代对于妇女在伦理行为方面有着完整严备的礼教规范,这种规范的落实得力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控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而,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女教”宣扬上的影响与作用未被前人足够重视。明季小说中大量采引节妇烈女故事,加之小说“教化为先”的创作传统,在明季盛行的小说一体亦足以成为除朝廷官方而外的更为普及、流传深广的“女教读物”。
[关键词]妇女;礼教;节烈;女教
我国古代对于妇女的伦理规范和行为约束,有着十分严整完备的礼教规范。在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尚死节、崇节烈”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妇女在遭遇事变之时所作出的抉择,是礼教规范下的必然。关于贞节烈妇现象的研究,前人已多有成果,大多以史书、方志为主,围绕“贞节观念”、“节烈旌表制度”、“区域节烈妇女行为”而展开。对于女子贞节观念教育研究的,有丛凤霞的《封建社会妇女礼教文献述评》,对历朝历代各时期的女教材料进行了概览式的梳理。费丝言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洁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则肯定了节烈故事的文本记载在社会上的流传,加快着社会意识中“典范”到“规范”的转换[1]。细考这些已有的研究,他们对女教读物中节烈故事的记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注意,然而对小说塑造的贞节烈妇形象的社会教化影响或多或少有所忽略。所以,对小说文本的节烈妇女形象的整理和分析,或可以为古代贞节妇女现象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一、小说中多有节烈妇女故事的记载
小说家收集闾闻逸事以合著书之需,其创作小说亦多符合市民情感需求,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即今《喻世明言》),绿天馆主人题序说:“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2]646市井小民中多有阅读群体的存在,贾人适才愿意甘冒风险出此一书,而小说内容亦多为“可以嘉惠里耳者”,其中亦不乏“节妇烈女”等故事,笔者试援引几例如下。
《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记载郑义娘之事,其与夫因乱分离,“为虏所掠”[2]369,而后“誓不受辱”[2]371,乃“自刎而死”[2]3712。其夫韩思厚乱离后另娶,郑义娘便还魂索命。虽然小说有虚构的成分,但文末“叹古今负义人皆如此,乃传之于人”[2]380之意甚明,义娘贞节守志,而韩思厚却负义另娶,终被义娘“拽入波心而死”[2]380,可谓该有所报,其教化之意传之里耳,岂能无有反思?
《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亦是讲节妇的。宋金是个落魄之人,被刘有才兼济,后被招赘,与刘宜春夫妻恩爱,后因病被刘有才嫌弃,骗入荒山。刘宜春得知后乃申明其志:“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岂可翻悔?”[3]331后多番寻觅而不见,已有了寻死之心,幸被刘妈拦住。后三年间,无不“朝哭五更,夜哭黄昏”[3]332,披麻戴孝,以祭亡夫。宋金后因奇缘发迹,返回旧地,与刘宜春相认,夫妇得以再续前缘。作者于文末称赞刘宜春之守节:“闺中节烈古今传,船女何曹阅简编?誓死不移金石志,《柏舟》端不愧前贤。”[3]333刘宜春守节而终得丈夫还来相聚,无不令读者嘘唏,此一回小说是劝世间女子守节、从一而终,而终得好报的。
《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入话讲烈妇陈氏。陈氏十四岁嫁人,其夫年小不知房事之乐,其母马氏“却是好风月淫澜之人”[4]664,偷奸在前,后撺掇陈氏,陈氏坚决守志,誓死不从,后孤立无援,只得自缢身亡。此事奏之朝廷,被表为“烈妇”。然后“有许多好事儒生,为文的为文,作传的作传”[4]666,使这等烈妇事迹得以在世间流传,背后的目的无非为搜奇猎异、新人耳目,从另一方面讲,亦有为此等形迹拍手叫好之意,著之成文,从而广人耳目,教化乡里。
诸如此类的通俗小说篇目不胜枚举,据笔者粗略统计,晚明“三言”“二拍”中节烈妇女形象不在少数,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张如春、《蔡瑞虹忍辱复仇》中的蔡瑞虹、《独孤生归途闹梦》中的白娟娟、《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赵京娘、《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单小姐与林潮音、《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中的俞氏、《陈御使巧勘金超钗钿》中的顾阿秀、《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等……
不独白话通俗小说,文人笔记小说亦有不少义夫节妇的故事记载。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三《琼奴传》讲琼奴受聘徐家后,老父病亡,徐家戍边辽海,琼奴仍不愿改适富家,更有“将俟夜引决”之念[5]27,后徐家公子被查已死,琼奴“哭送,自沉于冢侧池中”[5]27,礼部施其冢曰“贤义妇之墓”[5]27。琼奴形象,可谓为一代标准贞节烈妇形象。这部小说集子刊行之后,“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为谈资”[6]。卷四集子刊行于世,被广泛抄读,虽事涵多种,然贞节妇女故事亦在其列。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有《虾摸传》载史某之友,图史某之妻而设计害死史某,并骗史妻改嫁。其妻忠于史某,当得知后夫之图,状诉其夫,后得上高赏。这是出自明初文人笔下的烈妇形象,作者“扬其善”[7],而作此一回文章。西湖渔隐主人因其事另撰《陈之美巧计骗多娇》,情由相仿,只是情节敷衍稍有变化。文中“犹氏”当得知后夫行径后,竟“呈之公庭,必令偿前夫之命”[8]94,以报结发之恩。后夫家财万金,犹氏丝毫不取,空身回到前夫家,时人“皆服其高义”[8]95。
从这些概略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文人争相采引节烈妇女的故事,并乐于为其作传使其远传,创作目的不管是“扬善”、“服其高义”还是“好事而作传”,必须承认的是,一旦使节烈故事付诸文本,小说商品的社会流通即会使其遍诸社会,其远比故事本身的“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要便捷广泛很多。由此延伸,在明季流传的小说集中所有关于“节烈妇女”等故事在传播与被阅读的同时,集体性的创作机制与传播效应会加速这些故事在生活中的渗透。它们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小说中的节妇烈女故事充当女教材料的可能
小说家竞相采引节烈妇女一脉故事,总是为了有裨风化,大致亦基本以宣扬女子从一、妇人守节为主旨。这也是除统治者官方手段之外的宣扬女教规范的重要途径,何以见得呢?
统治者虽然不遗余力采取官方途径对女子进行礼教规范教育,但也并不否认小说的教化作用。在明朝文网高压之下,统治者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不遗余力的毁禁,并多次颁布禁令,详考这些禁毁法令的文本,可以发现其对“裨益于风化”的作品仍然有所宽赦。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之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9]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孝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架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私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10]。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出现了小说创作的萧条期。尽管如此,对于表彰“义夫节妇”之属的作品,朝廷是十分支持和鼓励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期内出现的都是“带有浓重的说教色彩或粉饰太平的意味”[11]的作品。表彰“义夫节妇”的小说,则渐有增多,如《刘盼春守志香囊怨》、《李妙清花里悟真如》,创作目的则主要是表彰主人公的“守志”、“贞节”行为。
可以想见这部分作品中关于“义夫节妇”故事的存在,目的则在于表彰和宣扬,实际上已成为统治者宣扬道统、树立女子规范的大众手段。
三、明季小说在社会中的教化意义
自唐传奇始,“谈祸福以寓惩劝”[12]已成为不少作品的创作目的,如《莺莺传》即以“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13]卷四百八十八402为其要旨。古来文人皆认为小说一道为文学之末流,于是小说家总要借“教化”、“惩戒”之意来提升小说的文学地位,“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14]。所以,在明季小说盛行之时,任何题材故事的演义,则必于世教风化有所裨益。
明代李昌祺认为前人所著《剪灯新话》“惜其措词美而风教少关”[15]609,继而“搜古今神异之事,人伦节义之实,著为诗文,纂集成集,名曰《剪灯余话》”[15]609。由“风教少关”到躬身执笔搜“人伦节义之实”以成新著,不难看出明人在创作动机方面更多倾向于“裨益风教”之念了。“有关风化,而足为世劝者”[16]607则基本成为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理念了。
这种理念的产生,除了小说发展方面的原因外,也有统治者方面的政策引导。朱元璋即位以后十分强调“教化为先”,更提出了“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堕于小人”[17]。统治者的号召,无疑是使文学创作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于是,小说“教化为先”的传统便深深扎根在了小说家的心里。
统治者为了确立女子道德与行为上的人伦规范,不得不注重礼教文献的宣扬,散布女教读物,并对符合标准节烈妇女对象加以旌表,亦或者“借助宗教力量强化节烈意识”[18]。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9],在这一系列的官方举措下,明代倡导“贞节”之风达到鼎盛。
在另一方面,小说演至明代,更为有明一代之文体,小说家们根据所处的时代,择取相应的真实人物和事况加工于小说内,为统治者的宣扬说教添补节烈妇女的个案实例。在“非含有教化,便不足道”[20]的小说创作与“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21]的小说传播中,这部分节烈妇女形象的塑造和存在,从更重要的方面来讲,则成为了除朝廷官方而外的更为流传深广的关于女子教育的“教化读物”。
陈良谟在《见闻纪训引》中说:“如《孔》、《孟》小学之书,里巷小生虽尝授读,率皆口耳占毕,卒无以警动其心,而俚俗常谈一入于耳,辄终身不忘。何则?无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22]通俗小说比《孔》、《孟》等书更易“警动人心”,直接地肯定了小说在传播的过程中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小说家大量采引“节烈妇女”故事,对于民间节烈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价值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洁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327.
[2]冯梦龙.古今小说[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冯梦龙.警世通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5]程毅中,薛洪绩.古体小说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1.
[7]陆容.菽园杂记[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93.
[8]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9]董含.三冈识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4.
[10]陆粲.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347.
[1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28.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13]元稹.莺莺传[M]//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1.
[14]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461.
[15]张光启.剪灯余话序[M]//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6]罗汝敬.剪灯余话序[M]//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07.
[17]夏燮.明通鉴: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6.
[18]赵秀丽.“礼”与“情”:明代女性在困厄之际的抉择[J].湖北:华中师范科技大学,2008:31.
[19]李东阳.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346.
[20]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205.
[21]丁日昌.抚吴公犊[M]//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417.
[22]陈良谟.见闻纪训[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51.
[责任编辑张亚君]
作者简介:汪垠涛(1990-),男,四川剑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收稿日期:2015-01-12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5)02-00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