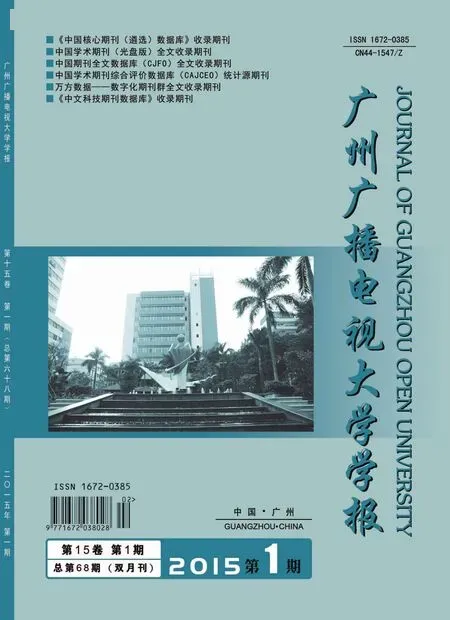桓谭奏议论略
王 征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桓谭奏议论略
王 征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任光武帝议郎、给事中等职,其今存《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两篇奏议,为东汉前期奏议之名篇,其文一反西汉后期的纡徐阐缓、典雅凝滞之流俗,为文锋芒毕露、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又能做到朴质简洁。表现了桓谭刚毅謇谔之性格。
桓谭;奏议;文风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人,两汉之际著名学者。《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1]《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又说其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2]其作品有《新论》29篇,《琴道》一篇,书、诔、赋、奏等26篇。《新论》已佚,清人严可均辑校成卷,这部著作是历来学者的研究重点。其奏议鲜有人论及,笔者遍检中外文献,至今只有日人大久保隆郎《桓谭の上奏文について ——〈陈时政疏〉考》①一文专论桓谭的《陈时政疏》。本文拟结合桓谭思想与其时社会文化背景,对桓谭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做较为深入的论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后汉书》本传说,桓谭 “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3]由此可见,桓谭是一位落拓不羁、不修威仪之士。其刚毅謇谔之性格,特立独行之思想为其奏议平添了一种尚情任气之风格。
刘勰《文心雕龙•奏启》说:“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后汉群贤,嘉言罔伏。”[4]“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是说后汉好的奏章不断出现。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桓谭奏议今存4篇,《上便宜》和《陈便宜》为残篇,《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保存完好。桓谭奏议虽然今存不多,但《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遇事便发,慷慨激昂,实属刘氏所谓之“嘉言”,足以使其名列“后汉群贤”之属。
先来看《陈时政疏》。该奏议是桓谭任议郎、给事中之职时所作。首先向朝廷提出要任用贤臣:
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②
桓谭认为国家的废与兴由政事决定,而政事的得失则在于贤者。辅佐贤明,人才就会充满朝廷,所做的事就会符合现实的需要。若是辅佐有失,政策就会变得不切实际。若是一个国家的君主有意“兴化建善”,而仍然治理不好国家,那就在于所用人才不同的缘故。意在建议贤明的君主若想治理好国家,必须任用贤才。这种观点在他的《新论》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云:
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王公大人则嘉得良师明辅,品庶凡民则乐畜仁贤哲士,皆国之柱栋,而人之羽翼。
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呂之见用,傳说通梦,管、鮑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
在这里桓谭把“大才”比喻为主之股肱羽翮,国之柱栋,人之羽翼,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接着,桓谭愤然指出:“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其慷慨不平之气逼人面目。
《陈时政疏》还提出“善政”之说:“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查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新论》也有关于善政之言论:“昔大戊遭桑谷生朝之怪,获中宗之号。武丁有雉升鼎之异,身享百年之寿。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而获反风岁熟之报。宋景公有萤惑守心之忧,星为徙三舍。”桓谭认为认为修德善政、省职慎行可以改变怪异,使祸转为福。正所谓:“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
随着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文士们的自主性越来越少,桓谭在此篇奏议中,从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该篇奏疏还对当时重商抑农的现象予以批判并提出具体的对策: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桓谭认为富商大贾不耕而食,会造成“通侈靡”、“淫耳目”的不良后果,从而提出让他们“归功田亩”的策略。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这样去做,就会损害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光武帝也曾经做过商贾,奏疏中对富商大贾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之,因而引起他的不满。《后汉书•桓谭传》载“(《陈时政疏》)书奏,不省。”[5]袁宏《后汉纪》曰:“桓谭以疏贱之质,屡干人主之情,不亦难乎!尝试言之,夫天下之所难,难于干人主之心。”[6]桓谭之所以不讨汉光武帝的喜欢,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后汉书》本传说:“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7]这里上书谈及何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失旨”一词可以看出,桓谭的这一次上书没有得到光武帝的认可。到上《陈时政疏》时,“书奏,不省”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再来看《抑谶重赏疏》。《后汉书》本传记载了桓谭上本奏议的原因:“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8]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也说光武登基之后,“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行事”,“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9]光武帝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包括桓谭在内的众多士人的不满。
建武时期的谶纬之学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10]自西汉末年以来,谶纬开始盛行。“谶纬在哀平之世泛滥,和当时社会阶级及政治矛盾极端尖锐,有密切的关系。……谶纬成为各种势力达到自己卑鄙目的的工具。”[11]在乱世中产生的谶纬之学,自然会被当权者利用。“谶纬是乱世的产物,它的直接简易与神秘性质,都易于被统治者或阴谋家拿来作为鼓动民众的工具。”[12]从一开始,谶纬学说就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统治者用谶语来预示政治上的事情或欺骗民众。谶纬之学和政治生活联系极为紧密,其时人们借谶纬语言表现其政治野心的情况在在皆是。西汉末,元始五年十二月,“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也。”[13]刘秀登基也是借助谶纬学说。当刘秀思考成熟,将要登基之时,其在长安时的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4]登基之时,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15]直至中元元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16]将谶纬之学作为了国宪。
对此,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趋之若鹜,但还是有不少智明之士避而远之,起而攻之。《后汉书•方术传》曰:“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17]特别是桓谭,《后汉书》本传载“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18]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不只是桓谭、尹敏不满于光武信谶,还有不少智明之士也认识到了谶纬的虚妄。《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载:“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大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19]《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东汉大儒郑兴反谶之事:“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20]有关谶纬思想的争论一直在最高统治者和士人们之间进行。
《抑谶重赏疏》首先对上一次上书(即《陈时政疏》)没有得到皇帝的诏报而深感不满:“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对最高统治者作如此态度,其胆识如此,令人敬畏。文中对谶纬之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又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
桓谭《新论》中也有许多关于非议谶纬的言论:“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当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用楚灵王等人的故事来说明卜筮維寡,祭祀用稀。讥刺用谶之非,反对迷信。
《抑谶重赏疏》接着又对皇帝提出建议:
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致,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
在急促的言语之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质直不忌、不尚用典,对偶及排比句式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感情气势。桓谭生不逢时,在谶纬之学盛行之时,他逆时而动,死于外贬途中。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表明了桓谭的正直与无畏。这种正气充弥于他的大多数文章中。曹丕说“文以气为主”[21];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22]桓谭的奏议在说理、议论中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丰沛的行文之气势。
汉代士人大多都具有立功意识、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直面现实,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桓谭的这两篇奏议都表现出其深沉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表现了桓谭忠君与爱国的思想。刘向说:“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23]桓谭身为谏官,心系国家,不顾自身之安危,直言谏诤,明知光武帝信谶纬之学,还要强言进谏,非议谶纬之害,体现了其令人敬服的胆识和勇气。
桓谭的奏疏在东汉初年是有代表性的。其文一反西汉后期的纡徐阐缓、典雅凝滞之流俗,即刘熙载所谓“汉文本色”。如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三篇首开其端,刘向的上元帝《封事》、《论起昌陵疏》等疏奏继踵其后,在援引经文、大谈灾异方面又超出前者,匡衡的《论治性正家疏》、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疏》都沿袭了这一文风。桓谭为文锋芒毕露、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又能做到朴质简洁,显示了两汉之际乱世之文风。
注释:
①大久保隆郎.《桓谭の上奏文について ——〈陈时政
疏〉考》《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第22号,1970年11月。《中国关系论说资料》(哲学宗教),第12号,1970年。
②本文所引桓谭文章均出自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3][5][7][8][14][15][16][17][18][19][2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904,1230,955-956,959,21,22,84,2705,961,773,1223.
[4][22]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15,376.
[6]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65.
[9]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88.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47.
[1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62.
[12]周桂钿,李祥俊.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0.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078-4079.
[2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8.
[23]刘向撰.向宗鲁校正.说苑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206.
I206.2
A
1672-0385(2015)01-0057-03
2014-10-28
王征,男,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以王嘉《拾遗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