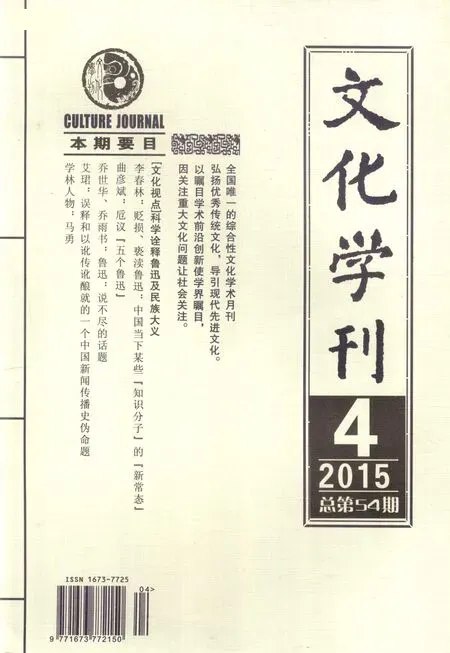鲁迅:说不尽的话题
乔世华 乔雨书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鲁迅:说不尽的话题
乔世华 乔雨书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鲁迅生前身后曾遭遇过许多无端的流言,这些恰恰能够反衬出鲁迅的伟岸身躯和无穷魅力。而有关鲁迅的种种争议最好不过地反映着世情的变化、时代的病症。从对鲁迅的各种挑战、否定以及媒体热炒的“鲁迅作品大撤退”等事实来看,鲁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需要我们认真地阅读,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还有待我们慢慢消化。鲁迅注定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鲁迅;工具;利用;话题
有句老话:“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人人都有思想与说话的权利,任何一个人也都可能会成为身边人评说的对象,至于公众人物被瞩目的万众议论个短长更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只要所说有事实有根据,不捕风捉影,不恶语中伤,则尽可以畅所欲言,果如是,则对激活人的思想、激发人对核心话题的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以更好地走向真理大有益处。只是现实往往并不能如有良知的人们所愿,“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1]鲁迅这番对自身所处文坛的评议,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仍不过时。就拿鲁迅来说,其在世时遭遇的各种流言蜚语可谓多矣,诸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著作、鲁迅是拿苏联政府卢布的“XX党”了、愿意做汉奸而充当日本特务的探伙头子、鲁迅偷看弟媳妇洗澡了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所以,鲁迅自己就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2]
至于鲁迅身后,就更是持续不断地遭遇着各种流言的困扰和毁谤。尤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有人继续添油加醋炒从前各种流言的“剩饭”外,还有人凭借着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肆意放飞想象的翅膀、别有用心地臆测和挖掘着鲁迅的绯闻:鲁迅有自渎、嫖妓等不堪行为,他和弟弟周作人之间存在着同性恋的关系,鲁迅与刘和珍、萧红之间的情感暧昧难明;鲁迅日记中不是有“寄羽太家信”一类的话吗?有人据此就言之凿凿地断定鲁迅和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是夫妇;鲁迅日记中有一句“夜为害马(指许广平——笔者注)剪去鬃毛”,有人便生发无限联想而“萌萌哒”发出疑问:“她(指许广平——笔者注)那晚留宿了吗?”这不由让人想起 80余年前鲁迅在忆念一位亡友时曾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3]的确,在生前,当遭遇到一切诬蔑中伤,你总有办法尽己所能用事实和行动给予对手以强有力的反击驳斥,但是到了身后,再遭遇到任何攻击或者被谬托知己者堂而皇之地利用,逝者都不可能起而回应了。这正是有着深刻洞察力的鲁迅早就清醒看到并感觉到无可奈何的事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许正是有了疾风劲雪无情而冷酷的摧残,才愈益显出“秀于林”的“木”的苍劲挺拔与不惧风霜。上述种种从私生活方面向鲁迅身上所泼的脏水,早就有知情者、明理者及时站出来道明了真相,还鲁迅以清白之身。而各种对鲁迅的诬蔑中伤,愈加能反衬出这位中国文化巨人的伟岸身躯与无穷魅力。鲁迅曾预言般地说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4]那些发见鲁迅身上“缺点和伤痕”的“完美的苍蝇”就仿佛《祝福》中鲁镇上那些无聊看客们一样——他们在厌倦了阿毛的故事之后又为发现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而沾沾自喜,“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除了能显示出“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5]之外,还将自身的肤浅无知、渺小低级暴露无遗。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迄于今天的这一波波在私生活方面肆意玷辱诋毁鲁迅的言论,正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文化病症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理想精神滑落,精英意识受挫,滑稽、调侃、浅薄、卑劣当道,肉麻、小丑、情色、物欲盛行,崇高遭颠覆,尊贵被消解,本该严肃认真而客观的学术研究也都沾染上了浓浓的市侩气息,低俗庸俗而又媚俗。一切正应了《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作者所说:“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6]
其实,一直以来围绕着鲁迅所发生的种种论争,就都是一张再灵验不过的人心和人性的试纸、社会与时代的晴雨表。仅以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出出进进”及主题思想解读来说,就都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中苏关系友好之时,《鸭的喜剧》《我们不再受骗了》等篇目获得入选且其对中苏之间友谊的见证、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揭示的主题得到强调;要痛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痛打“落水狗”的主张正当其时;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了,《文学和出汗》就是明证;需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铸剑》就有对“中国的脊梁”的肯定、有对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张扬;声讨美帝国主义罪行了,《“友邦惊诧”论》就有这样的笔墨;讲求阶级划分了,祥林嫂的婆婆、大伯、柳妈就都是来自地主阶级阵营……鲁迅及其作品在伴随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之时,也很容易在这种简单、粗暴、随意、功利化的运用和解读的无形当中变形成为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某种反感。更何况到了“文化大革命”,鲁迅被塑造成了反传统的标兵,其造反精神得到了“纪念”和尊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广大工农兵和英雄的红卫兵战士,正在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全世界革命人民”被认为“才是最有资格来纪念鲁迅的”,鲁迅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更被政治性地曲意阐释为“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7];当周扬一班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者被打倒时,他们过去与鲁迅之间所发生的龃龉是罪证:“他们攻击鲁迅,是为了攻击毛泽东思想,发泄他们对毛主席的仇恨!”[8]而“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流毒影响时,“美化周扬一伙,肆意诬蔑和攻击鲁迅,歪曲和篡改鲁迅著作”[9]是其累累罪行,“四人帮”“一贯十分仇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干了大量反对鲁迅的罪恶勾当,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10];鲁迅早年对“四人帮”成员姚文元的批评又被认为是其先知先觉之处。也就是说,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局变幻中,鲁迅总是能被“革命”的一方拿来指摘“反革命”的一方,人们总是能根据需要而断章取义地应用鲁迅言论、鲁迅事迹,鲁迅的无比正确恰好证明着“反革命”的倒行逆施。一句话,鲁迅是一根棍子——一根被用来打人且屡试不爽的棍子。
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杂文报》和《青海湖》上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何必言必称鲁迅》和《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就都能反映出来那个时代人们渴望重新认识鲁迅和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心理。前者不过是一篇七百多字的杂文,写作者提到自己在研究阅读一批写作指导方面的书籍时,发现“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从写作理论到举例,全是鲁迅,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由是感慨这些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书籍“大概是被‘鲁化’了吧”,觉得这些“鲁货”“搞得太多,实难令人欢迎”[11]。后者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一系列负面的看法,觉得“《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阿Q正传》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伤逝》是不成功的作品,毛病在于僵化”,《故事新编》“艺术价值不高”,杂文与翻译“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又一例证”等等。这两篇学理性并不强的文章远没有今天毁谤鲁迅者的那种刻毒劲,但在当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告别了过去“文革”文化专制的年代之后,两位写作者无疑是希望以鲁迅作为一个突破口,打破仍然流行的那种单调僵化的话语体系,并获取多元化的声音和气息,而重新认识曾被视作神灵般的“走在金光大道上”的鲁迅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就说得很明白:“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世界文学史,无疑会记载着鲁迅先生的名字,但是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将是一位作为人的艺术家,而不是一尊作为神的偶像。”[12]这两篇文章对鲁迅的臧否当然有矫枉过正之处,套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该属于对从前曲解鲁迅的“报复性反弹”吧?而这种“报复性反弹”在其后依然继续着,即如上个世纪末相继出现的“断裂”问卷和“悼词”事件。
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上刊登了一份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在被问及“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时,参与答卷的部分 60后(编注:1960年后)作家予以了否定性的回答,有的甚至明言“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13]……其实,这样一份调查及答卷本身的科学性、严肃性是很值得怀疑的。鲁迅之所以被单独刻意拿出来设计成问题,就表明制定这份“断裂”问卷的人颇为用心地在搞一次策划,而众多的参与答卷者以不假思索、只言片语的回答配合着问卷者完成了一次具有强烈叛逆色彩的“行为艺术”展或者说文学宣言书,他们希图借由对鲁迅的否定来达到对众多前代作家成就及影响的否定和“超越”。而稍后那份由有着强烈红卫兵思维特征的葛姓学者所撰写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就更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了。悼词的写作者在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责中,充当起了道德判官的角色,首先向鲁迅发难(这其实从反面证明了鲁迅在 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要求完人甚至神明的标准要求鲁迅且强词夺理:“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14]……看似咄咄逼人,实则信口雌黄、罔顾事实,完全摒弃了批评道德,在对鲁迅恶意的贬斥当中充分暴露出自己的浅薄粗鄙来。鲁迅早就说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15]鲁迅还说过:“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16]上述这几种针对鲁迅的“报复性反弹”一面显出挥棒者的不分青红皂白——本该深究打人者、利用者的责任,却将矛头指向了无辜的棍子,一面也是将鲁迅再度变成了棍子,在对他彻头彻尾的利用和问责中来达到否定传统、彰显自身地位和价值的目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鲁迅还成为一些挖空心思寻找热点话题的媒体们不断消费的对象,所谓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大撤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1年新课改方案出台、教材编写大权被放开,语文教材的编写从过去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尊而变为多家出版社数雄并峙的局面,既然各个出版社都可以编写中学语文教材,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语文课本可供各地方学校选择;自然而然,不同版本的教材不可能千篇一律,肯定都有自己的编选原则和特色;而且,这些教材的篇目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公之于众了,只是让人不明白的是媒体缘何当时对此视而不见,直到2006年开始,才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呼“《阿 Q正传》从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消失”;2007年、2008年又因为相继发现金庸《天龙八部》部分章节被选入“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雪山飞狐》出现在了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遂再度炒起“金庸PK鲁迅”“金庸要取代鲁迅”乃至“鲁迅被踢出中学语文教材”的话题;2009年又因为发现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选了“人教版”的语文教材,鲁迅作品由原来的5篇减少为3篇,又有“教材不再偏爱鲁迅”“鲁迅被梁实秋顶替”之议;到了2010年,“标题党”们看到“苏教版”中学语文课本删除了《雷雨》《孔雀东南飞》《阿 Q正传》等众多名篇,遂再度找到了兴奋点,大喊“中学语文教材大换血,鲁迅‘民族魂’的境遇值得关切”,什么“鲁迅成了教材改版的最大输家”,“鲁迅作品大撤退”了之类说法铺天盖地……照理来说,中学语文教材的修订、篇目的选择和调整都属于稀松平常的事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会有一代之教材和一代之选文的标准。若是以不变的教材来应对一代又一代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有着不同阅读期待的青年学生,其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教材篇目也应该允许有变化和尝试性的调整,像数年前“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风筝》被替换为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有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才能保证语文教材的鲜活性、时代感,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更何况,鲁迅等人的文章早在八九十年前能够走进学生语文课本中,也正是拜教材变革之赐。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由多到少、由具有浓烈战斗色彩的篇目到更具文学性人情味的篇目的变动也或多或少地显示着时代的讯息、展露着世情的变化和教材编选者的教育期待。新课改之前,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教材有 6册,使用时间为 6个学期,鲁迅作品有 5篇;现在的新课标教材已经变成了必修本 5册,需要在2个半学期学完,必修的课文总量自然需要大幅减少,减少到目前的六七十篇。以“人教版”5册必修教材论,全套5册共65篇课文,其中31篇是文言诗文,6篇是外国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达到 28篇,鲁迅作品就占据了 3篇,而其他诸多名家如巴金、曹禺、郁达夫、夏衍、朱自清、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余光中等都只有一篇(首)。如此看来,鲁迅作品被选录的情形并非如媒体反复叫嚣的那样“大撤退”,而是依然唱着重头戏。但习惯于吸引眼球的媒体偏偏对此视而不见,有意跳开中学语文必修教材篇目总量压缩的大背景,刻意凸显鲁迅作品“大撤退”的“事实”,更刻意将正常的篇目调整演化成鲁迅和金庸、梁实秋等人文学江湖上的“恩怨对决”,颇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了。
至于近些年来据说在中学校园中流传的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与其说它反映着中学生语文学习上对鲁迅文章的畏难情绪,倒莫如说其更真实地反映着当下部分没能真正读懂鲁迅、自然也不能很好地传播鲁迅作品和精神的中学语文教学者的畏难心态。诸多事实证明,当下的中学生并不像想象中、报道中那样对鲁迅作品望而生畏、唯恐避之不及,那只是不明就里者的想当然与生造出来的图景。当然,关于鲁迅的争论话题这些年还发生了很多,但举说这寥寥几例,就已经足够让人看到:其实,鲁迅一直以来都并没有很好地被国人读懂,更多人对他都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因为无知、或者是出于利用的心理才无畏地拿鲁迅来说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还需要我们认真地阅读和慢慢地消化,这也就注定了鲁迅必然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公众话题,鲁迅还要继续和我们、我们的后来者同行,他的作品、思想和精神本来就是说不尽的,自然也不会被遗忘,更是颠扑不破的。
[1]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A].鲁迅全集:第4卷 [C].北 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1981.452-453.
[2]鲁迅.并非闲话(三)[A].鲁迅全集:第 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1.
[3]鲁迅.忆韦素园君[A].鲁迅全集:第 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8.
[4]鲁迅.战士和苍蝇[A].鲁迅全集:第 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
[5]鲁迅.小杂感[A].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3.
[6]乔世华.追踪公共趣味的猎狗行径——读朱大可的鲁迅批评[J].粤海风,2001,(4).
[7]姚文元.纪念鲁迅,革命到底![N].人民日报,1966-11-01.
[8]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J].红旗,1966,(12).
[9]华迅.不许姚文元歪曲和诬蔑鲁迅[J].华中师院学报,1977,(1).
[10]黎舟.揭穿“四人帮”反对鲁迅的鬼蜮伎俩[J].福建师大学报,1977,(1-2).
[11]李不识.何必言必称鲁迅[N].杂文报,1985-08-06.
[12]邢孔荣.论鲁迅的创作生涯[J].青海湖,1985,(8).
[13]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J].北京文学,1998,(10).
[14]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J].芙蓉,1999,(6).
[15]鲁迅.“题未定”草[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2.
[16]鲁迅.“这也是生活”……[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03.
【责任编辑:董丽娟】
I210
A
1673-7725(2015)04-0029-06
2014-12-20
本文系2013年度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中小学生课外文学阅读研究”(项目编号:JG13CB004)的研究成果。
乔世华(1971-),男,辽宁大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