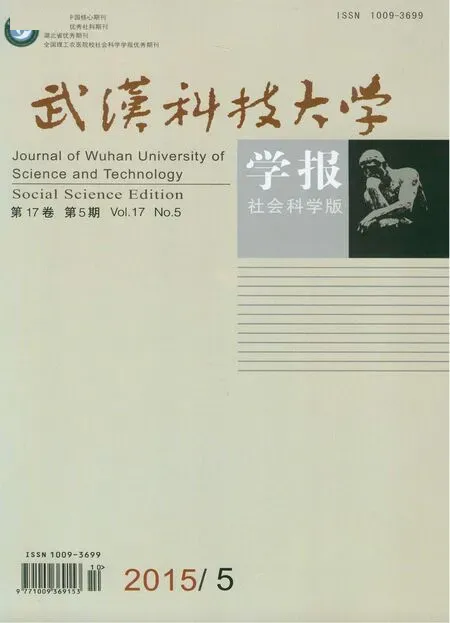概念证明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温兴琦 David Brown 黄起海
(1.武汉大学 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兰卡斯特大学 管理学院,英国 兰卡斯特 LA1 4YX)
概念证明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温兴琦1David Brown2黄起海2
(1.武汉大学 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兰卡斯特大学 管理学院,英国 兰卡斯特 LA1 4YX)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通过“死亡之谷”和“达尔文之海”对创新过程中研究成果产业化所遭遇的障碍和陷阱进行了阐述。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主管部门政策冲突、大学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配套服务滞后等瓶颈。美国研究型大学概念证明中心是一种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组织模式,文章分析了概念证明中心的产生背景、功能和运作模式,并阐述了其对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启示,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大学科研考评体系、完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和优化大学创业生态的建议。
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概念证明中心;创新;转化模式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使命,而科技成果转化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实现科技成果的顺利、高效转化,对于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经费获取、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扩大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能产生直接影响。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对科技成果转化给予了高度重视,纷纷出台具体方案和举措加以促进和实施。各地方政府也密集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如北京市出台了《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1],湖北省出台了《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2],等等,这些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已经或正在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现实影响。
美国是全球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发展的火车头,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模式,实现了科学研究与产业的对接,消除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使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证明中心模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技术转移模式,能对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创业绩效改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起到示范和借鉴作用。
一、创新的“死亡之谷”与“达尔文之海”
创新是一个由众多环节构成的连续过程,包含多种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各项创新活动及从事创新的各主体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前后呼应、密切联系的整体,呈“链条”形态,即“创新链条”[3]。从基础科学研究、研究成果转化直至产品商业化,这一创新链条必须要维持顺畅运转并无缝连接,创新活动才能取得理想成果,否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创新链条就会断裂,从而导致创新失败。
1.死亡之谷
“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是创新领域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源自美国国立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的一项研究,是指基础研究成果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沟谷。1998年,弗农·艾勒斯在研究中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并强调,基础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如果不能跨越这条沟谷,就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转化为生产力[4]。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都在转化过程中坠入了“死亡之谷”,而没能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商品。因此,对于“死亡之谷”的研究,一直是创新领域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研究的焦点。如Philip等通过对美国商务部先进技术项目运行的教训反思,提出了导致“死亡之谷”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了政府应该扮演的合理角色[5]。
“死亡之谷”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普遍存在,即便在科技成果转化相对较为成功的美国,其转化率仍然较低,有近75%的大学发明专利完全没有实现商业化。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在其2008年科技许可办公室收到的400项专利申请中,有200项专利获批,而最终实现商业化转化的仅有100项[4]。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死亡之谷”的影响就更加显著,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大学每年有1万项左右的科技成果通过鉴定,但其实现转化的比率仅为15%~20%[6]。
创新中的“死亡之谷”成为制约整个创新链和创新系统顺畅运转的天堑,因而也直接降低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有效衔接创新链条上的上下游环节,实现创新链良性运转,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大学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2. 达尔文之海
与“死亡之谷”类似,“达尔文之海”(Darwin Sea)是指创新过程中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后,在投入生产到大规模产业化之间出现的鸿沟,就像一片难以逾越的茫茫大海。在基础研究转化为现实的产品之后,整个创新活动并没有完成,因为从产品到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许多技术上具有先进性和可靠性的产品,往往在实现商品化和大规模生产时遇到障碍,使得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获得利润。这些障碍因素,既包括技术成果到产品的转化环境与现实市场环境的不一致,也包括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动态性,甚至与消费者的消费文化、消费心理及习惯有关。当前国内许多大学生创业失败的事实表明,“达尔文之海”的确存在,并阻碍着创新成果向商业化产品的进一步转化。
“死亡之谷”与“达尔文之海”尽管表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描述了在创新过程中研究成果产业化所遭遇的障碍和陷阱,表明创新活动面临着天生的困难与风险,难以通过创新主体自身的努力克服。这表明,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创新目标的完全实现,必须从外部施加影响,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也亟需这种外部作用力。
二、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大学是知识创造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源泉和主体,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及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集聚之地,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大学在实现基础科学研究中所取得成果的转化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较大困难,这导致了大学科研人员和经费投入的低效率,也弱化了大学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1.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界定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包括新知识、新产品或新流程的转化[7],这一转化过程是一个成果开发者与搜寻者之间交互的复杂过程,涉及内容广泛,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相关设施与装备,也包括知识与工艺[8]。Grimpe等将大学成果转化区分为正式转化与非正式转化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有关专利、特许权、版税转让的正式过程,后者则主要是产权位居次要地位的非正式交流与合作,比如联合发表学术成果、学术咨询、非正式交谈、大学与企业联合举行学术会议等[9]。学术界更多地将讨论重点集中于正式转化,但Siegel等人认为,两种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形式是互补的,在实践中都应得到重视[10]。
2.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内容与过程
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包含有各相关主体之间一系列知识交换活动。Mc Adam Maura等人认为,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几个基本环节是:技术创意形成—技术评估—获取风险投资—技术许可—联合企业[11]。这一观点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的内容与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来看,一般都包括发明创造—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市场研究—风险投资—技术许可等完整内容与过程。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对大学而言,从内部到外部的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频繁发生着许多关联活动,而且由于技术在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这些关联活动也充满着各种风险。这就对大学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识别与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网络
在Etzkowitz提出的三重螺旋模型中,他强调了政府、大学、企业建立互动合作创新网络,促进知识共享与转化网络的重要性[12]。只有这一网络得以建立和维系,大学科技成果才能顺利转化为有竞争优势的市场产品、工艺流程或服务。当然,正如Mc Adam Doug等人认为的一样,这一网络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成果转化早期,它能起到促进创意形成和知识创造的作用,而在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它的主要作用则在于评估科技成果的商业潜力及市场需求方面[13]。
4. 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瓶颈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转化率较低,究其原因,既有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不力、转化壁垒众多等因素,也有大学考评机制与大学发展定位的原因。当前,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瓶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我国大学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及地方政府所设立的纵向项目,因而,政府部门对经费分配、项目运作、费用开销控制等方面更加重视,缺乏对研究项目的目标及成果实用性的关注,而且一般纵向项目评审或验收的标准较为学术理论化,这导致大学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直接目标是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忽略了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据相关调查统计,我国现行大学科研活动基本决策依据中,只进行文献调查的项目所占比率达69%,进行前期市场调查的仅占34%。与此同时,有19.6%的大型企业和28%的中小企业认为,大学科研成果成熟度差、配套性能低,无法满足企业需求[14]。
(2)相关主管部门政策冲突。大学及其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行为,极大地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政策的约束和指引。其实,教育主管部门自身对于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积极的,在这方面我国教育部也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多个政策和文件,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的管理体制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还受到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党政部门的管辖,而且,在许多方面,各主管部门之间并未有效衔接,政出多门且互相冲突,使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处于夹缝之中,甚至寸步难行,严重拖累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例如,教育部和科技部鼓励大学科研人员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企业,而中组部则明确规定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创办企业,而我国大学中拥有高水平科研成果的科研人员,有许多是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专家教授。
(3)大学科研评价和激励指标不合理。当前我国大学基本都实行学术化评价指标体系,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聘)主要依据获得高水平项目数(且不关注项目完成情况)、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数、获得高级别奖项数等指标,而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益、服务社会贡献的价值等基本忽略不计,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大学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也斩断了科技创新链,导致科研成果普遍躺在实验室里的现象出现。
(4)配套服务严重滞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如项目对接、中试、融资、培训等。但当前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服务严重滞后,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现实需要,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配套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其供给职能由政府负责。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迅猛,一大批研究型大学开始朝着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努力迈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和绩效,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环节。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概念证明中心模式
美国是全球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其在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更体现在大学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方面。著名的硅谷,就是一个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高地,已成为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研发的重镇。在促进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美国政府部门多管齐下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其中,建立研究型大学概念证明中心,是较为独特而有效的措施之一。
1. 概念证明中心定义及产生背景
概念证明中心(POCC)产生于美国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在大学内部建立和运行并致力于促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机构,它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商业概念证明、知识产权保护、创业教育等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个性化支持,提升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和效果。一般认为,概念证明中心诞生于21世纪初,2001年和2002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建立了冯·李比希创业中心和德什潘德技术中心,成为概念证明中心的先驱。
概念证明中心的产生,源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创新知识溢出和科研成果转化所面临的困难局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Bayh-Dole法案的颁布,美国政府和公共部门对于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和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日益增加,许多大学都建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专门负责成果转化。然而,在实践中,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仍然面临一系列障碍,Shane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研发人员进行成果转化动力不足;②研发人员与投资者之间对于成果和市场信息不对称;③研发人员和企业具有不同的背景与期望;④研发人员与企业之间缺乏信任;⑤研究成果所瞄准的目标市场尚未形成;⑥成果转化面临的要求过于繁杂;⑦难以获得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⑧公共和私人部门提供的资金等方面支持不及时[15]。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大学普遍建立的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在运行中显现出效率低下和亏损的状态[16],一些部门和学者不断呼吁应建立新的机构,采用新的模式来从文化的角度着手,解决大学与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与冲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动力,提升转化绩效,于是概念证明中心应运而生。
2. 概念证明中心的功能
概念证明中心的功能主要包括:①为不能获得资金支持的大学早期研究成果提供资金支持;②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市场顾问与培训;③培育和促进创业文化;④进行创业教育。
Christine等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冯·李比希创业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德什潘德技术中心的运作模式及功能作用进行了对比(见表1)[17]。
从表1可以看出,两个中心都构建了一个为科研成果转化服务的资金支持、创业指导、信息联络的良好框架体系和机制,并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定制化的支持,以跨越成果转化初期的资金鸿沟。
从美国大学建立的新企业数量来看,在概念证明中心建立之后,新创企业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见表2)[17]。
3. 概念证明中心运行模式
作为大学内部设立的机构,概念证明中心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的领导下运行,通过加速已申请专利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从而对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与传统的科技“孵化器”相比,概念证明中心的运行模式有两个特征:①概念证明中心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研发,而科技“孵化器”进行的研发活动通常与大学是独立的;②概念证明中心必须对作为大学研究成果的产品的商业价值进行评估,科技“孵化器”则通常是为已有一个产品的新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分享工作环境。
截至2012年,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已建立起32个概念证明中心,它们的名称虽然不是全部冠以“概念证明中心”的称谓,但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以预测,随着科技经济融合需求日益旺盛,概念证明中心的数量将会不断增加。美国商务部在其发表的《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报告中指出,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地位上升最快的是概念证明中心,因为它们“提升校园创业的数量和多样性;改进校园内新公司和创业的质量;加强了与地方投资人和创业家之间的联系,以留住大学中成立的新型公司”[18]。概念证明中心也被美国总统奥巴马誉为“美国基础设施中极具潜力的要素之一”。
四、结论与启示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证明中心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有效的开放创新网络,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将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实现了大学科技与产业的有机衔接与协同发展,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大学研发成果与可市场化产品之间的鸿沟,是跨越研发活动与产品开发之间“死亡之谷”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探讨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新路径成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课题。结合前述关于美国大学概念证明中心的分析,推进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得到以下借鉴和启示:
1.改革和完善大学科研考评体系
改革现有以论文、专利、奖项为主体指标的大学考评体系,引入大学服务社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考评指标,鼓励大学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并愿意将科技成果转为现实产品,在政策导向上有利于大学科研人员从事实际转化活动,如创办企业、与企业合作等[19]。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学术理论与成果转化并重的大学考评体系,实行大学科研人员岗位分类管理和考评制度,鼓励科研人员的差异化发展,彻底打消大学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促使其更加主动、深入地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之中,真正激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2.完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体系
在全社会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上营造良好的氛围,诱导和帮助各相关领域和部门积极融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之中。深入推进科技金融改革,适度放开现行人事政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力度,降低科技创业门槛,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体系,真正实现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协同创新效应,提升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
3.构建和优化大学创业生态
促进大学现有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公室职能转变,提升其项目资金资助、市场信息、项目咨询、创业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功能,并通过个性化方案为各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提供成果转化服务。与此同时,加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部门与市场和企业的对接与交流,跟踪和捕捉市场动态,把握市场趋势,促进大学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强科研成果对市场的适应性。此外,积极推动大学主动融入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构建大学与外部机构的协同创新和创业网络,打造更为顺畅和强大的创新链条和创新网络。
4. 培育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介组织
中介组织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通过扫描和整合相关网络信息促进创新参与主体之间实现信息共享,而且通过网络挑选机制将创新系统中相近或互补的参与者聚焦到一起,促进网络中的技术转移,强化网络的合作文化和结构特征,完善网络运行规则。此外,一旦网络成员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中介机构则起到维护和促进这种合作关系发展并推动合作走向深化的作用。当前,我国技术中介和技术经纪刚刚兴起,但明显落后于创新发展实践的需求。由于大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约束,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应该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强化技术中介和经纪机构的培育和扶持,并通过立法和行业标准等进行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其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联结和促进作用。
总之,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必须加以重视和推进的重要方面,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各大学自身,都开始主动变革,积极求解。在具体实施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概念证明中心的运作模式,加快我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构建新型有效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已经具有现实可行性。当然,随着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这种借鉴也应不断变革和创新,并契合我国的创新情境。
[1]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EB/OL].[2015-05-10].http://zhengwu.beijing.gov.cn/gzdt/gggs/t1359078.htm
[2] 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EB/OL].[2015-05-10].http://www.hubei.gov.cn/2015change/2015sq/sa/zzql/201508/t20150817_704910.shtml
[3] 温兴琦,李燕萍.创新链条裂缝的表现、成因及接续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24):157-160.
[4] 赵中建,卓泽林.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美国路径[N].中国教育报,2015-04-15(11).
[5] Philip E Auerswald, Lewis M Branscomb.Valleys of death and darwinian seas: financing the invention to innovation tran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3,28(3/4):227.
[6] 康晓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J].中国高校科技,2014(8):82-83.
[7] 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 2000,29(2):109-123.
[8] Roupas P.Predictive modelling of dairy manufacturing processes[J].International Dairy Journal,2008,18(7):741-753.
[9] Christoph Grimpe,Heide Fier.Informal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0,35(6):637-650.
[10]Siegel D,Waldman D,Link A.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an exploratory study[J].Research Policy,2003,32(1):27-48.
[11]Mc Adam Maura,Marlow Susan.Sense and sensibility:the role of business incubator client advisers in assisting high-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to make sense of investment readiness status[J].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12,23(7-8):449-468.
[12]Etzkowitz H.Research groups as “quasi-firms”: the inven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Research Policy,2003,32(1): 109.
[13]Mc Adam Doug,W Richard Scott.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M]// Gerald F Davis, Doug Mc Adam, W Richard Scott,et al.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4-40.
[14]葛剑平.强化市场引领机制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EB/OL].[2015-05-16].http://cppcc.people.com.cn/n/2014/0305/c34955-24539096.html
[15]ShaneS.Sellinguniversitytechnology:patternsfrom MIT[J].Management Science,2002,48(1):122-138.
[16]Etzkowitz H.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action[M].London:Routledge,2008:45-47.
[17]Christine A Gulbranson,David B Audretsch.Proof of concept centers:accelerat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nnovation[J].Technol Transfer,2008,33(3):249-258.
[18]美国商务部.创建创新与创业型大学[EB/OL].[2015-05-16].http://eda.gov/pdf/The_Innovative_and_Entrepreneurial_University_Report.pdf
[19]温兴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困境与改革路径研究[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5(4):35-40.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5-05-27
湖北省软科学研究专项(编号:2012GDA01503);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编号:2014A001).
温兴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企业环境、产学研合作、创新环境与政策研究.
C939;G311
A
1009-3699(2015)05-05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