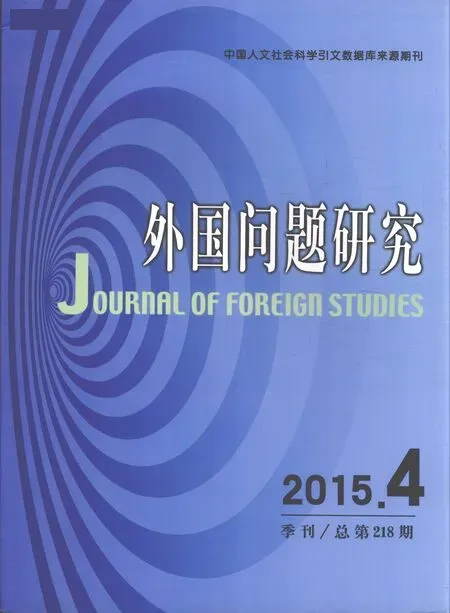希腊化与犹太传统的对话模式——以马加比起义历史动因为例
张 琳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希腊化与犹太传统的对话模式
——以马加比起义历史动因为例
张琳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内容 学界关于马加比起义成因的考察集中在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的宗教改革。根据比克尔曼的长时段研究方法,起义历史背景可分为耶逊希腊化改革、安条克四世的军事行动和宗教改革三组事件,它们本质上是希腊化与犹太传统两种力量的碰撞在文化、军事和宗教层面的具体体现,代表了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对话模式和犹太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主动接纳与积极肯定,外力强制与被动接受,外力强制与排斥反抗。
[关键词]马加比起义;希腊化;犹太传统;对话模式;历史动因
公元前167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颁发宗教禁令,废除犹太律法与宗教习俗,由此揭开了一系列亵渎耶路撒冷圣殿、推行异教崇拜等宗教迫害活动的序幕。以犹地亚(Judaea/Judea)*Judaea/Judea指《圣经》中的犹大王国(the Kingdom of Judah,c.a.930 BCE—586 BCE)的领地,大致相当于现以色列南部地区。波斯帝国时期,Judah被称为Yehud(阿拉米文),希腊化时期希腊作家称其为“Ioudaia”(Josephus,Against Api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1.90,179),罗马帝国将巴勒斯坦划分为3大行政区:犹地亚(Judaea)、撒玛利亚(Samaria)以及加利利(Galilee),Judaea为Judah的拉丁文或者是希腊文的拉丁化表达,并为现代英语世界所沿用。合和本中文《圣经》将Judah译为“犹大”,本文使用Judaea指代Judah,并根据《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将其译为“犹地亚”,与《圣经》译法不同,但所指相同。参见Fred Skolnik,ed.,Encyclopaedia Judaica,2nd edition,New York etc.:Thomson Gale,2007,vol.11,p.523;周定国主编:《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第434页。小镇莫德因(Modeïn)的祭司玛他提亚(Mattathias)为首的犹太人奋起反抗,马加比起义随即爆发,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64年玛他提亚之子犹大(Judas)清洗圣殿结束。马加比(Maccabee)为起义领导人犹大别名,希腊文与拉丁文分别为Makkabaios与Maccabaeus,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神学家用复数“Maccabees”(Makkabaioi)指代《马加比书》(TaMakkabaïka,直译为“马加比的历史”)中的所有英雄[1]3-4。
从表面来看,安条克四世的宗教改革是马加比起义的导火索,塔恩(Tarn)、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贝文(Bevan)等古典史学家也都将马卡比起义的原因归于安条克四世主导的这次改革[2][3][4]。比克尔曼(Bickerman)持不同看法,认为在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事件中,若从出现时间较晚的事件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很容易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因此需要对起义前的历史事件与事件发生的时代环境相联系,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宏观把握[5]3-5。比克尔曼的理论对于整合纷繁复杂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具启发意义。如果对起义背景进行长时段和不同层面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希腊化与犹太传统的对抗是起义前犹太社会的主要矛盾,耶逊希腊化改革、安条克四世入侵耶路撒冷、宗教改革这三个事件实则是希腊化与犹太传统矛盾在文化、军事和宗教层面冲突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希腊化与犹太传统对话的三种模式。
一、主动接纳与积极应对——耶逊希腊化改革
公元前334年的亚历山大东征,开创了希腊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大交流、大融合的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1877~1878年德国学者J.G.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三卷本《希腊化历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第二版问世,用“Hellenismus”指代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建立的希腊化王国统治时期(334BCE—30BCE),由此奠定了“Hellenism” (Hellenismus的英文)在现代学术界的基本内涵,并衍生出形容词“Hellenistic”。总体而言,它具有3层含义:一个历史时期——希腊化时期(通常认为是334 BCE—30 BCE);一种文化现象或过程——东西文化首次大规模的交融以及希腊化文明演进的过程;一个文化实体——希腊化文化,即希腊与东方文化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混合体。本文希腊化主要指第二层含义,即希腊文化在犹地亚社会传播过程中与犹太传统文化的碰撞,以犹太人对希腊化的态度为主线探讨二者交流的模式。参见杨巨平著《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eds.,A 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536; Fred Skolnik,ed.,Encyclopaedia Judaica,2nd edition,New York etc.:Thomson Gale,2007,vol.8,p.784。,巴勒斯坦被并入亚历山大帝国版图之内。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帝国被后继者瓜分,巴勒斯坦先后处于托勒密埃及(c.312BCE-220BCE)、塞琉古(c.220BCE-143/2BCE)两大希腊化王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无论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均难以避免与希腊文化的碰撞。犹太贵族或出于对希腊文化的钦羡或巩固地位、维护个人利益的现实需要,对希腊化持肯定态度,予以积极回应。公元前175年大祭司耶逊(Jason)发起“新文化”运动——希腊化改革,加剧了“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化与矛盾,招致宗主国塞琉古王国从军事和宗教两方面的干预,最终激起民愤,引发马加比起义。因此,耶逊的希腊化改革既是犹太人(主要限于犹太贵族)自我希腊化的典型案例,也是起义的文化动因,代表了犹太传统积极主动与希腊化文化对话的一种模式。
(一)圣城希腊文化建制的建立
根据《马加比二书》,耶逊呈请国王安条克四世授权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体育馆(gymnasium)和艾菲比亚(Ephebeia/Ephebia)*艾菲比(ephebos)泛指青春期的青少年,艾菲比亚既可指青年团体即艾菲比组织,也可指训练青年(尤其是军事训练)的制度。参见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eds.,A 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743.,并将该城所谓的“安条克人”登记在册,若此,他愿在440塔兰特的基础上额外上缴150塔兰特贡金。耶逊的请求获得了安条克四世的首肯。
耶逊改革的目的是在耶路撒冷建立希腊式的文化设施,让犹太青年接受希腊式的体育训练。但要对该城的“安条克人”进行登记,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这些所谓的安条克人的身份如何确定。其次,这是否意味着此前已经有一座希腊式的城市(Antioch/Antiocheia)在耶路撒冷城中或城边建立?目前学界对此有三种代表性观点:比克尔曼持将来建立说,认为“将耶路撒冷的安条克人登记在册”或者“为耶路撒冷的安条克人起草名册”表明国王批准耶逊建立一个以体育馆为中心、以国王安条克命名的社会团体,成员被称为安条克人(Antiochenes);它类似于politeuma*“Politeuma”内涵丰富,可指政府、国家、公民集体、公民权或国家政策等,也可作为一个术语特指正式(如希腊城市中的政治机构)或非正式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尤其是外来移民在流散地建立的社区。参见Henry George Liddel and Robbert Scott,eds.,A Greek-English Lexicon,p.1434; Lester L.Grabbe,A History of the Jews and Judaism in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London and New York:T &T Clark International,2008,vol.2,p.182.,即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团体或社区[5]39-40。科恩(Cohen)持现实存在说。他同意比克尔曼将“耶路撒冷的安条克人”(“antiochenes in Jerusalem”)视为一个社区(politeuma),但成员并非犹太人,而是来自托勒麦斯(Ptolemais)的安条克人;耶逊改革之时,他们已经以politeuma的形式定居耶路撒冷,所谓“登记在册”实指将这些外来移民招募到新成立的体育馆与艾菲比组织中,正式认可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的合法地位[6]。与上述学者不同,切利科夫持更名说。他认为,耶逊想请国王将耶路撒冷更名为安条克,使其荣升至希腊城市之列,以取代原来的犹太民族特区[7]。
在现在学者研究基础上,关于耶逊改革的探讨应回归现存史料。《马加比二书》以愤慨而又失望的语气细数改革所招致的祸患与后果:耶逊“引诱”犹太同胞效法希腊(生活)方式。他推翻传统旧制,引进违背律法之习俗。在“卫城”(acropolis)下建立体育馆,号召犹太青年(头戴希腊青年的礼帽)到此训练,接受希腊式教育。耶逊不洁与失格之恶行使耶路撒冷城的希腊化程度达到历史高峰,也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渗透的威胁。从此,祭司沉溺于体育馆,不再忠于圣职,司掌祭祀活动,他们抛弃了传统价值观,竞相角逐希腊人所崇尚的荣誉[8]4:10-15。据《马加比一书》记载,以色列兴起一批不法之徒(希腊化犹太人),他们巧言令色,“诱骗”犹太信徒,“与周边异族订立盟约”,使我们“遭受了诸多厄运。”[1]1:11-15约瑟夫《犹太古史》将改革发起者归于墨涅拉俄斯和托比雅兄弟二人,他们(希腊化犹太人)逃往王庭,表示愿放弃传统律法以及据此建立的社会制度,谨遵圣谕和希腊准则。他们舍弃传统,效仿异族之行,在国王的授权下,建立体育馆,甚至设法掩盖割礼印痕,以期被视为十足的希腊人[9]240-241。
上述史料因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立场问题对改革记载的详略与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所表达的主旨一致——希腊化犹太人放弃犹太传统,争相效仿希腊习俗。三份史料所强调的是耶逊对犹太律法的践踏、希腊化犹太人的罪恶以及希腊文化从物质、制度到精神层面对犹太民族的全面侵袭,但没有透露“建城”的讯息。若如切克利夫所言,耶逊推翻神权政治,建立希腊城市,如此巨大的政治变革和明显的希腊化趋势,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时被三部史料所忽略。如果确有此事,它们应浓墨重彩甚至夸大其词,而非保持沉默。所谓的“耶路撒冷的安条克人”只在《马加比二书》出现两次。一是说耶逊拟定“安条克人”名册,一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安条克人”作为使节团前往推罗(Tyre)参加四年一次的体育赛事。如果耶逊将圣城更名为安条克,城民顺势被称为“安条克人”,为何《马加比二书》的后续篇章或其他史料没有相关记载?以上论证模式虽然难以避免“无言声证”(“agumentum ex salentio”)的逻辑缺陷*由于史料缺失而否定历史存在或假设的论证方式被西方学者称为“agumentum ex salentio”,直译为“来自沉默的论证”,即“无言声证”。,但三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均“查无此证”并非偶然,它很可能表明耶路撒冷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安条克城”。就现存史料而言,关于“耶路撒冷安条克人”的定性以及“建城说”均证据不足。
上述三份史料对希腊化犹太人的指控应概括为五大罪行:兴建体育馆,成立艾菲比亚,招募“安条克人”,放弃割礼以及裸体运动,若暂且搁置尚存争议的“安条克人”,其他四项均与体育馆密切相关。希腊化时期,体育馆作为希腊人的身份象征,一方面是希腊传统得以维系的媒介,另一方面亦是外族融入希腊世界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某地的居民能否成为“希腊人”的关键并非该地有无希腊式城市的建立,而在于是否拥有体育馆这一承载希腊文化的地标建筑。由于它兼具运动、教育、社交以及娱乐等多重社会职能,当地贵族通常会通过体育馆组织的社团影响或管理当地居民[10]。兴建体育馆作为希腊化改革的第一步,耶逊对此应该有着清晰的认识。为表明其希腊化决心和对国王之忠心,他可能将其更名为“安条克体育馆”(Antiocheion/Antiocheum)*体育馆以人名命名的范例有雅典托勒麦昂(Ptolemaion/Ptolemaeum)体育馆,以托勒密四世命名;埃及的赫拉克斯体育馆(Heracleion/Heracleum);叙拉古城以将军泰摩利昂(Timoleon)命名的 体育馆(Timoleonteion/Timoleonteum)。参见J.A.S.Evans,Daily Life in the Hellenistic Age: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8,p.38; Clarence A.Forbes,Greek Physical education,New York and London:The Century Co.,1929,p.252; Plutarch,Liv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8,Timoleon,39.7.,成员称为“安条克人”。因此所谓的“将安条克人登记在册”实则表示耶逊为社团筛选“会员”(其中尤以青年贵族为重)。如此,则可理解作为耶路撒冷城的最高统治者的耶逊,为何要奏请国王同意兴建一座体育馆,甚至不惜为之“行贿”,也可理解为何耶逊要差遣“安条克人”出席推罗的体育赛事,因为耶逊所建立的社会组织以国王命名。安条克人作为体育馆社团代表,自然成为“体育外交”的最佳人选。因此,可将耶逊的改革简单理解为一场以引进体育馆为标志的希腊化文化活动。
(二)希腊化祭司贵族的文化改良运动
耶逊改革发生在犹太贵族内部矛盾升级以及大国交恶的内忧外患情势之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通过引进希腊生活方式,将犹太人纳入塞琉古王国的主流文化圈,另一方面博得国王赏识,以巩固祭司之位,攫取更多利益。由于它的动机和表现形式都不曾染指宗教领域。因此,可将其定性为由已经希腊化的犹太贵族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改良运动。至于耶逊改革的结果,是全盘吸收希腊文化,还是部分保留,以及是否推进到政治领域,目前无从查证,毕竟3年的在位时间未能给予他充分的施展空间。
公元前167年圣殿破坏运动之前,安条克四世基本延续前朝统治者开明的宗教政策,默许犹太社会内部自发的文化活动。因此这场改革不是塞琉古王朝强加的,传统的犹太人仍然能够信守其宗教信仰与仪式。然而,对于奉行政教合一的犹太人而言,教俗不可能完全分离。由于希腊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部分犹太人已不再恪守犹太律法,他们疏忽神事,放弃割礼,醉心于体育馆活动,甚至到外地参加希腊赛会,这些行为在虔诚的信徒看来显然属于叛教重罪。因此,耶逊改革在正式开启巴勒斯坦犹太人希腊化进程的同时,加剧了希腊化与传统势力的对抗和犹太社会内部的动荡,为马加比起义埋下伏笔。
二、外力强制与被动接受——安条克四世的军事行动
耶逊改革后犹太社会的动荡引发安条克四世对耶路撒冷圣城3次军事行动,由此建立王国军事据点——卫城(akra)。卫城居民由塞琉古王国的军队和希腊化犹太人两部分构成,它不仅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亦是希腊化犹太人对抗犹太传统势力的政治中心。如果说耶逊建立的体育馆和艾菲比亚是圣城希腊化的文化表征,卫城则是圣城希腊化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载体。它由希腊化国王以强制手段建立,而非犹太人的自发性行为,但迫于国王压力被动接受,体现了希腊化与犹太传统对话的第二种模式——外力强制与被动接受。
(一)“入侵”原因
公元前169、168年安条克四世结束与托勒密埃及第六次叙利亚战事后,改变了耶逊改革之时不干预犹太民族内部事务的基本国策,对耶路撒冷发动军事战争,圣殿被劫,8 000犹太人被俘虏或惨遭杀戮[1]1:20-24[8]5:14-16,原因何在?
其一,耶路撒冷持续紧张的态势是安条克四世对其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耶逊改革虽未触及宗教层面,但贵族对希腊生活的效仿无疑受到传统信徒的鄙夷和反感,加剧社会分化。公元前173/172年墨涅拉俄斯以高于耶逊300塔兰特的贡金被安条克四世指认为大祭司,他盗取、贩卖神庙财物,贿赂高官等种种恶行,引发了犹太平民小规模的武力反抗[8]4:23-50。公元前168年(夏)安条克四世二次远征埃及期间,耶路撒冷流传出国王暴毙的消息,流亡亚扪的耶逊趁势折返圣城企图重夺大祭司之位,行动失败,客死他乡[8]5:1-13,安条克四世随即以叛乱为由出兵圣城,并残酷地屠杀当地的居民。
其二,塞琉古王国同样面临现实的困境。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出兵耶路撒冷后,根据公元前188年的《阿帕米亚条约》(the peace of Apamea),塞琉古王国需支付罗马15 000银塔兰特战争赔款,安条克四世在位时期,欠款虽已付清(约公元前173年)[11][12],但它对国家造成的经济压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退。出于对希腊本土文化的钦羡,巩固和强化王国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安条克四世对小亚和希腊大陆广施恩惠,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王国的经济负担[13]55-63。而且安条克四世本人挥霍无度,骄奢成性,自然不会放弃任何聚敛财富的机会。公元前165年,他率军东征的原因之一便是弥补国王铺张浪费所造成的国库空虚*关于安条克四世此次东征路线史料不详,只记载他死于埃丽麦斯(Elymais),戈尔德施泰因认为它指代《圣经》中埃兰(Elam)或埃克巴坦那(Ecbatana),均在今伊朗境内。参见Jonathan A.Goldstein,I Maccabees,6:1,p.308 not 1; Daniel R.Schwartz,2 Maccabees,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9:3.。因此,安条克四世入侵耶路撒冷,劫掠圣殿的诱因首先出于对世俗利益即财政问题的考量,无关乎宗教,更不存在“反犹情绪”。此外,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安条克四世取得对埃及战争的胜利后,可能特意绕道耶路撒冷,以彰显王威,震慑此地蠢蠢欲动的亲托勒密埃及势力[9]247[14]31-32,以巩固南部边陲。
耶路撒冷的社会矛盾,统治者对神庙财产的觊觎以及稳定边疆的战略需要共同构成安条克四世对耶路撒冷军事行动的主客观因素。它非但没有缓和当地的紧张态势,反而激化犹太人与塞琉古王国的民族矛盾,迫使国王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严惩”犹太人——建立卫城,废除犹太“民族特区”的地位。
(二)“入侵”后果——希腊化王国卫城的建立
为彻底肃清叛乱势力,公元前167年春,安条克四世派米西亚(Mysia)雇佣军将领阿波罗尼乌斯前往耶路撒冷(第三次军事行动),修建卫城(Akra),由“罪恶之徒”与“不法分子”(塞琉古军队和希腊化犹太人)驻守,导致犹太众民被剥夺土地,流离失所[1]1:29-40[8]5:24-27[9]258。如何理解此处的“卫城”,它是否意味着一座希腊城市的建立? 比克尔曼认为卫城的建立是耶路撒冷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希腊城市的出现,圣城降格为乡村,与犹地亚其他地区共同沦为新城的军事殖民地(cleruchy/katoikia),犹太人由此丧失了“民族特区”的政治地位和自治权[1]212[5]42-53。
上述观点仅是比克尔曼从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制度史角度所做的合理推测,根据《马加比书》的两则史料,应得出相反结论。首先,安条克四世东征之前(公元前165年春),下旨围剿犹地亚(尤其是耶路撒冷城)犹太居民,清除“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记忆”[1]3:34;其二,宰相吕西亚斯曾率领八万大军围剿犹太人(公元前165年冬或公元前164年末至163年初),计划“将他们的城市变为希腊人领地,掠夺圣殿财富,将最高祭司一职每年出售一次。”[8]11:2-3它们表明至少到公元前165年,犹地亚大部分地区仍被犹太人占据,圣城依然存在。若如学者所言,公元前167年卫城建立后,犹地亚已沦为希腊人殖民地,上述军事计划和威胁(如清缴犹太人、变为希腊人领地)则毫无意义。因此公元前167年塞琉古国王可能只没收了犹地亚的部分土地,建立了以卫城为中心的军事殖民地,并废除了其地方民族自治的特权。
耶路撒冷的卫城通常表示位于城市制高点的要塞或哨所,具有军事防御或政治中心的职能。阿波罗尼乌斯之前,“卫城”一词在《马加比二书》出现3次——“卫城下的体育馆”、“卫城内的塞琉古将军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以及“墨涅拉俄斯逃往卫城”[8]4:12,28,5:5,第一个“卫城”指圣殿山,后两个指代塞琉古在圣殿山北侧建立的军事据点即哨所[15][8]223,233。《马加比一书》称阿波罗尼乌斯在“大卫城”建立卫城[1]1:29-35,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巩固旧哨所或者修建新的哨所,因此卫城本质上仍为希腊式的军事要塞,而非希腊式城市*此处的“大卫城”并非狭义上的大卫王所建立的城市(位于圣殿山以南),而是指塞琉古王国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城,城墙范围已包括整个东山(包括圣殿)。比克尔曼和戈尔德施泰因(Goldstein)认为卫城实质上为安条克四世建立的希腊式城市,旧城其他地区转变为新城的殖民地。参见Elias Bickerman,The God of Maccabees,pp.42-53; Jonathan A.Goldstein,I Maccabees,pp.211-212,213,218.。
阿波罗尼乌斯的军事行动给犹太人以沉重打击,卫城建立后,《马加比一书》使用抒情式的文学笔法哭诉了圣城所遭遇的劫难:它(哨所)是反对圣殿的邪恶势力,并将会成为以色列永恒的敌人。他们(哨所内的居民)在圣域内用无辜的鲜血玷污了圣殿。并将圣城合法的子民驱逐出境,使其变为了外族殖民地;由于亲子的离去,她(耶路撒冷)成为了犹太子孙的陌生人。如今她的圣殿被弃如荒漠,节庆变为国殇,她的安息日被众人啼笑,而昔日的辉煌亦遭到蔑视。她所受到的凌辱冲刷了昨日的荣耀,其傲骨柔情被打压为沉默与哀嚎。这些内容表明了犹太民众排斥卫城,难以接受土地被军事移民侵占的事实[1]1:38-40。
塞琉古王国三次军事行动的初衷旨在平息犹地亚自耶逊改革以来恶化的社会局势,打压亲托勒密埃及势力,但以暴制暴的手段反而激化了犹太信徒与希腊化贵族和塞琉古王国的矛盾,迫使安条克四世着手进行犹太教改革,试图通过宗教手段惩戒或压制犹太民族,但后者却成为战争导火索,引爆了犹太社会积怨已久的社会矛盾,马加比起义随即爆发。
三、外力强制与主动反抗——安条克四世的宗教改革
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强制推行的宗教改革为犹太信仰增加了新的希腊元素,本质上属于犹太教的希腊化,但对多数犹太人而言,即使他们能够接受或无视(保持中立态度)文化或政治、军事等世俗层面的希腊化,仍无法容忍异教染指犹太信仰。因此,他强制推行希腊化的举措由于触及犹太信仰而难以被多数犹太人所认可,招致马加比起义爆发,这种反应可视为希腊化与犹太传统对话的第三种模式——强制与反抗。
根据犹太史家记载[1]1:41-59[8]6:1-7[9]253-256,安条克四世宗教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第一,颁发文化大一统的敕令。国王号令各民族放弃传统习俗,“普天归一”。众多犹太人放弃安息日,追随(国王推行的)宗教和偶像崇拜。第二,废除犹太教习俗。公元前167年,使臣格龙(Geron)携带文书至耶路撒冷及犹地亚各地传达国王的命令,要求犹太人接受外来习俗,废除圣殿祭仪(如燔祭、酒祭和圣餐祭),宗教习俗(割礼、斋戒、安息日)以及节日庆典,焚毁《托拉》经卷,任何私藏或爱《托拉》者抑或违背以上禁令者,一律处以极刑。同时,在犹地亚各地设立祭坛、神庙,在家宅或广场均举行祭祀活动,使用野猪或其他不洁牺牲。国王命令将文书(副本)发往全国(告知天下),委派专员督查祭祀活动。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律法,接纳一切亵渎圣主和有违教规之事。第三,推行异教崇拜与祭祀仪式。将圣殿更名为宙斯(Zeus Olympios)庙,建立“万恶之恶的不洁之物”(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新祭坛*希伯来文“shiqquz shomem”,在阿拉米语“天神”(Ba‘alshamaim,简称Ba‘al,巴力神,西闪米特人最高天神的统称)基础上的变形,带有贬义色彩。比克尔曼认为“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为新的石质祭坛,是安条克四世在闪族圣石崇拜基础上建立的石头——祭坛崇拜(baetyl-altar/bomolatry);戈尔德施泰因认为它由三块陨石按照某种矩阵排列而成,分别代表天父、天母以及一位年轻的天神,对应宙斯、雅典娜和狄奥尼索斯。参见Elias Bickerman,The God of Maccabees,pp.73-75; Jonathan A.Goldstein,I Maccabees,pp.143-157;J.C.Dancy,A Commentary on I Maccabe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54,p.78.,并举行祭祀大典;准许神妓与异族进入圣殿。犹太人每月为国王庆生,分享牺牲内脏。狄奥尼索斯节庆之时,犹太人需列队游行。
上述犹太人的史料为强调国王和希腊化犹太人的罪恶,内容不免有失实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其历史内核的真实性。宗教禁令出台后,圣殿被亵渎,犹太人被迫或主动背弃律法(如另立祭坛,使用不洁祭品),不再遵守犹太教教仪(割礼、斋戒、安息日或其他祭祀活动),更甚者则是“新”宗教崇拜的出现。此处所谓的“新”是理解安条克四世宗教改革的关键。塞琉古王国疆域包括以叙利亚为核心的近东地区和原属于波斯帝国的中亚腹地,如何调和国内希腊与“东方”文化要素是希腊——马其顿统治阶层需长期应对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宗教领域亦不例外。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均属西闪米特人,对安条克四世而言,犹太圣主耶和华(Yahweh)与叙利亚的天神巴力(Ba‘al)并无差别,亦可等同于希腊神宙斯,均指最高天神,称谓和表现形式不同(前两者无形无名,后者神人同形同性),本质未变[5]62-65[16]。因此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推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古希腊神灵崇拜与西闪米特原始宗教共生共融的一个具体体现,本质上属于宗教共生(调试)或混生主义(syncretism)的范畴。
为神易名,随意用具体称谓或异教神名来直呼圣主以及建立新祭坛,这些行为已严重违背犹太人一神崇拜和禁止将神具象化的宗教传统。即使安条克四世本人认为自己只不过为耶和华加上了一个新的希腊神名——奥林匹亚山的宙斯,但他的“初衷”未能获得所有犹太人理解,对多数犹太人而言,宙斯为异教神,不能指代耶和华。而且与宗教迫害同时代的犹太人和其他古代作家可能并没有上升到神学思想层面的思考,相对于改革过程,他们更关注改革结果,焚毁经书、禁行割礼、废除祭仪以及另立祭坛等打破其宗教秩序的举措均超出他们忍耐的极限,故而采用武力方式回应异教国王强制改革犹太信仰体系以及希腊宗教元素的渗入。
结语
耶逊希腊化改革、安条克四世军事行动及其宗教改革为马加比起义的三大历史动因,它们前后相继,具有其内在逻辑联系。其一,因果联系,耶逊希腊化改革加剧社会分化和动荡局势,招致安条克四世军事行动,但后者并未缓解反而加剧犹太社会矛盾,致使国王以宗教改革手段破坏民族精神的支柱——犹太教,引发犹太人民的反抗。其二,并列关系,三者均源自希腊文化传播所导致的犹太社会的分化,本质上是希腊化与犹太传统两种力量的博弈在文化、军事和宗教层面的具体体现,由此出现了犹太人与希腊化进程之间的三种互动模式:主动接纳与积极肯定,外力强制与被动接受,外力强制与排斥反抗。
希腊化与犹太传统的矛盾是审视公元前2至公元前1世纪犹太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以马加比起义为分水岭,此前属于希腊与犹太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尝试阶段,因犹太人暴动遭受挫折。起义后出现犹太独立政权——哈希摩尼王国(the Hasmonean State),这一时期,犹太人对希腊文化理解加深,对其态度不是简单的认可,而是将其纳入犹太文化传统,积极寻求二者的共存共融。
[参 考 文 献]
[1] Jonathan A.Goldstein.I Maccabees [M].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76.
[2] 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5:215.
[3] 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1):64.
[4] E.R.Bevan.The House of Seleucus [M].London:Edward Arnold,1902(2):153-154.
[5] Elias Bickerman.The God of Maccabees:Studies on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the Maccabean Revolt [M].Horst R.Moehring (trans.),Leiden:E.J.Brill,1979.
[6] Getzel M.Cohen.The ‘Antiochenes in Jerusalem’.Again [I].John C.Reeves and John Kampen (eds.),Pursing the Text:Studies in Honor of Ben Zion Wachold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M].Englan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4:247-255.
[7] Victor Tcherikover.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M].S.Applebaum (trans.),Philadelphia: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58:406-407.
[8] Daniel R.Schwartz.2 Maccabees [M].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223,233.
[9] 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Book2) [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3:12.240-241,247,258,253-256.
[10] H.I.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M].New York:Sheed and Ward,Inc.,1956:150.
[11] Polybius.The Histories [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21,17.
[12] Livy.History of Rome [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and 1938:37.45.11-18,42.6.6-7.
[13] Otto Mørkholm.Antiochus IV of Syria [M].København:Gyldendal,1966:21-22,64-65,55-63.
[14] Josephus.Jewish War(Book1) [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1:31-32.
[15] Jonathan A.Goldstein.II Maccabees [M].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83:229.
[16] J.C.Dancy.A Commentary on I Maccabees [M].Oxford:Basil Blackwell,1954:81-82.
[责任编辑:冯雅]
The Mode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llenism and Judaism:
Taking the Historical Reasons of Maccabean Revolt as an Example
ZHANG Lin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In terms of the reasons of Maccabean revolt,Antiochus IV’s religious reform has been intensively concerned. According to the Bickermann’s researching method of long period,the essay will integrat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efore Maccabean revolt into three groups of invents,which forms the reasons of Maccabean revolt basing on the contradict between Hellenism and Judaism. Essentially the three reasons are concrete reflections of the contradict between Hellenism and Judaism in culture、military and religion,representing the various contradicting models,that is initiatively accepting and actively identification,compelling by outside power and receiving passively as well as forcing,rejecting and resisting,which compose the basic models of Jewish replying to foreign cultures.
Key words:Maccabean revolt;Hellenism;Judaism;models of communication;historical reasons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4-0048-07
[中图分类号]K545.2
[作者简介]张琳(1987-),女,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