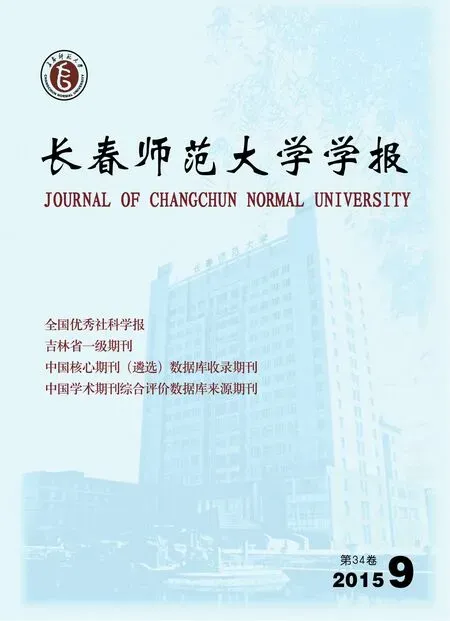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
凌 晔,何 玮,陈小炜2,
(1.铜陵学院法学院,安徽铜陵244000;2.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3.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江苏 南通22600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对外资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这种试点有可能会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中国境外投资近年来不断增长,但也经常受阻于各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或者反垄断审查。如果投资者能够善用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相关规则,则可以规避或者化解这一类风险的发生。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内涵
“准入前国民待遇”,又被称为“准入时国民待遇”,首先出现在美国的外资立法中[1]。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指东道国在“准入权”和“设业权”两方面给予外国投资者在相同或者相似条件下不低于或等同于内国投资者的待遇。在准入权方面,国民待遇要求东道国对外资进入本国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规定与内资相同;在设业权方面,国民待遇要求东道国赋予外资与内资一样的在内国设立子公司、代表处和分支机构等各种类型商业存在的权利。
在实践中,东道国可以通过制定国内法和缔结国际条约两种形式赋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并且通常以互惠或对等的条件为前提。在准入前国民待遇适用条件上,不同的条约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如美国对外签订的多数双边投资协定使用了“在相似情形下”(in like circumstances)的表述,而英国早期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更多地使用“在相同情形下”(in the same circumstance)的表述。这些条约没有对两种表述的具体内涵作出解释,这就赋予了争端解决机构以自由裁量权,由他们参照具体案件涉及的条约的缔约目的等因素加以确定[2]。
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既可以“等同于”内国投资者,也可以“不低于”内国投资者。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等同于”意味着给予外国和内国投资者的待遇完全相等;而“不低于”则意味着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可以高于给予内国投资者的待遇,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采用“不低于”的标准,准入前国民待遇并不排斥“超国民待遇”的存在。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条约实践
国民待遇向外资准入阶段的延伸集中体现了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自由化成为国际投资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其目的在于逐步消除歧视外资政策,铲除扭曲行为,建立一整套必要的竞争、监督、管理与服务的机制和规则[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自由化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趋向,表现为两者在是否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上激烈的博弈[4]。这种博弈最终体现为各类不同的条约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的接受程度不同。
发达国家曾试图在WTO的多边贸易协议中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但这一努力并未成功,最终仅在GATS中将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服务贸易领域中的具体承诺加以规定。根据GATS的规定,成员国对所提交的承诺开放清单中列明的服务贸易领域,承担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义务。欧洲国家主导缔结的《能源宪章条约》在能源勘探开发领域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但该条约没有在所有能源投资领域一般性地授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5]。总体来看,准入前国民待遇在全球性国际投资条约中进展缓慢。
在区域性一体化进程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呈现出较快发展的势头。欧共体是最先要求成员国相互给予投资权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要求消除对共同体成员的自由人和法人在外资准入方面的限制或自由提供服务方面的限制[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02条要求成员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的范围包括“设立、收购、扩大、管理、实施、经营以及销售或者其它安排”。《建立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的做法充分借鉴了NAFTA的经验,其关于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规定与NAFTA基本一致[7]。
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对外资准入采取限制态度,是否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取决于东道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相继签订了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定的投资协定。但至今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准入前国民待遇还是个别现象。美国在2012年修订了其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延续了自1982年以来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规定,该范本内容将在很大程度上落实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会有力地推动其他国家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8]。
总体来看,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国家对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呈现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对东道国外资监管和内资保护构成了挑战,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目标就在于消除较严密的外资监管对相互投资造成的阻碍,因此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方之间更能接受给予对方国家投资者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三、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限制措施
在实践中,各国在缔结国际条约时往往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定了种种例外情形,对准入前国民待遇提出保留,最为常见的保留是不符措施(non-conforming measures)。所谓不符措施是指缔约方在条约生效前所制定的与条约规定不相符的措施。最早采用这一例外的是NAFTA。在该条约中,不符措施既包括缔约方中央政府制定的措施,也包括地方政府制定的措施,还包括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制定的措施的修订,但NAFTA要求这种修订不得降低它与条约的相符性。除此之外,在国际条约中还经常规定一般例外和临时措施,以作为准入前国民待遇适用的例外。一般例外是在条约中列明所有缔约方均可在相关情形下援引的例外,在任何时间,只要出现了条约中规定的一般例外情形,东道国就可以援引一般例外拒绝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而临时措施则是指在条约适用的过程中东道国可以在出现特定情形时暂时停止对外国投资者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除了国际条约之外,各国在国内法中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也可以作出各种限制。国内法对准入前国民待遇最主要的限制方式是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列明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如美国向OECD提交了关于外控企业(foreign-controlled enterprises)国民待遇例外的负面清单,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渔业、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银行业、空运、海运、传媒和电信等领域,外资进入该清单中的限制性行业需要经过政府机构审批,并且这种批准还有互惠要求[9]。除此之外,各国往往通过外资审查对外资进行限制。这种审查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和市场竞争审查,前者如美国《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规定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应当对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进行审查,后者如澳大利亚《2010年外资收购法》规定对外资项目采取双重审查制度,即由外资审查委员会和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分别展开市场竞争审查。国际社会在外资审查方面发展的趋势是逐步明确审查的标准,以实现制度的透明化和可预期性,但这一目标在今天仍未完全实现,几乎所有国家外资审查都存在一些难以确定的因素。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能否避开或者通过外资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法律规定,而是取决于政治因素。
四、中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实施与完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准入前国民待遇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时我国企业在国外也遭遇了外资准入方面巨大的障碍,出现了多起中国公司收购外国公司未通过东道国外资审查的案例。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充分利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原则和规则,同时也要求我国在国家层面通过缔结双边协定等方式构建一个互惠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框架。
上海自贸区为中国设置了一个测试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可能带来的效果的实验室,在推进上海自贸区过程中需要根据测试结果不断校正相关的规则,以应对将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在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为进一步吸引外资,我国必须为将来可能与他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纳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做好充分准备。
虽然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当下中国必然要面临的选择,但我国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稳步推进,以防止制度环境的变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
首先,以互惠为基础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法律框架体系。准入前国民待遇蕴含着较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市场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协调好市场自由和政府监管、引进外资和保护内资的关系,互惠原则可用以平衡这些关系。我国以互惠作为赋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前提,既符合习惯国际法,也可以防止单向对外开放的被动局面,同时满足我国企业在缔约对方国家从事海外投资的需求。
其次,适度调整负面清单的范围。2014年4月,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其重要原因之一即2013年的清单对外资限制、禁止的内容太多,开放程度较小。适度缩小清单内容,将增强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效果。但对自贸区负面清单过于频繁的修改,也会引发外资对我国投资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因而有必要对负面清单内容进行梳理,制定出一个既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又能够根据将来扩大开放的需要适时修改的清单。
再次,准入前国民待遇应当严格规定以“等同于”为原则,并将特定时间或者领域内的“不低于”作为例外。外资准入法律应当适应我国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领域对外资的需要。在一般性的行业和领域,应当确立“等同于”内资的待遇基准,即外资所享有的待遇与内资完全一致,以确保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在亟待加快发展、缺乏资金、与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可以通过更优惠的“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采用“不低于”内资的待遇基准。至于在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采用“次国民待遇”,则完全可以由负面清单确定,而不需另行规定待遇基准。
最后,设立与准入前国民待遇相配套的外资审查机制。外资审查制度是对准入前国民待遇重要的补充,通过确立合理的外资审查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投资自由化状态下外资准入阶段监管不足的问题。设立外资审查制度,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考量。在实体上,外资审查内容应当包括国家安全、竞争影响、环境、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等内容。在程序上,对外资审查的提起和受理、审查方式和程序以及决定的作出,应当进行周密的设计,既要防止过度审查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国内经济发展,又要防止审查不足所带来的风险。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做法,设立专门的审查机构,在启动审查时以主动审查和申请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范丽娜.国外关于外资国民待遇的规定及立法实践[J].经济论坛,2006(8):127-128.
[2]任强.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中“相似/相同情形”考察[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8-22.
[3]马永梅.投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影响评析——兼谈中国外资立法的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5(11):131-133.
[4]徐泉.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排斥与吸引博弈关系法辨——以韩国为例[J].河北法学,2007(3):45-50.
[5]叶玉.石油投资与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1.
[6]赵玉敏.国际投资体系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从日韩投资国民待遇看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12(3):46-51.
[7]陈彬.东盟与NAFTA投资规则的比较分析[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4):29-33.
[8]朱文龙.我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国民待遇的选择[J].河北法学,2014(3):179-187.
[9]OECD.National Treatment for Foreign-Controlled Enterprises:Including Adhering Country Exceptions to National Treatment[R].20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