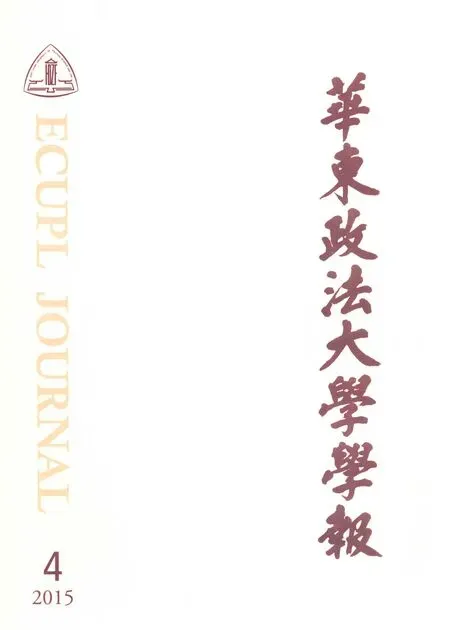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体系化解释及其完善
* 洪莹莹,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讲师。感谢刘蔚文博士和《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系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强化反垄断法公共实施机制研究”(项目号KYLX_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分歧的缘起:欧美差异化规制模式的双重影响和异向导引
三、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体系化解释
四、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完善
五、结语
摘 要 对于限制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国家发改委在眼镜企业案(2014)中对企业自主定价权的关注再一次凸显了与强生案(2013)中法院分析思路的不同。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两种不同进路反映了美国和欧盟经验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和实施的双重影响和异向导引。美欧模式存在体系化差异,制度背后的价值判断、事实假定和术语体系都不同。在理解上述差异的基础上,我国《反垄断法》第14、15条应解释为对限制转售价格推定违法并允许豁免抗辩。同时,我国应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指南等文件对此做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宏观上,应注意本国制度体系的一致性及特殊性、进一步明确价值目标和事实假定并充分考量实施成本;微观上,应以更多实证证据为支撑,在继续保持违法推定的同时,借鉴显著性标准和安全港制度,适度收窄禁止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8月1日,我国首例限制转售价格案件——北京锐邦诉上海强生案(以下简称强生案)终审宣判。该案因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评价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分析评价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而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仅就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而言,上海市中院和高院均认为限制转售价格必须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才构成《反垄断法》第14条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而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需要综合分析涉案行为对竞争的促进和抑制效果后方能确定。 〔2〕这一分析思路与美国的“合理规则”(ruleof reason)非常相似。目前,该案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2期收录,未来将对全国各级法院处理相同类型案件产生实质影响。
然而,执法机关在茅台、五粮液、奶粉企业及眼镜企业案中,态度却并不相同。茅台案中,贵州省物价局未做任何分析,直接认定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第14条。五粮液案中,四川省发改委通过简短的分析认为涉案企业达成并实施了白酒销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限制了同一品牌内经销商之间的竞争,损害了经济效率,同时还限制了行业内品牌之间的竞争,违反《反垄断法》第14条。 〔3〕奶粉企业案中,国家发改委在简要分析了反竞争效果后进行了豁免说明:
涉案企业的上述行为均达到了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或限定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效果,事实上达成并实施了销售乳粉的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涉案企业均承认自身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涉嫌违法,并且无法证明其控制价格的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条件。 〔4〕
而在眼镜企业案中,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5月29日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对依视路、博士伦等镜片生产企业共计罚款1900多万元的新闻公告。该案中,对于各生产企业强制下游经销商在“建议零售价”或“建议零售价统一折扣价”上进行销售的行为,国家发改委认为构成直接或变相维持转售价格,存在固定镜片转售价格或限定镜片最低转售价格的行为,并指出:
作为眼镜行业市场规模较大、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知名品牌商,涉案企业的上述行为限制了经销商的自主定价权,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达成并实施了销售镜片的价格垄断协议,达到了固定转售镜片价格或限定镜片最低转售价格的效果,排除和削弱了镜片市场价格竞争,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使相关镜片价格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5〕
上述案件中,虽然除了贵州省物价局外,四川省发改委和国家发改委在处罚公告中也简要提及了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也很难将其等同于强生案中的合理分析进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奶粉企业案中,国家发改委进行了豁免说明,而眼镜企业案中,国家发改委除了论及涉案企业的市场规模,还首次提出企业的自主定价权不受干涉,这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与司法机关的不同思路。
除执法、司法实践中的不一致外,学术界同样存在争议。黄勇教授、刘燕南博士总结道:“由于限制转售价格协议具有复杂的竞争效果,使得学者们对于如何解释和适用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逐渐形成了两种相冲突的对法律进行解释的主张,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理分析’和‘可抗辩的本身违法’两种进路不同的分析方法。” 〔6〕
于是,本文拟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分歧缘何产生?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对于限制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究竟应如何解释、适用并怎样完善? 〔7〕
二、分歧的缘起:欧美差异化规制模式的双重影响和异向导引
事实上,前述分歧反映出的正是美国和欧盟经验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及实施的双重影响和异向导引。王晓晔教授即指出:“借鉴美国反托拉斯法、欧共体竞争法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经验,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垄断协议分为横向协议和纵向协议。” 〔8〕然而,美国与欧盟差异迥然,对限制转售价格行为,它们在各自的法律传统与制度框架内走出了互不相同又自成体系的规制路径。
(一)美国模式:《谢尔曼法》第1条及其解释规则
1. 《谢尔曼法》第1条
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是对包括限制转售价格在内的垄断协议进行反垄断规制最主要的成文法依据。该条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 〔9〕对于这种极其概括、抽象的规定,如何进行解释和适用成为该法颁布之初美国联邦司法系统面临的最大难题。
起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严格的文字主义解释方法。United States v.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Decision(1897)中,大法官们以5:4的投票结果认为《谢尔曼法》毫无例外地谴责一切限制贸易的行为。 〔10〕但是这种“文字主义”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任何契约或是协议的订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贸易,于是,这一解释很快就在Hopkins v. United States (1898) 〔11〕和United States v. Joint Traffi c Ass’n (1898)两案中被软化到只适用于直接限制州际贸易的协议, 〔12〕并在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 (1911)案中被合理原则所推翻,“只有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才属于《谢尔曼法》的制裁范围,才被认为是违法的”。 〔13〕在这一解释框架下,之后的判例法中又发展出了作为案件具体裁判规则的“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
2.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及其变迁
抛开抽象的“《谢尔曼法》只禁止不合理的贸易限制”这一整体原则层面,从具体而言,对于本身违法与合理规则的确切涵义,不仅国内学者理解不同,在美国法上也同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 〔14〕概而言之,本身违法一般是指对某些类型的协议,不用逐案进行效果分析,仅需证明特定类型协议的存在即可认定违法并予以禁止。因为某些类型的垄断协议几乎经常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且因为限制竞争产生的其他价值不足以弥补其所带来的损害,若对其仍进行合理分析,势必影响垄断协议规制的效率性。 〔15〕而Leegin案(2007)中多数意见认为,依据合理规则,“事实调查者应该衡量案件中的所有因素,以决定一个限制行为是否应因为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而被禁止”。 〔16〕
美国对限制转售价格的法律规制大体上经历了从本身违法向合理规则的变迁。本身违法规则的确立始于Dr. Miles案(1911)。该案中印第安纳州的 Dr. Miles医药公司以违约为由起诉一家批发商,因为后者诱使其他批发商违反与Dr. Miles的固定价格协议,以此获得削价药品。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指出“商品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的情况下,经销商有权利自行确定商品价格,生产商固定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价格的行为是本身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公共利益。” 〔17〕由此,本案确立了固定转售价格的本身违法规则,但不难发现,其中并不蕴含经济分析的方法。而且,法院的主要判决依据也并非《谢尔曼法》,而是当时的一项普通法规则——“对转售的一般限制无效”(a general restraint upon alienation is ordinarily invalid)。
但是之后,这一规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守。Colgate案(1919)和General Electric案(1926)分别确立了Colgate 规则(Colgate Doctrine)和GE代理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本身违法规则的适用。 〔18〕此外,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中小型零售商的推动下,36个州通过了《公平贸易法》(Fair Trading Act),允许在州内贸易中实行限制转售价格。同时在联邦层面,1937年和1952年国会分别通过了《米勒—泰丁斯法案》(Miller-Tydings Fair Trade Act)和《麦奎尔法案》(McGuire Act),规定如果依据某一州的《公平贸易法》,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合同是合法的,那么《谢尔曼法》将不认为其非法。 〔19〕之后,这些法案为36个州的生产商在近40年内提供了豁免适用《谢尔曼法》的成文法依据。 〔20〕这意味着,限制转售价格非但不是本身违法,反而成为本身合法。
直到Albrecht案(1968)中, 〔21〕本身违法规则才又重启征途,被联邦最高法院扩张适用于固定最高转售价格行为。该案中,拜伦•怀特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认为:“许多情况下最高转售价格维持与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会有不同的影响,但是固定最高转售价格的协议代替了市场自由竞争定价的规则,可能极大地侵犯了买方进行竞争和生存的能力……而且,当产品真实价格接近甚至等同于最高定价时,该定价方案则符合固定最低零售价的所有特征。所以本案中,由被告发起的迫使原告维持特定价格的联合构成了谢尔曼法禁止的非法贸易限制。” 〔22〕此外至1975年,国会通过《消费品价格法》(Consumer Goods Pricing Act)废止了《米勒—泰丁斯法案》和《麦奎尔法案》,限制转售价格在许多州的本身合法状态被终止,相关违法性认定再次回到《谢尔曼法》第1条的范围。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被引入反垄断案例的分析过程,效率观念也渐居主导地位,本身违法因为对限制转售价格行为的严厉禁止而逐渐被瓦解。首先,在Sylvania案(1977)中,联邦最高法院对纵向非价格限制案件开始适用合理规则进行分析。该案中,代表多数意见的鲍威尔大法官认为“与市场考量相分离的反垄断政策将缺乏任何客观基准”。 〔23〕由此,效率分析正式进入美国的反垄断案件之中。以此为契机,之后的Khan案(1997)和Leegin案(2007)则在限制最高转售价格和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时相继完成了合理规则对本身违法规则的取代。尤其是Leegin案,该案虽然是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案件,但联邦最高法院统一指出:“大量表明制造商限制转售价格有促进竞争效果的经济学文献为合理规则提供了正当性依据;限制转售价格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反竞争的效果;尽管如此,限制转售价格也不能再被盲目地描述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限制竞争和减少产出……纵向价格限制应适用合理规则”。 〔24〕
3.规则变迁隐含的价值判断、事实假定及司法的核心推动
美国限制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在司法力量的核心推动下,完成了规则的变迁,而这种变迁背后蕴含着美国反托拉斯法价值判断及事实推定的变化。
首先,在价值判断上,美国的反垄断法规制经历了从公平自由向效率的转化。价值判断决定制度理念,制度理念依赖法技术转化为最终规则,反垄断法如何规制限制转售价格根本上取决于其价值目标。有学者认为,“本身违法”与“合理规则”是体现美国特定时期反垄断法主流价值的晴雨表。 〔25〕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运输和通信革命导致了托拉斯的出现,农民、劳工、小企业主受害甚深。国会收到许多请求,请求将托拉斯和铁路置于联邦政府的规制之下, 〔26〕因此在反托拉斯法的立法之初,维护自由市场体制的存续、确保市场竞争的平等参与无疑是其价值考量的核心,自由价值和公平价值因而也是最先体现在反托拉斯法价值体系中的。 〔27〕本身违法规则顺应了这种价值要求,一概禁止限制转售价格,从而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虽然,Dr. Miles案中本身违法规则是出于对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而得以确立,与竞争关联并不充分,但在之后的Albrecht案(1968)中,多数意见充分表明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市场主体竞争和生存能力的关切,对市场定价机制的维护。然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分析被引入到反垄断法中,效率价值逐渐居于核心地位。对此,最极致的主张莫过于波斯纳所言:“反托拉斯法的唯一目标应当是促进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 〔28〕伴随着由公平、自由到效率的转向,对限制转售价格行为的关注也从竞争秩序转移到行为对竞争造成的实际效果之上。
其次,基于经济学的知识更迭,人们对限制转售价格对竞争可能产生的效果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一般情况下,在个案中,事实应该被证明而不是被假定。然而,由于竞争的复杂性和早期的经验证据,将限制转售价格假定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限制竞争或减少产出并进而适用本身违法规则成为当然的选择。而随着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不断深化,限制转售价格促进竞争的效果日益得到认可。在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泰尔瑟(1960)、马修森和温特(1998)提出的限制转售价格可以促进零售商提供售前服务和质量证明理论成为影响最大并最为实证分析所支持的理论, 〔29〕它为限制转售价格提供了与本身违法规则不相容的事实假定,即该行为对竞争可能同时存在促进及限制效果,但几率不清,由此奠定了适用合理规则的基础。
最后,美国的限制转售价格制度最主要的发展和推动力量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活动。这不仅表现在本身违法和合理规则系由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而来,也表现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各自的执法中也需要遵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确立的各种评估框架和标准。在Leegin案中,对于用合理规则取代本身违法规则,虽然两部门与联邦最高法院观点相同,但仅仅是作为法庭之友递交了意见,不具决定性影响。对此,有学者认为:“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了其在解释《谢尔曼法》上的霸权。” 〔30〕在这种司法推动中,除了法学、经济学的因素影响,政治因素似乎也不可忽视。尽管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以及一系列制度能够有效保证司法独立,但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案件中,法官的意识形态与案件结果仿佛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限制转售价格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前3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代,在内政上,保守与进步共存,但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保守消解了进步,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保守理念的集大成者和坚实捍卫者。 〔31〕Stand Oil案(1911)中的合理原则正是由保守派掌控的怀特法院(1910-1921)确立的。Dr. Miles案(1911)虽然确立了本身违法规则,但该案是以“财产权进路优先于竞争进路的角度来处断的”, 〔32〕这与保守主义保护个人财产权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而Colgate案(1918)与GE案(1926)则恰好体现了保守理念支配下对本身违法规则的限缩。至开明的沃伦法院(1953-1969)时期,Albrecht案(1967)将本身违法规则扩张至限制最高转售价格。之后渐进保守的伯格法院(1969-1986)、伦奎斯特法院(1986-2005)、罗伯茨法院(2005至今)则相继在Sylvania案(1977)、Khan案(1997)、Leegin案(2007)逐步并最终全面确立了合理规则。在Leegin案中,正是相对保守的肯尼迪、斯卡利亚、托马斯、阿利托、罗伯茨五位大法官的多数意见压倒了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布雷耶和索托马约尔、卡根的异议意见。
(二)欧盟模式:《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及“核心限制”
与美国的判例法主导不同,对影响成员国间竞争的限制转售价格行为,欧盟通过基础条约及相关条例、指南明确规定了禁止及豁免条款。
1.欧盟限制转售价格规制的主要法律依据
《欧盟运行条约》(以下简称TEFU)第101条和《纵向限制协议集体豁免条例》(330/2010)(以下简称《条例》(2010))及《纵向限制指南》(2010)(以下简称《指南》(2010))构成规制限制转售价格的主要法律规定和规范性文件。 〔33〕其中TEFU是基础性法律渊源,《条例》(2010)是派生性法律渊源,而《指南》(2010)虽然不具强制约束力,但却对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及成员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TEFU101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了对限制性协议的原则禁止和例外豁免。第1款规定:“禁止一切损害成员国间贸易,以阻碍、限制或扭曲共同体市场竞争为目的或后果的企业间协议、企业联合组织决议和协同行为。尤其是(a)直接或间接地固定购买或者销售价格、或者任何其他交易条件”。 〔34〕然而,虽然使用禁止“一切”的表述,但事实上,仅仅产生显著限制竞争影响的协议才落入该条禁止范围。 〔35〕第3款则规定:“如果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可以获得豁免,不受第1款禁止:(1)有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或者有利于促进技术或者经济的发展;(2)使消费者能够公平分享由此项行为获得的利益;(3)限制竞争是为达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4)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所涉产品重要部分竞争的可能性。” 〔36〕
其次,《条例》(2010)及《指南》(2010)是专门针对纵向垄断协议的主要文件。依据这两个文件,纵向协议区分为核心限制(hardcore restriction)和非核心限制协议。对于非核心限制协议,文件规定了安全港制度,即当供货方和经销商在各自市场上的份额都不超过30%时,可以适用《条例》(2010)而推定合法,从而豁免。对于核心限制协议则不可以适用《条例》(2010)获得集体豁免,只有在个案中才可以主张效率抗辩。
2.限制转售价格的核心限制界定
依据《指南》(2010),限制转售价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属于核心限制协议,指以向购买商设立固定或最低转售价,或以固定或最低价格水平为直接或间接目的的协议或协同行为。 〔37〕《条例》(2010)也持相同立场,对于核心限制协议,即使其符合安全港的市场份额要求,亦不能获得集体豁免。 〔38〕相反,要面临强烈的非法假定:(1)假定违反《条约》第101条第1款;(2)假定不太可能满足《条约》第101条第3款的豁免要求。 〔39〕当然,这种假定也并非绝对不可推翻,如果涉案企业能够证明达成的协议可以促进效率,并可以同时满足4个豁免条件,则仍有可能获得个案豁免。 〔40〕
3.核心限制下的目的分析与效果分析
依据TEFU101条第1款,认定一项协议、决议或协同行为是损害成员国间贸易,阻碍、限制或扭曲共同体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既可以目的为要件,也可以效果为要件。通常情况下,欧盟委员会或欧洲法院会优先考虑该行为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目的”,如果有,则不需要再论证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如果不能证明该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目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41〕
而对于被界定为核心限制的限制转售价格,在具体案件中,当欧盟委员会面对达成限制转售价格的企业时,仅需要证明行为的存在和设立协议的目的即可以认定其违法,而无需证明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质言之,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违法性认定原则上在目的分析框架(object box)下进行,或者说适用目的要件。但是在个案中,当事人仍有机会主张效率抗辩,在效果分析框架下(effect box)要求豁免。但由于豁免条件极为严苛,举证责任过重,所以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据统计,在2010年《条例》和《指南》修订之前的50年中,还没有达成限制转售价格协议的企业成功在欧盟竞争法内进行过效率抗辩。 〔42〕
4.核心限制下的价值判断、事实假定及行政的主导力量
欧盟竞争法的产生受到德国《反限制竞争法》(1957)的极大影响。德国和欧共体竞争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对竞争法的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43〕而当时的德国竞争法对限制转售价格的禁止又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美国反托拉斯法和佛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之前,不仅纵向垄断协议,连横向卡特尔在德国都是被允许的,甚至被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组织。虽然1940年的《价格维持条例》对限制转售价格作出了较多规定,但没有一项政策是出于竞争考虑。真正的禁止限制转售价格的规则是体现在二战后美占区和英占区盟军的《解散卡特尔法》(1947)中,禁止的目的是保护竞争,而溯其根源,则是基于对美国本身违法规则的直接移植。 〔4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和欧盟竞争法对限制转售价格的价值判断及事实推定就停留在最初美国本身违法规则的层面,之后德国本土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对于塑造德国法和欧盟法的自主性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秩序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市场是必要的,然而市场是不完善的,所以市场经济下必须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竞争原则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宪法,要求用法律来保护和落实不受扭曲的竞争自由,这个法律不仅具有保护竞争的作用,而且具有融合整个社会的功能。 〔45〕由此,在美国经验与德国本土思想的双重作用下,欧盟竞争法对限制转售价格规定了原则禁止及例外豁免,并形成了核心限制的传统。于是,这种模式下隐含的价值判断表现为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当然,还包括欧盟特有的共同体统一市场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效率观也对欧盟竞争法逐渐有所影响和渗透,导致相关法律文件中对限制转售价格的态度呈现出一定的转变。尽管如此,总体上,欧盟竞争法对限制转售价格的事实推定仍然是比较严苛的,这不仅是其背后法理念尚未出现彻底更迭的体现,也是欧盟在缺乏更多经济学理论支撑和实证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审慎选择。
此外,欧盟竞争法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规制模式更多地体现了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等机构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既表现在对条例、决定等二级竞争法律和指南等文件的制定权,也表现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欧盟法中的裁量权边际原则(margin of appreciation),欧盟委员会有非常广泛的裁量权边际。虽然欧洲法院等司法机关享有司法审查权,但在适用条例等文件时,法院一般仅就企业是否满足条例的要求进行审查,而不就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可以说,法院通过发展有限的仅以围绕“明显的评价错误”为基石的司法审查已经确认了欧洲委员会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地位,其相当遵从欧盟委员会的执法活动和决策。 〔46〕但是,通过对条约和二级立法的解释以及对欧盟机构行为效力的判断,欧盟司法系统在竞争法实施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三)欧美模式的体系性差异
美国、欧盟在各自的法律文化、市场环境、制度传统之下发展出了自成体系的限制转售价格制度,这两种制度所隐含的价值判断、事实假定以及采用的术语体系都是不同的。
就价值判断而言,欧盟仍然更重视对竞争秩序的维护,每个企业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被视为一项基本规则, 〔47〕而美国已经更为强调效率观念。在事实推定上,由于欧盟仍然强调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因此限制转售价格产生的经济效果并不是最为重要的衡量因素,即便逐渐更重视效率观念,在没有压倒性实证证据的情况下,对其积极效果的事实推定仍然非常谨慎;而美国,至少在联邦层面上,已经作出了较为积极的事实推定。当然,在事实推定基础上的违法性假定也就存在很大差别。欧盟仍然是强烈的非法推定,而美国已经不作违法推定。“欧盟竞争法体系和美国反托拉斯法体系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市场竞争程度及其他因素的不同,美国更关注假阳性问题(威慑过度),欧盟更关注假阴性错误(威慑不足),进而欧盟竞争政策更为严厉”。 〔48〕
在术语体系上,欧盟竞争法中存在的个别豁免、核心限制及对应的目的限制、效果限制与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本身违法和合理规则也是不同的。
关于本身违法与核心限制或目的限制,一般认为,核心限制协议通常被欧盟委员会视为目的限制。而对于本身违法规则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美欧学者也尚未形成统一认知,经常混为一谈。有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显著的差异使相似性成为一种错觉,因为不同于美国法的是,即使一项协议被认为是一种目的限制性协议,在欧盟竞争法框架内,当事人仍然可以依据《不适用第101条的较小协议通告》主张该协议没有对竞争造成显著影响,或依据TEFU第101条第3款主张豁免。 〔49〕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区别仅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中区分并不清晰,或者说实践中区分的程度取决于竞争主管当局和法院对于依据TEFU第101第1款或第3款进行辩驳的接受程度。 〔50〕
笔者以为,差异仍然存在。本身违法是一种法律判断,一旦某一行为被归类为本身违法,则其法律后果不可推翻。若要改变这一法律后果,唯一的路径是将该行为类型化为非本身违法行为,而核心限制是一种事实判断,虽然面临强烈的非法假定,但这种非法假定仍然可以推翻,只是其难度取决于更具体的法技术安排。
关于合理规则与豁免制度或效果限制,广义上来说,合理规则一定是基于效果的分析,其可以被涵盖在效果限制的范围之内,但效果限制同样可适用于本身违法规则。同样,合理规则也不能简单对应于豁免制度,因为依据合理规则可以独立完成对一项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和禁止,而豁免制度则必须与概括禁止条款一起才能最终确定一个行为的违法及责任承担状态。而且,欧盟的豁免制度仅仅规定了基于经济上的效率抗辩,美国的合理规则还可以主张依据公共政策或其他社会利益的抗辩,二者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综上,作为典型的舶来品,我国《反垄断法》在从纸面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理解所借鉴制度的内在原理和逻辑、体系、术语差异,必然导致解释上的困境和适用上的冲突。
三、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体系化解释
在正确理解美欧模式及各自存在的差异之后,要正确解释我国现行规定,首先必须要保持体系的一致性。
(一)回归体系的一致性
我国《反垄断法》在借鉴欧美经验时存在着体系性混乱,产生了“用美国的内核填充欧盟的框架”这一奇特现象。例如,我国虽然以欧盟法为蓝本,对垄断协议规定了原则禁止和例外豁免,但立法释义却指出:“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不少国家针对垄断协议的性质和对竞争秩序的影响程度,在执法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认定原则,即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 〔51〕“对涉及价格内容的纵向协议,多数情况下采取本身违法原则”。 〔52〕然而释义中却始终没有正面谈及我国反垄断法到底采取何种立场。类似地,曹康泰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中也指出,“国外关于垄断协议的两大判断原则: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 〔53〕并进一步认为“欧盟对垄断协议都是采取合理原则进行分析”。 〔54〕但在诠释我国制度时却写道:“我国反垄断法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垄断协议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还是合理原则,而是对所有垄断协议规定了豁免制度”。 〔55〕这一描述同样未能传递出任何有效信息,而且愈发让人难以理解“本身违法”或“合理原则”与我国垄断协议的认定,乃至豁免制度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要解决这一分歧,当务之急是在解释法条之时回归体系的一致性。美国的本身违法与合理规则,欧盟核心限制下的目的分析与效果抗辩,各成体系,逻辑自洽。而中国若希望在欧盟的立法蓝本下直接融入美国的术语体系,显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制度文本、事实假定以及适用模式之下,本身违法或合理原则无法与我国现行的立法框架进行无缝对接和完美融合。
在现行框架下,解释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应当先回到欧盟模式的话语体系中,本身违法与合理规则这组术语在我国当前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就本身违法规则而言,因为我国《反垄断法》对所有垄断协议均规定了豁免制度,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与之严格适应的成文法基础。就合理规则而言,如果在现有体系下纳入这一术语,从制度面,我国现行的豁免条款将被架空;从前提假定上,则推翻了限制转售价格常常具有显著的反竞争效果这一当前假定。这种对现行法的背离成本太高,且在事实层面上,也缺乏证据支撑。
事实上,合理规则在美国本土也仍具有极大争议,Leegin案并没有统一美国国内对限制转售价格的态度。该案判决之后备受国会攻击,国会已经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试图通过立法废除Leegin案,同时使本身违法规则成文法化。 〔56〕从州一级来看,推翻Leegin案的活动也得到了38个州总检察长的支持,他们致信国会,认为此举具有正当性,因为允许限制转售价格会导致价格增高。 〔57〕而且,在O’Brien v.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2012) 案中,消费者再次将Leegin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三倍赔偿。堪萨斯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则明确适用本身违法规则,成为全美第一个反对合理规则的州最高法院 。 〔58〕
而回归到欧盟话语体系之下,下一步要明确的就是,我国现行立法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违法性认定究竟应采目的要件,还是效果要件?
(二)法解释学的结论
运用法解释学方法,系统分析《反垄断法》第13、14、15条,本文坚持认为我国目前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规定应解释为允许豁免抗辩的推定违法。进而,应在原则上适应目的要件的同时允许效果抗辩。
1.字义解释可能产生的两种理解
《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是对横向协议的禁止,但第2款中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 虽然这一规定附属于横向垄断协议之中,但因使用“本法所称”字样而使该界定同样适用于出现在该法其他地方的“垄断协议”。由此,对于第14条的解释,似乎有两种可能的路径:(1)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法律禁止垄断协议——固定转售价格、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属于垄断协议——法律予以一概禁止;(2)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法律禁止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固定转售价格、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属于垄断协议——法律予以个别禁止。在第一种逻辑下,垄断协议与限制转售价格是包含关系,限制转售价格是垄断协议的典型列举,对其只需进行目的分析便可直接进行违法推定,从而予以一概禁止;在第二种逻辑下,两者之间是交叉关系,在判定行为性质时必须进行具体的效果分析,之后予以个案判断。
2.体系解释后的明确涵义
在字义解释无法确定唯一涵义之时,我们再寻求体系解释。作为对第13、14条禁止条款的例外,第15条规定了明确的豁免条款。于是,与15条之间逻辑自洽的要求则决定了第二种解释应予以排除。因为豁免的适用前提是某一协议构成垄断协议而落入第14条的禁止范围,适用条件则是该协议产生经济上的效率或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如果将第14条解释为限制转售价格既可能排除、限制竞争,也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在决定一项行为是否落入第14条禁止范围之时就开始进行效率分析,则势必造成第15条中包含的效率抗辩条款成为多余。而且依此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的经营者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竞争这一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将是多余的,这将造成第15条对第14条而言,除了第1款的第6项内容外,将成为事实上不必要的一个条款。 〔59〕对此,相关条文解读中有关豁免制度功能的说明也可以印证体系解释的结论。 〔60〕
此外,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制转售价格概括禁止加列举的立法方式也表明,对于列举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固定转售价格应采直接的违法推定。原因在于如果对被列举的两种行为仍需在违法性认定上进行个案合理分析,那也就与限制最高转售价格、建议转售价格和其他纵向非价格限制没有实质区别,不具典型性,因而也就无列举之必要。
然而,解释论虽可以明确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些争议,却无法回应不同域外经验带来的冲击和应然思考。强生案中对合理分析规则的倾向和发改委的相反探索,都说明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正处在十字路口,未来的完善中必须作出选择。
四、我国限制转售价格制度的完善
限制转售价格制度未来应如何完善,这是一个更加需要深入研究和论证的问题,于此仅先初步提出应衡量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应明确价值判断与事实推定
如前所述,价值判断是决定具体制度设计的根本性因素。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对于这一规定,法条解读中指出,这是立法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终形成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即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 〔61〕在多元价值中,公平竞争与效率均是应有之意。然而二者如何权衡,现行立法并不清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62〕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反垄断法》的使命首先是塑造良好的竞争秩序,不具备效率目标至上的市场条件和理论支撑。也许正因如此,“眼镜企业案”中,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了对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保护。
而对于事实假定,我国在《反垄断法》颁布之时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认知仍然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其是极其严重的反竞争行为。对于这种假定,不可简单因美国经验而随之改变。须知,各国的市场环境有所不同,同样行为作用于不同市场亦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因此必须依赖于经济学上理论和本国实证的更多支撑,这就要求立法者对市场有更深刻的把握和更全面的认识。
(二)应在一致的体系逻辑下探索自主融合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是以欧盟法为蓝本,基于法制传统、法的安定性和制度惯性,我国仍应以此作为体系基础。但是,美国经验的冲击却不能忽视,必须在现有体系基础之上探寻应对之道。事实上,欧盟在Leegin案后也遭遇了许多挑战,正在改革探索之中。虽然限制转售价格在欧盟法中仍然被定性为核心限制,但是《指南》(2010)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指南不仅第一次明确承认限制转售价格潜在的效率,还分析了限制转售价格可能产生足够效率并因此可以依据TEFU第101条第3款豁免的具体情况。此外,在葛兰素史克案(2009)中,欧洲初审法院对核心限制协议的态度有所改变。该案并非限制转售价格案件,但其所涉及的平行贸易限制同样属于核心限制协议。该案中,欧洲初审法院认为:“限制平行贸易目的本身并不成立协议具有反竞争目的的假定……虽然意图限制平行贸易的协议原则上被认为是具有限制竞争的目的,但它仅适用于假定剥夺了最终消费者的利益的协议。” 〔63〕这意味着,要证明协议具有限制竞争的目的,先决条件是证明该协议会剥夺最终消费者在产品供应或价格上的利益。换句话说,欧洲初审法院没有一如既往地接受欧盟委员会的“目的分析”,而是在一开始就要求效果分析。 〔64〕虽然欧洲法院最终否定了初审法院的这一解释,但可以看出与合理规则类似的效果分析已经逐渐向欧洲司法系统渗透。
(三)应重视法律实施考量
“反垄断政策的健全不但依赖于法律规则,还依赖于执法机制。只有好的规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执法机制保障法律以合理的成本获得合理程序的遵守”。 〔65〕对于颁布仅七载的《反垄断法》来说,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非常重要,这有赖于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实施既涉及法条本身,也关乎成本考量、权力配置、程序性规则等各层次问题。
从制度本身来说,美国的合理规则虽具有个案审理的灵活性,但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对于缺乏反垄断经验的我国司法机关,显然并不具备美国法院系统丰富的审判经验,在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上,更是不具专业性。而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制定条例、实施细则的路径则具有比较优势。原因在于,一部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一定是建立在前期全面的调研基础上,并综合权威专家的意见,通过立法的程序将其成文化,这种方式与我国法院的个案裁判相比兼具专业性和确定性。而且我国《反垄断法》已经明确了公共实施的主体地位、私人实施的补充地位,这一点与欧盟竞争法更为近似。同时,我国现阶段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审判实践均不理想,在缺乏三倍赔偿制度等有效激励的情况下,过重的举证负担使得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前景更加堪忧。难以想象,在资源有限、经济学知识不足、实践经验难有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对美国模式进行完美驾驭。因此,在进行完善时,必须注意我国现阶段反垄断法实施的水平、资源、现状、实施机构之间权力的配置等。
五、结语
与现行立法目标、立法体系、事实假定相适应,我国《反垄断法》仍应保持对限制转售价格的违法推定。但同时,鉴于美国的经验冲击,不妨考虑适度降低严厉程度。具体制度上,可以借鉴欧盟的“显著性标准”和安全港制度。虽然在欧盟竞争法中,这两种制度并不能适用于限制转售价格这种核心限制,但我国可以尝试借鉴,充分利用市场份额实现对违法行为的筛选和过滤作用。当然,这些制度的科学与合理设计应该建立在对《反垄断法》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和我国市场的更深刻认识和把握之上,对此,经济学理论和更多的实证证据至为关键。此外,鉴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的分歧,由立法机关明确执法机关的准司法权,妥善协调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间的冲突亦是我国目前《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陈越峰)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来源:http://www.court.gov.cn/xwzx/yw/201310/t20131023_189076.htm,2013年12月1日访问。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丁一:《触及反垄断法,茅台五粮液吃最大罚单》,载《中国工业报》2013 年3 月6 日第B02 版。
《合生元等乳粉生产企业违反〈反垄断法〉限制竞争行为共被处罚6.6873亿元》,来源:http://xwzx.ndrc.gov.cn/xwfb/201308/t20130807_552992.html,2013年12月1日访问。
《部分眼镜片生产企业转售价格行为被依法查处》,来源: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5/t20140529_613562.html,2014年7月1日访问。
黄勇、刘燕南:《关于我国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基于我国立法和传统理论,本文主要探讨固定转售价格和限制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最高转售价格一般被认为有利于消费者,而真正的建议转售价格通常因不具有强制性而不受法律规制。但是,对于建议转售价格亦存在争议,例如李剑教授基于对消费者行为决策模式的分析认为,建议零售价的法律规制应当超越协议的视角,将其纳入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体系之中。参见李剑:《消费者价格决策方式与建议零售价的法律规制——行为经济学下的解释、验证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王晓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析评》,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此外,由于德国竞争法与欧盟竞争法(前欧共体竞争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2005年修订后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几乎全盘欧洲化,故本文不再单独论及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对中国《反垄断法》的独立影响。参见方小敏:《竞争法视野中的欧洲法律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
《谢尔曼法》自1890年颁布以来已经历了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2004年。修改后的第1条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实质要件未发生改变。
See 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 n , 166 U.S. 290 (1897).
See Hopkins v. United States, 171 U.S. 578 (1898).
See United States v. Joint-Traffi c Ass’n, 171 U.S. 505(1898).
See 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 221 U.S. 1 (1911).
李钟斌:《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页。
王玉辉:《垄断协议本身违法原则的运用与发展》,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
Se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See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1911).
依据Colgate规则,当生产商不具备制造或维持垄断的目的时,其事先宣布建议零售价并拒绝同削价的零售商进行交易是一种单边行为,而非协议或共谋。See United States v. Colgate& Co., 250 U.S.300( 1919).
依据GE规则,生产商可以通过将零售商作为代理人,以寄售协议的方式销售产品,从而避免适用本身违法规则。See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Co., 272 U.S. 476 ( 1926) .
Se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See Julie M. Olszewski, “Overruling a Nearly Century-Old Precedent: Why Leegin Got It Right”, 94 Iowa L. Rev. 375, 381 (2009).
Albrecht案中,被告是圣路易斯市“Globe-Democrat”晨报的出版发行商,拥有172个家庭投递区域,原告从被告处批发报纸并根据协议对99号投递区域进行独家投递。被告在报纸上标明了建议零售价,如果经销商超出最高建议价,其特定区域的独家投递资格将被终止。之后,原告多次加价销售,被告发函抗议并采取措施争夺其客源。之后,被告通知原告如果其同意在建议价格上销售,被告愿意将客源返还,否则将终止一切商业合作。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See Albrecht v. Herald Co., 390 U.S.145,146-149(1968).
See Albrecht v. Herald Co., 390 U.S.145,153(1968).
See 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 433 U.S. 36 ( 1977) .
See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郑鹏程:《美国反垄断法“本身违法”与“合理法则”适用范围探讨》,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0期。
Dewey, Monopoly in Economics and Law, 142 (1959). 转引自[美]基斯•N.希尔顿:《反垄断法》,赵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叶卫平:《反垄断法的价值构造》,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导言第3页。
唐要家:《转售价格维持的经济效应与反垄断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Marsela Maci, “The Assessment of RPM under EU Competition Rules: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Based on a Non-substantive Analysis”, 35(3) E.C.L.R. 103-109 (2014).
参见胡晓进、任东来:《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1889-1937年的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叶卫平:《反垄断法的价值构造》,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虽然上述文件在《纵向限制协议集体豁免条例》(2790/1999)和《纵向限制指南》(2000)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于我国《反垄断法》生效之后,但除了指南中相关内容有所调整,主要模式与我国立法时的版本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变更。
See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1.1.
如果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订立各方市场份额低于15%,一般认为不构成对竞争的显著影响,此种情况下,不落入TEFU101条的禁止范围。See European Commission, relat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1997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fall under Article 81(1) of the EC Treaty(2001/C 149/05), 或简称de minimis Notice(2001/C 149/05),point8,(b).
See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1.3.
European Commission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2010/C 130/01), paragraph (48).
Commission Regulation 330/2010/EU,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paragraph (10).
European Commission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2010/C 130/01), paragraph (47).
对于其他非核心限制型纵向协议,如果协议方市场份额超过了30%的市场份额,不能推定该纵向协议落入第101条(1)款的禁止范围,或不能满足第101条(3)款规定的条件,但也不能推定落入第101条(1)款的禁止范围的纵向协议通常将满足第101条(3)款规定的条件。European Commission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2010/C 130/01), paragraph (23).
王健《:垄断协议认定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研究》,载《法学》2014年第3期。
See Marsela Maci,“ The Assessment of RPM under EU Competition Rules: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Based on a Non-substantive Analysis”, 35(3) E.C.L.R. 103-109 (2014).
[美]戴维•J. 格贝尔:《欧洲竞争法故事中的某些德国角色》,王晓晔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
Wernhard Moeschel,“ Vertical Price Fixing: Myths and Loose Thinking”, 34(5) E.C.L.R. 233-238 (2013).
方小敏:《竞争法视野中的欧洲法律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See Marsela Maci, “The Assessment of RPM under EU Competition Rules: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Based on a Non-substantive Analysis”, 35(3) E.C.L.R. 103-109 (2014).
Dr. Nikolaos E. Zevgoli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Legal Certainty Versus Economic Theory?”34(1) E.C.L.R. 25-32 (2013).
李剑:《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体系冲突与化解》,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David Bailey, “Presumptions in EU Competition Law,” 31(9) E.C.L.R. 362-369 (2010).
George P. Kyprianides, “Should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Be Per Se Illegal?” 33(8) E.C.L.R. 376-385(2012).
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释义》,第41页。
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第73页。
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第73页。
John R Foote, Ernest N. Reddick,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fter Leegin: Defense Perspective,” 22(2) Competition: J. Anti. & Unfair Comp. L. Sec. St. B. Cal. 95(2013).
Nathaniel J. Harris, “Leegin’s Effect on Pri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9 J. L. Econ. & Pol’y 251, 262 (2013).
Michael L. Fessinger, “A Century Behind? The Kansas Supreme Court Opts Out of the Rule of Reason in O'brien v.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 Inc,” 52 Washburn L.J. 323,324 (2013).
黄勇、刘燕南:《关于我国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在诠释豁免制度时有这样一段内容:“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可能同时具有反竞争效果和其他积极的效果,判断该协议是否具有违法性,关键在于分析平衡其两方面的作用,从总体上判断该协议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只有利大于弊的垄断协议才认为不具有违法性。”参见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5页。
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suzhou/2013-11-12/c_118113773. htm,2013年11月22日访问。
See GlaxoSmithKline (2009) E.C.R. I-9291, pp.59-60.
Marsela Maci, “The Assessment of RPM under EU Competition Rules: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Based on a Non-substantive Analysis”, 35(3) E.C.L.R. 103-109 (2014).
[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二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