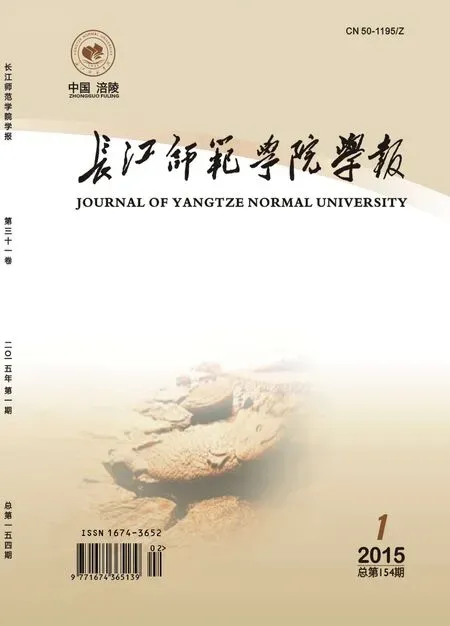明末丛林积弊及其颓败考察
明末丛林积弊及其颓败考察
刘晓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河南郑州451000)
[摘要]明末的佛教丛林戒律废弛,寺僧修持不力,僧团寙败日深,丛林积弊重重。明代中后期的宗教政策更随着帝王的个人倾向而代有变更,表现出一朝被废、一朝复兴的特点,以致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揆诸史实,国家不恰当的宗教管理方式正是导致明末佛教丛林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明末;丛林积弊;颓败考察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1-0049-06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刘晓玉,河南南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宗教哲学研究。
明末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政教关系问题、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其研究的路径多是以禅净合流、儒佛交涉、三教合一为视角的整体性研究,观点明确,论述颇丰。然而对明末佛教丛林寙败的具体状况,纵观有明一代国家宗教政策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鲜有做深入探讨者。这里主要以信史为据,爬梳来自佛教僧团内部以及官修正史两方面的史料,力图完整地呈现明末佛教丛林的真实状况,进而探析其颓败的真正原因。
一、积弊日深:丛林之规扫地尽矣
“明末四大士”之一的蕅益智旭(1599-1655年)是一位对佛教发展极具忧患意识的宗教大师。他曾于《寄剃度雪岭师》一文中痛心疾首地陈述了当时佛教界“三可痛哭,三可哀愍”之事。依智旭所见,“丛林三痛”之首当为戒律问题。他曾在《自传》中言:“二十七岁,遍阅律藏,方知举世积讹。”[1] 798当时律师少有师承者,精研律学、严持律仪更是无从谈起;所谓教门也只是依文解义,图一时言辞快意,未有在心地上悟入知解;而禅宗门人要么狂罔无知,要么落入知解偏见,更有盲修害炼者落入窠臼而不自知。智旭所哀之事,其一是本无佛心、佛行之人借佛法图名求利;其二是缺乏远识,无参究向学之心;其三是自高自大,轻视净土修行。智旭针砭出家者汲汲于名利以及禅、教、律三宗之士的种种偏谬之处反映出当时佛教丛林的弊病问题。非独智旭,与其同时代的曹洞宗湛然圆澄禅师(1561-1626年)也曾撰有《慨古录》一文,描述了当时“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2] 366,下的佛教僧团的寙败景象。
其一,圆澄认为今不如古者,首当其冲的就是师资关系。“是以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讥呵”[3] 367,上。师徒间关系不睦,信任度不高,一方面源自为师者品行不端,有载“今之师僧,见弟子有英俊之资,便乃关门就养,不许其动步。何也?恐近好人,不附于我也”[4] 371,中,为师者品质低劣,难怪学者疑惮;另一方面源于为弟子者非真心向学,不知礼敬师长,“今时沙门,曾不见为真灯故,回礼为师。或慕虚名,或依势道,或图利养,或谋田宅,或于本师闻气,弃旧从新,回礼于他,旧师眇然视为闲人”[5] 374,下,如此拜师,掺杂了太多的现实功利。另有求学者,“或师范诫训过严,或道反议论不合,便欲杀身以报之也,或造揭帖,或捏匿名,徧递缙绅檀越,诱彼不生敬信”[6] 373,上,如此行径,毫无师徒情谊可言。对禅宗而言,“机锋棒喝”历来被视为度化接引的重要方式,禅宗史传中也不乏“斩臂”“断腿”的公案被奉为经典,如今的情况是“为师徒者,一语呵及,则终身不近”[7] 374,中,可见“棒喝之法”于当世已不被普遍接受。对这种现象,圆澄以今古之人“根器利钝有差”来解释。所谓“古之用逆者,间
为一二利根而设,非谓槩施之丛林也。若纯以逆用,何能容千百众乎?故知慈爱者摄众之要枢,不可废也。”[8] 367,中
其二,僧团鱼龙混杂,僧品低下,出家者修学志趣不高,攀缘俗务,奢侈成风。圆澄指出,在当时丛林中,“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9]369,下他们要么“毋论神庙、天祠乃至人家享堂,苟衣食可足,皆往住焉”[10] 374,上,要么“毋论富贵贫贱,或妓女丐妇,或大士白衣,但有衣食可资,拜为父母,弃背至亲,不愿廉耻。”[11] 3732,中这些人出家动机不端,只是为逃避世俗压力而寄居佛门谋衣食,所以“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惟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或言我已成佛,或言我知过去未来,反指学问之师,谓是口头三昧,杜撰谓是真实修行。哄诱男女,致生他事。”[12]370,上在圆澄看来,正是这些人混入佛门才造成了僧品芜杂、丛林败落的情况。
其三,僧团领众者的选拔、任用存在问题,学养不高。住持、首座乃僧团的领众者,其修为高低直接地决定着僧团的整体素质,乃至佛教的兴衰。然从现有的史料看,明末佛教丛林领众者的整体素质令人堪忧。根据明朝的皇家礼俗,在新皇即位之初,会遴选童子作为他的替身出家修行,所建皇寺梵刹,也由这名童子担任主持。对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所记载,“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生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者沿故元俗也。”[13]卷27京师敕建寺,2621在圆澄看来,“夫住持之任,位侔佛祖,非三二十年精操苦行,博炼宗乘者不能也。若愚童子住持,非唯宗教不扬,抑亦规矩不振。所费巨金,当复何图……童子称师,宁不愧乎。”[14] 372,上如果说在皇权干涉下,由童子担任住持的现象属于特殊情况,其影响范围还不大,但若根据圆澄所述的情况,可知当时佛寺住持整体素质之低下,“前代住持,必推一方有道德者,有司推举,朝廷勅住,或为世主知名,持诏演道,由是千百共居,人不之疑。今也不然,才德一无所有,道学有所未闻,世缘颇足,便名住持,致使丛林衰落,礼义绝闻。更兼官府,不辨清白,动辄行禁,使真道者退身不就,而不肖者百计攒谋,佛法愈衰,丛林愈薄。复有屑屑之徒不知大体所开,才出家来,苟图声誉,以为己任,急急于名利之场,或私创山居,或神庙家祠,男女共住,或典赁民房,漫不可稽。”[18] 368,下有真道者退身不就,主持之位成为钻营之辈追逐名利、地位的对象,长此以往,佛教怎会不衰败呢?
其四,讲僧、禅僧悟解不力,瑜珈教僧滥行科仪,对僧人受戒修学的次第存有疑议。“古来十八家判教门人,各擅己宗,皆有悟入,所以诤论,有不已者。今之讲师,无经不讲,求其悟入,恐或未然”[19] 371,下,过去的讲僧因各依教判,所以才有所专精,今之讲僧看似无经不解,无典不通,实则专精悟入的程度不及前人。“古之为宗师者,高提祖印,活弄悬拈,用佛祖向上机关,作众生最后开示,学者参叩不及处,劝其日夜提持,不记年月,然后悟入。今之宗师,依本谈禅,惟讲评唱。大似戏场优人,虽本欲加半字不得,学者不审皂白,听了一遍,己谓通宗,宗果如是易者,古人三二十年参学,竟为何事,岂今人之根,利于古人耶?由是而推,今之谈宗者,实魔所持耳。”[20] 371,下依圆澄所见,当时所谓修禅之宗师照本宣科,落入文字功夫者众,真正悟入心地者鲜有其人。“世称焰口,即相应之法。所言相应者,乃三密严持之谓也,口密诵咒,手密结印,心密观想。是以古师授受,必择行解相应,堪绍灌顶者,方为传授。如缘起文中所说,今所言行解相应者谁?只如观想者必须坐禅集静,静功若就,则于一念静心流出,所谓变大地作黄金,搅长河为酥酪,非偶然也。近来新学晚辈曾不坐禅,又不习观,但学腔科,滥登此位,非唯生不可利,恐损己福祉。”[21] 374,上依圆澄所解,瑜珈教僧虽以经忏为业,但也须有禅、观两业的坚实基础才能发挥效用,而当时的教僧,只掌握了外在的科仪、音声,徒具其形,未掌握其中真义。
其五,沙门不谙律仪,戒律废弛。戒为三学之首,持守戒律乃出家僧人的本分。然值明末之际,佛教律典久已废弛,出家受戒者大多不谙律仪,整个僧团在戒律守持方面不尽人意。据圆澄所述,“今也沙门,多有傍女人住者,或有拜女人为师者,或女人为上辈,公然受沙门礼,而漫不知为非者。……唯破和合僧,则七逆罪收。彼果有过而告诸外人者,律所谓有根波罗夷。彼果无过而告诸外人者,律所谓无根波罗夷。故知有根、无根,皆犯谤罪。所以朔望布萨不许沙弥盗听者,盖佛祖恐沙弥无知,向外人说,故深防
之也。今则不然,诸方学者,自负英灵,几登法位者,多堕此谬,自损福祉,受三涂报,皆由不读戒律故也”[22] 373,上,“古之出院者,为众所弃,名同死罪,律制被弃比丘,不与同宿,犯波逸提,被弃者愧,不敢立于人前。今时沙门,视丛林为戏场,眇规矩为闲事,乍入乍出,不受约束。”[23] 373,下依“八敬法”,纵然是100岁比丘尼见到20岁的新戒比丘,也应礼敬供养,然在当时丛林中出现的“拜女人为师”“女人受沙门礼”的现象则反映出佛教戒律“八敬法”的废弛,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比丘尼在佛教僧团中地位的提高。而“波罗夷”“波逸提”属比丘、比丘尼所应持守的基本戒条,其中“波罗夷”还属戒律中的最重之罪,一旦违犯,将被永远摈除在僧团之外。所以根据文献记载的明末丛林的持戒情况,可以推知当时的僧人要么是不通律典,不谙律仪,要么就是无视戒律,知戒而不持,想必不通戒律而难持戒者众。
二、政令不常:一朝被废,一朝复兴
纵观有明一朝,除嘉靖皇帝对佛教强烈排斥外,明朝大部分皇帝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尊信倾向。洪武朝(1368-1398年)乃明代宗教政策的始定期,各项政令制度完备,对宗教的态度明确且相对合理。至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因皇帝个人的侫佛倾向,国家开始更改宗教政策,且有违明初的政令精神,是明代宗教政策随意变更的开始。在英宗之后的诸帝常因个人宗教倾向和政治认识的不同更改前朝法令,宗教政策表现出一朝被废、一朝复兴的特点,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
洪武朝(1368-1398年)是明朝宗教政策制定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家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与取向、国家管理佛教僧团的僧官制度、有关度僧的数额、度僧的条件、寺产数额等相关政策也都在这一时期订立和完成。从具体的条文可知,明太祖时期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控制加利用。一方面,严格限制出家人的数量、性别、年龄以及僧俗之间的交往,避免其对社会生产、政治稳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扶植佛教的发展,以图利用其“阴翊王度”“暗助王纲”的政治效用。明太祖之后的永乐(1403-1424年)、洪熙(1425年)、宣德(1426-1435年)三朝也基本延续了洪武时期(1368-1398年)的宗教政策,只是其中的永乐皇帝表现出了对西藏喇嘛教僧人的特别尊崇。据《明史》所记,“明兴,犹袭元习,崇事番僧。号帝释国师,倾国檀施,合宫膜拜”[24] 636,但是这三朝在度僧给牒方面都是理性而且有节制的。
英宗执政的正统朝(1436-1449年)和代宗执政的景泰朝(1450-1457年)是明代宗教政策由理性、节制向非理性、不节制演变的转折点。从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六年(1441年),国家基本上是年年度僧,且数额巨大。与明初相比,国家度僧政策之所以发生转变,乃因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侫信佛教,他以其个人因素影响了当时的国家政策。据《明史》记载,“王振侫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25]卷164列传第52,4457到正统朝(1436-1449年)后期,明朝则相对加强了对佛教的管束,并多次强调“通过考试”乃“得度”的条件。至景泰朝(1450-1457年),代宗也如英宗一般崇佛。据载,“当景泰(1450-1457年)时,廷臣谏事佛者甚重,帝卒不能从。而中官兴安最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建大隆福寺,庄严与兴隆并。”[26]卷164列传第52,4458自景泰二年(1451年)起,明朝变更度僧制度,僧人得度的条件不再是通过考试,而是缴纳钱粮,之所以实行此项政策乃因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剌军掳走,此后连年不断的边疆战事和政治赔款造成了明朝军费、粮草的紧张,为弥补亏空、供给钱粮,明朝政府实行鬻牒度僧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标志着自洪武时期开始实行的给牒“蠲免丁钱”政策的废除。
自宪宗成化朝(1465-1487年)到世宗嘉靖朝(1522-1566年)为明朝中期。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国家在度僧、控僧、寺产等方面的宗教政策又有重大的调整,这些变化直接地影响着明朝后期的佛教发展走向;嘉靖(1522-1566年)之后的隆庆(1567-1571年)、万历(1572-1620年)两朝直至崇祯(1627-1644年)亡国为明朝后期,这一时期以神宗统治的万历朝(1572-1620年)时间最久,占近5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直接地决定了明朝末年的佛教环境,是明末佛教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
宪宗即位之初,曾将清理无度牒僧、道作为“新政”之一,大有整饬佛教之决心,然自成化二年(1466年)起,明朝便开始以“赈济灾民”为由大肆鬻牒度僧。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年(1466年)共度僧、道13万[27]卷104,成化八年五月戊戌。自天顺元年(1457年)至成化二年(1466年),10年共度僧、
道13万2千2百余人[28]卷120,成化九年九月癸巳。自成化二年(1466年)至成化十二年(1476年),10年又度僧、道14万5千余人[29]卷195,成化十五年十月庚子。若以洪武(1368-1398年)、永乐(1403-1424年)时期的度僧数额为百计,正统(1436-1449年)、景泰(1450-1457年)时期为千计,到成化(1465-1487年)时期显然每次度额已达万计,比明朝初年,增长了10倍,可见度僧数额之巨。如果说国家为筹措钱粮,弥补亏空,大肆鬻牒度僧,可那么多的普通百姓愿意纳银为僧,主要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因为拥有僧籍就意味着可以免除徭役,甚至有的还可以避税。大量社会闲散人口涌入佛门,在寺田数额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给寺院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其中也不乏俗披僧衣之徒,混迹丛林,做出僧俗混杂、有伤风化的事情来。在明代诸如《三言》《两拍》这一类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僧人恶劣形像的描写,尽管有夸大之嫌,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大肆度僧后丛林芜杂、僧品低下的现实状况。
宪宗之后的弘治朝是对成化(1465-1487年)时期的弊制进行理性调整的时期。弘治元年(1488年),明朝先后下达限制寺产、检肃僧人的政令,更停止了“十年一度”的例令。然此禁令未实施多久,便于弘治九年(1496年)被废除。是年,明政府以通过考试为条件给牒度僧,当然人数与前朝相比多有节制。在此期间,请求开度的僧官和反对度僧的士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度与不度”“禁与开禁”的争论,双方各陈其利,均以打动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为目标。
弘治(1488-1505年)之后正德(1505-1521年)一朝的宗教政策,又开始走向混滥和无度。该朝不仅恢复了鬻牒度僧制,所度僧数多以万计,所收银钱倍于前朝,还明码标价,公然买卖僧官,其影响十分恶劣。此外,与前朝几位皇帝相比,明武宗更宠佞番僧。
明世宗崇信道教,有着强烈的排佛倾向,在其长达45年的统治时间里,先后颁布了多项针对佛教的宗教政令:诸如毁寺废僧、沙汰沙门、禁止游方、禁止集会讲经、禁止开坛传戒等,更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强令有田粮的僧人也编入黄册,同里甲一样供应赋役,这样出家僧人就失去了先前的身份优待,同俗人一样,既要缴纳税赋,又要承担徭役,不可不谓苛刻严厉。然考量这一政策的制定,除明世宗排斥佛教的个人倾向外,应该与国家试图以此控制俗人以出家逃税避徭有关,或许对社会生产有利,但对佛教的后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自隆庆(1567-1571年)、万历(1572-1620年)开始,明朝进入后期。隆庆一朝虽年代不长,但却多次以“筹措军饷”为由鬻牒度僧,可明穆宗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宗教倾向。万历(1572-1620年)时期,明朝的宗教政策又发生转向,一改嘉靖朝(1522-1566年)的毁佛、控僧政策,转而开始扶植佛教,其主要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内帑在全国复寺建庙,虽有庭臣多次劝谏但未被采纳。万历(1572-1620年)之后,国势日衰,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使得后世诸帝已无暇顾及宗教问题。
三、衰败之源:国家设教未尽善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固守陈规不符合变化了的现实情况,但如此肆意无度、朝令夕改必然是缺乏理性的,这也难怪明末的僧人圆澄以“高皇帝之《钦录集》犹在,高皇帝之圣旨绝不执行”[30] 375,上慨叹明朝宗教政策的演变对佛教发展的消极影响。圆澄于《慨古录》中提出的“国家设教未尽善”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是宗教集会;其二是度僧制度;其三是僧官制度;其四是赋役制度。
其一,国家禁止丛林讲经集会的政令对佛教发展最为不利。所谓“今之丛林满百余,辄称红莲、白莲之流,一例禁之,致使吾教之衰,莫可振救。”[31] 368,上“先代圣王,见一高僧,敦请出世,座下容五百一千二千,乃至三千同住,日夕讲论,尚不能尽佛之深妙,复不能尽挕顽类。今也,欲禁其不谈。岂今之辈,皆圣贤之资,不须学耶?为复任其狂悖而不必学耶?由是而推,执政者尽禁讲经论道,而资彼无名者流,狂悖懒惰,以为是者,其犹返戈倒授而养成其恶也。”[32] 368,中明初,国家并未禁绝丛林集会。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还专门颁旨令“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僧俗善人许令斋持戒牒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他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33] 929,上由于嘉靖时期(1522-1566年),民间白莲教一度活动猖獗,为防止白莲教徒利用宗教集会混入其中,挟惑媚众,危及政权,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政府下达禁令,要求“聚众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
止”。[34]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红莲教、白莲教属于宗教外衣包装下的民间组织,其神秘且颇具煽动力的表现形式使得生存于乡野之中的下层民众易受蛊惑,历来为政府所禁绝,明朝为防范白莲教,故而禁绝了一切形式的宗教集会。
其二,国家废除考试度僧制度,以致僧品芜杂、丛林衰败。洪武十年(1377年)国家定例《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为僧人必须通达的经典。若欲出家为僧者,必须先参加国家组织的试经考试,通过者方给牒披剃,不过者责令还俗[35] 928,上。直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明朝也是通过考试给牒度僧,沙汰沙门。但景泰二年(1451年),令“僧道赴四川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36]卷206,景泰二年秋七月辛亥,从而打破了先朝考试度僧、免费给牒的制度,至明末更是“立例上银。”[37] 368,中为定例圆澄认为“假如中试得度,则知僧之难得,非惟各为其道,又且竞慕其荣,利根者日夜读习,钝根者生胜渴仰,其种善根者,不亦多多矣。若不以学问为重,则贤愚不分,将佛法视之蔑如也,可谓愚者得其计,而智者空资叹息矣。”[38] 370,上较为严格的考试度僧制度,不仅是明朝控制人口流失,保障社会生产、人口繁衍的有效举措,也维护了佛教僧团的纯正性,而纳银即可得度的政策,最终造成丛林“无名之流,得以潜之,然则此之流类,满于天下”[39] 368,中的情形。
其三,“释受制于儒”的僧官选拔制度流弊甚大,致使高贤之士隐而退之,不肖之徒充而任之,僧官素质令人堪忧。明代的僧官制度作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经历了一个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曾命浙江之东西五府的名刹住持,聚集南京,于天界寺设立“善世院”,掌管天下僧务,当时德高望众的原璞禅师,独出方略,具有条叙,所提纲文、条款在全国推行[40]卷3,909,中。这是明代僧官的雏形,且整个制度、纲领的构建完全由僧人参与完成。洪武十四年(1383年),礼部颁旨曰:“释道二教流传已久,历代以来皆设官以领之。天下寺观僧道数多,未有总属,爰稽宋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41] 931,上,至此明代正式设立了掌管天下僧务的政府机构。具体设置是在京城设置僧录司,掌管天下僧教事。有善世二员,正六品,即左善世、右善世;阐教二员,从六品,即左阐教、右阐教;讲经二员,正八品,即左讲经、右讲经;觉义二员,从八品,即左觉义、右觉义①第一批僧录司官员名单为“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羲;左讲经玘太朴、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又在各地府、州、县,设僧纲、僧正、僧会,分掌其事。其中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教事;各州僧正司,设僧正一员,掌本州僧教事;各县僧会司,设僧会一员,掌本县僧教事。整个机构的设置,沿袭宋制,官不支俸[42] 931,中。出家人既要遵守佛门戒律,同时还要受到国家律令的管束,其界限就是所涉事务属僧对僧事,还是僧涉俗事。所谓“在京、在外僧道衙门,专一简束僧道,务要恪守戒律,阐扬教法,如有违犯清规不守戒律,及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如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情重者送问,在外即听有司断理。”[43] 931,下从明初制定的典章来看,僧官对教内事务的管理还是拥有较大自由的,举凡出家僧人户籍的审查,经文考试的组织,度牒的审核、发放等相关事宜都由僧官处理[44]卷2钦录集,220。到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当时的僧录司右善世南浦,左阐教清让两位僧官涉嫌在京城正式度牒审查资格中贪污舞弊,当时的礼部尚书胡潆上奏,遣给事中、御史、礼部官各一员共同考审[45]卷243,景泰五年秋七月辛亥。自此之后,明代僧官失去了自行审核出家资格的权限。
其四,僧人劳税过重,寺产被官府、豪强侵占,出家反累于俗。明初“太祖于试度之外立例:纳度上银五两,则终身免其差役。超然闲散,官府待以宾礼。”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一应差役不许僧应”[46] 934,下,“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听跪拜。”[47] 368,中按此典章行事,明初的僧人不仅没有劳役之苦,还可受官家礼待。然“今则不然,凡纳度之后,有田当差,有人当丁,迎官接府,祈晴请雨,集仪拜牌,过于亭长。夫欲远累出家,而不知反增其累也。且俗人当里长,子姓百十,皆止一户,更无二役。僧家则不然,毋论一人二人,以及千百,皆要人人上纳,似又不如俗人之安河也。又俗人纳农民者,则以优免,终则就仕成家。而不知僧者何所图?而上银纳光头役使耶?若迟缓不纳,则星牌火急催迸,过于他役。”[48] 373,上这种改变,始自嘉靖十九年起(1560年),出家人不仅要按例纳度上银,还要缴税、承担徭役[49]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戊戌,所
谓僧事、俗事无不牵涉其中,出家反累于俗。
四、结语
明末,在教门中一批像智旭、圆澄这样的有识之士有着匡正时弊、振济颓纲的救世情怀,他们痛陈明末丛林窳败、戒律废弛、禅净两仪修持不力的种种现象,直击佛门僧团弊端。从政教关系来看,自明代中后期的宗教政策常随着帝王的个人倾向代有变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排佛的士大夫、受宠的僧官、侫佛的宦官、崇佛的帝后等各种力量牵涉其中,其制定政策急功近利,更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对一些宗教问题的处理也过于简单、粗暴。应该说在以维护政权为第一要义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佛教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国家宗教管理的不恰当正是导致明末佛教丛林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1] [明]智旭.澫益大师自传[M]//灵峰宗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3][4][5][6][7][8][9][10][11][12][14][15][16][17][18][19][20][22][24][30][31][32][37][38][39][47][48] [明]圆澄.慨古录[M]//卍续藏经·册65.[中国台湾]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4]明书·异教传[M]//蓝吉富.大藏经补编·册17.[中国台湾]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
[25][26]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7][28][29] [明]刘吉.明宪宗实录[M]//明实录[M].[中国台湾]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33][35][41][42][43][46] [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M]//大正藏·册49.[中国台湾]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34][49] [明]徐阶.明世宗实录[M]//明实录.[中国台湾]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36][45] [明]孙继宗.明英宗实录[M]//明实录.[中国台湾]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40][明]如惺.大明高僧传[M]//大正藏·册50.[中国台湾]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44][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M]//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6册.[中国台湾]台北:明文书局,1980.
[责任编辑:丹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