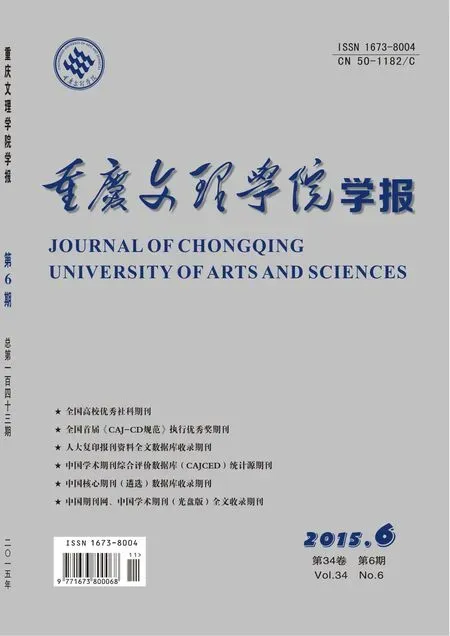审判管理的现代转型
——从形式公开向实质公开的嬗变
戴乔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重庆400000)
审判管理的现代转型
——从形式公开向实质公开的嬗变
戴乔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重庆400000)
在司法实践中,高歌猛进的审判公开过多地注重其形式表现,而忽视了实质内容。在制度层面,宏观性审判公开制度缺乏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在目标上,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知情与监督要求的开放性需求被异化成了“选择性部分公开”中的保守性供给;在价值上,原控制司法权力的功能定位被人民法院的自保性策略所取代,最终导致了应当成为原则的审判公开退缩成了一种例外。只有努力开启审判公开的制度化,落实审判信息公开的规范管理,不断拓展法官素质的职业化,提升审判信息公开的自我管理,及时抑制司法心思的内卷化,优化审判信息公开的质效管理,充分打造审判设备的数字化,加强审判信息公开的技术管理,才能有效克服审判公开的形式主义倾向,将审判公开真正推向司法公开的实质化道路,从而真正保障社会主体与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督促法官不断提升其法律素养与职业道德,引导与教育社会公众知法守法,最终防止司法腐败并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审判信息公开;权利保障;形式公开;实质公开
当法官从天国降临尘世,我们看到,他也是人,为了赋予其判决价值,我们开始在司法过程的更为精确的机制中找寻某些保障措施,以确保每个判决总将是理性而非恣意行为的产物。
——皮罗·克拉玛德雷
司法是现代社会解决纠纷、化解民怨的一种低成本的法律机制,是一种充满智慧、富有理性的控制社会秩序的常规手段[1]。为了维持与提升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权威,近年来我国的司法体制在中央的主导之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在审判公开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操作上均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无论是审判公开的具体内容,还是审判公开的抽象内涵,统一化与制度化已是大势所趋。审判公开已然从近代市民革命的一项政治要求,开始成为司法裁判活动的旗帜性话语,并发展成为人权保护的必要方式。
然而,由于目前的审判公开过多地局限于形式公开的范畴,未能在实质上有效应对互联网与自媒体等信息化浪潮所凝聚的公众期待,故其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可回避且亟须化解的深层矛盾。否则,公信力极度缺失的司法现状不但不能在愈演愈烈的审判公开中得到遏制,反而会由于形式公开本身的欺骗性而遭受更为沉重的打击,最终将使得司法改革无功而返。因此,本文试图向公众勾勒出审判公开在实务中的形式化倾向,对其实质性转型的必要性进行详细讨论,最终希冀能为审判信息公开的实质性重构提供智力上的参考。
一、现状检视:实质性审判公开的实证性缺漏
近年来,随着《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等纲领性文件的不断出台,审判公开工作在形式上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无论是庭审直播之亲临审判过程,还是裁判文书上网之捕获法院内卷,抑或是诉讼流程平台之掌控审判流程,甚至审务信息之详细发布,均极大地缩减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距离感,也减轻了诉讼主体对人民法院的抵触情绪。同时,法院开放日的继续推进、示范法院的不断辐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努力构建等均极大地拓展了审判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但遗憾的是,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以及举措的实施并未有效实现“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宏大目标。审判公开并未内生为法院的行为自觉,而仅仅是在应对法院内部考核时的一种无奈之举,故无论是案件信息的选择,还是方式时机的把握,抑或是程序过程的限制,均出于法院的自由裁量之下。在不断演进的审判公开中,“开小不开大,开表不开里”等现象标志着当前的审判公开“形式有余,实质不足”,司法公开依然进退维谷。从基本表征来看,审判信息实质性公开存在较大缺漏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制度缺乏:宏观性制度缺乏操作性细则
在回应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诉求之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出台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等相关文件,各地法院也纷纷构建起了初步的司法公开制度,但究其内容而言,过于宏观与笼统,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操作性细则与强制性效果,致使审判公开的初衷远未实现。以2010年发布的《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为例,仅仅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审判公开的目标,而不注重当事人的民主参与,显然难以达到法院无所保留地公开相关司法信息的初衷。即便个别法院规定了考核和奖惩,但亦存在较大随意性。以河南省高院印发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管理办法》为例,该办法第五条赋予了法院在敏感性、群体性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等案件上的自主决定权,而何为“敏感性、群体性或社会影响较大”本身便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均含糊不清。这无疑变相地削减了审判公开原则,曲径通幽地实现了“选择性公开”的合法性。正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制裁与约束,更多的法院往往将审判公开当成一种自由裁量,而非其必须履行的职责与义务。
除却对法院自身的约束之外,现有的法律制度也未能提升公民相关司法公开的权利。一方面,法律对于公众参与庭审的权利未进行细致化的规定,尤其是对媒体相关自由的旁听权未予放开,导致了已有的庭审公开几乎成了摆设。另一方面,法律也未对社会主体享有的司法公开讼权加以重视。在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可诉的前提之下,作为信息公开诉讼裁决者的法院,其司法信息却处于免诉的规则之下,这不失为一个讽刺。另外,社会主体若遭遇了司法公开侵权行为的损害,往往难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尤其是商誉权、隐私权等权利被非法侵犯,却无法获得充分的救济安排。
更为重要的是,自从审判公开成为一项政策性任务之后,广泛存在的地方性制度、不计其数的会议座谈纪要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但这些规范性文件缺乏统一性,文件内容往往参差不齐、表里不一。在实践中,启动审判公开的申请条件、期限、批准机构、审核机关、救济与责任等重大事项均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使得是否公开、如何公开等事项的最终解释权集中到法院。这种混乱的局面与政府信息公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旦司法改革的政策出现了某种专项,缺乏制度维系的审判公开就很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二)目标偏移:开放性需求偏移为保守性供给
1.全面性监督偏移为选择性宣传
由于缺乏制度性规制,我国的审判公开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在于提升江河日下的司法公信力。在若干关注度较高的案件被媒体和网络舆论冲击之后,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审判公开的方式去重塑自我的价值功能。因此,宣传功能成为了“审判公开”的核心目标。如有论者便直接提出,“让人民法院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司法资讯以消除不合理、不正确的舆论攻击和猜疑,让人民法院掌握宣传的主动权,让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在第一时间内向公众传输和播放,净化舆论空气,为司法审判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2]
也就是说,“审判公开”成为了一种政治策略。因此,法院往往不会将应当公开的所有案件加以公开,而是在权衡相关政策与法制目标之后,选择那些争议较小、法官掌控能力较大、能够实现某种政策导向的案件进行详细报道。例如,在酒驾入刑之后,各地法院均纷纷对酒驾的案件适当加以开放;而在打击贪污腐败力度加大的背景之下,贪污腐败犯罪案件的公开程度也超过了一般案件。同时,法院多注重公开宣判,但属于公开审判核心内容的公开审理却被冲淡[3]。这就使得全面公开审判过程以接受司法监督的目标被政策性的宣传目标所替代,偏离了应然目标。
2.便于外部知情偏移为便于内部管理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将世界推入了一个自媒体爆炸的时代,在这种技术设备革新的背景之下,数字化司法公开平台的构建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必需品。从传统文字性材料的书面保存,到文字文档的数字保存,再到全程录音录像保存、裁判文书上网,法院对司法过程的管理也日新月异。例如,早在2009年前,重庆法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裁判卷宗的全部上网。在其构建的审判管理系统中,每一个时间节点,法院应当干什么以及干了什么均一目了然。相关的当事人信息、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所有诉讼文书均可在这个数字化系统加以阅读与查看。
但是,我国在建设数字化法院过程中,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即数字化法院建设有利于实现公开审判和公众知情权[4]。除却降低司法管理的成本、提升审判活动的效率、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间接监督之外,数字化审判管理系统可方便社会查询与监督的作用并未凸显。这一点可以从数字化的裁判卷宗并未及时公之于众,而仅仅被公布于法院内网系统便可以窥见一斑。可以说,裁判手段的数字化,其本身所包含的便于公众知悉与评判的目标被内部审判管理的便捷化所替代了,也偏离了应然目标。
(三)价值异化:权力控制异化为权力自保
就审判公开的价值功能而言,最大限度地将司法权力压缩到法定空间之内,促使司法权在透明运作之中接受社会公众质疑目光的打量,并间接督促法官为了维持其社会荣誉、职业发展以及既有地位而不断提升水平,最终顺利化解社会矛盾、强化裁判可接受性,可谓是“审判公开的四驾马车”。然而,本来为了既保持司法理性,又实现对司法的有效监督的审判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却异化了司法权力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手段。在信息快速传播与公信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之下,人民法院往往从舆情控制和危机应对的层面去考虑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度与范围。对于一些可能存在着问题的审判信息,人民法院经常会采取一种保守的自卫方式,即进行适度封闭。
尤其是,针对社会广泛关注且争议不断的案件,法院还会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虽然各级人民法院仍会以公开审判的“名义”进行案件审理,但对于要求旁听案件的群众多以“法庭较小”“指定内部旁听人员”等方式“婉言谢绝”。甚至,因出于“维稳”的导向需求,法院还会直接拒绝将有关审判信息予以公开。另一方面,即便是允许旁听,法院也会设置各种障碍防范旁听人士“不恰当”地透露审判过程信息,如禁止发送微博、没收“通讯设备”等。这就使得所谓的“被公开的司法信息”均是层层把关后“无害”的“信息”。
在与司法公开程度较高G省S市38名法官交流“其所在法院为何会加强审判公开力度”时,笔者发现60%的法官选择了“在于消灭‘暗箱操作’的舆论批判”,39%的法官选了“在于实现司法公正”,至于选择“在于监督司法”与“在于保障权利”的人数均不超过30%。在交流过程中,有基层法院的庭长甚至表示,一年4 000余件的司法案件,公开两三千件便行了。至于审判中存在着问题的案件,“即便遭受了高院点名批评,也坚决不予公开”。
(四)范围狭隘:公开原则狭隘至公开例外
正是由于审判公开的效果取决于法院的争执自觉,而非制度程序的拘束,使得原本“公开为主、不公开为例外”的理想图景被现实倒置。公开与否反而成了一种选择性的自保策略。第一,法庭旁听权的实现还存在限制和被变相剥夺的情况,难以很好地体现司法的程序公正性[5]。第二,审委会定案制度与法院系统内部的请示汇报制度,使得公开的审判内容等同于被掩藏的形式公开,秘密化的合议意见与上级要求致使庭审公开的实际意义被人为地降低与虚置。第三,裁判文书上网不及时且不全面、庭审直播呈个位数数量、网站栏目设置简单重复、甚至提供的网络衔接无法打开等现象比比皆是。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2)》中司法透明度排名第一的深圳市中院为例,笔者发现其上传的最新裁判文书居然是2011年的,而深圳市中院2013年11月发布《深圳法院司法公开白皮书》却标榜其两级法院共上网生效裁判文书4万余份。而其庭审直播回顾中2013年直播的庭审仅12件,月均仅一件,且该12件庭审90%集中于2013年1月份与2013年4月份,至于2012年,庭审数量更是少得可怜,才区区一件。第四,裁判文书说理不清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对于诉讼主体争执的问题不公开其决策理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间的逻辑联系往往一笔带过。这就使得所谓公开审判却只让公众知道裁判结果,却未让他们知晓做出裁判的理由。
二、功能重塑:实质性审判公开的必要性征程
权力的运行必须置于阳光的照射之下,才能防止腐败、保证公正。这已然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定论。然而,由于法官业务素质与审判能力低下之“内忧”,以及担心社会公众与媒体挖掘负面信息之“外患”,已经如火如荼的审判公开尚仅停留在形式公开的阶段,法院审判信息的实质性公开可谓步履维艰。那么缘何要突破形式公开的拘囿,向实质性公开阶段迈进?其理由如下:
(一)权利保障功能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民众如果不掌握足够的信息,就不可能知道什么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就不可能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有效地斗争,也就只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甚至不能作自己的主人[6]。可以说,对社会公众来说,他们对裁判结果的认同,首先来自对诉讼程序的直接体验[7]。
那么,就审判公开而言,“形式公开”往往对审判过程中的实质问题遮遮掩掩,如法院会“人为”地限制庭审人数与听审自由,也会对争议较大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不予详加分析,甚至对于那些社会质疑声音较多的案件还会拒绝提供任何信息。这就使得社会公众没有机会与途径充分获取到实质上的司法信息,他们可能仅仅了解了司法裁判的程序与结果,但对于法院作出司法判断的原因却知之不详。这样,他们自然无法对未来可采取的法律行为建立一种十分稳定的预判,从而无法合理地指引和安排自身的行为,自然也就无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通过审判信息的实质性公开,才能在审判机构与社会主体之间构架起一座沟通与对话的桥梁,才能使得人们不但在形式上获得了真实可靠的司法信息,而且从实质上能更加理解司法、认同法律和信仰法治,最终促使社会主体按照法律指引的合法方向行使并救济自身权利。
(二)公正促进功能
司法公正是法治本身所蕴含的一种价值,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最高权威的基础和前提,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包含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个要素,而审判公开便是程序正义的关键要素。即审判公开为社会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和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条件,降低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的可能性,保障了司法公正的实现[8]。
然而,审判公开的形式主义其表征便是将司法过程的某些环节或要素加以隐藏,使得社会公众无法对司法过程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无疑是对程序正义的一种违背,其实质是以一种表面的程序替代程序的真正内涵。因此,必须抛弃形式公开的忧虑与恐慌,将实质性审判公开的要求落实到位,才能使得人们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不至于虚构,从而从程序上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同时,通过实质性的审判公开还可以加强各地方司法资源的共享和利用,西部地区的法院可以借鉴和学习具有优势的东部地区法官审判案件的法律逻辑模式,从而推进各地区法院办案的协调与统一,实现司法公正。
(三)腐败防范功能
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和人民的授予,但缺乏监督制约的国家权力完全可能异化为满足私欲并侵犯公民权益的工具[9]。因此,审判活动必须要充分接受公众和专业的监督与批评,否则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盛行。然而,形式公开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性公开”。它所公开的过程与材料往往隐瞒了对法院不利的因素,这样人们的全面监督权便形同虚设。因此,必须通过实质性公开,将除却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均不受限制地公之于众,才能使得广大公众准确真实地掌握司法过程中的全部信息。这样,法官对案件审理合不合法、合不合理才不再是法官自己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而是要接受公众眼睛的考验与审核,进而克减权力、人情和贿赂等法外因素对法官的影响,最终起到遏制和防止法官利用裁判权谋取私利的效果。
(四)裁判勤勉功能
对于法官而言,庭审上网意味着审判庭的大门向全社会敞开,将自身置于“全民监督”之下,这无疑会促使其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更为谨慎严格,以免受到公众的指责及对其行为正当性的怀疑。毕竟,如果裁判文书逻辑混淆、颠倒是非,那么一旦公开前述裁判文书,则制作该裁判文书的法官将会受到当事人和公众的质问与考验,将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就“迫使”法官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学理论水平。
如果审判公开只停留在形式公开的阶段,“可公开可不公开”的自由裁量便无法督促法官主动将其所制作的裁判文书上网。此时,行文语法错误连篇、论理极其不清的裁判文书,完全可能被法院免于公开,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直接、有效的倒逼机制,促使法官认真对待审判。只有通过实质性公开,不留司法公开的死角,将法官的能力与素质全方位地展现在社会面前,那么法官必然会更加注重提升自己在认定事实、分析证据、解释法律、控制庭审和撰写裁判文书等方面的能力,以更高更好的司法水平适应司法公开的社会需求。同时,全面的司法公开,还将提高法官自身的职业道德。法官在公众视野下会倾向于表现自身社会责任强、司法能力高的形象,从而增强法官内心的理性自律、司法良知和职业责任感,以公正的裁判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五)教育引导功能
公开性创造了一种客观性的氛围,使法院的司法过程与司法结果获得正当性,使公众亲眼看到法院在伸张正义,相信法院的判决确实表达了法律的规定[10]。法院提供普适性公开服务,不仅仅是姿态的表明和话语权的获得,避免公众关注案件的传播失效与传播实践中大量无用信息的传播过度而产生的公众心理挫折,以及潜伏的诱发过激行为的情绪,更是在积极引导公众树立法律理性与法治意识,强化和实化对司法的社会监督[11]。
然而,形式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往往更加注重表面的和谐与顺利。一些地方法院为了保证庭审“顺利”进行而先判后审,直播也就失去了让更多普通百姓见证司法的意义。至此,人为的设置旁听障碍、故意隐瞒实质性审判信息,则可能不仅无助于发挥其教育引导功能,反而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只有将法律具体应用于各类纷争解决,并将纠纷解决全程公诸于下,才能使法律所具有的指引、预测、评价、强制和教育五大作用完美地展现出来[12]。而且,它对于促进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激情,促使民众法律信仰和民主政治参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也同样功不可没。
三、路径选择:实质性审判公开的体系性重构
仅仅将审判公开的理解局限于形式意义的审理公开或宣判公开,而没有使当事人及社会主体的监督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真正制约,则审判公开所要求的相对义务只停留在被虚化的保障行为这一层面,也使它容易被异化为背离诉讼基本规律的、空洞的和毫无约束力的制度。因此,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法院应进一步提高司法透明度,实行阳光审判,向当事人公开到向全社会公开,使更多的人亲身体验司法本身的魅力[13]。
(一)开启制度化,落实审判信息公开的规范管理
1.责任化与诉权化
作为基本原则和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审判公开,应当在司法诉讼的各类程序中得到贯彻。公开审判制度渗透着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实质,包含着接受裁判权、情报获知权、参与审判权和治理国家权等多重层次的权利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就承担着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的义务[14]。如果审判公开的救济途径通畅有效,惩戒制度威严有力,那么法院就难以变相地对抗实质性审判公开的制度要求。
但是,目前审判公开的相关权利仅仅局限于宪法、法律等原则性规范之中,缺乏具体、刚性的指引与规范。因此,我们必须在将来的信息公开法中,将法院纳入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将审判公开的权利主体扩大到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利害关系人。这也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将不依法公开或不当公开的情形作为程序错误予以处理,可在不额外增加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开的制度化。
2.统一化与差异化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非某一个法院的职责与义务,它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统一的操作性规定,细化各个环节的公开规则,实现司法公开制度的统一化、流程化和标准化,提高司法公开制度的实效。但毕竟受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各个地方的法院在人才引进与资源配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部地方法官的平均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方,在审判设施的数字化投入上也明显存在着严重不足。对不同地方的法院,在设立考核目标时,应当差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地进行责任追究。同时,不同的司法信息,其受限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解释性规定,将不应公开的信息类别予以明确化,防止司法公开侵权行为或违法不公开的行为的发生。且即便是应当不予公开的信息,区别于一般公众,法律工作者也应当受到查阅上的优待,即可以允许法律工作者以申请的方式获得特定范围的阅读权限。当然,此后该法律工作者若滥用受限司法信息则应当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拓展职业化,提升审判信息公开的自我管理
“徙法不足以自行”,欲真正实现审判公开的实质化目标,必须落实到审判程序的主导者法官的身上。法官具备了较高的综合能力,才能匹配现代庭审模式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进程,通过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提升审判信息公开的积极性。
首先,法官要从内心上转变司法理念。虽然,社会主体的法治意识上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司法机关不能一味地以防止网络暴力、保持司法独立为由害怕并抗拒司法公开。法官必须正确认识司法公开在消除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重要内涵,着重提高其司法审判水平与解决纠纷能力,增强实行审判公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做到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并重,从而在依法裁判的过程中将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持法律权威的目标落到实处。
其次,要构建完善的法官遴选制度。专业及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法官公正审判的基础。因此,必须更加注重法官职业素养与专业水平的提升,打破以考试为纲、以学历为重的用人界限和僵硬模式,继续完善从律所、高校中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的途径与方式。应当减轻年龄对法官提拔造成的限制,毕竟,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在调解纠纷等方面能够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同时,提高任职薪金以减轻法官的生活压力,免除其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后顾之忧,可以促使法官降低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可能性。
(三)抑制内卷化,优化审判信息公开的质效管理
推理决定案件判决结果的过程必须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所有当事人就可了解法庭遵循的是何种法律原则和判法以及何种逻辑,这样就可实现充分的公开性。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法独裁倾向、对司法独裁倾向的无端怀疑和对司法错误的无端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对高效的司法行为的一个有力激励[15]。
1.庭审充分开放
现存的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规定对庭审公开作出了相应的要求,但与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要求还存在差距,有待改进。在未来的审判公开中,必须进一步开放庭审过程,包括落实有争议的重要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的制度,加强庭审的实质性以及审判信息公开的实质性,避免过去那种因某些证据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就将全案作不公开审理的做法,努力扩大审判公开范围。同时,要尽量提供便于旁听的场所,在参加庭审人员的选取上应以更加透明的方式随机抽取,避免“旁听人员的内部化”。
2.理由充分表达
司法不仅不会受民意左右,而且还可以引导民意尊重法律。审判公开的实质要求则是使诉讼主体和民众能够知悉作为司法裁判基础的事实、证据,裁判的法律根据和理由以及裁判的过程[16]。其目的在于使社会公众了解司法裁判的内容,通过公布裁判形成的逻辑过程,确保裁判建立在证据和论理的基础之上,从而增加裁判的社会公信力。如果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词不达意,只能使民众对司法的误解进一步加深,这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如果不能控制或消除的话,不但司法权威丧失殆尽,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17]。
3.文书充分上网
裁判文书是法官或其他裁断者综合本案所有证据,根据社会生活常识、专业知识以及司法经验,能动运用法律,确定权利义务分配的实体性结论[18]。裁判文书公开是审判公开原则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内容,是实质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只有通过裁判文书的公开,才能对法官具有真正的约束力,即一方面使当事人程序参与的结果能够对法官的裁判内容产生约束,另一方面也借助社会的监督力量对法官的裁判行为形成制约[19]。
(四)打造数字化,加强审判信息公开的技术管理
当事人行使权利是有时效的。法院所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应保持最新的状态,不能给公众以过时的和陈旧的信息,使当事人贻误行使权利的最佳时机,或者影响公众对法院工作情况的当前评价[20]。这就需要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司法审判的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压缩司法公开的空间与时间限制。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不能仅仅用于装扮摩登的法庭,更应在亲民、便民方面拥有宽广的舞台[21]。
首先,坚持发展审判公开的数字化系统,就必须加大人财物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方更需要专项资金的补助。否则,法院的数字化系统便无法跟上时代的需求。其次,对于构造数字化的诉讼流程系统、加强裁判文书上网、落实庭审直播等数字化措施而言,最高法院应当以制度的形式进行统一规范,例如,不予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裁判文书上网的基本格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审判信息公开数字化建设的常态化。再次,法院应该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运用技术手段,形成系统保障,实现立案、审判、执行、归档、监督和信访等法院工作各个环节的全覆盖,使审判公开的载体和形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最后,考虑到网络信息数据的庞大与复杂,人民法院应当构建一套合理的分类检索系统,并方便查询者有效地适用该网络的搜索功能。
四、结语:实质性审判公开的未来
司法公开正以令人心潮澎湃的方式快速推进,制度创新举措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审判公开模式和理念仍有较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公开的权限和内容仍需进一步的明确、公开的方式方法仍需进一步的灵活、公开的实际效果仍需进一步的提升[22]。只有努力开启审判公开的制度化,落实审判信息公开的规范管理,不断拓展法官素质的职业化,提升审判信息公开的自我管理,及时抑制司法心理的内卷化,优化审判信息公开的质效管理,充分打造审判设备的数字化,加强审判信息公开的技术管理,才能有效克服审判公开的形式主义倾向,将审判公开真正推向司法公开的实质化道路,从而真正保障社会主体与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督促法官不断提升其法律素养与职业道德,引导与教育社会公众知法守法,最终防止司法腐败并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胡锦光,张光宏,王锴.司法公信力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11.
[2]邓俊明.坚持三个并重,构建法院大新闻宣传格局[EB/OL].[2014-2-28].h ttp://www.chinacourt.org/ article/detail/2013/05/id/959662.shtm l.
[3]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1978-2008)[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3.
[4]高一飞.论数字化时代美国审判公开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0(10):55.
[5]刘用军,王美丽,梁静.论监督司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209.
[6]胡铭.刑事司法民主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211.
[7]崔敏.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287.
[8]刘广三.刑事司法环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0.
[9]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4.
[10]宋世杰.刑事审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37.
[11]高晋康.光华法律:第3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5.
[1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公开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00.
[13]胡锦光,张光宏,王锴.司法公信力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11.
[14]刘风景.裁判的法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2.
[15]怀效锋.法院与媒体[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2.
[16]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4.
[17]陈婴虹.网络舆论与司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59.
[18]胡帅.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28.
[19]张卫平.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7.
[20]刘风景.裁判的法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0.
[21]高晋康.光华法律:第3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6.
[2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公开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44.
责任编辑:罗清恋
M 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ial M anagement—Changing from the Surface Publicity to the Essence Publicity
DAIQiao
(Chongqing Dadukou People’s Court,Chongqing 400000,China)
In the practice of jurisdiction,the trial publicity paysmuch attention to the surface publicity rather than the essence publicity.In terms of the system,themacro trial publicity system is lack of th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rules;in view of the purpose,tomeet the publicity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people’s knowing the fact and supervising has been changed into the conservative supply of selectively partial publicity;in view of the value,the function of former controlling jurisdiction power has been positioned the self-protection strategy for the people’s court;all lead to the fact that the trial publicity has been reduced into the exception.Only to put the effort into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trail publicity,practice the regularmanagement of trail information publicity,extend continuously the quality of the judge’s occupation,promote the self-management of trial information publicity, restrain the involution of jurisdiction thought,optimize the qualitymanagement of trial information publicity,full create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jurisdiction equipment,strengthen the technologymanagement of trial information publicity,which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surface publicity,to promote the essence publicity of the trial publicity to the jurisdiction publicity,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social subject and parties of litigation,to supervise the judg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law and occupationalmorality,to guide and educate the social people to know the law and abide by the law,and finally to prevent the jurisdiction corruption and achiev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cial publicity.
trial information publicity;guarantee the rights;surface publicity;essence publicity
D915.18
:A
:1673-8004(2015)06-0077-08
2015-05-07
戴乔(1981—),男,四川巴中人,硕士,主要从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