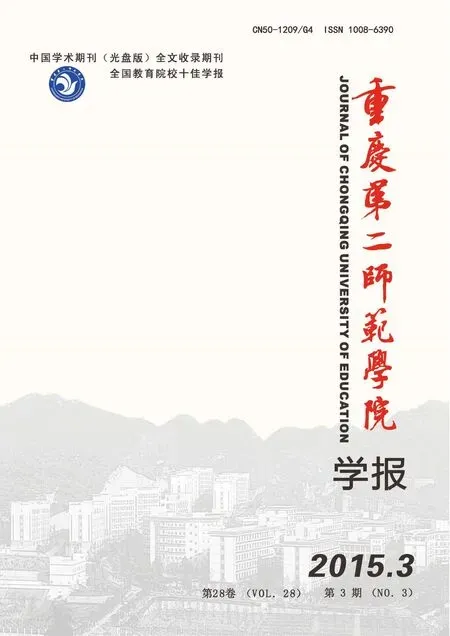文革时期科技法制的破坏及其教训
侯 强
(江苏理工学院 思政部,江苏 常州 213001)
文革时期科技法制的破坏及其教训
侯强
(江苏理工学院 思政部,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的恶性泛滥,使得新中国科技法制建设很快便被动乱的狂涛所摧毁,科技法制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历史地进入其发展的低潮期。其不仅阻滞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常发展进程,而且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摧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延缓了我国现代化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沉痛历史教训。
关键词:文革时期;科技法制;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侯强(1966-),男,江苏句容人,江苏理工学院思政部,教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识码:A
文章编号:编号:1008-6390(2015)03-0009-05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政治浪潮的冲刷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得“要‘革命’,不要法制”占得上风,以致宪法和法制很快被强权所打碎。是时,由于政治与法制运行的全面失序,科技法制建设已变得无足轻重,不仅几乎没有相关的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新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原有的一系列调整科技关系的法律、法规实际上也已大多失效,有的甚至还被明令废止。由此,科技法制建设遭到全面破坏,科技战线陷于动荡不止的严重混乱局面。
一、科技机关的功能丧失
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苏联科学批判和国内思想改造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新中国就开展过对科学的批判活动,并形成了一股左倾错误思潮。1958年,毛泽东在几次会议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我们“应以狗屁视之”,就像“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118。在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驱动下,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具有莫大的政治权威。此后,这种对科学荒谬批判的思潮,便如同鬼魅一般,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时高时低。及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种对科学的批判活动,在不断高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口号声中,如狂飙般极速涌起,肆意践踏建国初期制定的科技法制,以致文革十年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科技事业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以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抛弃政权、法制和秩序开始的”[2]105,所以其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以政治运动方式为科技活动的主要形式,在科技管理上大批“专家治厂”“技术第一”。自1966年2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后,及至4月5日止,该报接连发表了6篇突出政治的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从属的地位,对科学本身实行全面专政,使得科技政策被极度扭曲。同年5月,《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题为《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社论,把学有专长的科技专家统统视为“阻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并将其一概纳入“横扫”“打倒”之列,以致科技运行陷入极度无序和混乱之中。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虽明确规定“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但在全国陷于动乱的时局下,这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的第12条规定,事实上很快被“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巨浪冲得无影无踪。在以“破”代立的方针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被撤销,一部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研究机构被关闭或下放地方,一些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全国300多种科技刊物被停刊,学术会议制度被破坏,科研经费大幅下降,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几乎全部中断。由此,建国以来培养起来的科技队伍顷刻间陷于崩溃的边缘,造成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和职能部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科研和生产大多难以为继。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为号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运动,其集聚了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及其爆炸性的社会力量,所以它的爆发不是各社会群体本身所能控制的。在“全面夺权”的恶浪中,整个社会必然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1967年3月,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了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后,全国上下通过大批大斗大联合的夺权斗争,自上而下普遍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科研单位也不例外。文革十年,其权力高度集中且达到了顶点。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根据当事人后来追记,“‘十年动乱’开始后,科学院及其领导的各研究所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院部各局长、所长、党委书记等多数被批判斗争,靠边站了。各级领导机关都成立了由造反派掌握的‘革命委员会’。科学院及各所都设‘革命委员会’”[3]355。
为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确立无产阶级的科研路线,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又刊载了《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各科研单位,领导科技领域内的“斗、批、改”。同年10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后,各地又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由此,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整个科技队伍被拆得七零八落,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科研活动已难以为继。“在‘彻底砸烂’、‘拆庙撵神’的反动口号下,仅辽宁一省,就有近万名科技人员被迫带着家属下乡落户。”[4]570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意义的下放劳动,不仅消耗了大批专家学者的宝贵时光,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体质,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
文化大革命作为建国17年体制的产物,其以更极端的“左”对17年体制进行了摧毁。文化大革命理论、形式和对象的错误,构成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造成了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5]135在呼啸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接受“再教育”和被改造的政治处境,许多专家、学者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应有的环境和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5月,仅北京师范大学一校,在全校90名教授、副教授中,受到审查的达73人之多。其中,全校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有19人。[6]862而雪上加霜的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下,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被打倒、批臭后,“新一代科技人才培养并无组织保障,大学基本停办,高等教育严重倒退,科技人才出现断层”。[7]41是时,全国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被撤并为1971年的328所,共减少了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文革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大约少培养了几百万专业人才,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由此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这不仅耽误了整整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使得我国原本就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严重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建国之初制定的一切正确的科技政策大多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而被毁弃,但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等在逆境中,仍然以“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坚持力所能及的纠“左”,千方百计帮助科技人员渡过难关。1966年6月,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意在“文革”动乱中尽可能地保护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同年12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中科院京外单位代表时又提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应当保护。[8]100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时,亲自抓了处于半瘫痪、半取消状态的科研机构的恢复工作,指出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9]毋庸置疑,这些对极左路线的斗争和抵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左”倾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生态下,再好的科技政策也不会得到尊重和维护,其作用和成果自然是十分有限的。
二、科技法制的全面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的恶性泛滥,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漩涡,使得新中国科技法制建设事业很快便被动乱的狂涛所摧毁,科技法制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历史地进入其发展的低潮期。是时,在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中,1962年的广州会议被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科研十四条》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我国的科技法制建设不仅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而且既有的科技法制也不断遭到践踏,严重偏离了正规化科技法制建设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是“左”的指导思想极端发展的产物,它又把“左”的指导思想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对科技法制的大破坏,首先是从政治体制的畸变开始的。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建国以来政治体制的弊端彻底暴露出来,导致权力结构更加僵化、运行规则更加混乱。是时,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立既不需要法律依据,也不需要合法的程序。根据《十六条》的第九条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但这种非宪法性权力机构又从未真正履行过立法功能。是时,作为国家法定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几乎停止了包括科技立法在内的所有立法工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如此。以全国人大为例,从1965年2月起长达10年不开会,除1975年对“五四宪法”作了修订外,没有制定过一部新的法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除了1972年10月21日财政部与国务院科教组联合发布的《关于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科学研究补助费使用管理的几项规定》外,国务院也基本没有制定与科技有关的行政法规。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其要解决现行政治运行条件下难以奏效的问题,所以必然以民主和法制的破坏为代价。文革十年,在“彻底砸乱公检法”的口号下,司法机关被取消,国家由此陷入混乱状态。至于1968年9月以后在全国普遍成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虽名为“解放以来最具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也是在排斥法制以及违背社会正常秩序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政权机构。在文革完全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中,“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法大权于一身,“把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多功能都简单化为政治功能,又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其惟一的政治任务”[10]396。这与1954年宪法和各种组织法的规定完全背道而驰,其自然也不可能履行包括科技立法在内的立法功能。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在政治体制发生畸变的同时,科技法制宪政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75年,党内极左势力为把“革命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各项“左”的政策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借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二部宪法(1975年宪法)。1975年宪法在其总纲中,把科学技术人为地抹上了强烈的阶级色彩,并将其归入上层建筑范畴,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主张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扩大到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与之相适应,删改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代之以“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味着公民拥有进行科学研究等自由的正当权益已失去了应有的法律保护。这是新中国科技法制从1957年后就开始停滞、削弱、不断下滑以至迅速倒退的必然结果,不仅严重扭曲了科技立法的指导思想,而且全面破坏和摧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文化大革命以运动的方式发动,其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秩序状态,它必然会破坏科技法的正常实施。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科技立法几近停顿,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而且在科技法制的具体实施层面上又大肆推行法律虚无主义,原先行之有效的科技法规基本被弃之不用,成为一纸空文。例如,根据1963年国务院颁布的《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经国家科委批准,拟奖励评选出的296项发明项目,除给发明者颁发《发明证书》和奖章外,还要按等级发给相应的奖金。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这近300项发明,既未发奖金,也未召开大会,只是冒着‘风险’将《发明证书》、奖章寄给发明人了”[3]253。又如,作为高等教育一项重要内容的学位制度,其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其被荒谬地归之为资产阶级法权范畴,最终导致196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草案)》未完成法律程序被无期限搁置下来,研究生招生也全面停止,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再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稿酬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被全部取消,从1979年10月1日起,稿酬制度才得以恢复。
法虽立而自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政治生活在科技活动中已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结果是科技政策代替了科技法律,科技活动全凭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来进行。是时,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科技活动的正常法律秩序遭到破坏,科技已实际沦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正由于此,文革爆发后,《1963—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执行受到巨大冲击,许多重要科研项目被迫停顿下来,以致规划中的若干目标未能实现。在文革这个法制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悲剧时代,聂荣臻为竭力保护和支持国防科研的发展,甚至两次找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他派兵保护科研专家,并特别叮嘱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科技的机密材料。[11]73
科技法律在文革中的破坏,使人们对其逐渐由尊崇、满怀希望而变为失望乃至不信任。与此同时,科技政策则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别法”,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以致建国以来形成的科技秩序被彻底打乱。
三、科技法制破坏的深刻教训
文革十年,科技法制的破坏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文本,其不仅阻滞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常发展进程,而且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摧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延缓了我国现代化科技事业发展的进程,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沉痛历史教训。
其一,没有正确处理好党的科技政策与科技法律之间的关系。政策与法律作为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政策与法律的共性,特别是在国家初创时期。建国初期,我们党虽然在科技法制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当时依法治国的条件还不具备,依法治国的方略还不可能被提到首位,各种科技关系也不可能都通过法律程序来调整,所以科技法律的地位还从属于政治手段。这不仅决定了科技政策在建国初期整个社会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科技政策体系和使其得以执行的制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科技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科技法律,而且科技法律被不同程度政策化,并被赋予了政策的形式和被政策性地运用。这种对科技政策的过分推崇和科技政策被运用到极致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建国之初具体历史条件和时局特点造成的。
法律服从政策是建国初期就确立的一项法制建设原则。但党的科技政策毕竟不具有科技法律那么广泛的约束力,片面地把科技政策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以致过分地依赖科技政策,必然会给科技法律本身带来消极的影响。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政治生态下,把阶级性强加于科学技术领域,“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党的科技政策主流,以致反科学的活动盛行。它导致了我国科技领域法治化的夭折,中断了我国科技法制现代化的正常发展进程,以致人治观念横行。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科技领域产生和发展的这种法律虚无主义,一方面,弱化了社会对党和政府科技守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众对科技守法的漠然和屈从。最终,其化作一股巨大无比的破坏力量,遏止了科技法律的生长。
其二,科技法律所调整的科技领域内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科技法律作为国家对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出现不是随意和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究其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并且对传统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决定了对科学技术活动中社会关系实行法律调整已成为现代法律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调整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社会关系自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法不仅担负着调整科技领域内社会关系的任务,而且通过调整这些社会关系,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的僵化和集中体制的强化,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泛政治化,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10]336,堵塞了人们学习掌握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途径。是时,在“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的特殊政治语境下,科学研究被赋予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性,科研单位实际成为执行科研任务的政治实体,所有的社会关系似乎都被革命化,一切群体关系均被淡化在“阶级斗争”的前提下,造成了全国上下普遍的过量的政治焦虑。正是在中国社会关系全面“革命化”的背景下,科技活动领域内的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个需要国家充分调整的关系体存在,而是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之中,服从于社会关系的“革命化”。因而,一切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社会关系的准则和规律都被革命化,科技特点和科技关系发展规律自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以致科技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猖獗,科学研究完全失去了科学性。文革时期,因为“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12]91,所以除个别科技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外,我国的科研水平全面滑坡,充分暴露了科技领域政治运动的社会破坏作用。
其三,没有建立起富有成效的科技法律监督机制。一个国家的法律监督状况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文化大革命科技法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法律、法规的制定只是科技法制建设的第一步,在加强科技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科技法律实施的监督工作,形成一个严密的层层相应的权力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网络和体系,否则依法办事就不可能成为科技工作中的自觉行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科技法律、法规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法律功能。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科技工作中强调政治挂帅,科技成就的取得被认为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时,对于科技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实际已无法可依。这一时期提拔和任用的科技干部最重要的是看其革命性如何,而所谓的革命性如何就是看其是否能紧跟极左路线走。“一些从造反派上来的学阀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混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对所谓的‘反动观点’动辄大批判”[11]80,大搞“全面专政”。据当事人回忆,由于科技法律监督已完全失语,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罢官”,有的被下放干校劳动,院部处于瘫痪状态,对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已根本无法实现实际领导。[3]348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科技法律监督制度,实现监督的法制化,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科技法律得到严格执行。
其四,没有正确理顺科技管理中权与法的关系。树立法律的权威,让法律支配权力,在我国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程。建国之初,党没有摆正权力和法律的关系,把一切社会权力集于一身,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会性事务,造成权力高度集中,以致文化大革命把建国以来政治体制的弊端推到了极端。[5]143文革时期,这种长期存在的体制痼疾在科技领域的持续发作,不仅固化了原有科技体制的弊端,而且将其推到了既乱且死的极端,导致科技运行机制更加无序和混乱,以致建国初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科技法制根本抵挡不住权力的挑战,很快就被强权所打碎。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下,极左势力通过“全面夺权”建立起来的所谓“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以一种新的权力取代宪法规定的政权和法律秩序。其在科技领域开展的“斗、批、改”,把建国以来的科技法制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而将其化为乌有,造成了一种否定科技法制,蔑视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局面。是时,在权大于法的政治生态下,政治权力以其无所不在的实在性,使科技活动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以致领导者的讲话具有类似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严重扭曲了权与法的关系。这不仅对我国科技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妨碍了科技法制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左”的指导思想极端发展的产物,而且它又把“左”的指导思想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十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科技领域内“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科技法制被破坏殆尽,以致人们在“左”的因果循环中倍受困扰和伤害,并由此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失望之中。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4]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陶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朱乔森,李玲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6]李罗力,张春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纪录:第二卷[M].北京:海天出版社,2000.
[7]丁德厚.中国科技运行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9]张化.张爱萍将军整顿国防科委[J].百年潮,2001(2):9-17.
[10]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1]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2]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于湘]
De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ts less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y HOU Qiang p.9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ultra left trend of thought and anarchism malignant proliferation overran people’s minds. It made the new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on destroyed by waves of unrest. Legal system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eared a serious backward, into its low tide developing period. It not only hinder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but also dampen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nthusiasm of intellectu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it also destroy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elayed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our country, leaving some painful historical lessons.
Key words: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legal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cal l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