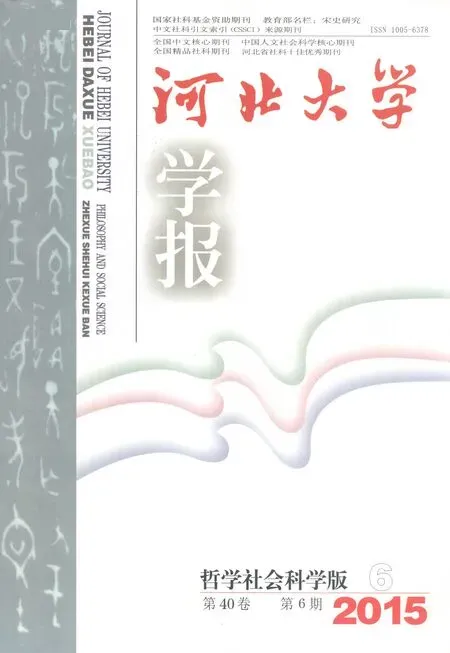德国定向阶段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内涵解析
赵子剑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德国定向阶段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内涵解析
赵子剑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定向阶段教育是联邦德国独有的教育现象。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教育全面恢复魏玛时期的传统,学生完成四年的共同基础教育之后被筛选和分流到不同类型的中等学校之中。六十年代教育改革开始,在推迟分轨和学校统一化的呼声中,联邦德国创立了定向阶段教育以改良传统体制。正当其作为教育政策在全联邦推广之时,却突然遭遇改革中断,因而形成步调不一的格局,并持续至今。定向阶段教育与德国早期分轨制紧密相关,虽然社会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体现了德国传统的因材施教理念,并注入了新时代精神。
定向阶段;联邦德国基础教育;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筛选分轨制
二战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引领下,世界大多数国家迈入教育大发展时期,学校和学生的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教育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角度出发,学生的教育通道可以分为学术和职业两个方向,因此需要对学生进行筛选和分流,以便于因材施教。由于传统和国情不同,教育分轨制在各国的解决方案既有共性,也具有民族特点。对多数国家而言,学生在完成一定年限的共同教育之后便走上了不同的升学道路。但是在联邦德国,在筛选和分流的节点处还存在着一个为期两年的“定向阶段”(Orientierungsstufe),它好似一座桥梁,把共同的小学教育和不同类型的中学教育连接到一起。在其初创年代,这种教育过渡措施在全球独有,即使到当今也鲜有其比;再者,德国国力发达,教育影响广泛,因而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举措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国内涉及该主题的文献很多还局限于情况介绍,没有将其置于教育和社会发生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利于读者准确理解这一教育形式。要了解定向阶段的意义和价值,就有必要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为何只有联邦德国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教育阶段呢?它是如何形成,效果作用如何,是否达成了当初设计者所设想的目标?本文将梳理定向阶段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历史角度探讨其社会内涵。
一、产生背景 :战后联邦德国继承早期化的分轨制传统
定向阶段在联邦德国不同的地域和时期还被称为 “促进阶段”(Foerdersstufe)或者“观察阶段”(Beobachtungsstufe),它属于二战之后的新生事物,是西德在继承分轨学制的传统之上而逐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社会重建,教育事业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虽然盟军和德国对教育民主化方向达成了共识,但在恢复教学秩序后,双方对如何实现平等教育权、是否保留传统教育等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显然,如果传统教育对于德国的罪行负有责任,就必然加以革新改造。对德国人而言,尽管经历过纳粹教育的深重灾难,但是他们对自身传统的教育制度依然信心十足。19世纪初,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进行了教育改革,奠定了其后百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基础,直到二战前后“这些学校在原则上是按照洪堡所创立的基础保存下来的”[1]1-2。洪堡当初设计了“单纯的教育概念”来实现自己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1]3,但终究受制于封建贵族统治,这些理想没有完全得以实现,而是形成了学术和非学术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轨而行的教育制度。虽然如此,洪堡终究把原来的贵族教育推进到了精英教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教育面向更广泛的阶层,向教育民主化迈进一步。尽管19世纪德意志帝国民主发育和社会结构改良落后于西方国家,教育始终在国家严密控制之下,但是在洪堡教育精神的指引下,德国的科、技、文、教等方面发展迅速,取得巨大的成就,德国由此也获得世界科学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殊荣。与此同时,教育的伟大成就促成德国各界人士对其传统的过分自信与迷恋,历来反对改革。即使二战之后德国认识并全面反思本民族发展中的偏差和错误,但是在教育方面依然拥护19世纪以来的传统。
但是盟军并不认同德国发展的 “特殊道路”模式,认为正是社会发展的“跛足而行”造成了德国社会的堕落和罪恶。英国人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早在四十年代初就认为德国侵略性的扩张政策并非只关乎统治者独裁专政,它是全体德国民族的罪责,他们也应该为纳粹暴政和战争负责。范西塔特主义(Vansittartismus)在知识界、官方甚至是民众间受到极大重视。1945年战争结束伊始,美国为了准备对德的“再教育”就派出了代表团考察德国教育状况,在次年发表的《美国赴德教育代表团报告》中,美国专家指出德国教育在邪恶势力发展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有学校组织中强调阶级差别,造成精英阶层的傲慢专制和普通民众的自卑屈从,专制得以发展[2]226,246。进入20世纪的德国教育仍然僵化在19世纪初期所设计的模式之中,它裹足不前,时代错位,在事实上为纳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代表团考察报告进一步指出,德国教育的双轨制割裂了学生群体,仅有5%到10%的优势群体进入学术教育途径,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在小学4年之后只能接受职业教育,结果是国家的教育制度强化了“阶级社会”的基础,这与现代社会追求民主,共享人类文明和文化成果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美国代表团批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概念在德国被“首先想象为两种不同类型或质量的教育”,指出它们应该是“两股连贯的教育层次”[2]250。代表团按照“美国经验”进一步指出,共同的初等教育应该延长到6年,中等教育应同时包含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它们在共同的综合中学之中;德国未来的从6年基础学校到综合中学整个的学校计划必须保证“对民主经验应做出重大贡献”[2]250。英国和法国占领当局也分别提出类似的主张,都认为德国小学生在10岁就被定性和分轨的制度不合理,建议推迟。1945年6月盟军综合各方意见,发布了关于教育民主化的《第54号指令》,内容包括了对于6至15岁学生实行全日制普通义务教育;实行综合教育制度;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应该是两个衔接的教学阶段,而不是两类重叠的课程类型等若干方面要求[3]。
面对盟军取消双轨制的教育政策,美国占领区的巴伐利亚州很快提交了自己主张的《教育远景计划》,既反对废除和统一多类型学校,又反对推迟分轨。尽管盟军后来以多种方式指示地方当局执行教育改革方案,但德国各方抵触强烈,盟军最终在实际上妥协,放弃了原来的构想。1949年,联邦各州关于教育的法规和联邦《基本法》先后颁布,宣告教育重建基本完成。这些法规都没有涉及教育结构改革问题,实际上,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基本上恢复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制度。简言之,联邦德国的学校持续了严格的分轨择校体系,所有儿童读完4年共同的国民学校低年级之后,经过选拔考试,分别进入教育目标和途径不同、质量水平各异的三类中等学校之中。由小学到中学的分轨过程也不存在过渡,升学道路完全由考试成绩而定。
二、提出计划 :设置过渡期以推迟分轨
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很快就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之后几年继续大幅稳步增长,创造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引领西方各工业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五十年代”[4]。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市场活跃,人员和家庭迁移日渐频繁,学生转学成为常见现象。而在联邦主义体制下,国家实行分权管理,各州民选政党交替执政,各州拥有包括文教等方面很大自主权, 各州之间文教政策难以统一,于是造成了迁移家庭的子女转学困难问题,而且日渐突出。负责协调联邦教育政策的“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 经过努力,促成各州州长在 1955年签订了《联邦各州关于教育领域统一的协定》(即《杜塞尔多夫协定》)。这一协定所规定的诸多要点中,其中一条特别强调保留原有的学校类型,即使出于教育学理由需要开展学校类型试验,也必须保留原有类型学习的特点[5]268。也就是说,二战结束10年之后,德国不但没有执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教育结构的要求,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分轨择校学制,并且为改革设置了障碍。另外,战后回归传统的教育一味满足现状,各界人士对于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缺乏认识,思想观念落后于其他国家,《杜塞尔多夫协定》的签订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然而,尽管保守势力强大,社会上也并非完全缺乏改革的呼吁,比如在《杜塞尔多夫协定》签订后,为联邦教育提供咨询和建议而成立的机构“德国教育及教学委员会”就批评该政策思想陈旧,反映了过时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观[6]。
从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教育改革之前的几十年间,德国教育实际上走向衰微。由于受纳粹统治、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发展相对迟缓的影响,联邦德国的教育已经丧失了领先世界的地位,普遍落后于其它西方工业国,也与其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状况极不相称。与其他西方工业国相比,教育发展缓慢的突出表现不但是普通义务教育后的青少年升学率低(初中升高中),而且其中接受学术教育的比率同样处于低水平。这与爆发式的教育需求之间出现严重的不适应。一方面,战后科技发达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大批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和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平民子弟也希望接受高层次教育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基础学校毕业生就读国民学校高级阶段(相当于初中层次的职业教育)的数量逐年递减,而为升学做准备的中间学校和文科中学学生越来越拥挤,人满为患。
起先,教育保守和落后状况被“经济奇迹”所掩盖。但是五十年代末两个事件突如其来,打破了原本的沉寂 :其一,在东、西方阵营对峙和竞争中,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它给西方国家以极大刺激,使他们意识到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落后局面。其二,1957-1958年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煤钢工业过剩危机,使联邦德国丧失了在各西方工业国中的经济增长领头羊地位,经济增长率明显放缓。这些事件促使德国人开始反思和质疑自己的教育传统。1958年,哲学家和教育家魏因斯托克(Heinrich Weinstock)率先指出了德国陷入了“教育困境”[7]。而教育经济学家埃丁(Friedrich Edding)的国际比较研究成果则揭示了联邦德国教育已经落后于其它西方工业国的现实[8]。改革的呼吁越来越强,并在几年之后终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哲学家和教育家皮希特(Georg Picht)发出了改革要求的最强音,他在1964年发表的专栏文章《德国的教育灾难》中痛斥德国教育“吃老本”,而老本已经消耗殆尽,在国际比较中名次垫底,必须改革落后的德国教育制度,这才是摆脱经济困境,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9]。此文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由此掀起了全社会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
在上述国内外背景之下,联邦德国教育界开始提出各种对策。曾经批评《杜塞尔多夫协定》保守落后的“德国教育及教学委员会”经过五年调查审议,在1959年发表了提案《关于普通教育改革和统一的总纲计划》(简称《总纲计划》),主张改革学校体制结构,尽可能拓宽培养科技人才的途径。对于原有三轨制虽然还坚持保留,但是该计划认为应该改革以达到分层次的教育目标;它既反对过早的分轨,也反对通过延长小学阶段来推迟分轨,而是提出在基础学校之上建立一个中间阶段,称之为“促进阶段”。这种方案试图取代对毕业生突击选拔的方法[10],把分轨的决定由“突然跨越”变得“细致和平顺”,避免过早分轨造成的不恰当和失误,又可以通过分组教学达到因材施教,保障对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较早进行高水平教育,以免延误他们智力发展。
《总纲计划》的提出在世界范围之内并非突破性的创举,但是对于传统势力强大的德国而言却显得非常具有革命性,因而遭到了保守派的抵制,认为设立促进阶段的做法会威胁到分轨制传统;同时,改革派也批评它谨小慎微,对分轨制而言只是改良,与战后所树立的统一学校制度的目标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这个计划对“复辟的”教育制度无疑形成冲击,它力图将德国教育带入新时代,因而被称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二次教育改革”[11]。次年,另外一个教育组织“德国教师联合会”也发表了《不来梅计划》,它同样力主改革僵化的分轨制,反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区别对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术性教师和非学术性教师,而是强调让所有学生都获得科学教育。
在越来越强的改革呼声之中,德国各界逐渐统一了对自己教育的认识。1964年3月,各州文教部长联系会议拟定了《柏林声明》,承认教育落后地位,认为应该更新教育目标,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但是声明中依然没有支持统一学制,而是主张了教育机会的提供应该适合个人的能力情况,因而应该“采取措施,使学生进入他们相适应的教育轨道(例如,观察阶段)”[12]。当年10月,各州州长签订了新的《联邦各州关于教育领域统一的协定》(简称《汉堡协定》),取代有效期已满的《杜塞尔多夫协定》。在新协定中,《总纲计划》和《不来梅计划》中的很多建议被采纳,虽然依然保留三轨学制(三类中学名称在此被规范为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但是把普通义务教育延长到9到10年,明确了“对于所有学生共同就学的第5和第6学年,可以使用‘促进阶段或观察阶段’名称”[13]。从该条款中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实现9年单轨学制,但是共同教育已经由4年延长到6年,分轨得以推迟,被延长的2年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促进或观察”的任务。在新协定中,不再像老协定一样阻碍改革分轨制,而是鼓励改革实验。以新协定的签订为标志,联邦德国终于结束了战后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无改革时期,由此步入教育改革的新时代。
三、实验和推广 :保证分轨制更加合理化
《汉堡协定》拉开了教育改革序幕。其中关于定向阶段的教学设想兼顾双重任务 :延长共同教育,并为学生接受高一级的教育做准备。但是如若作为一项教育政策推出,必须得到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支持。60年代教育改革运动空前发展,定向阶段从中获得了这些条件。
在教育实践方面,德国教育与教学委员会在推出《总纲计划》五年之前(1955年)就开始了在黑森州(Hessen)的教育实验。各州政府在1964年签订《汉堡协定》之后,又继续委托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进行定向阶段的教学实验。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十余年的教育实践不断积累着经验。
与此同时,相关的教育理论也取得了突破。“德国审议会”(Deutscher Bildungsrat)以提供基础教育咨询和推动教育改革为使命,它于1969年发表了论文集《天赋与学习》。该文集由支持改革的教育家罗特(Heinrich Roth)主编,它有力地反驳了分轨制存在的基础,因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长期以来,德国教育学认为儿童天生具有差异,存在着三种类型智力水平的学生。这是分轨制存在的理论基础,也就产生了分层、分类对待不同天赋儿童之说。例如,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企图取消双轨制教学之时,巴伐利亚州文教部长极力反对,并辩称德国不同类型学校的制度在教育理论上被证明是站得住脚的,并且心理学研究支持应该不得晚于10岁之后进行分轨[14]。但是《天赋与学习》所展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儿童的智力并非天生,而是受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决定,因而智力具有很大可塑性,可以加以促进。如果儿童先天差异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改革三轨制的学校体系,应该让各阶段、各类型的学校都进行面向科学的教育,而且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应该存在转学渠道,便于学生根据学生成绩变化而转学。最后,解决问题根本之道还在于建立综合性的学校,即三轨制合并[15]。
在具备上述的实践和理论双方面条件之后,德国教育审议会于1970年发表的《教育结构计划》中再次建议设立定向阶段。最终,“联邦和州教育计划和研究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教育总体计划》中决定在联邦各地试行这一制度,并计划到1976年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行。至此,定向阶段的教学终于被各州所认可,教育分轨向后推迟,学生获得了附加两年的共同课程。过渡阶段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任务 :促进学生个体的学习意愿和能力;完成对学生个体学习天赋、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测定;改进学生个体教育途径的抉择;权衡社会化的教育差异,使家庭和学生在选择教育途径时,尽量排除家庭出身和性别差异等干扰,达到客观化[16]165。从中可见,这个过渡阶段不是由学校方面单向测试和选拔学生,学生方面也不是被动接受挑选,而是从学生发展角度出发,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积极介入和全方位促进。也因如此,这个过渡期虽然被统一命名为“定向阶段”,但不同方面根据各自理解和侧重不同而称之为“促进阶段”或者“观察阶段”。面对最新的发展形势,即使由保守政党执政的联邦州也不再完全反对新事物,而是做出一定妥协,但是依旧呼吁应该保留两种教育途径,允许学生进入独立的定向阶段学校或者各类中学。在各方达成妥协后,1974年各州的文教部长签订了关于实行定向阶段的协定,允许了这两种组织方式,即独立于学校形式的定向阶段和依附于一定学校类型的定向阶段。
四、停滞和维持 :作为不统一的教育政策而存在
就在教育改革向前推进之时,德国社会发展突然遭遇打击,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猛增,毕业生甚至教师都出现大批失业。社会舆论自此转向,焦点不再关注教育,教育改革因而被迫中断,始终指导改革方向的教育审议会也于1975年解散。而这之后下一轮的教育改革热潮的关注点转移到课程方面,而非教育结构。由于结构改革的停滞和调整,中学综合化发展目标并没有在全联邦范围内实现,新兴的“总和学校”和以往的三类中学一起构成了德国更为复杂的四轨学制。在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之中,“没有一个联邦州能够取消分轨的结构和消除学校形式之间的分隔”[17]729。基础教育阶段其他年级改革成效甚微,只有“五六年级的结构改革发展最快”[17]727。虽然“独立的定向阶段在教育政策上还未能站得住脚”[18]116,但是作为“对筛选精致化处理”的举措已经在全联邦铺开,只是其在各州推广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图景。其中推进速度较快的州,如下萨克森州以及不来梅市(Bremen),已经实现了把定向阶段作为唯一和普通的学校形式。他们与已经更为彻底地实现六年制基础教育的柏林市(Berlin)和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一起实现了6年的共同基础教育。
虽然有些联邦州实现了教育推迟分轨,但是其余的大部分州的教育改革陷入停滞状态甚至逆转。例如, 80年代末期,由于持保守政策的政党夺得执政权,最早实验定向阶段教学的黑森州取消了原本必须全面推进定向阶段教学的政策,重新赋予学生家长以自由权,自愿选择到定向阶段学校还是各类型中学就读。而保守之风最盛的巴伐利亚州在1990年甚至取消了定向阶段的教学,成为全联邦特例,这里的学生依然要根据学习成绩和能力选择或申请不同类型中学,只有小部分学生在读完五年级之后才会获得机会转入到文科中学[19]。其他大多数州则选择依托于某种类型的学校实现定向功能,独立的定向阶段学校只是以逐步进行的试验形式存在。
德国重新统一后,东部五个新联邦州全面引进西部老联邦州的做法,教育也同样逐步融合和转型。1992年新联邦州议会通过了学校法案,正式采用高度差异化的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广受争议的早期筛选和分流措施[20]。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教育发展问题有了新进展,因此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组织了从2000年到2002年的教育改革论坛。论坛大量的调查显示德国教育整体质量不佳,且存在“教育盲区”,例如外来移民和较低阶层子女成绩明显差,它表明教育不公平仍然存在。在平衡各方利益之后,改革论坛提出了“十二条教改建议”。这个建议的指导思想与六、七十年代所推行的学校一体化理念不再相同,而是强调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化促进”,重点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质量。“促进”已经不单单限制在为期两年的定向阶段之上了,而是覆盖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21]。对于分轨的学校系统,教改建议强调继续打破不同教育道路之间的封闭性,使它们相互贯通,形成立交桥,而且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作为连接中学与小学的定向阶段依然保持原有功能,使筛选和分流的过程更加合理和精细。
结 语
从上述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定向阶段教育不是德国为了独树一帜而设立的制度,其重心也并非是采取独立存在或者依附于他者的学校形式,它的中心和关键是德国早期化的教育筛选和与之相随的分轨学制。改革力量为了教育公平而主张学校和教育统一化,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传统力量最终做出有限的让步,给四年级之后的学生“一定适应和调整的权利”,因而定向阶段是对于“传统教育体制反思、 改良和妥协的结果”,其作用是采取措施使“分流的决定做得更细致些”[22]。
定向阶段所服务的分轨制作为教育平等的话题由来已久,国际社会对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18]108。与此相对应,美国推行统一化的学校制度,其大部分民众也反对过早的分流(tracking),但是在教育实践中,诸如基于学生读写能力而采取的分组(ability grouping)措施却受到鼓励。其实,两个概念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由此看来,何时和如何筛选和分流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研究其有效性和合法性。这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主要议题,而是关注作为过渡程序的定向阶段它同样“一直以来就是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所争辩的课题”[16]39。一般认为,它作为“把教育的多样、高效及完善融于一体的重要交汇点,体现了德国教育注重人的发展的精神,强调人的发展的合理性,避免了教育的浪费”[6]164。定向阶段没有——也不可能满足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与愿望。作为教育结构改革运动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措施从创立到被认可和推广,在波折中还能延续至今,其过程本身就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诸多矛盾,完成了社会和教育所赋予的使命。
[1]贝格拉 P. 威廉·冯·洪堡传[M].袁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1-2,3.
[2]美国赴德教育代表团报告[M].黄志成,译//李其龙, 孙祖复. 联邦德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3]埃尔德曼 K D. 德意志史: 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 (1914-1950) :下册[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269.
[4]哈达赫 K.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M].杨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联邦德国各州关于统一教育事业的协定[M].孙汇琪,译//李其龙,孙祖复.联邦德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268.
[6]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22.
[7]WEINSTOCK H. Der Bildungsnotstand Der Hoeheren Schule[J]. Frankfurter Hefte: Zeitschrift Fuer Kultur und Politik, 1958,13(11):765-777.
[8]EDDING F. Bildung und Wirtschaft Ansaetze Zu Einer Oekonomie Des Bildungswesen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u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d-ucation,1960,6(2):129-140.
[9]PICHT G. Die Deutsche Bildungskatastrophe,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M]. Olten und Freiburg im Breisgau:Walter-Verlag,1964:16-35.
[10]佩茨 H, 普罗科普 E. 联邦德国及巴伐利亚州教育手册[M].杭州大学中德翻译情报中心,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134.
[11]王桂.当代外国教育——教育改革的浪潮与趋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99.
[12]文化教育部长会议.柏林声明[M].孙汇琪,译//李其龙,孙祖复.联邦德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372.
[1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州州长会议.联邦德国各州就教育领域中的统一问题签订的协定[M].孙汇琪,译//李其龙,孙祖复.联邦德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375-376.
[14]KLAFKI W.Aspekte Kritisch-konstruktiv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Gesammelte Beitraege Zur Theorie-Pra-xis-Diskussion[M].Winheim:Beltz Verlag,1976:278.
[15]ROTH H.Begabung und Lernen:Ergebnisse und Folge-rungen Neuer Forschungen[D]. 1. Aufl. Stuttgart: Klett, 1969.
[16]张可创,李其龙.德国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165.
[17]克莱姆.教育改革总结[M].马庆发,译//李其龙,孙祖复.联邦德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18]FUEHR C.Deutsches Bildungswesen seit 1945:Gr- un-dzuege und Probleme[M].Bonn:Inter Natio-nes,1996. [19]杭州大学中德翻译中心,巴伐利亚州文教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教育制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37-38.
[20]MÜHLENWEG A M. Educational Effects of Early or Later Secondary School Tracking in Germany[J]. Zew Discussion Papers, 2007:1-4.
[21]周丽华.德国基础教育的改革理念与行动策略——解读德国教育论坛“十二条教改建议”[J]. 比较教育研究,2003(12):6-10.
[22]郑也夫 :德国教育与早分流之利弊[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33(6) :6-15.
【责任编辑 侯翠环】
An Analysis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Orientation Stage in Federal Germany and on Its Connotation
ZHAO Zi-j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Hebei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The orientation stage (Orientierungsstufe)of German education is a peculiar phenomeno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recovered the educational tradition of the Weimar Republic after the WW II.The pupils are selected and tracked in different typical secondary educational schools after their common four-year educ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1960s, the society called for delaying the selec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schools. The orientation stage was founded in order to rationalize the tracking system. With the stagnancy of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the popularization broke down and its progresses are different in each federal state. The orientation stage is closely tied with German separate track educational system. Although people pass different judgments, the system reflects German traditional idea of catering for all abilities, has completed its miss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s given the spirit of the new era.
Orientation stage(Orientierungsstufe); primary educa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re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structure; separate track educational system
2015-05-20
赵子剑(1974—),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外国教育史。
G53
A
1005-6378(2015)06-0102-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6.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