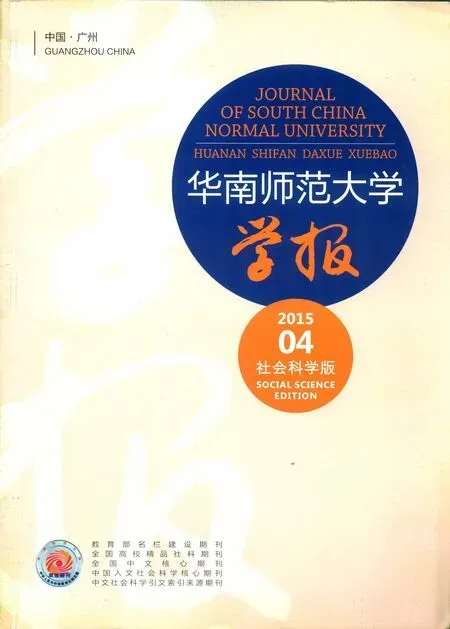《玉梨魂》的“言情”再解读——从写情的角度看《玉梨魂》对《茶花女》的改写
陈 瑜
《玉梨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徐枕亚的代表作,也是《茶花女》在民国时期的重要仿作。作为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言情作品之一,《玉梨魂》的“言情”最常为人诟病但也最为人所赏识。“诟病”派提出,《玉梨魂》堆砌辞藻、矫揉造作,常作“无病呻吟”①按平襟亚介绍,刘半农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18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而赏识派则认为《玉梨魂》的言情充分展现了人物内心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夏志清更是提出,《玉梨魂》承继了自李商隐、杜牧等诗词至《西厢记》《牡丹亭》乃至《红楼梦》一脉古老的中国旧文学“感伤—言情”(sentimental-erotic)传统,并代表了这一传统的最终发展。②夏志清:《〈玉梨魂〉新论》,欧阳子译,载(台湾)《联合文学》1985年第12 期。英文原文见:C.T.Hsia. Hsü Chen-ya’s Yü-li hun: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 in Liu Ts’un- yan ed.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4:199—241。可见,如何认识和评价《玉梨魂》的“言情”,是《玉梨魂》研究不可忽略之处,也是反映其在中国言情文学传统价值地位的核心。
海内外学者对《玉梨魂》的“言情”及其作品价值有不同的解读。袁进认为,《玉梨魂》中真诚热烈的情爱与呆板僵硬的说教构成了作品的病态情调。③袁进:《过渡时代的投影——论〈玉梨魂〉》,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 期。林培瑞提出徐枕亚在《玉梨魂》中追求一种“极致的感伤主义”(extreme sentimentalism),而这种感伤主义比《红楼梦》有过之而无不及。④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51.姚玳玫认为《玉梨魂》的特别在于“纯情的坚守、对述情的痴迷以及对驱情手法别出心裁的运用”⑤姚玳玫:《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第1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联芬提出,《玉梨魂》具有向内转、抒情化倾向,且《玉梨魂》内聚焦的主观视点、大量的内心独白式的话语,自我宣泄的等风格,延续到了五四浪漫小说中。⑥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第79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以上研究各有精彩,但对于《玉梨魂》如何创造性地化用西方小说的“现代养分”,并如何在中国旧文学“感伤—言情”传统和现代浪漫言情之间实现勾连,却仍留有研究的空间。在笔者看来,有关《玉梨魂》的感伤言情及其价值,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补充,那就是探讨《玉梨魂》对小说《茶花女》的师承与改写:即《玉梨魂》如何创造性地化用了《茶花女》的言情资源,做出适应中国文化的改写,并形成新的感伤言情风格。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究,《玉梨魂》常为人所称道的“感伤”“矛盾”的情感书写对言情主体的塑造有什么新贡献?它在中国现代的言情写作和情感启蒙历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笔者看来,《玉梨魂》对《茶花女》的学习借鉴,不在其“形”而在其“神”,它十分注重从“内在自我”层面表现人物的情感矛盾。而这,也是《玉梨魂》为中国言情小说进入“现代”提供的一个转向。
一、矛盾内在化
《玉梨魂》讲述的是“寡妇恋爱”故事。男主人公何梦霞怀才不遇,在乡村任教,遇到寡妇梨娘,两人情愫暗生。不料梨娘不愿耽误梦霞前程,她想出僵桃代李的办法,将自己的小姑筠倩婚配给梦霞,并以病自殁。筠倩为回报梨娘,也无意求生,最终同赴黄泉。此后,梦霞以报国殉情,在武昌战役中壮烈牺牲。
从故事情节上看,《玉梨魂》与《茶花女》似乎无太多相似之处。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玉梨魂》对《茶花女》的学习,并没有像《新茶花》等《茶花女》改写作品那样照搬情节;而是巧妙化用了“茶花女式爱情”的故事情感内核来重置人物与故事结构,聚焦于人物内心,努力发掘由“爱情之难”而带来的人物内心波澜,突出描写人物的内在矛盾。
第一,与《茶花女》相比,《玉梨魂》的作者刻意消除爱情故事的外在矛盾,将笔墨聚焦于恋人们内心的情感变化上。
这一做法首先体现在对家长形象的塑造上。《茶花女》中,家长成为儿女恋情发展的主要障碍;而《玉梨魂》中,无论是女方的家长崔翁还是男主人公的母亲,他们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都给予儿女极大的自由,这使得一贯阻挠男女主角爱情发展的家庭力量消弭无形。
其次,小说对人物的社会活动着墨甚简,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都被设置在相对隔绝的家庭空间里,这也有利于排除外部因素如社会环境、经济压力等对爱情的影响而聚焦于人物内心情感。在《茶花女》中,小仲马十分注重写男女主角在歌剧院、公园、舞会等公共空间中的社交及娱乐。但《玉梨魂》男主角梦霞的生活内容基本只有两件事情:一是教书,二是恋爱。不独梦霞,寡妇梨娘更是如此。她足不出户,全部的生活内容都局限于伺奉家翁、照料儿子。徐枕亚的这番设置,明显让梦霞和梨娘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真空化”,他们的恋爱像被密封似的,无需面对任何外来的经济或社会的有形压力。
第二,《玉梨魂》强化了《茶花女》中的“三角恋”人物关系,让人物情感经历新的挑战,从而为人物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创造机会。
《玉梨魂》学习《茶花女》,虽写的是梦霞和梨娘的恋爱故事,但其中横生一笔,让梨娘将筠倩许配给梦霞,这使得三人间原本简单的姑嫂及远亲关系,转变为“一男二女三角恋”。在这个三角恋中,梨娘爱梦霞,梦霞爱梨娘,而筠倩又被许聘给梦霞。至此,三个人开始卷入爱情的纠葛,人物关系渐趋复杂,其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
第三,女主人公内心的自我矛盾推动着《玉梨魂》的情节发展,这一点和《茶花女》一脉相承。
在小说中,梨娘不单一手挑起爱情,更一手毁灭爱情。徐枕亚深入描写了女主角的矛盾心态。梨娘主动向梦霞示好,但发现梦霞对她爱意渐浓时,她却为自己的寡妇身份而果断终止这段爱情。此外,她深爱梦霞,但却要为梦霞另觅爱人。小说中写道,梦霞起誓要与她生死与共时,她“感之深,怨之亦深”①徐枕亚:《玉梨魂》,第57 页,(上海)民权出版部1913年版。,由此设计出一个僵桃代李的办法来解决爱情困境。徐枕亚通过上述描写,揭示了女主角的自我分裂,并呈现了这种分裂的情感逻辑。梨娘追逐爱,遵循的是来自“情感自我”的本性需求;她拒绝爱,却是受到伦理责任的制约,基于对“道德自我”的意识。
不独梨娘,在作者的笔下,其他两位男女主角梦霞和筠倩的内心,也常处于“分裂”状态。他们的“自我”,同样经受着新与旧、传统与西方两套价值体系的折磨。
这些人物的矛盾状态,从当今读者的角度看,可能会有不可思议之感。但是就《玉梨魂》而言,作家正是通过人物自我的分裂,赋予此爱情悲剧一种独特美感。它是一种由于人物的内在价值观念的分裂而形成的“不得不然”①按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悲剧的分类,“由叔本华之说,悲剧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玉梨魂》所营造的悲剧,正是这里的第三种。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集于《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14 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的悲剧,根植于个体的内心冲突,其中蕴含了那个时代各种观念的抵牾和对抗。此内在情感矛盾,甚至比《红楼梦》中的悲剧更强烈和不可调和。难怪夏志清会认为《玉梨魂》代表着中国旧文学从李商隐至《红楼梦》等一贯的“感伤—言情”传统的最终发展。②夏志清:《〈玉梨魂〉新论》,欧阳子译,第10 页,载(台湾)《联合文学》1985年第12 期。可值得思考的是,《玉梨魂》仅代表这一传统的终结点吗?笔者认为,它既是某种意义上的巅峰,同时它也昭示了这一传统的现代发展。
二、知己之恋
《玉梨魂》化用了《茶花女》和中国悠久的“感伤—言情”传统。在恋人的关系设置上,重置了一种注重内在情感交流的知己般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中国人的情感观念开始暂露“现代”特征,即注重个体间情感的交流和体认。
首先,与《茶花女》相比,《玉梨魂》中真爱的驱动力并非是“欲”而是“才”,恋人间的爱情是一种才与情交流的精神恋爱。
在《茶花女》所演绎的浪漫爱情中,阿尔芒和玛格丽特之间几乎每一次交往都是以肉体的亲密接触作为激烈爱情的表达和宣泄的。但《玉梨魂》并不将“情”与“欲”挂钩,而是将“情”与“才”关联,建构了以“怜才”为基础的知己式精神恋爱。梦霞和梨娘起初虽未谋面,却因欣赏对方的“才华”而渐生爱意。将“情”与“才”相连,并不是徐枕亚的独创,这种做法在中国言情小说里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玉梨魂》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用“才情”建构出男女主角之间知己式的精神恋爱。这种爱情无需凭借身体的吸引力,而是寄托于“才情”的体认、沟通、交流。梦霞和梨娘爱情交往,都是通过诗歌书信互诉衷肠,再无超出此界限的任何肉体接触。直至两人爱情终结,他们也只见过两面。
其次,《玉梨魂》中所建构的是一种既出于传统、却又颇具现代个体情感色彩的“知己”之爱。
《茶花女》所塑造的爱情,虽然可称为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浪漫爱情,但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恋仍带有强烈的征服意识。相反,《玉梨魂》塑造的恋情,虽然带有中国传统言情色彩,但是作者在描写这份恋情时,却十分注重表现恋人间的情感体认,着重表现两位恋人志趣相投、倾心共鸣、自由交往的情态。
我们可以看到,处在恋爱关系中的梦霞和梨娘,他们所认同的不仅是“情人”,更是“知己”。“知己”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让他们可以超离现实生活中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获得一种新的身份。
徐枕亚在小说中用了相当篇幅来描绘此知己与知己之爱,小说写道:
所谓知己者,心与心相知,我以彼为知己,彼亦以我为知己。两相知故两相感,既两相感矣,则穷达不变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语相要,终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难。③徐枕亚:《玉梨魂》,第17 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作者眼中,“知己之爱”的核心在于“相知”“相感”。由此,他在建构梦霞和梨娘的恋情时也十分注重展现这种“相感”的状态。梨娘和梦霞的情感交流,除了隐晦地表达爱意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同病相怜、相知相识的情感体认。纳撒尼尔·布兰登在分析浪漫爱情的心理时提到:“人类渴望并需要自我意识的经验,这来自把自我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人来体验,并且他们通过和其他人的意识互动获得这种体验。”④[美]纳撒尼尔·布兰登:《浪漫爱情的心理:反浪漫时代的浪漫爱情》,林本椿、林尧译,第82 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玉梨魂》中的男女主角,也正是从对方的行为中得到与自我一致的价值和情感的共鸣。通过与他人情感的交流,他们不仅体认了对方的知觉情感;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用这种爱情来体认了自我。这种情感体认在小说叙述者不时提及的《桃花扇》和《花月痕》等作品中,虽然也有,但是不如《玉梨魂》那样细腻和真切。
需要注意的是,徐枕亚在《玉梨魂》中塑造的这种知己式精神恋爱,不止是情人之间的相知,还包含了他们共同信守的礼法制度的规范要求,特别是梨娘作为寡妇所必须遵从的道德伦理。这部作品以梨娘病殁、梦霞殉国来终结俩人的感情,造成了极致的“感伤”效果,也在这个层面上暗含了新的寓意:一方面表达了爱的不可能,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在现有的礼法体制内这种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的“爱的情感”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从个意义上看,《玉梨魂》也可以说是一座小说的桥梁:从一边可以看到言情小说的传统的终结,从另一边已经可以眺望浪漫小说新的彼岸。
三、“内聚焦式”抒情
徐枕亚除了在小说中建构一种精神恋爱,让人物在恪守礼教的偏执中不断挣扎外,也模仿《茶花女》创造“文本内的文本”(如穿插书信和日记等),让叙事的视角发生变化,使得人物得以充分抒发自我感情,向内挖掘了一个有深度的精神世界。笔者将此称为内聚焦式的叙事手法。这种从“外”向“内”的转向,为中国言情小说的现代转向,在抒情方式上做了某种铺垫。
第一,《玉梨魂》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框架内,通过第一人称书信表达,有效地补充了人物的“内在”叙事视角,为他们的内心情感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徐枕亚从《茶花女》中得到启发,采用恋人的情书来构成这部章回体小说的主体。小说共30 章,其中25 章都是梦霞和梨娘书所写的诗词、信函,从而细致入微地呈现人物的情绪起伏和精神交流。
书信体小说带有个性化、主观化的特点,在西方小说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类。将《玉梨魂》置于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还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徐枕亚首开国内书信体小说先河。陈平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中国作家最早大量引书信入小说的数徐枕亚。”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19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夏志清还提出,徐枕亚的书信体小说,“实际上为五四时期的许多白话恋爱小说(包括从头到尾采用书信形式者)开辟出一条路”②夏志清:《〈玉梨魂〉新论》,欧阳子译,第23 页,载(台湾)《联合文学》1985年第12 期。。
第二,《玉梨魂》借鉴了《茶花女》的写法,在小说中插入人物日记,这样的内心独白是其突破全知叙事的另一方式。
《茶花女》超越于一般的通俗小说,其重要特点在于对人物感情复杂性的揭示。这里常为人称道的是通过第一人称独白来展开叙述。但不仅如此,它在主要故事之后附录人物的日记的做法也引人追捧。
《玉梨魂》小说第二十九章就题为日记,这一章借筠倩日记交代出《玉梨魂》第二位女主角筠倩的情感。作为接受了自由思想教育的新式女子,筠倩哀叹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更为梨娘、梦霞和自己的命运而悲悼。这里的九篇日记,让全书的哀情风格掀起新的波澜。在死前数日,她用日记记下了自己对人生的哀叹和对男主角梦霞的隐匿情愫。在日记中,筠倩对孤独、病痛和感情创伤的描述,宛如《茶花女》中玛格丽特弥留之际的再现。
如果我们把日记这种内心独白看做是人物与自我的交流,或者类似于遗书——作者期待与自己的理想读者交流(如筠倩希望梦霞可以读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徐枕亚的小说所传达的情感的另一现代特征,那就是自我情感体认的重要性。日记体的使用呈现了一个人如何形成对自我的同情共感,亦即自我意识。日记提供了自我得以记录个人经验的形式,而记录本身则是承认、接受和回味各种经验的过程。把日记引入小说,将促进中国传统言情小说抒情方式的个人化转变,改变中国小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非人格化的叙述,从而使小说进入现代历程,让个人(包括女人)以第一人称的姿态畅言自我的经验。
第三,《玉梨魂》用骈文铺陈人物心理,通过古奥婉转的文句展现人物纠结、矛盾的内心。
相对于小说中的诗词,在第三人称的散文体叙述中,徐枕亚还常用骈文抒发人物情感,他借助工整的对仗和排比句,有效地强化了人物的感受。
在《玉梨魂》中,梨娘第一次读到梦霞的来信,心中惊喜交错:“梨娘读毕,且惊且喜。情语融心,略含微恼;约潮晕颊,半带娇羞。始则执书而痴想,继则掷书而长叹,终则对书而下泪。九转柔肠,四飞热血,心灰寸寸,死尽复燃。”③徐枕亚:《玉梨魂》,第22 页。句与句之间,对仗排比,层层递进,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那种欲拒还迎的矛盾状态以及欲罢不能的曲折心理,全都跃然纸上。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玉梨魂》的叙事特点。除了上述穿插日记、书信等叙事技巧外,《玉梨魂》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抒情手法,包括通过诗化的意象来传达人物感伤的情绪等。这些手法虽然不及上述书信穿插等方式特点鲜明,但它们对《玉梨魂》来说都不是孤立一体的,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玉梨魂》感伤抒情的叙事风格。
四、《玉梨魂》之“爱”
《玉梨魂》模仿《茶花女》进行创作,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上述小说的写作和叙述上;更为重要的是,《玉梨魂》借用《茶花女》的浪漫爱情模式,深入探索爱情困境,呈现了爱情主体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从“自我”的层面推进新时代情感启蒙的历史进程,为“五四”时期的情感解放和感伤型浪漫主义抒情写作奠定了基础。而这一点,恰恰最易为人所忽略。
(一)爱情主体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
《玉梨魂》与之前的“感伤—言情”传统小说相比,其出彩之处,在于徐枕亚对爱情主体的自我意识做了相当丰富的表达。笔者用“朦胧觉醒”来形容这种状态是想说明,这部作品中人物的自我意识,相比以往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为五四时期一代人情感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首先,《玉梨魂》中的人物通过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来体认自我、重构自我。
《玉梨魂》中的男女主角,将维护礼教的责任内化于自身。他们对自我的形塑,也常以道德礼法要求为准绳,不敢甚至也无意去直面自我的内心需求;可是对爱情的渴望,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释放“自我”。我们可以看到,梨娘在日常生活中不敢逾越雷池半步,恪守自己作为寡妇的身份;但是面对爱情,她却如此地主动、自主,在诗词的酬答和书信的往来中,肆意表达内心情感。
梨娘在爱情领域中对“自我”的发掘与重构,其实显示出那个时代人们体认自我的一个特别途径,即通过爱来感知自身。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个体在爱情的追逐中不断审视自我,不断趋近内心。爱情的探索越是深入,自我的形象越是清晰。考虑到自1912年开始,此后十余年间《玉梨魂》再版了三十多次,我们可以说,《玉梨魂》启发了一代读者对待感情的态度,使他们可以在争取自由的恋爱路上走得更远。
其次,《玉梨魂》中的人物开始注重体验个体情感深刻的内心矛盾,为五四时期言情小说“感伤性主体”的形成埋下伏笔。
李今提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五四文学所发生的影响,在情感特征上的又一表现是感伤性……感伤的情绪又是个性觉醒,尤其是把文学描写的重点转向个人内部的标志。”①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第63 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在徐枕亚笔下,《玉梨魂》的男女主角都带有浓郁的感伤情绪。这些情绪的产生,虽然受到个体多愁善感性格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他们对爱情生活中无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体悟和感知。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性格,也是一种“感情内省”的表现。
《玉梨魂》的人物虽然没能像五四时期的青年男女那样,充分肯定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对人类的生存境遇的孤独和苦痛有自觉的反思,但他们在情感问题上的自省和反思,无疑也是一种个性觉醒的表现。
(二)“感伤—言情”传统的现代转换
在笔者看来,《玉梨魂》的感伤抒情和之前的作品相比,其最大不同在于,它显示出了类似西方感伤主义作品的抒情色彩,是“五四”感伤主义作品的先声之作。《玉梨魂》为中国“感伤—言情”传统的现代转换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将中国传统感伤言情从关注“境遇”转变为关注“心灵”,注重主体的内在感受。
《玉梨魂》所写的爱情悲剧,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②徐枕亚在无锡任小学教员,因学生蔡如松而认识其寡母陈佩芬。徐枕亚和陈佩芬惺惺相惜,最终都没有勇气走到一起,反倒是陈佩芬将其侄女介绍给徐枕亚,了结了这段爱情。可参考以下研究。黄天石(杰克):《状元女婿徐枕亚》,载(香港)《万象》1975年第1 期;袁进:《〈玉梨魂〉作者徐枕亚三次爱情悲剧》,载《上海滩》1992年第8 期;郑逸梅:《徐枕亚与〈玉梨魂〉》,见《郑逸梅笔下的文化名人》;《状元女婿徐枕亚》,见《郑逸梅美文类编》等。但徐枕亚在创作《玉梨魂》时,并没有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故事的讲述上,而是放在人物心理矛盾的描摹中,将关注的重心从“境遇”转变为“心灵”。而且,《玉梨魂》化用《茶花女》的言情资源,强化了人物的内在矛盾,使传统感伤言情的悲情来源从“境遇之惨”变为了“心灵之痛”,让人物的内心感受成为感伤言情的主导。
第二,如前所述,它将中国传统感伤言情常用的“向外投射式”的抒情,发展为“向内聚焦式”的倾诉,以情绪的发展带动叙述。
虽然《玉梨魂》中也有很多将个体情感投射于景物、情境中,通过比兴、隐喻等修辞,以景抒情、以境传情的例子,但是它又增加了《茶花女》中的抒情手法,诸如穿插书信、日记等方式,使人物的倾诉变成向内聚焦。这种内聚焦,则是西方感伤主义的抒情特点。
当然,中国“感伤—言情”传统的现代转换也并不是一部《玉梨魂》就能完成的。民初小说中,除了徐枕亚的这部承上启下之作外,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作品也功不可没。也正是在以《玉梨魂》为代表的系列言情作品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感伤—言情”脉络才得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身。
《玉梨魂》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吸引过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甚少有人将它放在《茶花女》改写作品的脉络中去细致考察。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重新考察了《玉梨魂》的言情特点;探讨徐枕亚如何巧妙化用《茶花女》言情资源,强化人物内心矛盾,构建出知己式的精神恋爱;并运用“内聚焦式”抒情手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茶花女式爱情悲剧》。
这个爱情悲剧,虽然没有表达出“五四时期”自由自主的恋爱观念,也没有将主人公塑造成追求爱情的楷模;甚至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都不愿直面男主角殉情而死的事实,以致要用“以爱殉国”的说辞来“美化”这段爱情。但是,这部作品在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它写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男女青年在情感解放的历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及礼教对个人情感及欲望的否定和戕害,而且这种戕害是借助内化于个人和情侣之间的自我束缚来实现的。
《玉梨魂》曾因其作品所弥漫的感伤情绪被嘲笑为“鼻涕眼泪小说”①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180 页。。但按李今的研究,“感伤性”却是“以自我,一个精神个体的体验为特征的情感类型”②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第57,63 页。。它是个性觉醒,“尤其是把文学描写的重点转向个人内部的标志”③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第57,63 页。。《玉梨魂》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这样的转向。它开始跳出了简单的对错是非评价,探索在新旧伦理准则中爱情主体两难的困境。我们可以在“五四时期”的很多爱情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思考。如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陈翔鹤的《西风沉醉的夜晚》等,这些作家都开始探索在新旧道德伦理中,爱情主体的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