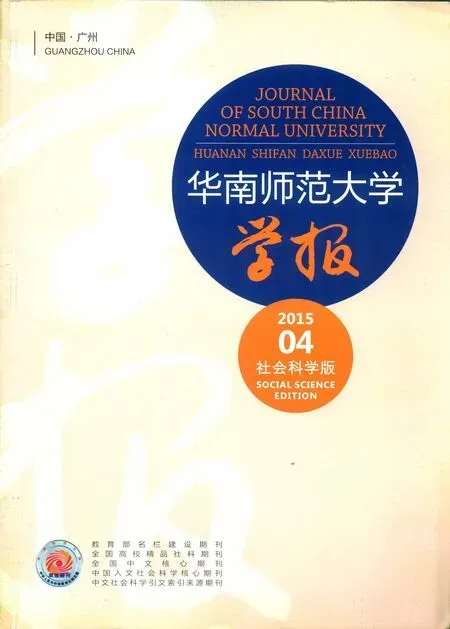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中国现代白话散文
刘茉琳
一、作为过渡形态的“新文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一场疾风暴雨涤荡了整个古代文学及文化。随着一批新文学运动家的着力推进,散文的现代转型显得尤为亮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役,鲁迅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而曹聚仁则干脆指出:“五四”之后,白话文替代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垒中了。就当时的情形看,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散文运动显得妥切。”①梁向阳:《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第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真正的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诞生的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并不代表从古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转型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在“五四”之前,古代散文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分化、转型、改变,开始孕育新的散文文体。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文化目的,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坚持在文学的方方面面进行变革。他们的鼓动及创作推动了古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转型,为之做好了思想、语言、内容、形式以及作者、读者、阅读期待与写作追求等诸多方面的准备。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梁启超。“他的‘新文体’是传统古文和‘五四’现代白话散文之间的过渡桥梁。”②张梦新:《中国散文发展史》,第134 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在其名文《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③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第83 册,1901年6月。所谓过渡时代,就是在“政体”“学术”“道德”等方面都面临着对旧有形制的不满或者现有体制的崩解,而新政体、新学术、新道德又未能建立。梁启超对时代和自我的认识是清醒的,他心甘情愿做一“过渡时代之英雄”,其笔下的“新文体”则成为古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过渡形态。
“新文体”作为散文文体形态的“过渡性”甚至在命名上已有所体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这种“解放”了古文约束的平易畅达的文体使青年学子深受影响并争相效仿,而“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新文体”一方面不符合非韵非骈的古代散文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因其语言是浅近文言故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白话散文。老辈以“新文体”之名将其排斥于古代散文之外,年轻学子则以“新文体”之名表达对这种文体的理解与热爱。“新文体”之名正是过渡形态的最好表征。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回顾自己的散文观,十年前曾经将现代散文的成就归于引进西学,如今却是另一种态度了:“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①余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第214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可是,尽管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认识到散文发展的历史基础之重要,在考察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时,他与许多新文学家一样将重点放在公安派身上,认为自身情趣志向的追求与公安派有超越时空的不谋而合之处,而绝少甚至几乎没有提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梁启超的“新文体”本身也不是“纯正的内应”,而是西洋科学哲学与历史上的言志派相结合的典型产物,是在外援与内应的两条腿支撑下走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的。由此也可以证明梁启超的“新文体”本身就是现代散文无法回避的“前身”,是一个巨大的辉煌的开端。
二、“新文体”于现代白话散文之过渡作用
梁启超的新文体作为一种近代转型期的散文文体,对于现代散文有着“前摄性意义”②朱寿桐曾经在讨论到文明戏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时提出“前摄性意义”,认为文明戏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前摄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所谓前摄性意义是指前一个事物及其运作过程对后一个事物及其运作过程客观上所起到的建构、启迪并使之更加趋于充实的作用。”这个“前摄性意义”用于讨论梁启超的新文体对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意义也非常合适。见朱寿桐:《论文明戏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价值》,载《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 期。,在特殊的时间点上,起到了桥梁式的过渡作用:从散文本体而言,它努力进行着或完成了语言特色、思想内容、文体形式等数个方面的变革;从散文发展的历史而言,它改变了延续千年的读者群体与阅读期待;并且从这些读者中准备了现代白话散文的作者队伍,培养了具备现代性的书写追求。
其一,“新文体”在语言特色方面的过渡作用。
梁启超(1873—1929),一生跨越中国近代从晚清到民国的重要转折时刻。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转折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包括语言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读梁启超的文章,从年轻时的政论文、到流亡时代的报刊体、传记文,以及中年的游记散文,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分明的文学语言变化轨迹。
从时间上划分,在1910年之前,梁启超的文字处于由古文向浅近文言的转换阶段。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1900年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1901年在《清议报》发表《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等一系列政论文章都是辞藻华丽、情感丰沛的古文。其中《变法通议》中“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连用数个四字词语,描述大厦将倾国之危矣的状况,形象生动仿佛绘于眼前,语气急促与危急形势相扣。而《少年中国说》中“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整段文字逻辑清晰、前后相连、对仗工整,不仅在当年震撼人心,即使今日依然是青年学子们朗诵演讲的极好范文。在《积弱之源于政术者》一文中用大量感叹句式,以及“呜呼”等古文感叹词。这些早期新文体都显示出梁启超优秀的古文功底,而这些文章在情感、词语、语气等方面的变化则是深受报刊这一载体形式影响的。出于政治宣传目的,梁启超此时的新文体在语言上虽然有大量新名词涌入,但基本还是属于变形的古文。1905年前后,梁启超的新文体开始发生语言变化。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开明专制论》一文云:“发表其权利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谓之制。据此定义,更进而研究其所发表之形式……”这一段文字中虽然“谓”“据”“之”等动词、助词属于文言表述,但整体语言风格已经明显走向通俗化。至1910年前,梁启超写作大量短文后来收入《自由书》一辑:“希望者,灵魂之粮也,而希望常与失望相乘,失望者希望之魔也。”(《希望与失望》)“自杀之种类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也。”(《国民之自杀》)这一类语言不是真正的白话文,却是介于古文白话之间的过渡体,即浅近文言。许多文言词汇、新名词得以通俗化并进行传播,大量新词语、新概念,以及改造的西文、日文名词成为现代白话最重要的词汇基础进入中国现代语言系统。这种浅近文言语词通俗之余同时保留文言雅致审美,可说是兼有古文之雅致与白话之通俗,彰显的正是过渡时代的语言特色。
1919 白话文运动狂飙突进。许多国内的旧派人物翘首企盼正在欧游的梁启超回国与这种新文学白话文学做一对决,不想梁启超直接用白话写起了《欧游心影录》,且写得有模有样,弄得许多旧派人物灰心丧气。章士钊大骂梁启超“从风而靡”,可胡适却赞赏地说“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般少年人向前跑”。此时的梁启超放弃浅近文言的写作,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甚至还尝试写作白话诗歌,正是他一贯的力求进步的精神体现。当“新文体”的浅近文言已经发挥作用完成历史使命时,他选择适应时代潮流,如郑振铎则说梁启超“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①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主编:《追忆梁启超》,第54 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其二,梁启超之“新文体”在思想、观念、内容等多方面深刻影响了现代散文。
梁启超的一生,早期以政治改革为人生目标;流亡日本之后,全面展开报刊创办舆论宣传之工作,意识到依靠写文章来传递新思想,以起到疗救国人之思想的目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新民”思想。梁启超曾将笔名改为“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四年11 万字内容的《新民说》。梁启超以“新民”为立国之本,希望国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学自新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民。在梁启超的新民体系中,第一要旨就是“我之自由”,包括了“人身自由”与“精神自由”,将人身不自由比喻为“身奴”,将“精神不自由”比喻为“心奴”(《新民说·论自由》);他提出新民应该具有利群、爱国之公德(《新民说·论公德》);指出新民应具有权力、义务观念(《新民说·论义务思想》);最后还要求新民必须有冒险精神(《新民说·论进取冒险》)。《新民说》在当年对胡适、鲁迅一代人影响深远,曾被认为是启蒙方面最有价值、影响最大的文章。现代白话散文在内容上主要呈现出对现代科学、民主、人权与自由的追求,通过对新文体尤其是《新民说》一文的梳理会发现,这些内容早在梁启超的新文体中已不断出现,在现代白话散文中贯彻这些内容的学人无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新文体”从内容上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养分,深深影响了创造现代白话散文的一批学人。梁启超曾将自己1899年至1910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发表的大量杂文挑选其中六十多篇辑为《自由书》。他自言:“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内容驳杂,政治(《地球第一守旧党》)、文化(《文野三界之别》)、文学(《烟士披里纯》)、社会(《维新图说》《俄人之自由思想》《二十世纪之新鬼》)、哲学(《无欲与多欲》《希望与失望》)、人生(《成败》《理想与气力》)……包罗万象、巨细并存。其内容之丰富与中国古代散文囿于精英社会圈子的散文书写有了很大区别。梁启超阅历丰富,思想自由,文章的目标读者群阶层广、数量众,因此突破了长久以来散文创作的内容局限。
梁启超“新文体”还从文体观念上全方位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崇古”之风,展现出梁启超鲜明的“个性追求”与“自由追求”,为“五四”一代开风气之先,也为现代白话散文搭起了过渡之桥梁。“五四”学人认为中国古代散文最大的问题就是“崇古”以致于尽受古人束缚:“从前散文的心是如此,从前的散文的体也是一样。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需取诸六经;不是前人用过的字,用过的句,绝对不能任意造作。”②余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第256 页。但其实对古文的挣脱与解放并不是等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在晚清已经有大批“古文逆子”出现,至梁启超的笔下这种叛逆性更强。如梁所言“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的“新文体”显然就是对这种崇古散文的一大背反,当然也是“五四”学人们大胆破坏崇古传统叛逆祖训的最大营养来源之一。“新文体”之个性比梁启超之前的任何散文都强,比梁启超之后的“五四”散文也毫不逊色。“新文体”分明已经展现出一个面向世界的现代学人的精气神。梁启超以开风气之先的现代性对“五四”一代学人发现“个人”、展现“个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三,新文体在文学功能即散文使用方面也发挥了过渡文体之作用。
中国文学数千年来延续精英写作精英阅读的传统。这种模式直到近代才被打破,尤其是报刊的出现使得文人的书写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面对下层民众。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为现代白话散文彻底改变读者群体与阅读期待的准备,同时也从这些读者中准备了现代白话散文的作者队伍,培养了具备现代性的书写追求。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活跃在中国报刊业、政治界、文坛的一批精英分子已经开始了用白话启蒙民智的“白话文运作”;而梁启超的“新文体”正在这一时期风云九州,其文章使用的浅近文言在这一过渡时期俘获了最大范围的读者群,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点,渐渐软化了顽固的文言文壁垒,培养了语言观念革新的一代新读者。钱玄同就曾正面评价梁启超说“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①《通信·寄独秀》,载《新青年》第三卷1 号,1917年3月。。的确,“新文体”的读者群涵盖面之广,阅读影响力之大都是惊人的,所谓“二十年来之学子”可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代年青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不管是理解还是争论,梁启超的“新文体”吸引了当时社会的大部分读者,他们统一在追求变革、追求共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观念下,继而发展为现代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当然,也是现代白话散文的创作者。
三、现代白话散文对“新文体”之超越
1920年代,梁启超已经50岁。此时,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青壮年走上了历史舞台。在他们手里,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转型与成熟。“新文体”对现代白话散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毕竟“新文体”不是真正的现代白话散文,只是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的过渡体。“五四”学人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文体”,从而实现了现代白话散文的诞生。
在现代白话散文的诞生中,最重要的是“文体的自觉”。梁启超的“新文体”是在实践中诞生的,其名字甚至都是二十年来喜欢阅读“新文体”的学子冠名的。与梁启超的这种无心插柳相比较,“五四”学人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对“散文”进行界定与辨析,对散文的概念、性质与特征进行了广泛讨论。正式提出狭义散文概念的是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将散文看成ESSAY 一流,进而将散文与小说、戏剧、诗歌并提;而比较具体地描述文学散文面貌的则是周作人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美文》。他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学里的那种“记述的”“艺术性”的“论文”(也称“美文”),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②余树森:《现代作家谈散文》,第4 页。“五四”学人有意识地发展现代白话散文,他们在梁启超“新文体”的基础上将这种杂以俚语俗语的报刊体文章作为基础,引进外国的散文观念,结合文化、政治、思想尤其是语言的转换,实现了现代白话散文的转型与成熟。
在语言方面,梁启超所坚持的是从“文言之文学”到“俗语之文学”的进化观,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要求语言随着思想、词汇、内容的变化慢慢发展。这种改良方案到“五四”学人手里被彻底颠覆。他们用语言的彻底颠覆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阶级分野,打破精英阶级与贫民阶级的分野,打破文化资源的占有,以此来实现整个社会在文化上的根本转型。要实现这种语言上的转换,最容易开刀的文体的显然是散文。傅斯年1918年的文章《怎样写白话文》就是专门论述白话散文写作的,可见推广白话文最好的承载体就是白话散文。所以,现代白话散文与现代白话同时发展,从文体概念到语言使用,共同超越了梁启超时代。
梁启超一生追求打破陈旧、建立新制,对自我要求严格:“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6 页。也不惜让后起之学者踏在他的身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迅速地被一批新文学家代替了,在其建立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学、文化追求。有人为之总结道:“梁启超一直追随着时代不断进步,虽不免从大步前行的领路人降为步履蹒跚的随行者;然而,终其一生,梁启超与过渡时代自救取信的方向毕竟保持了一致。”④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262 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美国批评家赛义德曾经指出:“文本总是无法逃脱环境、时间、空间和社会的纠缠——简言之,文本存在于世界之中,所以,文本是世界之物。”从梁启超的“新文体”到“五四”的现代白话散文,都在不断实现着文体的超越与突破,并且与社会语言、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文学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情澎湃的时代里,社会需要适应新形势、容纳新信息、以新的表达方法承载思想内容的实用文体。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新文体”的诞生是时代造就了他,也是他本人对时代的积极回应。“新文体”从思想、内容、语言、文体都实现了从古文到今文的桥梁作用,从方方面面影响了后来者的散文创作,为现代白话散文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