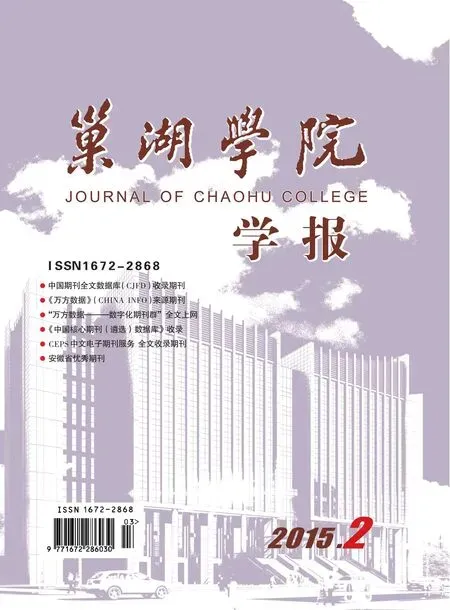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流变
周建华
(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 巢湖 238000)
1 引言
从电影的诞生之日起,文学电影改编对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据统计获得奥斯卡奖的80%的好莱坞电影都是文学改编作品[1],而在好莱坞盈利最多的十部影片中有五部是根据小说改编的[2]。蒙太奇、平行剪辑等电影中最基本的手法均取自文学[3]。电影改编作为两种艺术之间最典型和最直接互动,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和深远的研究前景。2006年“文学与荧幕改编研究学会”(后更名为“改编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改编研究已进入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4]。
然而电影改编的研究却大大滞后于电影改编的实践。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一直作为纯文学研究的附属而忽视,电影艺术自身理论的匮乏导致改编研究几乎片面依赖于其他艺术理论,很难自成体系。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评论家开始系统研究电影改编,七十年代改编研究才正式进入学术研究体系。而由于改编一直被看做是对原文本的复制,因而忠实于原文本成为电影改编研究无法逃脱桎梏,大大限制了改编研究的发展。这种形势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改观。
国际改编研究方兴未艾,国内的电影改编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国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一次关于忠实问题的大论战①《电影艺术》编辑部,中国电影出版社.再创作——电影改编问题讨论集[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虽大大促进了改编研究的发展,可惜未有结论。而且国内的改编理论一直过多拘泥于忠实性的桎梏,难以拓展,八十年代末以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电影人从两种媒介的差异出发,质疑绝对忠实的改编,强调改编中的适度创作。但他们的“适度创作”始终局限在形式上,原著中心地位依然牢不可破。并且研究者们大多从电影自身美学出发研究文学电影改编,因此他们的改编研究始终附属于电影创作研究,是一种独特电影种类的创作论。此外,也有一些文学电影改编作品的个案研究。它们或利用叙事学等文学理论进行单纯的文本比较,或是利用电影技术和电影美学理论讨论电影作品对小说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展现,零零散散未成体系。
因而,结合文学电影改编的发展历程,系统梳理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研究发展的脉络,解构文学电影的二元对立,拓展改编研究的视野,为今后改编研究尤其是国内改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及其迫切的。
2 早期的文学电影改编思想
电影诞生伊始,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街头杂耍。即使在它的创造者爱迪生兄弟眼中,它也只不过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照相技术。而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电影的叙事功能凸显出来,电影开始与文学亲密接触。除了各种叙事技巧之外,精美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中传达的人生智慧都成了电影人取之不竭的宝库。
2.1 默片时期——忠实原文的终极诉求
早在1900年,乔治·梅里爱就将安徒生的《灰姑娘》搬上了荧幕,此后他又改编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如 《格里弗游记》、《鲁宾逊漂流记》、《浮士德博士》、《从地球到月球》等[5]。梅里埃对文学电影改编和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的影片仍显得粗糙简陋,是对原小说故事梗概的图解或原戏剧舞台表演的录放。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批判他的改编没有突破 “舞台表演”的限制,是利用照相术对戏剧舞台的复制,缺乏“真正电影化的题材”[6]。
许多梅里埃同时代的电影人也不断的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但他们均没有超越梅里埃的改编范式。直到1915年,美国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将小说《同族人》改编成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文学电影改编才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部电影被公认为是电影成为一门艺术的标志,电影的成功掩盖了原小说的光芒。因此这既是电影艺术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文学电影改编历史上的一次飞跃。格里菲斯还改编了莎士比亚、杰克·伦敦、爱伦·坡、托尔斯泰等一系列作家的经典作品[2]。他将文学故事与电影表现手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对于文学电影改编的发展影响深远。
默片时代,电影在众多成熟的艺术范式面前只是一个“小学生”。由于艺术手段的匮乏,改编作品对于原文学作品的忠实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梦幻。对于原作的忠实不但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向这一目标的每前进一步都是电影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
2.2 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产业化时期改编中的非文本因素的凸显
在战争和经济危机阴影笼罩下的三、四十年代,作为世界电影中心的好莱坞为生活困顿精神压抑的民众营造了一个梦幻的避风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电影改编高潮时期。根据莱斯特·阿什海姆(Lester Asheim)的调查,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共拍摄了5807部电影,其中有976部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2]。而1939-1940年间就有如 《大篷车》、《呼啸山庄》、《绿野仙踪》、《乱世佳人》、《蝴蝶梦》、《愤怒的葡萄》、《傲慢与偏见》等多部质量和利润双赢的改编精品的出现。
而作为电影商业化工业化典范的经典好莱坞时代,利润的追求成为电影生产的主要的动力。根据塞缪尔·马克思(Samuel MarX)在好莱坞的亲身经历,好莱坞金牌制片人艾尔文·萨尔伯格(Irving Thalberg)、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哈里·考恩(Harry Cohn)等,对于文学原著甚至电影的拍摄都知之甚少,但他们对观众的喜好和娱乐的走向都异常敏锐[7]。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在讨论这一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电影改编则认为好莱坞改编范式应该是莎翁所钟爱的。莎翁本人就在环球剧院拥有份额,他所做的决定无法不考虑观众和利润。而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人的处境则与他相同[7]。
在以利润为主导的好莱坞,改编第一次遭遇是否该忠实原著这一问题。表面上电影制造者们热衷改编名著并标榜他们的作品完全忠实原著,因为原著的名声是票房的保证。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吸引观众而不是忠实原著:选择情节性较强的作品并加强其戏剧冲突;调整原著的内容来套用已成功的电影范式和类型;根据明星的个性特征重新塑造人物;弱化激进的主题思想而弘扬普世性的价值观。在阿什海姆(L.Asheim)分析的24部好莱坞改编影片,有17部增强了爱情的比重,65%的影片是大团圆的结局,其中40%原著的结局并不完满[2]。
三、四十年代文学电影改编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联,更与电影技术、艺术和电影工业的迅猛发展分不开。但这一时期的改编仍受到戏剧美学的束缚,戏剧电影成为主要的改编范式。改编虽然享有更多的自由,不再完全拘泥于原著。但是这种自由仅仅受到市场利润的支配,而且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
3 系统改编理论的出现——从“差异论”到“聚合论”
改编理论的发展大大滞后于改编实践的发展,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有系统改编理论的出现。这既与电影自身历时性的发展相关,也与五十年代共时性的背景环境分不开。作为一门新兴艺术门类,电影艺术不断地从其他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来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随着自身技术和艺术手段的日益完善,电影艺术越来越强调其艺术的独立性。系统的电影理论研究包括改编理论研究应运而生。而五十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这为电影改编研究提供了外部的契机。电视的出现又使得电影日益精英化,这进一步促进了改编研究的发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电影客观现实性的强调,法国新浪潮运动对于“作者电影”的推崇,还有民族电影的兴起所产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改编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忠实性标准”和“文本中心论”,为改编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
3.1 五、六十年代——差异论和电影的独立诉求
1956年,乔治·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发表了第一部改编理论专著 《从小说到电影》(Novel into Film)。 在这部奠基式的著作中,布鲁斯东系统分析了小说和电影两种媒介的差异,并由此对忠实原著这一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小说是“语言的、抽象的、间接的”,而电影是“视觉的、直观的、表象的”;因而“一旦舍弃了把语言作为唯一的媒介,就必须丢弃只有语言才能传达的抽象内容”[2]。由此他鼓励改编者将原著仅仅当做“改编的素材”,并利用新媒介对这些素材进行“重述”[2]。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将改编电影与原文本一一比对,分析改编电影如何展现原著的内容,并着重讨论在电影无法直接呈现原著时,应该如何利用各种电影表现手法来弥补意义的缺失。他还批判好莱坞由于经济、政治、审查制度等多种因素对文本中进行的不必要修改。这种以文本为中心,以忠实为评判尺度的分析显然与他最初的目的和前半段的论述背道而驰了。
1960年克拉考尔他的电影理论著作中也分析了文学和电影的艺术差异。他认为小说和电影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形式上不同,而在于两者着力展现的世界不同。小说的世界是“精神的连续”而电影的世界是“物质的连续”[6]。因而,一部电影越少反应精神世界它就越富于“电影性”。由此评价一部改编电影优劣不是看它是否忠实原著而是看它是否具有“电影性”,是否是“电影化”的改编[6]。然而他的“媒介差异论”和他的“电影化”的改编评价标准只能导致了所谓“不宜改编论”,即某些文学作品的内容无法“通过物质现象的连续加以再现和模拟”[6],是“非电影所能掌控的世界”[6],这样的小说就不适合搬上银幕。
强调文学和电影两种媒介的差异是对改编“忠实性标准”的一次大规模挑战。既然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两种不同的媒介系统,那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改编。但是仅仅强调媒介的差异而不质疑文学文本在改编中的中心地位,必然沦为“不可改”这一窘境。无论布鲁斯东的“不当改编”和克拉考尔的“不宜改编”都是这种“不可改”的表现。当然,克拉考尔的“不宜改编”将改编的失误归于原文本,似乎也可以看做是对原文本绝对中心地位的一种潜在的质疑。
3.2 七、八十年代——“聚合论”和忠实性改编标准的动摇
五、六十年代的改编研究强调电影的独特个性,而到了七十年代研究改编的学者则更多的关注电影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爱德华·茂莱(Edwarde Murray)在他的专著就曾着力讨论过电影对于戏剧和小说的影响。他认为《尤利西斯》之后的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作家们“电影化的想象”,是小说作家应对 “二十世纪最有生命力的艺术”的历史[8]。
1979年凯斯·科恩(Keith Cohen)在他的改编专著中从现代符号学理论出发,认为“文字和影像是两种不同的符合体系”,“在一定的抽象层面上两者是相似的”,因而叙述意义单位是可以在两种符号间相互转换的[3]。但是他认为改编不可能照搬原文,因为这违背了电影符号的特性。在1977的另一篇论文中他则鼓励电影人对原著进行“颠覆性的改编”[9]。
七十年代这种强调两种艺术门类的相互作用的改编理论,第一次挑战了改编中的“文本中心论”的思想。茂莱的“电影化小说”将文学拉下了神坛,科恩电影符号学的观点则第一次将电影和文学放到了一个平等的层面上。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差异论”仅仅挑战了“忠实原文”的可能性,七十年代的“聚合论”则质疑了“忠实原文”的合理性。而将电影和文学放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是电影艺术进一步发展,进一步要求独立的结果。从这两点上来说,“聚合论”是对五、六十年代的“差异论”的继承和发展。
4 改编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改编理论的多元化
忠实性改编原著和原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在八十年代后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这主要因为改编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受到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之后,作者在在文本的意义建构中逐步丧失了原有的绝对权威。而读者在文本的阐释和意义建构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作者中心地位的消退和读者地位的加强又消解了文本的绝对意义。文本绝对意义的消失又进一步解构了忠实性改编原则和改编中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兴起大大拓宽了改编研究的领域,改编中的文化因素和历史文化背景对改编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互文和对话理论在改编研究中的应用则不但进一步拓宽了改编研究的视野,而且几乎彻底解构了改编中文学与电影的二元对立。
4.1 八、九十年代——原文本中心论的解构
八、九十年代改编的忠实性原则和文本中心论受到了进一步的抨击。在1988年的一部改编论文集中改编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的对文本中心论提出了质疑。霍顿·福特(Horton Foote)宣称改编作品应该有自己独有的“节奏和生命”,因而“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文学电影改编不可或缺的因素[10]。桑普尔·马克思(Sample Marx)则认为电影改编不必遵从原文本而应该关注电影观众的视听感受[7]。还有多位作者将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引入改编研究。
罗伯特·吉丁斯(Robert Giddings),基思·赛尔比 (Keith Selby) 和克里斯·温斯利(Chris Whensley)在他们的专著中指出电影人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和要求,忠实原文本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他们眼中改编是“电影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对历史进行重塑”[9]。
1996年,布赖恩·麦克法兰(Brian Mcfarlane)在他的改编专著中指出忠实性改编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忠实性原则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的前提下,那就是文本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且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可以传达给读者。而他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这种“唯一正确的文本意义”是不存在的,任何改编都只能是“原文本的一种解读”,而且这种解读与读者对原著的解读和观众对改编影片的解读都不可能重合[11]。
在黛博拉·卡特梅尔(Deborah Cartmell)和伊梅尔达·恵莱翰(Imelda Whelehan)编纂的论文集中,改编研究领域日益开放的特点显露无疑。卡特梅尔援引互文理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原处的、唯一的作者”和“唯一的意义”都是不存在的[12]。恵莱翰则从读者接受论的角度出发抨击了忠实性改编原则。他认为绝大多数名著改编影片的观众并未读过原著,即使在那些接触过原著的观众心中,原文本也大多是儿时久远的模糊记忆[13]。
4.2 新千年后——文学与电影的二元对立的解构
新千年后文学改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各种改编理论更是层出不穷。如2005年米里安·阿拉盖(Mireia Aragay)主编的论文集中就囊括了互文理论、对话理论、文化批评理论、表演论、翻译论、电影作者论等各种改编理论。这些改编理论不但解构了忠实性改编原则和文本中心论,更是试图在原文本、改编作品及其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互文和对话的关系,彻底挑战文学和电影百年来的二元对立关系,将改编研究推向更广更深的领域。
其中,吉恩·马斯登(Jean I.Marsden)宣称对原文的解读只是“改编语境的一部分”,而原文的各种解读和改编作品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意义之间的交叉和联合[14]。约翰·斯达尔(John Style)认为一旦原文本“语境化”,‘原初’的界定就受到了挑战,因而改编可能更忠实于“原历史语境”而不是原著[15]。何塞·兰达(Jose A.G.Landa)则把改编看做是对 “已存在的话语结构的一次演绎化干预”,是对原著在“特定语境和交际互动范式”下的阐释[16]。米里安·阿拉盖和吉玛·洛佩兹(Mireia Aragay&Gemma Lopez)改编作品和原文之间不是一种“线性的历时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共时性”的互动和流变[17]。
罗伯特·斯塔姆编辑的《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与改编艺术》以及他和亚历桑德拉·雷恩格合编的《文学和电影指南》、《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和实践指南》系统归纳了文学电影改编新时期的研究成果。斯塔姆认为改编是“时代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是原文在新的历史坐标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读和重新解释”,而改编作品和文学原著都是”开放的体系”,是在“无限延展的语境中的不断的重塑和重释”,并通过这种重塑和重释形成变化无穷的互文关系[18]。
新千年后的改编研究几乎引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研究理论,再加上其本身的跨学科特征,改编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的文学电影改编,改编研究日益细化、系统化。这不仅避免了跨学科所导致的泛化趋势,还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电影改编研究的深入。
5 结语
系统地回顾文学电影改编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文学电影改编的历史是文学和电影碰撞、交流和互动的历史,而电影改编忠实原文到改编作品独立性的强调再到改编和原文的互动和对话是改编研究发展的主线。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电影的叙事功能被发掘之际,电影就开始与文学联姻了。早期的电影由于技术和艺术手段的限制,始终以文学为学习榜样。因而早期文学电影改编受到戏剧美学和文本中心论的束缚,以忠实原文学文本为终极目标。到了三、四十年代,黄金时期的好莱坞成为了世界电影的中心。这时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以追求利润为电影改编的最终目的,在改编实践中改编者享有较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没有理论的支撑。无论是在商业宣传还是改编电影评论中,“忠实”仍是最基本的标准而戏剧美学仍备受推崇。
二十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电影自身艺术手段和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完善,电影开始寻求与文学平等的艺术地位,系统的改编理论也应运而生。这时的改编和改编研究逐步关注电影自身的特性,文本中心论和忠实改编标准逐步受到挑战。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艺术更加成熟,它的独立诉求也愈加强烈。而随着电影逐步取代文学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导,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也日益加强。电影和文学的互动受到关注,文学电影改编研究日益摆脱了文本中心论和忠实改编标准的束缚。
九十年代后各种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逐步动摇了文本和作者的中心地位,消解了文本的绝对意义。文学电影改编研究也因此从忠实改编的桎梏中彻底解脱出来,文学与电影的二元对立终于得到了解构。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改编研究中文化因素和历史文化语境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改编研究者的逐步达成一种共识,即改编作品、原文学文本和改编语境之间是一种复杂的互文同构关系。新世纪以来改编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改编研究也日益深入。
国际改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我国改编研究始终纠结于“忠实性”问题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回顾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研究的历史,介绍西方改编研究的最新成果,或可给国内改编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助力。
[1]李骏.中西方电影改编之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4,(1):124-127.
[2]George Bluestone.Novel into film[M].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7:3、2、3、42、IX、62.
[3]Keith Cohen.Film and fiction:the dynamics of exchange[M].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4、104.
[4]张冲.改编学与改编研究:语境理论应用[J].外国文学评论,2009,(3):207-218.
[5]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3.
[6]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复原[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41-42、301、4-5、304、310.
[7]Samuel Marx.A Mythical Kingdom: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Wendell Aycock&Michael Shoenecke.Film and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daptation[C].Texas: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1988:30、25-26、32.
[8]Edwarde Murray.The cinematic imagination:writers and the motion pictures[M].New York:Fred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2:5.
[9]Robert Giddings&Keith Selby&Chris Whensley.Screening the novel: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dramatization[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12、XIX.
[10]Horton Foote.Writing for Film.Wendell Aycock&Michael Shoenecke.Film and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daptation[M].Texas: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1988:19.
[11]Brian Mcfarlane.Novel to film: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19.
[12]Deborah Cartmell.Introduction.Deborah Cartmell&Imelda Whelehan.Adaptations:from text to screen,screen to text[C].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28
[13]Imelda Whelehan.Adaptation:The Contemporary dilemmas.Deborah Cartmell&Imelda Whelehan.Adaptations:from text to screen,screen to text[C].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4
[14]Mireia Aragay.Reflection:to Refraction:Adaptation Studies Then and Now.Mireia Aragay Books in motion:adaptation,intertexuality,authorship[C].New York:Amsterdam,2005:26
[15]John Style.Dirk Bogarde’s Sidney Carton─More Faithful to the Character than Dickens Himself.Mireia Aragay.Books in motion:adaptation,intertexuality,authorship[C].New York:Amsterdam,2005:69.
[16]Jose Angel Gercia Landa.Adaptation,Appropriation,Restroaction:Symbolic Interaction with Henry V.Mireia Aragay.Books in motion:adaptation,intertexuality,authorship[C].New York:Amsterdam,2005:181
[17]Aragay Mireia&Gemma Lopez.Inflecting Pride and Prejudice:Dialogism,Intertextuality,and Adaptiton.Mireia Aragay.Books in motion:adaptation,intertexuality,authorship[C].New York:Amsterdam,2005 :201
[18]Robert Stam.Introdu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daptation.Stam,Robert.&Alessandra Raengo.Literature and Film: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C].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