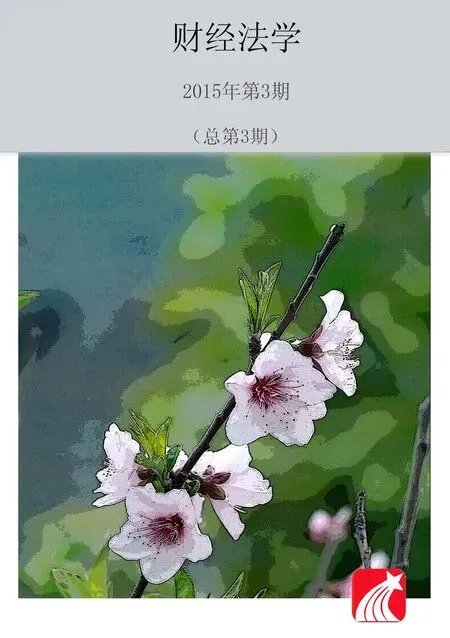从经济惩戒到程序规训
——公务员行政侵权个人责任制的规范分析与制度建构
陈国栋
一、是行政追偿,还是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
从规范上来说,行政追偿制度的价值就是将公务员个人直接作为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对象,将其纳入法治渠道,由其个人承担责任,使其无法经由国家责任制逃逸于法律之外。因此,在实行行政赔偿国家责任制的国家与地区,必须建立相应的追偿制度,否则国家赔偿责任制就会成为古典的英国法治主义者戴雪所批评的保护特权、违背法治的制度。[注][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诚然,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也是法治的体现,但国家终究只是抽象化的拟制主体,缺乏实在的身体和意志去感受法治的制裁。因此,赔偿责任很难给国家行政机关带来训诫之苦并由此实现法律的约束、惩戒、教育与引导作用,纵然有也只是隔靴搔痒。而不管如何,行政职务侵权行为总是公务员做出的。[注][法]让·里维罗、让·瓦利纳:《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13页。但在国家承担行政职务赔偿责任的体制下,公务员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在名义上,公务员并未被明确确立为侵权赔偿义务主体;在程序上,公务员也不作为赔偿事务当事人而参与赔偿程序;在实质上,公务员也不承担金钱赔偿责任。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赔偿法的制裁功能,使赔偿制度不仅作为救火队员还作为巡视员,不仅发挥补救作用还发挥预防作用,就必须在行政赔偿制度中引入追偿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将法律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公务员身上,通过制裁他们来强化、落实赔偿法的法治功能。否则的话,公务员群体就会成为法治不入之地,国家赔偿法之法治功能、控制权力滥用的功能就无从实现。对此,戴雪的同胞哈耶克的一番论断可作为有力佐证:“当今人们责任观念淡漠,要归咎于责任的集体化,而要解决人们责任心淡漠的问题,就必须摒弃责任的集体化,诉诸于责任的个体化。”[注][英]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9-100页。也就是说,依据哈耶克的逻辑,行政职务侵权责任由国家或行政机关这一集体而非公务员个体承担,难以实现责任行政。奥托·迈耶也指出:“如果这些公职人员应为其违法行为而承担个人责任的话,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相对公权力而对臣民的有效保护。这样就使得公权力由其不可或缺的机构出于可理解的顾虑而自行保持在法律轨道之中。”[注][德]奥托·麦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3页。在这里,所谓不可或缺的机构,即指作为公权力机构之组成单位的公务员。一言以蔽之,必须依照合理标准,在公务赔偿领域确立公务员个人负责制,由公务员个人对侵权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此,尽管我国主流学说采国家赔偿自己责任说,[注]参见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但和采国家赔偿责任代位责任说的德国、日本等国一样,[注]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20页;[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页以下。建立了追偿制度。然而,我国追偿制度沦为具文已是不争事实,立法者所设想的“监督公务员依法行政,忠于职守增加其道德感和责任心”、“减轻了国家的财力负担”等目的业已成空。[注]本页注⑤,第127页。面对如此困境,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引入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注]张卫英、王梅霞:《确立我国公务员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那么,我们到底是改弦更张采取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还是内部挖潜、改善追偿制度呢? 对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追偿制与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制度逻辑与规范性内在,比较两种制度各自的优劣,从而决定是改变当前追偿制度而取后者还是坚持前者并完善之。
二、殊途而同源:追偿制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规范性分析
(一)追偿制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之简析
追偿制度的基本构造是:首先,国家对一切公务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公务员并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国家对重过错公务员实行追偿。
与追偿制这种国家履行赔偿责任后再区分公务员是否有重过错不同,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则从受害人追究行政赔偿责任之始,就区分公务侵权行为中公务员的过错程度,进而根据重过错与非重过错之区分,决定是由国家还是公务员个人直接面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公务员存在重过错,那么由公务员个人而不是国家来面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因为不承担赔偿责任,自然无需也不能向已经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务员实施追偿。反之,则由国家面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公务员个人既不承担个人赔偿责任也不承受追偿责任。
最早确立该制度的是法国。1873年权限争议法院佩尔蒂埃判决确定了国家和公务员各自承担公务过错与个人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就是指不履行既定义务的行为。[注]70页注②,第612页。所谓个人过错,或者表现为行为人是一个有着自己弱点、情欲和轻率的世俗人,或者表现为无需评判政府部门一般行为之标准即可断定的过错;[注]同上,第650页。公务过错,则指未达到中等公务运作水平的职务行为。[注]同上,第613页。如果损害是公务员的个人过错所致,那么公务员个人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损害是公务过错所致,那么国家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言之,个人过错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公务过错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相互排斥,国家不可能对个人过错负责任,个人也不可能对公务过错负责任;即使在国家基于公务过错和个人基于个人过错而形成的过错混合侵权情形与责任混合情形中,国家承担全部责任后向公务员个人索赔,也是基于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逻辑。换言之,这种情形下公务员个人依然存在个人赔偿责任。[注]同上,第588-593页。受害人因此得依据私法、通过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以获得赔偿。[注]同上,第654页。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公务员个人责任逻辑。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犯有重过错时,他不再是行政机器的一部分,其行为不属于公共职能范畴,自然不应享受行政法院的保护,犹如在美国没有豁免权的公务员不能享受《联邦侵权求偿法》之豁免保护一样。就此而言,法国的国家赔偿责任纯粹是国家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对公务员的代位责任。
美国联邦政府与法国的做法颇为相似。它一方面通过《联邦侵权求偿法》保护在职务范围内行事的公务员免受追诉和制裁,另一方面则通过确定公务员对恶意、欺诈等行为承担个人赔偿责任而实现对公务员的惩戒。《联邦侵权求偿法》保护过失或失误(fault)[注]我们一般将fault翻译为过错,但过错包含过失和故意两方面,而联邦侵权求偿法将故意行为(intentional act)排除在政府赔偿责任范围外,因此此处的fault显然不是过错的意思,译为失误更为恰当。行为,但不保护诸如袭击、殴打、错误监禁、逮捕、恶意起诉、滥用控告权、造谣、诽谤等故意侵权行为;[注]28 U.S.C. § 2680(h).在其他情况下,比如联邦公务员在侵犯宪法权利或是违反制定法时,除非他具有绝对豁免权,否则一旦被认定是基于恶意,或是并非真诚,或是怀有不适当或恶意目的、或是并非基于合理及理性的基础,[注]John W.Wade. Tort Law as Ombudsman. Oregon Law Review. 1986(65).也要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在总体上,联邦公务员是否能免除责任,要视其有无有限豁免权而定,而其是否具有有限豁免权,则又取决于其行为时是否有故意。[注]实际上,在美国学者眼中,有限豁免与善意豁免是一回事,可以相互换用,因为善意是有限豁免的要件。See Antieau.C.J, Mecham.M.R,Tort Liability of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Employees,John Wiley﹠Sons,Inc,1990.p4。因此,在美国联邦层面,虽然比文斯判决和1871年民事诉讼法第1983节导致赔偿责任分配 “极度复杂、不可预测、经常反复”,[注]K·C·Davis,R·J·Pierce,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Volume Ш)(3ed),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202.但在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是以公务员在公务行为中的过错程度为标准来决定是由国家还是由公务员个人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注]当然,此处的过错也是客观化的过错。比如,在harlow v. fitzgerald(457 U. S. 818 )(1982)中,最高法院认为公务员的主观动机并不重要:“执行裁量职能的政府官员,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侵犯一个正常理性人所应当知道的、明确公认的制定法或宪法所确认的权利,一般而言,都被免予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二)追偿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规范性分析
综上可见,不管是采取个人责任说还是自己责任说,在两种学说下的追偿制度,与法、美等国实施的公务员个人直接责任制,在实体要件上是一致的,即都基于重过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公务员个人责任实现的途径:前者以国家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向公务员实施追偿为途径,后者则以受害人个人直接向公务员个人主张赔偿责任为途径。那么,为什么这两种制度仅仅在程序上存在区别却在实体上一致呢?为什么两种制度下公务员都只因重过错而承担责任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这两种制度下国家与公务员责任分担的标准都在于过错程度?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追偿和公务员个人直接责任制在规范性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公务员对重过错侵权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的方式,都是公平区分并实现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在行政侵权行为中各自责任的方式。两种制度之所以同源而殊途,是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对此,下文将予以分析。本节目的,在于借鉴法国的理论与制度,总结追偿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责任制共同的规范性与法理如下。
首先,不仅公务员作为独立的理性主体而存在,而且国家也被拟制为一个有自我意志的理性法律主体。它虽然是由具体的公务员组成并以公务员作为意志载体的,但它是独立的理性法律主体,同样承载着法律对它的规范。这就意味着,国家要作为自主的主体独立承当对其他法律主体的法律义务。因此,虽然作为国家机关之组成单位的公务员承担这种义务的具体履行,但其作为自然人是不承担这种义务的。
其次,国家也会出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国家作为拟制法“人”,既然是由人而非圣贤、上帝组成,就不可能是全能的上帝这一绝对理性与自由的主体,就不可避免地因为人的有限理性而犯错。也就是说,不管法律设计得如何精美严密,也不可能使得国家不出错。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出错在总体上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预知的客观风险。[注]虽然康德证成了人作为道德主体与理性主体的地位,但康德没有也无法证成人的绝对自由主体地位。在康德看来,至善以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为公设,而人既不能灵魂不朽,也非上帝,因此只能在道德上无限接近至善,却永远不能达到至善。这样,人因为理性的有限性而犯错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3-144页。进言之,从微观的管理过程来看,管理上的出错往往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管理活动过程中人为地偏离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但从宏观制度的层面来看,这种风险仍然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然会发生。[注]也正因为这种不可避免性,在国家而不是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国家赔偿责任具有危险责任的性质。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29页。
再次,国家不会犯重过错。因为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存在,组成国家的公务员不应犯严重的过错,所以国家比一般人更理性,不会犯那种一般人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犯的过错。细言之,虽然现代法律不再如同近代法律那样仅将法律上的“人”定性为理性的“强人”,而是对人进行分类,将之分为“强人”与“弱而愚”的人,[注]参见[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371页。但公务员却不属于“弱而愚”人,他仍然必须承载着法律对他所应具有的、超越一般人理性的期待。因为他们作为具有行政知识与经验的专家,作为现代公正、严格的公务员考试所筛选出来的优秀人才,本身就是“强人”的原型之一:“作为《德国民法典》基础的人类形象,因此就不再是小手工业者或工厂工人的人类形象,而是富有的企业家、农场主或政府官员的人类形象;换言之,就是这样一种人,即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以契约自由、营业自由和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中理智地活动并避免损失。”[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也正因为如此,在界分追偿制度中的一般过错与重过错时,有学者主张结合一般人的注意能力来界定,即公务人员连一般人所应达到的注意程度都达不到时,就构成重过错。参见刘志:《行政追偿制度探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10期。因此,就其预设的理性水平而言,公务员所组成的、作为法律主体的国家是不会犯一般人所犯的过错的。
最后,公务员所犯过错因此可以被归属为不同主体。即,其在公务所允许的出错范围内的一般过错,可被视为国家这一法律人格所犯的过错,而不是公务员作为自然人、作为独立法律主体所犯的过错;而在此之外犯的错,就是个人过错。换言之,在作为国家法人之机关而犯有一般过错时,公务员并不作为独立法律主体而存在,其意志及相应的责任为国家吸收、承担。但公务员要是犯了严重过错,因为这不是作为更高理性主体的国家法人所能为之的,那就只能是作为个人的公务员所犯的错,因此公务员得自我承担责任。[注]我国台湾学者张孝昭也采类似观点。参见张孝昭:《国家赔偿法逐条论述》,台湾金汤书局1987年版,第55页。进言之,虽然公务责任因为公务而来,但因为公务员具有公务身份,国家机关给他赋予的权力使得他具有控制一定公共资源的能力,而他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滥用或不用这种能力时,就使得这种行为在主观上变成了服务于个人目的的违法行为,从而构成了普通侵权行为。[注]德国刑法学提出的义务犯理论,可对此予以解释。即这种义务虽然来自国家身份,但并不因此而免个人之责,个人由此对特定人员或财产负有法定义务,并基于此法定义务而承担刑事责任。同理,公务员个人得由此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不是由国家承担责任。关于义务犯理论的中文文献,参见柯庆仁:《德国刑法学中的义务犯理论》,载《刑事法评论》第24卷。比如,监管人员因为公职身份而负有照顾被监管人员人身安全之义务,但他唆使、放纵牢头狱霸殴打被监管人员的行为,实际上也表明了其侵犯他人人身的犯意;又比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救火任务,但其在可救火之时不管不问,则表明其有故意或间接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犯意。进言之,这样情况下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是他本应当注意之物,而他放纵不管,就足以表明他有破坏的蓄意,放任殴打或是放任灾害蔓延,就变成了他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因此,对这样的行为,要由公务员个人担责。
(三)追偿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之合理性分析
抛开追偿制与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之所以分野的那些因素不论,纯粹从自由主义法哲学角度来说,依照过错程度而分别由国家与公务员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做法,极具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重过错与非重过错的过错二元论,不仅解释了为何可以由公务员个人来承担重过错行政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也从根本上解释了追偿责任的性质,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建构追偿制度具有无可估量的启示意义。
其一,它体现了对公务员自由意志的肯定与尊重。对过错进行区分,将不为公务所允许的重过错归属于公务员个人,表面上是给公务员施加了沉重的负担,但它实际上是对公务员个人作为自由意志主体的肯定与尊重。公务员首先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道德有意志之理性主体而存在的,而不是完全作为国家机关的一分子——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执法机器而存在的。他能作为外在于官僚机器的独立意志主体而存在,他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应该控制自己的行为,在作为机关的组织依法行政之余,仍然要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承担法律义务,并通过控制能力与义务主体地位证明其意志与道德主体之本质,进而作为这样的主体而承担相应的不法行为责任。换言之,若是公务员不对任何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反倒说明他完全不是一个理性主体,失去了为法律所规范的资格。同时,这种制度将公务员的一般过错归属为国家的公务过错而非个人过错,也体现了法律对公务员理性能力的尊重。
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公务员虽被认为是高于一般人的理性主体,但毕竟不是绝对理性的存在,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过错,而这些过错也是他为了公务而不得不犯下的,他因为公益的需要而不得不背负无法推卸的职务责任,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面对可能侵权的风险那样而决定是否退避三舍。[注]有些学者认为,公务赔偿并不完全适用私法领域的雇主责任与企业责任原则,因为国家不是企业,市场竞争并不能驱动政府不做那些导致侵害的行为,政府为了公益必须冒一些风险而不是为了回避风险而不去做某些可能导致侵害的事情。See Stephen G.Breyer, Richard B.Stewart, Cass R.Sunstein, Matthew L.Spitzer,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4th ed), Aspen Law﹠Business,1999,p.813。因此若将公务中的一般过错归咎于他,其实就是将国家基于公益应当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了公务员个人,这就违背了理性法则与自由主义原理,剥夺了公务员作为理性、自由主体之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公务过错可说是公务员作为国家这一法律主体之机关(organ)所应达到的最低标准,达到这一标准就表明其符合公务理性主体之资格,就有资格免于个人赔偿责任。因此,通过这样的有限国家赔偿责任制度,公务员既获得了必要的自由,也受到了法律的必要约束。
其二,它贯彻了现代法制的自负其责原则。[注]关于自负其责原则,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冯军:《刑法中的自我答责》,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自启蒙时代确立人的自由主体地位以来,自负其责就成为现代法制的核心原则,即法律主体应当为自己而非他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不能将责任推给他人。所以,公务过错与个人过错(或一般过错与重过错)的区分既然决定了公务领域责任主体的二元化,那么公务员就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自己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公务员个人直接责任制与追偿制正是这种自负其责原则的体现。
其三,从自负其责原则我们可以推导出追偿责任的代位责任本质。[注]当前主流观点视追偿权为国家机关基于特别权力关系而拥有的内部人事惩戒权(70页注⑤,第129页)。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存在解释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合理性方面也不如代位追偿权。第一,特别权力关系预设了公务员的非权利主体地位,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被破除的今天,将追偿的法理建基于特别权力关系既不合宜,也无必要。而将追偿理解为保障受害人权利而由国家偿付后的代位追偿权,既不妨碍国家基于代位追偿权而提出经济要求、启动经济惩戒的权利,同时也保留了公务员面对此种请求时的权利主体地位,为追偿程序的正当程序化提供了法理根基,实在是一举多得且融贯自洽;第二,将追偿理解为人事惩戒责任难以解释人事关系断绝后追偿权继续存在的现象。如瑞士1958年《公职责任法》第7条规定:如果联邦已经支付赔偿,则联邦对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公务员有追偿权,即使职务关系已经解除也不例外。在人事关系断绝后,就不存在基于人事管理权力继续施加内部惩戒的正当理由。只有在追偿责任不是内部惩戒责任、而只是公务员承担但由国家代位履行后的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追偿权才有不因人事关系的断绝而消灭的法理。如上所述,在自由主义精神与自负其责原则主导的现代法制中,如果某人要为某事承担责任,则必然是因为损害因他而起,责任归咎于他,除非他因为法律的安排而承担代位或连带责任。而且,自负其责的逻辑也决定了代位责任必须配套以相应的追偿制度。同样,如果一行为导致多个主体承担责任,则要么这些责任是连带责任,要么是一主体因为法律的安排而作为形式上的责任主体,另一主体则是实质责任主体。因此,当机关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时,要么是机关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么是遵循法律的安排为他人承担代位责任,而后者又必然要求以追偿制度来贯彻自负其责原则。因此国家对公务员追偿,要么是因为作为连带责任主体在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后追偿连带责任,[注]因此法国没有国家完全责任制下的追偿,只有共同侵权连带责任制下的求偿。不过法国却认为这种求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行使(70页注② ,第592页)。这一做法让人疑惑,因为这显然违背了该国所界定的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与国家所承担的连带之责的内在本质。要么作为形式主体承担代位责任后求偿。总之,追偿责任本质上是公务员个人的责任,是国家承担代位责任的逻辑结果。
综上可见,无论是追偿制还是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其本质都是公务员对重过错侵权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的方式。反过来说,在没有重过错的情况下,公务员个人尽管也会承担其他性质的责任——比如我国所确立的公务员执法过错责任制,但他们不会对非重过错侵权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非重过错责任由国家自己来承担。也就是说,过错程度是区分国家自己责任与公务员自己责任的规范性理由与标准。由此一来,我们可以认定,公务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二元侵权责任主体,即国家对一般过错行为承担自己的赔偿责任,而公务员则对重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进言之,在追偿制下,重过错情况下国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都是代位责任,而非重过错情况下国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都是国家自己责任。
三、同源而殊途:两种责任制的自优劣及启示
如上所述,个人赔偿责任制与追偿的规范性、制度逻辑及实体要件本属一致,它们都是公务员个人就其重过错行政侵权行为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方式,都体现了对公务员的尊重;所区别者,不过是国家是先行赔偿再追偿,还是国家不管,任凭受害人自行向公务员求偿。但是,最好的办法是这种法国、美国式的无追偿而由公务员与国家各自直接负责的做法,还是“将责任强加于政府并给予政府通过追偿诉讼或惩戒性程序来起诉公务员”?[注]Stephen G.Breyer, Richard B.Stewart, Cass R.Sunstein, Matthew L.Spitzer,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Aspen Law﹠Business(4th ed),1999,p.814.换言之,为什么两者规范性基础一致,但却又同源而殊途呢?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两种制度同源而殊途的原因所在,从而为选择并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中的公务员个人责任制提供参考。
(一)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优点
其一,它能更为有力地实现法治。是追偿还是由公务员个人直接承担重过错行为的赔偿责任、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法治,在美国曾掀起持久的争论。虽然诸如戴维斯这样的学者认为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纪律惩戒以及追偿能更好地督促公务员审慎运用权力,[注]Kenneth.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 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7,p.493;Kenneth F Warren,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3rd ed),Prentice-Hall, 1996,p.486.但其他学者和法官并不赞同,认为这既缺乏文献支持,也不符合美国人事管理制度之现状。如布伦南法官认为,证据显示,由受害人直接对公务员提起诉讼比通过联邦侵权求偿法向政府求偿更有效,它对合众国起到了更有效的制约作用。[注]Carlson v.Green,446U.S.14(1980)。布伦南法官认为,对联邦公务员提起诉讼,除了惩戒方面的优势外,还因为这样做可以提出联邦侵权求偿法所不允许的惩罚性赔偿,可以请求陪审团,并拓宽了救济渠道,创设非正式的救济方式,使得被州法所允许的合法侵权行为能得到联邦层面的救济。考虑到美国对联邦公务员的保护,肯尼斯·沃伦对布伦南法官的观点更为认同。[注]本页注③第2个文献,p.487。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法官之所以通过诸如比文斯这样的案例来确定公务员个人的赔偿责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文官制度对公务员形成强大的保护,以致除了以普通法侵权诉讼的形式来实施惩戒,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惩戒办法。
从根本上来说,追偿的制度困境根源于一个古老难题:体系内部的监督如何能够有效实现。追偿是由赔偿义务机关启动并操作的,因此从属性来说属于内部监督、问责。这种内部监督属性决定了追偿在落实法治这一层面要远逊于由重过错公务员个人直接面向受害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做法。的确,对于赔偿义务机关来说,在没有强大外力制约的情况下,启动追偿对他来说只是在履行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义务,而不意味着现实可见的利益,而且追偿失败反而会造成被追偿的公务员与其所属行政机关离心离德,因此,行政首长通常在惩处自己的同事时总是犹豫不决的,[注][法]夏尔·巴里什:《行政科学》,施雪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行政机关也总是不愿意落实代位责任。[注]法国行政机关总是基于共同侵权的逻辑而承担连带责任,但却很少落实因此而生的代位求偿权,结果引发老百姓的不满。参见70页注②,第591页。
而将公务侵权行为区分为重过错行为与一般过错行为,并规定受害人只能向有重过错的公务员求偿,则将追偿变为求偿,从内部监督方式转换为外部监督方式。从此,不再是行政机关对其系统之内的公务员进行监督,而是受害人基于权利逻辑对公务员进行外部监督。为了救济自己的权利,受害人必然有足够的动力与信念对重过错公务员展开坚定、持续的监督,由此公务赔偿制度的法治维度得到有效实现,公务员也由此时刻置于公民监督之中。因此,从监督原理上来说,公务员个人直接承担重过错侵权行为的责任,实际上是“权利制约权力”逻辑的体现,其要义就在于以受害人的求偿权来制约公务员的行政权,从而避免了内部监督难以实现的困境,而不是像追偿制度那样,以受害人的求偿权来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再由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去制约公务员的行政权,由此陷入内部监督困境。
其二,它更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一是财政利益。如果由国家对一切公务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后对重过错公务员实施追偿,那么国家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风险:公务员无钱可赔或是追偿决定机关不愿意让公务员赔。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构成对国家财政权益的侵害,进而构成对全体纳税人乃是全体国民的损害,因为国家公共财政利益的受损意味着国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利益受损。因此不追偿也有损民主价值。所以,由公民直接向重过错公务员求偿,而不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能够有力地维护国家财政利益。二是政府形象。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然后追偿的情况下,在受害人以及其他公民的心目中,是政府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公务员侵犯了公民权益,公务员反而借由追偿制度置身事外。因此,政府的廉正形象(integrity)不免受损。[注]Carlson v.Green,, 446 U. S. 14 (1980).反之,由公务员个人直接面对受害人承担责任,政府就可以置身事外,避免形象受损。
其三,它有力地规避了赔偿义务机关因追偿所要面临的管理风险。对公务员进行追偿,意味着赔偿义务机关实际上和公务员之间处于对立、对抗位置。如果追偿程序高度正当程序化,追偿机关因此能够充分听取公务员意见,充分尊重公务员利益,并在符合法治的前提下使公务员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那么追偿不会产生公务员对追偿机关的怨怼;如果追偿程序并不正当程序化,或是正当程序化的追偿失败因而追偿并不能使公务员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情况下,追偿反而可能使自认被无辜问责的公务员对领导、同事心怀不满,与其所属机关离心离德。这样一来,机关内部的团结与协作气氛会被破坏,被追偿公务员与其同事、领导一起共事时就会效率低下、效果不佳。因此,从管理效益的角度来看,由赔偿义务机关来追偿具有相当的不合宜性,因为它会严重地影响通过官僚等级制权威行使的控制和指挥,并使上级和下属间的敌对关系扩大化。[注]罗森布鲁姆指出,内部问责会加剧机关内部的对抗,不利于机关上下一体的团结行政。David H.Rosenbloom, Robert S. Kravchuk, Public Administration:Uderstanding Management,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6th ed),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p.245。相形之下,由受害人直接向公务员提起诉讼这样一种让侵权法充当监察专员的方法,[注]71页注⑧。既比较好地保证了法治程序的公正性,也使行政机构无需面对追偿这样一种内部问责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还转移了追偿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二)追偿制的优点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法国与美国联邦的做法能够更好地实现公务赔偿制度的法治功能而不让重过错公务员逍遥法外,但这种制度也同样面临着种种争议,有着追偿制度所没有的不足;反过来说,追偿制度在如下两个方面却具有公务员个人重过错公务侵权责任制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一,追偿制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权利。美国学者戴维斯强烈要求国家对一切公务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反对公务员个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这样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因为公务员可能比较贫穷,没有能力履行赔偿判决;而民事侵权诉讼中的法官和陪审团也可能因为出于对履行公务却要个人承担责任的公务员的同情,而做出有利于被告公务员的判决,并降低损害赔偿的额度。[注]K.C.Davis、R.J.Pierce,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Volume Ш)(3rd ed),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206.的确,保障受害人人权是我们在建构重过错公务员侵权责任制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国家赔偿法首先是人权保障法,是保护受害人人权的法,决不能为了落实公务员的个人责任就将求偿的风险转移到风险抵御能力微弱的受害人身上,使得受害人在历经艰难的求偿诉讼后即使胜诉也难以切实实现权利。在这一点上,实施追偿制度,由拥有雄厚财力、也更有能力和受害人达成妥协的国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再追偿,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人权。
第二,更有利于保护公务员人权。尽管由公务员直接面临因重过错侵权行为而生之损害赔偿之诉符合自由主义法哲学,但公务员毕竟是在执行公务时犯下的过错,而且,公务员是否具有重过错是在诉讼中认定的,因此,在重过错还未认定时就由公务员个人来面对受害人向其提起的求偿诉讼,就必然使得公务员要承受超出赔偿金之外其他沉重负担:时间、精力、诉讼费用以及心理压力。[注]United States V. Gilman, 347 U. S. 507 (1954).因此,由公务员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利于保护其人权。同时,这种做法也不公平。这等于说,公务员为执行职务惹上官司,还要以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诉讼,去承担明断是非曲直的诉讼成本,而国家则可以隔岸观火、不费司法成本就能知晓最终结果。因此,以发明侵权法上“汉德公式”而闻名的汉德法官就主张,不管公务员处于何种情形,都应该享受完全豁免,免予个人赔偿诉讼的侵扰,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那么“只有到案件完全审理完之后,才可能知道原告的主张是否完全成立。而所有的公务员,不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却都要承担受审的责任并面对案件结果那种惯常的威胁,这会挫伤公务员大胆地执行其职务时的热情。”[注]Gregoire v. Biddle,177 F.2d 579,581 (2d Cir.1949).Cf Alfred C.Aman,William T.Mayton. Administrative Law, 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2,p.542.也正是因为由公务员个人面对求偿诉讼不够公平,所以,为了保护公务员,施行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法国总是以共同侵权的名义、以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先替公务员承担赔偿责任,而且事后还很少追偿。[注]70页注②,第591页。换言之,尽管法国制度理论上能够更为有效地落实公务员个人责任,但为了保护公务员,为了管理效益,国家还是通过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帮助公务员规避其个人在程序与实体上的风险。因此,实施追偿制度,由国家作为赔偿诉讼的被告来承担责任而公务员承担追偿责任的话,公务员的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三)一点启示:设计兼顾责任追究与权利保障的公务员个人责任制
综上可见,在一个韦伯所言的诸神反复争斗的价值多元世界里,决定直接赔偿责任主体是公务员还是国家,公务员的个人责任是通过直接责任制还是追偿制来实现,不仅要基于行政侵权行为所体现的自由意志,不仅要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与管理效益,还要综合其中所涉另外两方主体即公务员与受害人的利益与价值追求。而在其中,落实公务员个人责任、保障国家财政利益等价值与保障受害人、公务员权利等价值存在着紧张与冲突。也正是因为对各种价值、利益的权衡与取舍上的不同,才出现了追偿与公务员个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这两种实体要件相同但程序不同的追责制。
应该说,面对上述各种价值与利益,难说有一个明确、清晰而合理的权衡与排序标准。到底采取何种制度,取决于立法者及其所处的各种制度乃至文化环境,因此很难说哪种选择更为合理,哪种选择缺少合理性。即使是在同一法制体系乃至法治文化里,也有不同选择。比如,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就没有采取联邦政府的做法,而是规定由州对公务员承担雇主责任,州公务员承担追偿责任。其责任区分的标准是公务员行为是否具有“欺诈、腐败与恶意”,即是否有重过错。[注]West’s Ann.Cal.Gov.Code,§§825.4 and 825.6.这得到了戴维斯的肯定与支持,认为是其他州法以及联邦法的效仿榜样。[注]Kenneth.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Text. 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7,p.493.
然而,也正如前文对两种责任制优劣的分析所显示的,在这个价值多元世界里,基于不同的价值排序,不论哪种制度,它在保障一些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另一些价值被牺牲、不能有效实现的窘境:如果要充分实现法治,落实公务员的经济责任,那么受害人权利、公务员权利就难以充分保障;如果要充分保护受害人权利、公务员利益,那么法治就难以充分实现、公务员个人经济责任就难以落实。一言以蔽之,保护受害人权益与管理价值、法治处于深深紧张之中,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寻求得完美的法则来实现所有目的,而只能接受一些价值被更好地实现,而另一些价值不能有效实现的现实。
反过来说,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无论为优先实现哪些价值而确立哪种制度,都意味着该制度必须适度尊重并采取可行措施以便争取能多实现另一些价值,否则它的正当性就存在重大欠缺。因此,我们必须带着镣铐跳舞,设计尽可能兼容多重价值的公务员个人责任制。
四、两全权利保障与责任追究的追偿:从经济惩戒转向程序规训
如上所述,无论是追偿制,还是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点与不足。相较而言,采取追偿制度来落实公务员个人责任制并完善之也许更为适合我国。首先,我国国家赔偿法业已确立追偿制度,短期内修法改弦更张,采取法、美等国的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不太可能。其次,即使是采取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的法国,为了保护公务员与受害人,其制度也无法真正得到落实,从而面临与追偿制度一样的窘境。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公务员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无法有效保护受害人与公务员,而追偿制在保障受害人与公务员的同时,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完善而有效实现其规范功能。因此,与其去建构一个无法保障其实效的新制度,不如内部挖潜,完善行政追偿制度。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弱化其经济惩戒色彩以减轻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抵触之心,强化其程序规训功能,实现追偿从经济惩戒向程序规训的转变,使之能够尽可能两全权利保障与责任追究,从而落实其作为公务员个人责任制之责任追究功能。
(一)为什么要从经济惩戒转向程序规训
为了保障人权,我国立法者没有选择公务员个人直接对重过错公务员侵权行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而是选择了追偿,这样就将以管理价值为主要目标的赔偿义务机关置于法治与管理价值的紧张之中。而在看不到追偿的显著效益且追偿还会负面影响管理效益的情况下,掌握追偿决定权的赔偿义务机关根本就没有多少主动启动并落实追偿的动力。这是追偿制度实施不力、法治功能不彰的直接原因。
因此,为落实法治功能,追偿制度建构的首要关键,并不在于追偿程序的正当程序化——当然这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于尽可能地调动追偿机关的追偿积极性的同时尽量限制追偿机关不追偿的裁量权,在强化追偿的法治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地削弱追偿对管理效益的负面影响。
破题的关键在于转换视角、改变方法,即保留并弱化追偿作为实体制度的经济惩戒功能,突出并强化追偿作为程序的规训功能,通过程序的规训功能来实现追偿的法治功能。换言之,追偿制度的经济惩戒面向可以减免、弱化,但追偿程序的规训维度要强化,从而主要通过追偿程序而不是追偿责任本身来尽可能实现公务赔偿制度的法治功能。弱化经济惩戒或许有违追偿制度的本义,也会减损追偿制度之维护国家财政利益的价值维度,但在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或许这是为了保障权利、落实法治与管理效益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注]许多国家封顶追偿金额。如加拿大规定,公务员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所承担的追偿责任不得超过250加元。捷克则规定:“除非劳动法有特别规定,除非过错系被追偿人故意,国家求偿额原则上不超过已赔偿额的1/6,1 000克朗为最高额。”俄罗斯联邦也规定:“致害公务员赔偿数额不得超过其月工资的1/3,法院确定其违法后,责成其交付该损害赔偿诉讼的诉讼费。”转引自谢祥为、叶雨:《国家追偿标准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2期。但反过来说,正因为经济惩戒弱化,所以才更要加强程序对公务员的规训,否则就会损害追偿制度的公平性与法治功能。
细言之,一方面,要保留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而不是刻意追求实现追偿的经济惩戒功能与补偿功能。之所以要保留追偿制度,是因为追偿的实体维度是程序维度的基础,是赔偿义务机关启动追偿程序的权力来源所在,也是赔偿义务机关激励公务员配合追偿程序、以更为积极理性诚恳的态度接受程序规训的后盾。之所以要淡化,是因为强化经济惩戒只能是和赔偿义务机关所追求的管理效益直接对撞从而致使追偿难以启动,因此要以这种妥协来降低公务员对追偿制度的抵触,换取其对追偿程序的配合,进而换取赔偿义务机关启动、操作追偿程序的积极性。因为不以可见、可量化的剥夺经济利益方式来落实惩罚,公务员、赔偿义务机关对追偿程序的抵触之心必将降低一些,追偿程序之规训功能才可以尽量发挥。
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并加强追偿作为程序的规训功能。追偿制度的法治功能不仅体现在作为结果的追偿决定,还体现在作为过程的追偿程序本身。正如美国诉吉尔曼案(United States V. Gilman)中联邦法官所宣称的,对公务员启动法律问责程序本身就是惩戒,追偿制度的实施过程本身是一个对公务员本人个人意志及道德进行审判追究的过程。因为追偿在实体与程序上具有分离性,即公务员在实体上可能不会被追偿,但只要启动追偿程序,那么公务员就会通过这一程序被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至于成为法律的化外之民。通过追偿过程,他接受了法律的评价、教育与引导,能够因此更好地领悟如何执法才是合法合理的。因此,追偿不仅具有结果的惩罚价值,还有过程的规训价值;不仅具有结果维度,还有过程维度。追偿过程本身就是公务员被规训的过程。
(二)制度建构的基本方向与思路:尽可能糅合赔偿程序与追偿程序
要落实追偿制度的程序规训功能,首要之处在于限制赔偿义务机关启动追偿程序的自由,否则,连追偿程序都不启动,何来追偿程序对公务员的规训?笔者认为,在现行追偿法律体制下,尽量糅合赔偿程序与追偿程序,通过赔偿程序来实施追偿,让追偿程序的启动尽量不以机关意志为转移,可以很好地能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要放弃那种赔偿程序与追偿程序是前后两个阶段的观念,尽可能地在赔偿程序中一并解决追偿问题或尽量在赔偿程序中实现追偿制度的功能。笔者认为,基于如下两个理由,这是完全可能的。
1.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在程序上存在重合性
追偿必须以赔偿为前提仅仅意味着,追偿只是赔偿的可能结果,赔偿并不意味着一定追偿。因此,在结果意义上,赔偿和追偿存在分离的可能,即有赔偿但无追偿。但在程序上,则存在着两者合一的可能,即赔偿与追偿在某些环节和步骤上可能合一,赔偿程序既可以决定是否赔偿又可以决定是否追偿。一方面,从追偿的制度价值来说,不管最终追偿的实体结果如何,追偿作为责任追究程序是必须启动进行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查清到底是国家自己责任还是公务员个人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对公共资金的使用有所交待,所以追偿程序是赔偿的逻辑衍生物,两者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追偿的某些实体要件是可以通过赔偿程序来确定的,即追偿的实体要件——重过错。
2.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在功能上存在一致性
如前所述,追偿的惩戒与规训功能既通过追偿金额来体现,也通过追偿程序来体现,追偿具有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而且,因为程序剧场化所带来的规训效果,[注]关于程序的剧场化效应,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追偿程序的规训效果比单纯的追偿金额更强。因此,从追偿的程序维度与规训价值来理解,凡是发生于赔偿程序过程且让公务员感受到法律之惩戒与规训功能的赔偿程序,就是追偿程序。比如,赔偿以公务员存在违法性和过错为前提,因此认定赔偿责任之违法、过错要件是否存在的程序,其实就是一个考问与训诫公务员执法水平与道德良知的追偿程序。
基于二者在程序上的重合性与功能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将赔偿制度与追偿制度融合起来,利用现行的赔偿程序来进行追偿,进而将内部问责式追偿程序变为外部程序。这样做,具有如下意义:
1.可以解决内部问责式追偿程序难以启动缺乏启动动力的问题
将赔偿程序与追偿程序结合起来,由赔偿程序带动追偿程序,其实就是变相剥夺和限制行政机关启动追偿的裁量权,将追偿的权利交给了赔偿请求人。这样就有效解决了赔偿义务机关追偿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这一安排,一旦赔偿程序启动,相应的追偿程序也就随之启动,与赔偿责任相关的公务员就必须进入赔偿程序,来接受相应程序所带来的考问与训诫。
2.可以避免或减少内部问责式追偿程序对管理效益的负面冲击
在单纯地将追偿视为经济惩戒的观念与制度中,追偿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赔偿义务机关。如前所述,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赔偿义务机关推向了被追偿公务员的对立面,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内部的不合,进而导致管理效益的降低。而经由制度设计,将追偿糅和于赔偿程序之中,由赔偿程序来启动追偿程序,给公务员一种是由受害人启动追偿程序而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启动追偿程序的感觉,就可以避免被追偿公务员对追偿义务机关的不满,从而降低追偿制度对管理效益的负面冲击。
3.强化追偿的规训功能并避免内部问责式追偿程序公正性不足的问题
只有将追偿与开放公正的程序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追偿的法治功能,最小化由赔偿义务机关所操作的追偿程序的反法律意义。因为追偿是赔偿义务机关所操作的,且传统上这一程序被视为内部程序,因此这一程序客观上必然具有人事惩戒的味道,等于是变相地授予了机关领导新的人事惩戒权。如果这一程序不公正,那么它就只能从本质上的法律程序变成反法律的纪律惩戒程序。[注]See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9,p.223.反之,如果它和赔偿程序尽量合为一体,则可以使之从以往的人事纪律维护程序变成法律问责程序,减少人事管理权力对于公务员的压迫意义上的训诫意味,实现法治的柔软化,并有效地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换言之,如果机关内部的法律问责制不通过公正程序来进行,那么内部法律问责制就会沦落为单纯的人事纪律问责制,就会沦落为反法律,从而违背问责本应该遵守的法治原则,并因缺乏开放、反思、公正性而变得机会主义,成为上级恣意打压下级的工具。因此,将追偿程序与赔偿程序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解决追偿的救济问题。如前所述,追偿是一种代位求偿制度,追偿义务机关只有要求但无强制公务员交钱的权力。但我们的制度对此语焉不详,法院对此是否可以救济、该如何救济也同样语焉不详,加之主流学说认为其是内部人事惩戒制度,倾向于认为其不为行政诉讼法所调整,因此一旦行政机关强制实施追偿,被追偿公务员将求救无门。因此,我们将赔偿程序与追偿融合起来,至少可以因为赔偿程序的公正性而保障追偿在过错认定方面的公正性,保障追偿金额之基数——赔偿金额确定上的公正性。其中关键在于,利用先行程序、赔偿诉讼程序,我们可以把机关、公务员和受害人、甚至法院引入到程序之中,使原本封闭的程序变成开放、反思的程序,实现规训程序的理性化。
4.可以实现受害人的报复正义与情感抚慰要求
将追偿程序与赔偿程序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实现追偿的外部化与公务员吏治管理的公共化,还可以更好地满足受害人的报复正义要求。这是因为,受害人因此得以通过参与赔偿程序而参与追偿程序,直接参与对公务员的责任评定过程。这就在形式上给予了受害人实现报复正义、发泄其怒气的机会。同时,通过赔偿程序来进行追偿,确定公务员的责任,可以让受害人直观地感受到国家惩戒公务员的诚意和对他们情感的尊重。
5.促进赔偿纠纷的更好解决与公务员责任心的增强
一方面,受害人通过赔偿程序来参与追偿程序,使得公务员能够更加直接、直观地感受受害人的痛苦与愤怒,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其行为上的瑕疵、不足与错误。这不仅会促使公务员真诚地向受害人道歉悔过,满足受害人的情感需要,从而更好地了结赔偿纠纷,还会促使公务员提高执法的责任心与水平,尽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即使公务员没有重大过错,不能被追偿,这样做也一样可以起到促进公务员反省的效果。有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另一方面,只有基于正当程序,通过尽可能地听取并回应被问责公务员的意见和申辩,才能更好地通过规范、公正的程序和合理的依据对公务员的主观状态进行反复的剖析与考问,才能让公务员在庄严的场合、隆重的仪式与规范化的交涉中,在开放、反思而反复的程序对抗中审视自己的主观状态上的不足,切实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理性的要求。这必将有力促进他们改过自新,实现追偿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也就是说,正当程序化的追偿更具有教化功能。
(三)相关制度的建构
第一,在赔偿程序上要进行相应改革,设定侵权公务员之赔偿程序中第三人法律地位。无论是先行程序还是赔偿诉讼程序,都可以允许赔偿请求人将侵权公务员列为第三人,赔偿义务机关得要求侵权公务员参与程序,[注]如中国台湾“国家赔偿法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以书面通知为侵害行为之所属公务员或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个人,或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而就损害原因有应负责之人,于协议期日到场陈述意见。法院得发出传票传唤侵权公务员参与诉讼。公务员自己也可以主动要求参与程序。其实,公务员本身就应该享有诉讼中独立第三人地位。其一,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直接和公务员的经济责任紧密关联,因此,为了避免赔偿责任延及己身,公务员自然拥有参与诉讼、行使抗辩权的权利。其二,赔偿诉讼必然要对职务行为的有责性即过错进行认定,这种认定因为程序的权威性而要作为内部行政处分之依据。[注]如奥地利先公务员惩戒程序再赔偿诉讼程序,赔偿诉讼程序以惩戒程序为前提。该国《国家赔偿法》第12条规定:国家损害赔偿之诉,取决于公务员惩戒程序之结果的,法院得于审判期日开始之前依职权或依申请中止诉讼程序,至惩戒结果确定后,继续审判。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公务员惩戒程序高度法治化且具权威性,而我国目前恰恰缺乏这样的制度,因此,将这种赔偿诉讼程序制度移植入我国难以发挥效用。
第二,赔偿制度在实体上要以过错为归责原则。无论是在先行程序还是在赔偿诉讼程序中,都需要讨论公务员的过错。法官应当积极引导参与诉讼各方就过错程度进行讨论,并在判决文书中认定过错程度,并说明理由。
第三,公务员仅仅对于法定范围和标准的赔偿责任承担追偿责任,但对超出此范围的补偿不负追偿责任。同时,和解程序中若存在着基于定性不清的事实的赔偿决定,公务员对这种基于不确定事实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承担追偿责任。
第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制度化法院的司法建议职能。应当允许求偿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就侵权行为所体现的过错程度请求法院进行主动审查。法院也可以主动进行审查,并就相关证据听取侵权公务员意见。应该说,这在技术上并不构成重大障碍,因为法院也必须对侵权行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审查。
第五,发挥民主代议制机关对追偿资金的监督功能。立法机关或上级机关应当就赔偿资金的使用进行审查,看有没有至少启动程序层面的追偿,监督行政机关去落实追偿程序,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立法机关或监察机关说明赔偿金额、不追偿原因以及启动追偿程序之后的结果等。[注]相近观点,参见王兆鹏、陈长文:《应求偿而不求偿——揭开司法机关赔偿五亿元的黑盒子》,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9年第5期。
第六,制定关于追偿占赔偿金额比例的裁量基准,限制行政机关对追偿金额的裁量权。当前,我国已经有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有关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对追偿的标准与额度作出了规定,[注]相关立法的梳理,参见谢祥为、叶雨:《国家追偿标准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2期。但还应该更加具体一些。具体而言,赔偿义务机关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裁量追偿金额:平时表现好的就少赔,反之则多赔;公务员积极主动参与赔偿程序的,能降低影响、减少损害的,认错态度好、反思深刻、教训总结好的,能取得受害人原谅的,少赔,反之则多赔;故意侵权的多赔,重大过失的少赔。
五、结语
吏治整顿向来是政府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也是国家社会治理体制能否有效运转的关键之一。它不仅需要疾风骤雨、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或运动,更需要体系严整、执行有力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更需要防微杜渐、惩戒那些不构成贪腐但违法乱纪的行为。然而,吏治一般来说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事务,这就给了公务员逃离法律规训、脱离人民权利之规范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吏治总是难以取得有效成果。而公务侵权赔偿制度中公务员个人责任制则提供了一种将公务员纳入规范化、外部化的问责机制的途径,也就给吏治整顿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
基于权利规范行政的逻辑,个人直接赔偿责任制能够更为有力地约束公务员,但有可能因此而导致受害人权益无法实现或因此而导致国家与公务员之间不公平的责任与风险之分配。追偿的这种规范功能相较而言稍弱,有因为内部监督之痼疾而落空的风险,但只要将赔偿程序与追偿程序关联起来,就依然可以依托公民主观权利之逻辑,通过其对赔偿程序的启动来启动追偿程序,进而实现追偿对公务员的规训。可以说,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追偿制度,为公民启动对一般公务员的法制问责,开辟了一条具有较高确定性的通道。因此,作为过错认定机制和责任追究程序,追偿应当在这个时代积极发挥其作用。这不仅为了民主,也为了法治与社会正义。进言之,追偿程序必须启动并进行——虽然它本身是需要改革的,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是不完整的,法治也是残缺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身处价值多元世界的追偿,反过来也可能会对行政管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当追偿纯粹沦为内部监督时其实施不力的主要原因。即,追偿通过经济惩戒的逻辑惩戒公务员,导致了赔偿义务机关为了其管理效益而不积极实施追偿。因此,我们需要设计精妙的追偿制度,尽可能地协调各种价值。相应地,我们需要加深和拓展对追偿的认识。我们需要认识到追偿不能仅局限于追“偿”,即侵权公务员对国家所承担的代位责任的偿还,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对公务员的执法水平、能力与责任心进行审查,确定其行政责任、道德责任,从而实现法制的规训功能;追偿功能不仅体现于追偿金额,更体现于程序与过程,因此尽可能地发挥程序意义上的追偿,通过程序来发挥追偿的规训价值。因此,我们不妨弱化行政追偿的经济惩戒属性,强化其程序规训功能,实现行政追偿从经济惩戒到程序规训的转化。
细心读者会发现,本文主要以行政赔偿制度中的追偿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司法赔偿制度中的追偿制度着墨不多。的确,鉴于司法行为与行政职务行为受法律规范的程度不一样,司法人员与行政机关公务员受法律保护的机制与逻辑不一样,司法赔偿与行政赔偿所牵涉的价值及其权重不一样,因此司法赔偿中的追偿制度与行政赔偿中的追偿制度很不一样。[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6条与第31条。但是,在价值多元的世界,司法赔偿中的追偿同样深深地内嵌于其中,受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的制约,因此其制度设计必然和行政赔偿中的追偿一样,要尽可能地兼容各种价值并安排不同权重。因此,本文提出的一些结论或许同样适用于司法赔偿中的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