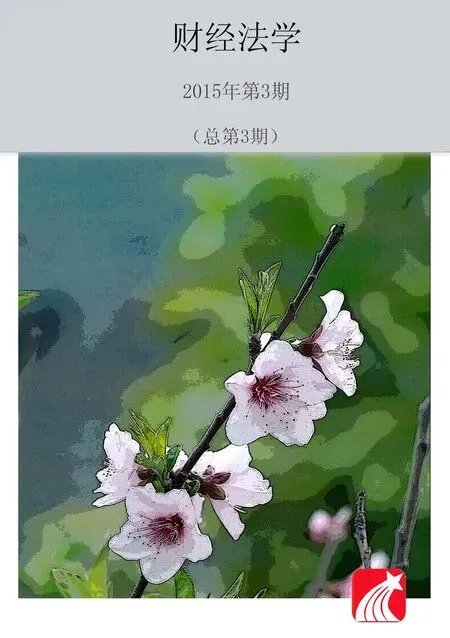合法行为的规范体系问题
——以民法学为考察领域
常鹏翱
KeyWords: Legal Act;Illegal Act;Norm System;Legal Fact;Norm’s Component
一、引言
我国大陆民法学理向认为,进入民法视野并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动举措,如买卖、结婚等,就是在法律事实中与事件对立的行为。[注]参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1957年版,第16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6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183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版,第34页。这意味着,在民法学中,行为是规范机制作用下的产物,并非人的所有的行动举措均为行为,只有通过民法标准过滤的,才能升格为行为。这种升格标准主要有:(1)有意识的或可为行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行动举措,用德国民法学理的话来说,就是主体有认知理解其行动举措的识别能力(Erkenntnisfaehigkeit)以及控制该举措的意思能力(Willensfaehigkeit),这为主体承受行为效果提供了最根本的正当性根据。[注]Vgl. Pawlowski,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 Heidelberg 2003, S. 87 f.据此,行为以主体有意识或受意识控制为决定要素,睡眠、麻醉等无意识的举措,以及不由意识决定的、完全受制于外力直接强制作用的举措,如被强摁着签合同,就被排除在外。[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2)有被民法调整的意义,能产生民事法律效果,这就排除了散步、读书之类的行为,德国同样如此,如为反对啤酒涨价而举着标语在大街上奔跑示威、邀请熟人到家里喝酒等行为均无民法意义。[注]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在符合这些标准限定的前提下,行为在学理中呈金字塔架构,以德国、瑞士、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德国法系通常以是否合法为基点,分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两大类别,前者包括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后者主要具体化为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我国大陆民法学理也有这种分类。[注]参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1957年版,第16页;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6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版,第34页。这五种下级行为并非神经末梢,它们各有更细致的分类,如法律行为有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侵权行为可细化为过错侵权行为、违反保护性法律行为与违反善良风俗行为。[注]德国的情况,参见Siedler, Zurechnung von Realakten im Buergerlichen Recht, Hamburg 1999, S. 112 f;[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64页。瑞士的情况,参见Gauch/Schluep/Schmid, 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 9. Aufl., Zuerich 2008, S. 27 ff;Honsell, Schweizerisches Haftpflichtrecht, Zuerich 2005, S. 25 ff。台湾地区的情况,参见黄立:《民法总则》,2005年修订4版,第189-194页;王泽鉴:《侵权行为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294页。通过上述的层层分级,民法中的行为规范有了体系架构。
不过,在我国大陆民法学语境中,该体系看上去似乎逻辑并不周延完整,疑问时有发生,比如,既然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对立,那么,违法的法律行为为何仍留在合法行为序列?又如,侵权行为与事实行为结构类同,为何它们分属不同类型?这两个常见的悖论问题直指行为分类的基点,若不能妥当解释,该体系势必岌岌可危。再者,属于违法行为的违约与侵权界分清晰,学理对二者异同、竞合等规范关系的讨论相当充分,但合法行为却非如此,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事实行为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要约邀请是意思表示、准法律行为抑或事实行为的困惑即为适例,[注]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2版,第39页。它们之间的规范关系也未见有充分讨论。
这些问题究竟是合法行为的规范体系结构本身,还是属于对该体系的认知问题,值得认真讨论。若为前者,则划分不清表明德国法系的行为体系逻辑自身有问题,要么应再审视体系基点和分类标准,要么行为在整体上应是平面构制,各类行为虽独立但无层级。若为后者,就应阐释体系架构的基本原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在揭示并解释问题及其原因到底何在时,本文先从德国法系民法学理入手,力图潜入其中把握合法行为归类的认识脉络。正是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本文发现行为尽管源于并最终在法律适用中指向现实的具体行为,但定位出发点是将它作为在法律规范构成中引致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由此出发,本文针对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基本区分,从厘清生活事实、法律事实和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入手,特别强调行为的规范意义,从构成要件这一规范层面来确定行为属性的判别标准(第二部分)。这意味着本文着眼点是行为规范及其学理认识,由此展开规范分析,至于客观存在的具体行为形态及其构造要素,如行为人意图、实际后果等并不在关注范围。在厘定行为最基本的区分后,应予辨析的合法行为的内部界分问题,思路仍然未变,即在构成要件的平台上,分析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事实行为相互间的关系(第三部分)。
二、行为合法或违法的标准
(一)行为的意义层次
民法总论著述之所以把合法或违法作为行为的基本划分点,不外乎以归类手法理顺引致法律关系得丧变更的行为类法律事实,从而便于法学理论的归类探讨和法律规范的体系编排。这里的逻辑起点是“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是受法律规整的生活事实,特点在于具体性和事实性,即发生于或者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的事实,[注]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顺此逻辑进展,行为对应的是诸如雇用合同、伤害他人等受民法调整的具体行为。个案的具体行为在法律秩序中受合法与否的评价后,就是意义特定的客观存在,如雇凶杀人和恶意伤人均为违法行为,只要该定性确定,就不能回转为合法。这意味着,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在此凸显的是“法律事实”和“合法违法”的符号价值,它们对具体的生活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性质界定,行为因此有了合法或违法的本质区别。
尽管法律事实指向具体的生活事实,但它是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坐标所得到的定位,隐含了法律适用的动态过程,比如,伤害他人的个案行为是否侵权行为,既要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应规范来考察该行为的具体情节构成,又要看该行为本身与这些规范构成要件是否相符,只有在个案行为符合这些规范构成要件时,伤害他人才能成为作为法律事实的侵权行为。换言之,法律事实虽然最终落脚于作为法律适用小前提的生活事实,但左右它的、与其形影不离的是作为大前提的构成要件,这二者的意义相互约束,一个变化必将导致另一个变化,由此,忽略构成要件来定性法律事实,后者的意义必将陷于不确定。仍以伤害他人为例,若不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应规范的构成要件予以限定,其意义将因约束要素变化而不同,如报复伤人和正当防卫伤人就不能划入同一意义范畴。
显然,法律事实的意义并不只是用抽象表达来涵盖具体生活事实,更重要的是成为构成要件和生活事实的联结点,用以沟通一般化的法律规范和具体性的生活事实。更确切地讲,在构成要件和生活事实之间,意义可被言说表达、且能被类型化的是前者,后者是被认识的对象,前者则为后者提供了定性标准。故而,如果说法律事实的内涵取决于构成要件,那么,作为生活事实的个案行为并无合法或违法的本质,其定性因构成要件的类型不同而不同。
综上,与其说个案的具体行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不如更准确地说与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包括了合法行为类型和违法行为类型,对应前者的个案行为归入作为法律事实的合法行为,符合后者的则属于违法行为。由此,行为内含了两层不可分割的意义,即作为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行为,以及受其制约的、用以表征生活事实、但被称为法律事实的行为,前者是其规范意义,后者表明其事实属性,它们实属同一硬币的两面。法律行为就是这样的硬币,它一方面蕴含了本欲达成的法律效果,显示出法律规范的性格,另一方面则以其具体形态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显示出法律事实的性格。[注]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31页。事实行为同样如此,它一方面是因个性特征而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法律事实,另一方面是事实行为规范的构成要件,在该要件的构造只要求单一的行为要素时,符合要求的具体行为就是作为法律事实的事实行为,[注]Vgl. Siedler, Zurechnung von Realakten im Buergerlichen Recht, Hamburg 1999, S. 9 f.其适例如遗失物拾得、埋藏物发现等无需与其他行为结合即有法律效果的事实行为。
(二)规范意义的标准
既然行为兼具构成要件和生活事实的两层意义,后者又受制于前者,那么,从构成要件的规范意义层面来认识行为的合法与违法的区别,所取角度应更恰当,所论也更有针对性。要使这种理解准确到位,不能单就构成要件来论构成要件,而必须借助法律规范中的法律效果,因为构成要件只有与法律效果无缝结合,才能形成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完全法条。[注]参见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受制于此,在确定构成要件是合法行为类型或违法行为类型时,法律效果起到了决定作用,若使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之类的不利益结果,对应的就是违法行为构成要件,迎合该要件的具体行为即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法律事实。[注]参见黄立:《民法总则》,2005年修订4版,第193页。反之,没有上述导向的法律效果对应的是合法行为构成要件,迎合该要件的即作为法律事实的合法行为。既然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分别指向不同的构成要件,分属不同的法律规范,它们当然不应交错或混同,从而能根据构成要件的差异分别统领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违约行为、侵权行为等下层行为类别,为行为的体系化奠定基础。
正是在规范意义上,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才有分类价值。[注]更具体的阐述,参见常鹏翱:《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分及其意义》,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在此分类指引下,以不利益结果为指向的侵权行为才定然不同于无此导向的事实行为。不过,不同的法律规范可能指向同一具体个案行为,进而因为同一行为符合不同的构成要件而产生法条竞合,此时,该行为会因迎合不同的构成要件而融不同的法律事实属性于一身。以毁损他人物品的行为为例,在事实行为的法律规范下,它是导致所有权消灭的法律事实,具体属性为事实行为,而在侵权行为的法律规范下,它是导致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事实,具体属性是侵权行为。正因为法律事实必须受构成要件的约束,毁损他人物品的行为才能将事实行为和侵权行为合二为一,也只有在此语境下,说侵权行为是事实行为才合理。
(三)行为分类再审视
从规范层面上来界定行为的合法与违法,基本上能说清分类标准,但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间更细致的关联未展现出来,还需从构成要件上再予审视。合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的构造比较简单,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主导,事实行为是行为和事实后果的结合。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包含了行为、违法性等要素,其中的行为要素如何定性是个问题:界定为合法行为,就与它是违法行为的最终定性相悖;界定为违法行为,就与违法性要素重合,与该要素在构成要件中独立存在的地位不合。基于此,再审视合法与违法的分类标准的立足点应是违法行为,其问题纠结于行为与违法性在构成要件中的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此处的违法性要素不能像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那样,以不利益的法律效果来定位其内涵,而是指行为逾越了法律规范前置的界限。在合同法中,合同约定的主给付义务设定了该行为界限,此外法律也可设定从给付义务,背离这些义务就可能构成违约行为,违背义务即属违约行为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注]Vgl. Esser/Schmidt, Schuldrecht, Bd. I, Teilband 2, 8. Aufl., Heidelberg 2000, S. 63 ff; Gauch/Schluep/Emmenegger, 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II, 9. Aufl., Zuerich 2008, S. 107 f.不难看出,在构成要件中,违法性要素是针对行为要素的评价,如果不履约的具体行为在合同义务界限之内,如履行期未届至的不履约、因债权人受领迟延而导致的给付迟延等,即未通过违法性评价,不会产生不利益的法律效果,属于合法行为。只有通过违法性评价,才能说该行为符合违约行为的构成要件,是违约行为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在违约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中,独立于违法性要素的行为要素在逻辑上未经违法性评价,在此阶段,对它有规范作用只能是合法行为规范,故其应是合法行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相比,侵权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稍微复杂一些,表现为侵害他人的绝对权、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核心是对法规范所定义务的违反,[注]参见王千维:《由“民法”第一八四条到第一九一条之三》,载《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30页。但仍然是外置于行为的评价因素,即虽有加害行为,但相应地未触犯不得侵害绝对权等行为义务,就不是违法行为。同样,在逻辑上看,未经违法性评价的加害行为对应的是合法行为规范,其法律事实的具体表现可以是事实行为,如毁损他人之物,也可以是法律行为,如处分他人之物。
这里隐藏着一个逻辑跳跃,即个案的具体行为首先符合相应的合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再具备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等评价因素,才是作为法律事实的违法行为。这一思路表明,合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无需设置行为界限及相关的评价要素,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这同时意味着,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分类不仅在对行为的定性认识上有排除法的便利,只要厘清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其余的行为皆为合法行为;还表明它们之间并不绝对分离和互斥,反而有递进的逻辑关联,上述分析已经显示,合法行为是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的基础,以此为基点再辅以违法性等规范要素,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才得以完全框定。基于这种理解,我们甚至可以把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底色界定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无非是用违法性等要素对合法行为的限制而已,在行为这一基础范畴中,违法行为无法摆脱合法行为的根本制约。只有明白这层关联,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史尚宽先生的界定,即合法行为是法律所许可的构成法律事实的行为,违法行为是法律加于行为人以不利益结果的违法或有过失的行为。[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上述表明,违法行为不仅是引致不利益后果的规范构成要件,还有挑明行为逾越了规范前置的行为界限的含义。这种界定的价值取向是在承担责任(Verantwortlichkeit)的意义上,围绕损害等行为后果来决定法律效果的归属,与之配套的制度支持是侵权行为能力(Deliktsfaehigkeit),只有在此意义上,行为才有合法或违法的界定。法律行为的违法则不同,它是在约束力(Bindung)意义上决定行为有无效力及无效程度,与之配套的制度支持是行为能力(Geschaeftsfaehigkeit)。[注]Vgl. Pawlowski,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 Heidelberg 2003, S. 165 f.申言之,法律行为的违法现象若指向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则表明法律行为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但它本身仍不失为合法行为;若指向符合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的具体行为,则它会转性成违法行为。故而,诸如无权处分这样的违法的法律行为,是一个涉及不同问题领域的话语现象,在不同意义视角中,它既是法律行为也是侵权行为,全无矛盾可言。当然,如果违法的法律行为并不符合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其定性只能是效力有瑕疵的合法行为。
概括而言,只有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这一角度中,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分类才有意义,也才能理解,在法律事实的意义层面上,同一行为同时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并不会制造话语悖论和规范矛盾。而且,只有理解了违法行为的规范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与违法性等要素的关系,才能明白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所有这些无非表明,同一词语乃至同一行为因规范语境不同而有不同意义,只有在特定限制因素的约束下,才能辨明其内涵所指。
三、合法行为间的界分
(一)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界分
从构成要件上看,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有以下区别:(1)作为法律行为的意思实现并非表示行为,《合同法》第22条[注]《合同法》第22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规定的无需通知的承诺就为适例,而准法律行为无一例外地属于表示行为;(2)意思表示无需相对人,遗嘱即如此,而准法律行为均需相对人受领;(3)意思表示中的意思有行为意思、表示意思和效果意思之分,表示行为的对象是效果意思,准法律行为有行为意思和表示意思,没有效果意思,其表示的对象是某种认识、事实或情感。在法律效果上,两者的区分如下:(1)法律行为的效果通常是权利变动,如买卖合同创设买卖债权,或至少是权利变动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授予代理权,而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是为权利变动提供相对间接的条件或诱因;(2)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源自效果意思,而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取决于法律规定。[注]更具体的阐述,参见常鹏翱:《对准法律行为的体系化解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上述区分构成了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界分标准。
在上述界分的基础上,应特别注意法律行为的效果由效果意定决定这一点,因为它表明了法律行为的规范属性,这使其与准法律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买卖合同对法律行为的上述特质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如在A买B的货物的交易中,正是在买卖合同自身作用力的影响下,才有约束A和B的债权请求权,《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实证法中的法律行为规范、合同规范或买卖合同规范只是承认该效果而已。正是在此意义上,才说意思自治是法律行为的生命和灵魂。
说法律规范承认法律行为,实际是从消极角度设置强制规范来排除不合格行为,《合同法》第52条[注]《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定,就属于这类规范。鉴于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交易没有效力瑕疵,合格的法律行为属于交易常态,这些强制规范因此通常存而不用,与实际发生的具体行为基本绝缘。只要不背离强制规范,在效果意定的前提下,就应以A与B的买卖合同这样的具体行为为标准,而不是以法律规范为标准,来判断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买卖合同只拘束特定的债务人,没有波及其他人的溢出效应,也无需借助实体财物来支撑其存在,是意思自治和效果意定的典型代表。受这种特性约束,法律规范对买卖合同的涉猎,除了前述的强制排除,主要是紧跟现实,描绘标准的行为图像,如买卖合同规范就用标准的法言法语再现买卖合同的应有要素,这就像法律专家提供的买卖合同标准范本一样,能弥补实际合同在非核心要素方面存在的漏缺。但法律规范并不强制安排买卖合同的内容,而基本上是以任意规范的方式展现出专家建议的特点,当事人完全能排除这些规范的适用。
这样看来,《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典型合同规范,无一例外不在发挥着专家建议的作用,当事人完全能无视这种标准范本,自行订立非典型合同,进而使得典型合同规范在自己的个案中无甚意义。这种使法律规范无用的结果仍然要受到尊重,因为它正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本有之义。再用这种认识来看颇有争论的悬赏广告,无论法律把它规定为合同或是单方行为,也仅是提出标准范本,在意思自治机制下,这些法律规定不影响当事人实际作出相反的行为,也不影响实际行为如当事人所愿地发生预期效果。[注]参见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页。概言之,在法律行为和涉及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之间,前者处在主导地位,只要不背离强制规范,它能超越法律规范而存在。
也就是说,在法律规范提供的标准范本与某一行为的现实样态之间,后者能被前者覆盖的,就属于典型的法律行为,在解释时遵循其一般规律即可;前者不能或不能完全覆盖后者的,未被覆盖的样态就是非典型的法律行为,在解释时视情况适用或参照《合同法》第125条[注]《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第2款: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的意思表示解释规范。以悬赏广告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3条规制了悬赏广告,在“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目的引导下,该司法解释显然把悬赏广告当成了合同来看待,从这个基点往前推,该规范应与《合同法》第14条、第21条[注]《合同法》第14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21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等规定的要约和承诺相配套,它适用于相对人知道悬赏且完成特定行为的情形。至于相对人不知悬赏且完成特定行为的情形,当然无法适用上述规范,但只要悬赏广告未明确排除该情形下的相对人报酬请求权,就表明它是单方行为,仍不免为相对人创设报酬请求权。
既然买卖合同之类的法律行为能在法律规范之外创造权利变动的后果,它也就能成为民法的法源,为法官裁判提供依据。[注]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就此而言,是A与B之间的买卖合同这类法律行为,而非涉及此类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决定了相应的法律效果,法律行为因此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而在规范构成要件层面上的准法律行为,指向以表示行为为构成要件,且效果完全法定的法律规范,如《合同法》第48条第2款[注]《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合同法》第80条第1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2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的催告、《合同法》第80条的债权转让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的被继承人对继承人的谅解。两相对比,虽然二者均在规范层面上,但法律行为的具体性与准法律行为的抽象性无疑有巨大鸿沟。
由以上思路继续延伸,问题仍未完结。A、B的买卖合同因有无效事由而被归为无效法律行为,它是表示行为,结果由法律规定,与准法律行为的构造完全相符,那它应否归入准法律行为?回答该问题的起点仍是构成要件的规范意义,它是遴选具体生活事实并对号入座的标准,至于迎合该标准而被符号化的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其他要件。在法律行为中,构成要件即成立要件,符合者就是作为法律事实的法律行为,在此基础上再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生效要件。构成要件和效力状态的区分,在理论上不仅将无效法律行为留在法律行为范畴之中,进而可适用法律行为的其他规范,如无效法律行为可再被撤销或再被认定无效;[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页;王泽鉴:《无效法律行为之撤销》,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8页。还表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区分并非纸上空谈,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不符合成立要件的行为无从补救,不符合生效要件的有可能补救,[注]Vgl. Koe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Muenchen 2009, S. 36.这意味着,构成要件对应着法律行为的成立状态,不符合就从根本上否定其存续可能,符合的仅表明行为成立,是否生效还需结合其他要件判断。
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平分了表示行为的天下,不符合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表示行为即准法律行为,它同样有能否生效的延伸问题,对此,基于表示行为的共性,学理主张准用意思表示规范,自有道理。不过,准法律行为是该类构成要件的抽象总称,包含了诸多形态不同的、法律效果法定的表示行为,无法像意思表示那样被法律一体规划,故而,能否以及如何适用意思表示规范,只能针对不同情形予以具体判断。[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2-713页。而且,准法律行为通常以既有的法律关系为基础,主要是与请求权或法律关系有关的催告和通知,[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712页。对其效力判断必须考虑该基础,除了准用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瑕疵等规范外,还要有与具体规范旨意相符的要件,如催告时点不得在清偿期届至之前、不得附条件等。[注]Vgl.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Bd. I, 18. Aufl., Muenchen 2008, S. 226 f.
准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虽然截然有别,但它们仍会衔接并存,经由履行催告的合同解除即为适例,在通常情况下,先有作为法律行为的合同,后有作为准法律行为的债权人催告,再有作为法律行为的解除权行使,在此层层递进的规范布局中,合同是催告的基础,催告则是合同步入解除的连接点以及解除权行使的条件,规范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相当清晰。不过,如果催告的具体内容包括不在相当期限内履行即解除合同的意思,则它是以债务人于此期限内不履行作为生效条件的解除意思表示,[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540页。催告的内容因此成为引致不同解除路径的选择点。就此来看,具体的催告行为在不同的规范语境中会涵盖意思通知与意思表示,如何定性完全视其内容而定,这表明在不同构成要件指引下,具体行为能在规范意义上被分解或区分,结果产生属性不同的法律事实,这应当是有普适性的一般规律。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分
在界定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分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事实行为应否独立存在。有德国民法学理认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根本不同在于法律效果与行为人意思无关,行为人有无意思能力或意思如何不在考虑范围,比如,精神病人A用B的画布绘制一幅画,这不妨碍A基于《德国民法典》第950条的加工规范而取得画的所有权;又如,X依据《德国民法典》第984条取得所发现埋藏物的一半所有权,该效果与其取得所有权的意思无关。[注]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4页。这一定性既简要又确切,但似乎简化过度,沿其逻辑推演,事实行为势必难以独立存续。试想,既然事实行为不考虑意思能力,又与行为能力、侵权行为能力无关,那么,其效果归属着眼点并非人的行为,而是客观事实情况,比如,对谷物混合后的所有权界定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混杂不可分的状态,并不考虑混合出自行为或者风力;又如,只要创作产生了艺术品,无论创作人是否智障,均可取得艺术品所有权。这些情况说明,事实行为应归为自然事实才合适。[注]Vgl. Pawlowski,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 Heidelberg 2003, S. 166.果真如此的话,在合法行为中舍弃事实行为这一类型也不为过。
然而,在人体举措被确定为行为的前提下,上述的加工和发现均属于对法律效果无目的意思的事实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50条、第984条的构成要件虽未给意思要素提供位置,但要求有加工或发现的行为以及有作品或发现埋藏物的事实后果,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有相应的法律效果,显然,效果归属的关键点是行为而非其他。[注]Vgl.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 Bd. II, 4. Aufl., Berlin u.a. 1992, S. 108 f.正因为法律规范注重行为的作用,此类构成要件才得以与法律只关注事实后果而不注重其原因的自然事实区分开来。在此方面,作为事实行为的加工与作为自然事实的附合、混合的区别堪称适例;而且,行为以意思能力为前提,若将此类事实行为与自然事实混杂,将从根本上混淆行为与自然事实的区分点,难谓妥当。故而,事实行为应有独立性。
除了上述不要求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类型,以下两类事实行为均包括意思要素:(1)有取得或丧失占有意思的事实行为,既包括占有得丧的一般规范,如《物权法》第23条的现实交付,还有《物权法》第109条的遗失物拾得等特殊规范,它们有占有得丧的意思,但该意思不独立于占有得丧的客观外形,故该类行为称为目的意思不独立的事实行为。(2)意思要素独立的事实行为,包括《民法通则》第93条的无因管理等,与上一事实行为相比,其意思要素的独立地位更突出,故该类行为称为目的意思独立的事实行为。可以说,正是意思要素的有无及独立与否,促成事实行为的体系化。[注]更具体的阐述,参见常鹏翱:《事实行为的基础规范》,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这也说明,在判断某一具体行为是否事实行为时,必须从事实行为构成要件的具体类型入手加以确定。
无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区别一目了然,即便有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与意思表示也完全不同,因为事实行为中的意思无需表示,与法律效果也无关,这与意思表示大相径庭。概括而言,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分点在于,前者的法律效果由效果意思决定,后者的法律效果由法律在行为事实后果基础上决定。这一区分使二者各自制度设计迥异,比如,意思表示有表示内心意思的过程,法律对此需专设意思表示瑕疵规范,而事实行为无此过程,通常不能以准用意思表示规范;又如,法律行为受生效要件的制约,而事实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即有法律效果,只有成立而无生效问题。这些差异还牵涉到周边的相关规范,比如,同为效果归属规范,对应法律行为的是代理,对应占有行为的通常是间接占有或占有辅助;又如,同为不动产所有权移转规范,基于法律行为者以登记为要件,基于事实行为者则无该要件。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再来看交付的定性。虽然交付在动产物权变动中起着决定作用,但其自身仅指向占有得丧的事实过程,且其包含的占有得丧意思与物权变动没有任何关联,故其仍为事实行为,不能因其具有决定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而将其定性为法律行为。以《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句、第1032条第1句、第1205条第1款为例,在规范构成上,交付与物权合意是通向物权变动的必备要素,交付显然不是物权合意。但要注意,在此的物权合意并不以明示的方式表示出来,需借助外力推断,交付标的物的现实行为就成为推定物权合意的工具,[注]Vgl. Wieling, Sachenrecht, 3. Aufl., Berlin u.a. 1997, S. 9 f, 88 f.它由此在现实交易中成为引致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的表征,这让它看上去迈向了法律行为,但也仅仅是看上去如此,因为它作为事实行为介入动产物权变动,并成为物权合意的推定手段,是占有公示功能的使然和交易客观需求的必然。这也表明,现实中发生的具体交付行为在受交付规范调整的同时,在买卖等引致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的引导下,还能推定物权变动合意的存在,这给法律行为提供了介入空间。
此外,说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根本不同,在于法律效果不取决于行为人的意思,的确十分精当,这对界定意思实现的法律地位相当有用。与意思表示不同,意思实现是有效果意思而无表示,[注]参见邵建东编著:《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这种结构看上去与有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近似,但法律效果由效果意思决定这一定位,将意思实现划入法律行为。比如,动产所有权的抛弃为意思实现,目的是抛弃所有权,正是该目的产生了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注]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I》,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反之,先占的法律效果是取得动产所有权,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产生的自主占有无主物的事实后果,故为事实行为。又如,承诺的意思实现不仅要有可认为承诺的客观事实,行为人主观上还须有承诺意思,一旦舍去主观意思而取客观事实来认定意思实现,无异于事实行为,这不仅违背私法自治原则,还不能保护相对人利益。[注]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故而,意思实现的定位重点是效果意思,这正是它与意思表示共享同等地位的基础。
(三)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分
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它们也因为法律效果法定而与法律行为不同,在此双重否定意义上,它们在学理上通常被捆绑处理,属于与法律行为相对立的合法行为。[注]Vgl.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 Bd. II, 4. Aufl., Berlin u.a. 1992, S. 105.虽然如此,也不是说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有高度的同一性,究其各自实质,应当说差异大于共性,主要表现为:(1)在行为形态上,事实行为并非表示行为,没有对外表达内心意念的过程,而准法律行为是表示行为;(2)在意思要素上,准法律行为有行为意思和表示意思,而事实行为没有表示意思,但有取得占有的意思、管理意思等目的意思;(3)在法律效果上,准法律行为不能直接导致权利变动,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主要是权利变动,此外还有纯粹的事实结果,如占有得丧。[注]更具体的阐述,参见常鹏翱:《对准法律行为的体系化解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可以说,是否表示行为这一分界,将准法律行为与有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彻底区分开来。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可能指向特定的事实后果,如被害人的允诺以承受自己权益受侵害为内容,从而赋予他人加害行为的合法性,但它是表示行为,故非事实行为,同时,它不以法效意思为必要,不同于事后承认侵害或事先免除责任等抛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行为,故属于准法律行为。[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要约邀请也同样如此,它是把行为人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图向外界表达的行为,显然不是事实行为。与此不同,事实行为中的意思尽管也指向事实后果,但因无表示而不能跨入准法律行为的领域。
两相对比,准法律行为更接近意思表示,因此可准用意思表示规范,故而,若把住所的设立定位成准法律行为,则行为人要有完全行为能力。[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至于事实行为,即便它可能有意思要素,但该意思无需表示,这种构造与意思表示相差甚远,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难以准用法律行为规范,故而,把住所的设立定位为事实行为时,行为人只需有意思能力即可。[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不过,不是说只要是表示行为,就必定排除事实行为,因为在事实行为的框架内所为的表示,是事实表示而非意思表示,比如,在自主占有向他主占有的变更中,以及在其相反形态的变更中,所需的表示不以行为人有行为能力为必要,也无需使其占有之人的承诺。[注]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2010年修订5版,第487页。对于该表示,遵循的是事实行为规范自身的要求。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差异主要是形式上的,并不妨碍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在具体制度中发挥相似乃至相同的功能,如债务人提出给付是债权人受领迟延的要件之一,它可以是现实提出,这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言词提出,这是准法律行为。但它们终归属性不同,法律规制不可能同日而语,必须分别对待,如现实提出是债务人向债权人陈示准备事实,无需特别通知,但须在清偿地实施,言词提出无需陈示准备事实,但有通知的必要,且可在清偿地之外实施。[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当然,现实提出和言词提出设置了功能相同的选择项,债务人可择一而为,只要符合各自要件,结果没有差别。与此相比,有些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互斥性很强,不容当事人事先选择,如被害人允诺和无因管理同为侵权行为违法性的阻却事由,但前者需向加害人表示,行为人应有处分权限和识别能力,[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而后者无需表示管理意思,管理人的能力也无特别要求,[注]参见黄茂荣:《债法各论》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面对差异如此大的构造,当事人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只能基于规范构造择一而定。
此外,准法律行为以既有的法律关系为存续基础,旨在为该法律关系的得丧变更提供条件或诱因,不能直接导致得丧变更的法律效果,这决定了它只能浮在有相对人的表示行为的层面,无从像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那样渗入法律关系得丧变更的法律效果层面。比如,加工、先占等事实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准法律行为无此效用;又如,无因管理、占有他人之物等事实行为能引起债的发生,准法律行为通常不能;再如,债的履行涉及权利变动的,需要法律行为落实,否则即为事实行为的任务,准法律行为在此也无用武之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事实行为远比准法律行为的价值重要,这显示出二者的实质差异。
准法律行为终归是表示行为,是否表示的决定权掌握在行为人手中,它因此有意思自治的因素,行为人能决定表示的方式和内容,如债权人可预先催告债务履行或催告其他给付。[注]Vgl.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Bd. I, 18. Aufl., Muenchen 2008, S. 226 ff.在准法律行为成立后,能否产生法律效果就是后续的问题。显然,准法律行为和法律行为共享意思自治的价值,并因此有成立、生效等复杂的规范体制。而大体上看,事实行为与自然事实一起被该价值隔离,在法律上只需判断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故将它们属于法律包装塑造最少的法律事实。[注]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这也说明,因为意思自治的推动,准法律行为在法律规范复杂性上远较事实行为为甚。
但要注意,上述结论对于无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没有问题,因其构成相当客观,完全以法定而非自治为导向,与准法律行为没有相似性。有意思要素的事实行为就有所不同,它在构成上为主管意思留有空间,尽管该意思可能只指向诸如占有得丧的事实后果,看上去与法律效果无关,但因为法律效果须基于事实后果而定,事实后果由此成为该意思与法律效果的联结点,无该意思即无事实后果,进而也无法律介入下的法律效果,故而,这一结构从整体上以法定为导向,但行为人自我决定的自治色彩也相当明显,这使其与准法律行为在架构上极其类似,即它们均内含非效果意思的意思,法律效果均由法律规定,它们因此均是法定导向下的自治。这样一来,有目的意思的事实行为参照适用代理规范,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注]Vgl. Siedler, Zurechnung von Realakten im Buergerlichen Recht, Hamburg 1999, S. 147 ff.
四、结语
在民法中,行为融事实和规范的双重意义于一体。如果仅以前一意义为观察基点,往往会陷入事实形态的具体构造而遮蔽应有的后一意义,无效的法律行为是违法行为、侵权行为是事实行为的认识均源与此,行为体系因此笼罩在重重问题疑云之中。反之,从规范意义来认识行为,定位操作的基础是构成要件,所谓的行为实际上是构造各异但数目有限的抽象规范,无效的法律行为仍是合法行为、事实行为不同于侵权行为因此理所当然。在此视角下,作为客观事实的具体行为是被认知的对象,它本身没有任何规范性,之所以说它是法律事实,因其是被构成要件格式化的结果。这样看来,构成要件恰似眼镜,眼睛中的事物即法律事实,其颜色取决于镜片颜色,而镜片度数也影响其清晰度。
作为引发民事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行为是民法的最基本关键词,它以高度抽象性涵盖了世间难以尽数的具体行为,并将它们化约为类型有限的法律事实。因为规范功能不同,行为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也不同,它们各有自成一体的边界,有上下层级之分,在整体上有了体系架构。这一错落有致的差序格局得益于异同并举的手法,即基于构成要件的相异性,生成各不交错的垂直分支线条,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分等无不如此;同时又抽取各类构成要件的相同性,将它们包容在共同的上级范畴中,涵括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合法行为、涵括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法律行为等均为适例。
如此这般的异中有同、同中存异,不仅不会导致规范错位,反而是搭建规整的行为规范体系的必需方法。不过,这不意味着只要着眼于构成要件的异同,即可明辨行为属性及其地位,要准确达此目标,还须有规范功能的引导,如合法与否导致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区分,但这二者并不因此有同一起跑线,因为违法行为通过设置违法性标准而有评价功能,合法行为恰无此功能,合法行为由此堪称行为的起点,而违法行为是以此为基础的衍生。
通过构成要件以及规范功能的引导,我们得到了更充分也更立体的行为规范信息,但它们仍未从抽象的规范走向鲜活的现实,在经历了从规范到现实的过程后,行为规范会呈现出更动态也更灵活的组合搭配。最常见的是为了全方位调整现实情况,行为规范尽管有各自边界,但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可能实现无缝衔接,从而勾连成意义相互关联的体系网络,经由履行催告的合同解除即为适例。当然,无论行为规范在运用中的组合形态如何,均无从偏离它们各异的实质,这才是行为体系架构的根本。
还应重申的是,尽管本文对合法行为规范体系的讨论,采用了规范分析的模式,但这不是纯粹的概念逻辑游戏,它在法律运用方面的实益相当明显。最直观的莫过于通过厘定不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把握各自不同的运作机制,明确要件与效果之间的关联,避免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出现张冠李戴的错位后果。在这方面,若某一行为与另一行为的规范要求和实践表达反差大,如某人不受委托就管理他人事务,当然是无因管理而非委托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不大。一旦反差较小,明确规范差异的意义即非同寻常,如迟延催告究竟为法律行为还是准法律行为,绝不能僵化定性,而必须针对催告具体内容,结合不同的规范要求才能准确判定。当然,诸如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这样的相似规范之间存在准用现象,但准用无论如何不是适用,之间差异在此不赘。
除了解释并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化功能,通过理顺合法行为的体系,还便于辨析规范语境的异同,进而有助于精细化地准确适用法律,这一点对于形态相同的具体行为的认定特别有价值,因为受制于不同的情景,具体行为会处于不同的规范语境,定性也因此不同,如同为承认,在无权处分中要适用意思表示规范,而在无因管理这一事实行为规范大背景下,本人的承认就不是法律行为,不能直接适用意思表示规范。[注]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此外,针对同一具体行为有多重规范予以调整是常态现象,而这些多重规范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需要结合具体行为进行分析,不能笼统地一体处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当然是准确界定各类行为。比如,故意毁损他人财物既是事实行为又是侵权行为,前者着眼于毁损的事实后果,后者除了这一事实后果,还着眼于毁损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适用上后者完全涵盖了前者,故前者只能存在不用;又如,移转动产所有权中的交付一方面是占有移转的事实行为,另一方面为物权合意提供推定依据,这两类规范即可并存适用,不因属性不同而相悖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