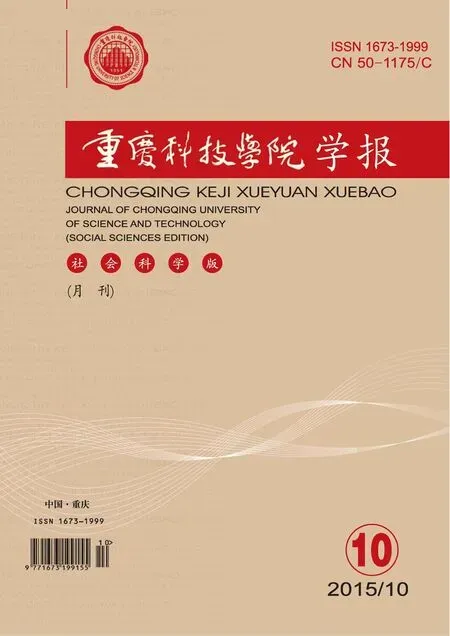解析《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维多利亚社会
王成峰
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铸就了英国 “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英国都对全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通过讲述男女主人公查尔斯·史密逊和莎拉·伍德拉夫的爱情故事这一主线,借助高超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技巧,再现了英国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正如小说中神秘的女主人公莎拉一样,《法国中尉的女人》本身浓郁的实验性也为其增添了不少的玄妙。自其出版以来,不断地吸引着众多的普通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近些年,国内的研究亦不一而足。学者王冰等对福尔斯研究的述评显示,国内研究成果产出较多的期刊论文和优秀硕士论文中超过70%均集中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上,且研究角度上多偏重于元小说、陌生化、对话性等实验性手法上,而研究主题上则侧重于自由追寻和自我界定等存在主义论题上。本文试图通过《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女性规训和两性关系两个角度的探讨进而关注小说折射的伦理思想,同时,指出福尔斯并非是一味解构的虚无主义者,其作品也在积极建构更加合理的伦理标准。
一、女性规训:囚禁女性的监狱
规训最原本是针对人的肉体,旨在生产“驯服的肉体”,但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控。”[1]福尔斯笔下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规训的一个典型人物即波尔蒂尼夫人,即《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女主人公莎拉的雇主,一位残忍的富有寡妇。她不仅自己完全接受男权话语的控制,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做人行事的准则,维护男权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正如当时社会风尚所要求的,她绝不容忍两样东西:脏和伤风败俗。家里佣人出现任何不注意卫生的行为,都会成为被解雇的直接原因,她对任何形式的不洁表现都异常的敏感和痛恨,然而,她最不能容忍的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坚决禁止的种种伤风败俗现象。当时,以新教徒为主的中上阶层对女性性问题采取极为苛刻的态度,女性沦为应该没有性欲的动物,哪怕正常的性要求也被视为伤风败俗的表现。小说第五章在描述另外一位女性人物欧内斯蒂娜时间接但有力地抨击了这一点。她是查尔斯的未婚妻,来自一个富商家庭,长相标致,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福尔斯介绍了她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但这并未使她满足而别无他求,对爱情的憧憬、对婚姻的期待让“她的脑海里闪过性的念头”,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身体上产生性冲动的反应,使她想到那种事儿,她便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无论如何也不干’。 ”[2]34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任性千金在性问题上竟也如此规矩,可见,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性规范的约束几近有违人性。然而,这个时代对女性的规训远不止此,在家庭中她们还要扮演“家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的角色,日常的义务有:“1.使大家高高兴兴;2.每天给他们做饭;3.给每人衣服穿;4.令每人干净整洁;5.教育他们。 ”[3]这一麻痹大众女性的美称将她们限制在家庭之内,脱离了与主流社会的正常交流,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并被男权社会逐步地隔离和边缘化。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莎拉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训下的另一位受害者。莎拉出身社会下层,但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因而得以在当地的一位船长家里做家庭教师,因传与船长救下的一位法国中尉有染而丢掉了工作并被世人所弃,在小说开头即以“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污名现身。然而,福尔斯笔下的莎拉虽生于维多利亚时期却超越了这个时期,她否认甚至意欲颠覆社会对女性的规训。面对各种不雅的谣传,莎拉并未出面澄清或予以解释,相反,她常常站在海边,远眺大海。在旁人看来,她仍在留恋旧情,用实际行动坐实各种传言。莎拉的反常行为开始可能始于无奈,毕竟她只是一个出身寒微、在男权社会中毫无话语权的普通女子。在小说中,她虽为女主人公,出场却被冠以各种男权话语赋予的符号,如“悲剧人物”“法国中尉的女人”等等,直至第四章结尾,读者才得以知道其真名——莎拉·伍德拉夫。作为一个被主体社会排挤、边缘化甚至除名的个体,即使她提供解释、做出重新融入群体的努力,也终将是徒劳一场。因此,非凡的她并未臣服于当时社会的女性规训,她积极地探索自己抗争和生存的策略。她多次出现在鲜有人迹的海边,故意独自一人去正经人的禁地康芒岭…这一切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行为首先引起了雇主波尔蒂尼夫人的关注,更确切地说,是刺激了这位男权话语的维护者。莎拉被斥为“狡猾的坏东西”“罪人”,面对指责,莎拉勇于捍卫自我的尊严和地位,毫不畏惧地为自己辩解,“这不能算罪过,我不希望因此而被人叫做罪人。”[2]106通过对男权话语的公然反抗和对女性规训的有力颠覆,莎拉开始改变了自己被主体社会边缘化或除名的境遇,虽未被接纳,但起码她得到了关注和重视。
查尔斯作为一位男权社会话语和权力的操纵者,他也成为了莎拉反抗社会秩序、颠覆女性规训的另一支点。莎拉出身底层社会,扮演着世人口中的“娼妇”,正常人都避而远之的角色,但是通过重构自我的一系列行为,使得身为贵族的青年查尔斯最终不顾惜身份荣誉,解除婚约,放弃了原本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甘愿追求她这个贫贱女子,追寻这份虚无缥缈、不为世人所容的爱情。他们的初次相见就使查尔斯“难以忘怀”,莎拉的神情让他觉得“象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一样,纯净、自然、难以遮拦。 ”[2]10莎拉没有让查尔斯觉得自己是个“娼妇”,是个神经错乱、歇斯底里的疯子,并且当他们在康芒岭再次相遇,查尔斯提出希望能够帮助她离开莱姆镇摆脱困境时,莎拉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坚持留在莱姆镇,更反对到伦敦谋生。对于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莎拉的解释是,“倘若我离开了这儿,我便离开了耻辱,那我就完了”。[2]208莎拉坚持留下来通过自己的方式体现自我,而不是到伦敦城像很多失去名声的女人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她正是通过别人眼中的耻辱来营造自己的自由空间,构建不同于、不屈从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训下的自我,就如她自揭“法国中尉的女人”伤疤时所言,“我一钱不值,我几乎不再是人了,我只是法国中尉的娼妇”,但是,“我有时候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2]202。这种自由恰是颠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训、反抗一切不公正女性束缚和压迫的产物,它更对维多利亚社会男女两性关系的现状直接提出了挑战。
二、两性关系:无限斗争中的有限进步
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第二章《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人俗录》的引言中印证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男女人数不平衡的现象,“1851年,英国人口中十岁以上的女性人数约为815.5万,而男性人数仅有760万。”[2]5英国历来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维多利亚时期男女人数悬殊的社会现实更是将崇尚社会地位的风气、男尊女卑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女性之于男性可以轻如一笔财产,正如福尔斯所言,在十九世纪花几镑钱便可以买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弗里曼先生是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营着巨大的商业帝国,富甲一方。他鄙视封建贵族因循守旧、顽固不化,在工商业蓬勃发展并日益担当社会重任的维多利亚时期,像查尔斯这样的旧贵族仍固步自封地认为经商是不体面、不适宜贵族的职业,他不失时机地借用查尔斯信奉的进化论思想予以辛辣的批判。然而,这样一位看似进步的商人却要把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女欧内斯蒂娜许给连自己事业都鄙夷的查尔斯。这种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查尔斯生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贵族家庭,若欧内斯蒂娜联姻成功,整个弗里曼的社会地位都会得到极大提升,就像当初他自己结婚时就“娶了一位比自己门第高的女子”[2]90,只有这样,对于他这样一位精于算计的商人来说,才是“一笔极好的交易”[2]95。 由此可见,女性在父权社会显然成为了男性达到某种目的的筹码或棋子。
在维多利亚社会,“女性只能充当被观看的客体,成为被男性审视的对象和他者”[4]110,男性“总是把女性建构成供男人占有的商品,有待男人征服的领地,或者是男人追逐的欲望对象”[4]123,进而模糊或者遮蔽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和身份。《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最复杂、最典型的两性关系体现在男女主人公查尔斯和莎拉身上。二人间的纠葛缘于海边的初次偶遇,之后查尔斯便给出了当时当地一个男权主流话语者观看审视后的感受:“不论什么时代,也不管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衡量,那确实不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但那却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一张悲凉凄切的脸。”[2]10查尔斯没有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莎拉已神经错乱、歇斯底里,他抱怨乡间人们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导致了莎拉遭到周围镇民的一致排挤,而在第二次偶遇时,福尔斯直接地表达了查尔斯对莎拉的同情,“这个可怜的人儿是无辜的,她被社会遗弃是不公正的。”[2]81查尔斯此时只是想作为一个绅士拯救“这个可怜人儿”,但随着他们见面次数增多,他对莎拉有了新的认识,莎拉不同于同时代女性的面孔,使他“想到了外国女人…想到了外国床铺”[2]139,而且,莎拉的容貌也给他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样的光线下,也不管是什么心情,怎么看她都十分漂亮。 ”[2]159一番“审视”之后,莎拉成了查尔斯怜悯、拯救和欲望的客体。
然而,随着小说的发展,福尔斯向读者展示的却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莎拉身上透着 “一种纯洁的野性,一种近乎热望的野性”,[2]286查尔斯也意识到莎拉是一位富有智慧和独立自主精神的非凡女性。在与莎拉的交流中,作为一位男权话语操纵者,查尔斯一直视其为一个亟待脱离水火的不幸女性,他试图以一个拯救者的姿态帮助莎拉摆脱来自波尔蒂尼夫人的身心监控、离开漫天流言蜚语的莱姆镇。但是,凭借福尔斯高超的元小说叙事技巧,读者得以明晰地看到实际情形:莎拉一直在决定着二人见面的时间、地点,甚至散步和爬山崖时都是她走在查尔斯的前头,她一步步地使查尔斯对自己心生怜悯、产生好感,继而心生钦佩和爱慕之情,莎拉始终把握着二人关系发展的节奏,并且在不断地引导查尔斯重新审视所处的时代、审视自我,使他开始“意识到其存在的、隐藏着的自我”[2]150,查尔斯在经历与莎拉关系起起落落、分分合合后,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好像觉得自己再一次刚刚出生”[2]526。 他做出了自己人生重大的伦理选择——解除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放下贵族的荣誉和婚姻将带给自己的帝国般的财富。像莎拉一样,查尔斯选择了面对解除婚约后随之而来的名誉扫地,他也将背负耻辱与虚伪腐朽的维多利亚社会背道而驰,孤立地生存下去。某种意义上说,查尔斯并未能成为莎拉的“拯救者”,相反,莎拉扮演了查尔斯人生中的引路人和精神导师,帮助他追寻真正的自我。
这样的莎拉获得了“面对维多利亚时期守旧、虚伪的社会道德意识而顺势装疯、以反抗整个旧礼教和父权制的现代新女性形象”[5]等诸如此类的评价,这样的形象刻画与福尔斯“男人只看见事物,而女人看见事物间的关系”的论调是一致的,他本人也曾宣称“尽力做一个女性主义者”[6]。但是,福尔斯作品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却是抹杀不去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主体部分虽描述了莎拉如何颠覆维多利亚社会女性规训、与社会中掌控话语权的男性周旋、如何通过牺牲自己名誉来追寻自我和自由的空间、如何帮助男性认清自我完成精神蜕变,但在小说最令人信服的第三个结局中,福尔斯将莎拉安置在了但丁·罗塞蒂的家中,充当其模特和助手。但丁·罗塞蒂是英国十九世纪的诗人和画家,先锋派艺术的代表,其人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清规戒律和虚伪道德话语,其作品反对学院派的因循守旧、刻画女性的神秘性感、触及情欲等禁忌主题。对其生活的社会来说,他可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独行侠。福尔斯如此安排,用意无非是体现莎拉对当时社会的反叛和决裂、突显她自由斗士的形象。但历史中的罗塞蒂远非特立独行,他的感情生活以及创作方式无不揭露其浓重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女性只是其感情生活和创作过程中的欲望客体。他为莎拉提供工作,在莎拉怀孕期间悉心照料,并主动认作其孩子的教父,扮演着莎拉母女拯救者的角色,但是他的恩惠并非源自对莎拉天赋或艺术才能的赏识,正如莎拉自己所说,她只能在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上给罗塞蒂这些真正的艺术家们提供一些帮助,她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容貌符合罗塞蒂的审美标准,可以作为他们艺术描摹甚至个人欲望的客体。
虽然,莎拉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设置的种种樊篱,争取了自我生存的空间,并且打破了与以查尔斯为代表的男性之间“观看”主客体、“欲望”主客体以及“救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但莎拉最终乐于接受罗塞蒂庇护下的幸福,表明莎拉又回到了父权社会的俗囿,只不过变换了一个新的主体而已,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在男权社会女性真正打破男权束缚、颠覆两性关系在一定阶段内只能是空中楼阁,仍需较长期的斗争。
三、结语
约翰·福尔斯被评论界推崇为伟大的英语作家,不仅仅是因为其不落窠臼的小说创作手法打破了二十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山穷水尽的窘境、影响了大批后学之辈,更在于其作品中深切的伦理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通过对莎拉的刻画及对其与他人尤其是男性关系的描述,更加翔实地再现和解构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规训和两性关系等伦理现象,但福尔斯并非是一味地否定、解构,正如小说中莎拉拒绝查尔斯的帮助一样,所有这一切皆是福尔斯及其笔下人物追寻自由、重构社会伦理思想的有力工具。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155-156.
[2]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 [M].刘宪之,蔺延梓,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3]陈静.从维多利亚时代看《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J].甘肃社会科学,2009(1).
[4]张和龙.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宁梅.论约翰·福尔斯对“疯女人”形象和心理医生形象塑造的延续与创新 [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6]王卫新.福尔斯小说的艺术自由主题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