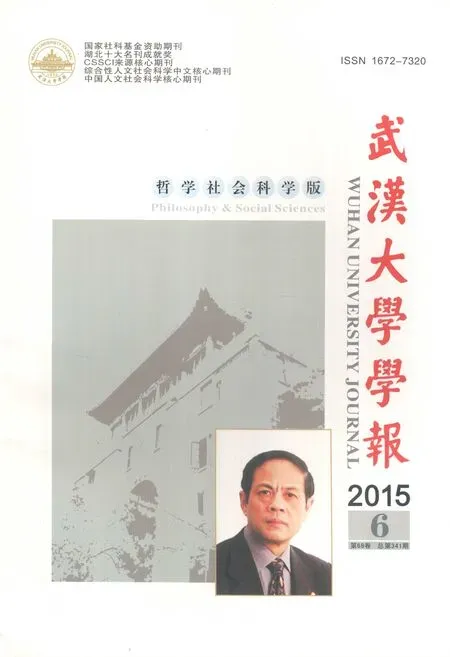中国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理论基础与现实逻辑
赵永红
中国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理论基础与现实逻辑
赵永红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妥善安排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以马克思人民主权理论和民主集中制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得到了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确立,但实践中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性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使其难以完全落实;它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府际关系法治化、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社会全面发展而得以推进,并逐渐接近地方民主与中央集中和谐平衡的理想状态。
地方政府;民主性质;民主集中制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6.004
妥善设置中央与地方关系并在其中恰当定位地方政府的性质,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即“一定区域的公民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选举自己的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等,对该地方的事务实行自主管理的一种法律制度,它也是国家对于地方行政区域所采取的一种管理形式”(张千帆、葛维宝,2009:152)。在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自治以外,中国一般地方政府是一种混合型地方政府,而不是自治型地方政府(李明强,2010:106);也有学者从宪法和相关法律文本分析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具有自治性质,甚至其职权“远比实行地方自治国家的地方政府所享有的权限宽泛”(胡肖华、欧爱民,1999:528)。这两种观点对我国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自治性质看法不一,但都不否认我国地方政府具有民主性质,因为地方政府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民主原则,建立了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轴心的民主治理框架。然而,前者对地方民主与中央集中之间关系的探索还有待深化,后者对宪法和法律文本中体现中央集中条款的分析不够充分,因而都不能完整揭示我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制度基础及其现实状态。笔者从我国国家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即人民主权理论和民主集中制思想出发,分析宪法和相关法律关于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实现路径。
一、中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实行地方民主?地方政府民主治理权利从何而来?地方民主和中央集中领导之间是何种关系?这是国家结构设计和地方民主实践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关于地方民主权利的来源共有四种思想:自然权利思想、国家赋权思想、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和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后两者。
西方学者将地方民主形式确定为地方自治,并认为其权利来源的论证主要有四种理论:“固有权”学说、“传来权”学说、制度保障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熊文钊,2005:11)。对这四种学说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关于地方自治权利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思想:自然权利思想和国家赋权思想。中国地方政府民主属性的论证主要以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理论为理论基础,但不能说这一思想体系与西方主流的地方自治思想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
关于地方自治的自然权利思想有两种分支:团体自然权利说和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团体自然权利说认为,地方团体像个人拥有自然权利一样拥有天然的自治权,在时间上它的实践先于国家主权的实践,因此比国家主权具有优先性(张庆福,1998:372)。但是,团体自然权利说有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将地方自治权实践上的先发性作为论证其价值上与国家主权相比具有优先性的根据,这是不可靠的论证。在价值上,地方自治权与国家主权谁重要谁优先的问题需要另外的论证。二是地方团体、国家与人的存在毕竟不一样,它们是人们生活与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与天赋人权说相比,地方自治权天赋说的理论根基并不牢靠;三是团体自然权利说没有深入分析团体自治权与团体成员人权之间的关系,如果它认为这种自治权来源于团体成员的人权,那么它就可以归结为人民主权说,如果它认为不是来源于人权,那么团体自治权就可能成为团体控制其成员命运的工具。
契约论人民主权理论认为,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是最高的目的,一切政治制度的选择都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都是个体自主选择、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但是,在处理共同体与公民及其组织的权利关系上,可以将契约论人民主权理论分为卢梭的整体主义和洛克的自由主义两个体系。整体主义人民主权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将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从而形成政治共同体,共同体的重大问题只能由共同体整体决定,不能由公民个体、社团和地域性组织决定(卢梭,1980:12-14),因此共同体可以决定是否给予地方自治权,这样地方自治权就不能直接从个体自然权利中延伸出来。而自由主义契约论体系认为,人民将部分权利委托给了国家,但还保留了其他权利(洛克,2007:138),因此通过行使自然权利而形成的国家主权与人民的地域性自治权具有同等地位与价值,都是人民主权的重要形式,这一点在人民结成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契约中就被承认与保障。因此,按照这种理论,各种层级的政府是实现人民主权的不同形式,虽然在地域上它们之间存在包含关系,但在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它们之间是职能分工的并列关系。
国家赋权思想认为地方自治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不是地方公民和团体所固有的(张庆福,1998:371)。由于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国家赋权存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国家具体的统治者,如中世纪的国王给地方赋权,从而形成地方自治权利。阿尔伯特·怀特在其专著《国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英国民主起源的研究》中认为,“在英格兰,从12世纪起到中世纪末期,国王实现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臣民,而不是完善的官僚体系。国王主观上为自己的利益在政府中广泛利用民众,长久地把负担与责任加在民众身上,这大大有助于民众产生‘英国人政府’的感觉与能力。在自治政府形成过程中诺曼与安茹王朝的训练比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起的作用更大”(陈日华,2008:111-117)。另一种是国家整体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给地方政府赋权,其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统治阶级的赋权,在自由主义看来是人民主权的赋权。但是,国家赋权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困境,并不能解释地方自治权利的最终来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权利只能来源于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人们认识到了这种需要,就为自己确认了这种权利。国家统治者的赋权只是确认或培育了民众的这种现实需求,国家整体意志的赋权不过是从法律上肯定了民众的这种需求。
马克思形成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包括地方民主将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和其他领域,从而得以彻底实现。马克思认为,人权、自治权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反映人的价值追求的规范性概念,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天赋的、自然的。马克思批判了自然权利的唯心主义根基,但没有否定自然权利思想的价值,他认为,自然权利、人权等概念与范畴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人对其现实存在状态的不满,为人建构了一种理想的存在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仅靠文化、政治、法律的建设与保障是不能实现的,而主要通过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来逐步实现;因此,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2003:18)。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整个社会的高度自治,自治在各个层次和领域中实现,地方自治是社会自治的一部分,是国家消亡、权力真正回归社会的形式。而历史上的地方自治,一方面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社会自治的属性,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社会的手段。
列宁和毛泽东在领导党和国家建设中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并将之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列宁出于加强党内民主的需要在1905年将他以前提出的“集中制”改为“民主集中制”,并在俄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对其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是说,党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处理或者通过代表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由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可以撤换的。”(列宁,1963:418)以后,俄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思想有一定的发展,认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1952:1058),从而指出民主与集中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目的;他还从领导决策、领导方法等角度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走群众路线,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要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行集体决策。新中国成立前,他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思考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1952:670);中共七大上他对这一点再次进行了肯定和阐述,拟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国家制度(应克夏,2012:24)。建国后,民主集中制被用到国家结构设置和政治生活组织之中,其基本要求在几部宪法中都得到了确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主权的国家权力组织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国家结构设计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经过民主程序而产生,并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央是这个体系的领导者和代表,但这种地位是建立在地方民主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是这个体系的地方代理者,它依据民主原则进行地方治理活动,但地方性事务是整个政治共同体事务的一部分,代表共同体整体意志的中央政府有权对地方事务直接治理或领导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因此地方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并不是纯粹由地方力量决定的自治型组织。所以,民主集中制包含对人民民主和地方民主的肯定,既强调个体和地方政府民主治理权利的运用,也要求政治共同体中部分意志服从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意志。
二、中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制度设计
中国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八二宪法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从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
八二宪法把国家的人民主权性质规定与国家机构设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分成两条进行表述,一改前三部宪法将二者集中在一条中进行表述的做法。宪法第2条对国家的人民主权性质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3条接着对国家机构设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原则”,宪法其它条款、《立法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政府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条款对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产生、职权的规定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中可以明确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运用,是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会行使民主权利和中央领导地方原则的统一:第一,在国家机构与人民的关系方面,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通过选举和权利委托组织国家机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为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第二,在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国家权力机关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国家机构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地方民主而产生决定了中央国家机构意志的最终来源是地方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民主原则,它在国家机构设置中的运用就是从横向上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及地方依托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治理的权力,纵向上确立了各级人大代表从下向上产生的途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从下到上经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国家主席、一府两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体现了中央国家机构的产生和权力获得是从下向上的过程,体现了人民主权和高度民主的原则;全国人大的地位和产生方式决定了在中央层面国家的政治活动是以地方民主及来自地方的人大代表对全国性事务治理的参与为基础的,应当体现地方民主的要求,当然地方民主的要求是在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中得到平衡与实现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关于地方国家机构的产生及其权力规定体现了地方民主的原则。宪法第9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97条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由地方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第99、100、104条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地重大事务的管理权力和省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第101条规定地方“一府两院”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宪法第107条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这些宪法规定赋予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对它负责的地方行政机关高度的民主自治权。另外,《立法法》第63条、73条分别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地方性法规立法权、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规章制定权,并且第86条又规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这条规定是对地方人大立法权的保护。还应注意的是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之间具有上下级从属关系。宪法、《立法法》等对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权力进行了规定,并规定地方人大要负责全国性法律、规章在本地区的落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人大是全国人大的下属机构。相反,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地方和团体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因此,全国人大的产生和权力来源在地方和社会。所以,地方人大以及由它产生、对它负责的地方国家机构,被宪法和相关法律赋予了高度的民主自治权,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另一原则就是集中,集中是民主的应有之义。所谓集中,指在横向上政治生活应当遵循在保护少数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在纵向国家结构关系中就是下级政府要服从上级政府、地方要服从中央,其本质是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根据这一原则,宪法和相关法律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规定。一是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权限的规定。全国人大对全国性事务进行立法、作出决定,地方人大和政府要落实这些法律、服从这些决定,全国人大具有对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宣布无效等权力,这些规定都是民主基础上集中的表现。二是关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之间关系的规定。宪法第89条第四款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第11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所以,集中是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在横向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分别是全国意志集中与执行的组织载体,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行政机构是地方意志集中与执行的组织场所;在纵向层面,就是地方人大要保障全国性法律和高层人大制定的法律在本区域的落实,下级行政机关要服从上级行政机关,所有地方行政机关都要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地方事务的管理者,还是国家事务在地方上的执行者。那么从制度设计逻辑上讲,中央集中是否否定了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呢?根据前面对民主集中制的分析,国家权力设置及运作以人大为轴心能够实现纵向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因为全国人大的意志是在地方民主基础上形成的,而国务院要服从全国人大的意志,因此全国人大的集中行为和国务院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易否定地方人大的意志以及地方行政机构执行这一意志的行为。
三、中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践状态
中国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被赋予的,因此,民主集中制的运作直接影响其实践状态。总体上,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化制度逻辑无法完全落实,纵向上中央集中与地方自主之间的关系摇摆不定,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制度性自主,地方民主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制度空间;横向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民政治参与等民主机制不太成熟,无法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提供现实支撑。
一方面,民主集中制的现实运作没有使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制度自主性,使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失去了前提。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发展一盘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主要偏向于中央。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必然导向权力集中和严密的社会管控,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科层制组织,地方不仅无法实现民主而且只能作为整个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命于中央的集中领导。但是,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统一的政策制度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为了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往往不得不向地方放权;但是,地方过多自主性又不利于中央政策的统一执行和计划体制的运作,于是又需要对地方收权;因此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就出现了集权与放权的摇摆。在这种利益的反复平衡中,失去人大民主治理作用有效支撑的中央集中居于主导地位,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自主性和民主性的发展空间相当有限。
市场化改革后,地方社会成长使得民主集中制运行不得不更多考虑地方并在中央集中与地方自主之间进行平衡。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就是国家向社会、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过程。社会开始从国家控制下获得自主发展的力量,在市场运作和权力干预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利益分化,单位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体利益呈现复杂纠结的局面。民主集中制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在横向上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观认同无法通过简单的“集中”达致和谐;在纵向上地方社会和利益获得了独立发展,地方治理不得不更多考虑地方利益诉求,在很多政策问题上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央不断在行政、财政等方面向地方分权,地方自主性日益增强并与中央集中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张力,这使得地方人大表现出“国家代理人”和“地方代理人”双重角色(何俊志,2007:53-59)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行政机构对本级人大负责和对中央与上级政府负责之间的矛盾。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一种“行为性联邦”关系(郑永年、吴国光,1995:23)和财政联邦关系(Jin,Qian&Weingast,2005:1719-1742),但国家始终没有依据这种现实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重新划分;相反,按照宪法文本中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中央政府对一切国家事务,包括地方事务有权管理,并且执政党由于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级党委领导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为上级党委领导的政府的执行者;所以,“中央‘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都不等于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也不等于地方民主”(马岭,2013:7),地方政府依然缺乏制度上的权力自主性,从而制约了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
从理论上讲,建立在各级人大有效运作基础之上的中央集中并不以损失地方民主为代价,相反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但现实中人大的民主治理作用比较有限,各级人大之间并没有完全实现各级地域共同体民意的纵向贯通,因此中央集中更多是一种行政性集中,而非建立在人大民主治理作用有效发挥基础上的政治性集中。所以,这种集中只能是以牺牲宪法和法律中设计的地方自主性和地方民主为代价的。另外,即使各级人大能够有效运作,但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国务院事实上都没有能力对全国各地地方事务的民主治理进行具体领导与监督,因而很难实现中央集中与地方民主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央政府依靠地方层层职责同构的压力型政府体系来领导地方治理(杨雪冬,2012:6),中央根据国家治理需要为地方治理提供战略框架、主要目标和方针政策,中间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将政策本地化并将治理任务和压力向下层层分解,县乡政府主要承担直接治理社会的责任;地方政府因此成为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延伸机构,虽然有完成任务的强烈主动性,但缺乏制度性自主权,很难为地方人大等民主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稳定的制度性自主空间。
另一方面,以人大为轴心的民主治理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是地方政府民主性质无法落实的重要原因。宪法中民主集中制的主要组织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各级人大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使各级政权横向上的民主治理得以实现,以及纵向上各级建立在人大意志基础之上的集中得以协调起来。但由于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链条并不紧密,人大立法权、预算审批权、监督权等重要宪定权的履行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以及人大很少运用重大事项决定权就地方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决策等方面的原因,各级人大的民主治理作用还比较有限,制约了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市场化改革后,地方民主治理的压力日益增大,各级人大的民主治理作用不断增强,但是其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在现实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离地方民主治理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既有人大制度不完善及其治理能力有限等方面的制约,也与地方治理结构中党、人大和行政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关。党是人大、行政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的领导力量,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但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这一制度优势能否充分实现。现实情况是,党委是地方治理中的重要领导者和决策主体,诸如地方性法律制定、预算审批、人事任用等方面党委的决策通过人大变成国家意志并交由其他国家机关得以执行;但日常大量重要问题的决策并没有经过人大审议变成国家意志,再交给行政机关执行这一程序,而是直接通过行政机构来落实,这就制约了日常治理中人大审议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落实,不利于党对人大民主治理作用的开发和利用。
另外,地方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不成熟也制约了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地方民主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不仅可以弥补人大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且对培育地方民众民主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后,各地进行了民主治理创新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但总体上地方治理还是一种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地方居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还不完善,他们这方面的素质与能力也不强,使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缺乏民主主体和实践的支撑。因此,地方政府获得的非制度化行政自主权不仅没有为地方民主治理创造有效前提,而且强化了行政性治理的主导地位,挤压了地方民主治理发展的空间。
总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政治制度上的主要承载者,这一制度为各级政府设定了民主性质,同时它的有效运作能够使中央集中与地方民主和谐统一,但现实中民主集中制运作和人大作用的发挥遇到了诸多制约因素,从而使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不甚理想。计划体制之下,国家治理主要是一种行政性治理模式,因而人大的民主治理作用相当有限,中央行政性集中取代了地方自主和民主;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彻底重构了民主集中制运行的社会基础,中央集中和地方自主之间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张力,地方民主处于成长与发展过程之中,但是人大依然没有很好承担政治性集中的职能,中央行政性集中使地方政府缺乏稳定和制度化自主性,因而无法为地方民主提供基本前提;同时,地方人大等民主机制比较薄弱,无力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提供直接支撑。因此,民主集中制只有顺应市场化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进一步发挥人大的治理作用,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进行更加具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中央集中与地方民主的和谐平衡。
四、中国地方政府民主性质落实的路径
地方政府民主自治的落实不仅需要地方民主治理机制的建设,还需要在法律层面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使地方政府具有自主性。这关系到国家治理结构的改革完善,是国家宪法秩序建设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地方民主自治建设往往与宪政发展交织在一起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路径:英美地方自治先于宪政并成为后者发展的基石,日本和东欧转轨国家在宪政建设过程中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地位(阿姆纳等,2005:19-37)。中国地方民主建设可以参考中外历史上地方自治建设的经验得失,但不可能在西方宪政框架下进行,而只能是在宪法完善与实施过程中推进。中国宪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设计的国家结构,规定了一般地方政府具有民主性质。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宣示要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所以应当按照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推进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这种落实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理论,制度框架是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宏观操作方向是通过宪法层面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以及地方人大等民主治理机制的有效运作和社会自治条件的全面发展,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创造制度和社会条件。
首先,要完善宪法和相关法律,实现中央与地方法治化分权,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创造前提。民主集中制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的统一领导,但事实上即使各级人大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并形成上下意志的和谐贯通,中央也不可能直接领导全国各地地方性事务的治理,或者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进行审查性监督,现实可行的只能是中央与地方进行分权,当前这一分权主要是极不稳定的行政性分权,而不是法治化分权,因而不能使地方政府获得制度性自主,并充分发挥其民主治理的潜能。因此,应当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领导什么、怎样领导”,并对中央和地方管理的事务进行分解:全国性事务中,中央专属性事务由中央管,牵涉到地方的由中央、地方合作管,可以委托地方管的由地方代管;专属地方的事务由地方管,中央主要从政治和法律上对地方进行监督。并且要根据事权划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地方有处理本区域事务的财政保障。与此相应,地方政府纵向间也需要进行法治化分权。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纵向府际间事权和财权的法治化划分将为地方自主提供法治保障,从而为地方政府民主的实现提供前提。
其次,要充分发挥人大民主治理的作用,使之成为民主集中制运作的枢纽,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提供支撑。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民主不仅包含了集中的环节,而且集中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符合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才能使中央集中与地方民主和谐统一。我国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其有效运作才能使民主集中制的运作保持民主性质,并充分实现国家的人民主权性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发挥平衡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政治作用,对地方民主起到政治性集中与监督作用,保证地方民主的运作符合全国整体意志和利益的需要。但是,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就必须从制度上理顺党、人大和行政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党应更加注重利用人大这一制度平台进行国家治理,“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胡锦涛,2012:23),使各级人大成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落实的基本制度形式,并通过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推进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
最后,要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创造社会条件。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不仅需要法律、制度、权力和财政的保障,还需要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动力,是民主和法治进步的基础,是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解决、民主与集中不断得到更好平衡的条件。民主法治理念要深入民心成为习性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民众民主法治精神的培育,既靠文化和公民素养教育,也有赖于民主和法律实践,尤其是基层民主实践。基层民主包括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乡镇民主,既是地方政府民主性质落实的基础,也是民众民主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途径。国家应当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及时清除制度运转的障碍,想方设法让基层民主运转起来,为民主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创造社会条件。
五、结 语
地方民主治理是国家民主性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八二宪法在国家结构设计时以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理论为依据,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具有民主性质;但是民主集中制的现实运作决定了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程度。计划经济时期,民主集中制运作更倾向于中央集中,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延伸机构,缺乏制度化自主性,无法获得民主性质实现的有效前提。在市场经济社会,地方利益成长使得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行政和财政上的自主性,地方民主治理的压力也日益增大,从而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与动力。但是由于现实中人大民主治理作用的有限性,以及中央行政性集中与行政分权依然无法为地方民主运作提供制度性自主空间,使得民主集中制运作的理想逻辑很难在现实中实现,地方政府的民主性质也无法充分落实。因此,民主集中制应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法治化分权,进一步确立人大民主机制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经济和民主法治文化的发展,为地方政府民主性质的落实及其与中央集中的和谐平衡提供坚实的制度和社会基础。
[1] 埃里克·阿姆纳等(2005).趋向地方自治的新理念.杨立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陈日华(2008).中古英国地方自治研究综述.世界历史,5.
[3] 何俊志(2007).中国地方人大的双重性质与发展逻辑.岭南学刊,3.
[4]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5] 胡肖华(1999).地方自治:当代中国的实践与背离.湘江法律评论,3.
[6] 李明强(2010).地方政府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7] 卢 梭(1980).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 洛 克(2007).政府论.刘晓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9] 马克思(2003).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马 岭(2013).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4.
[11]毛泽东(195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列 宁(1963).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3]熊文钊(2005).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杨雪冬(2012).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11.
[15]应克夏(2012).“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炎黄春秋,10.
[16]张庆福(1998).宪政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
[17]张千帆、葛维宝(2010).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南京:译林出版社.
[18]郑永年、吴国光(1995).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H.Jin,Y.Qian&B.Weingast(2005).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
◆Vol.68.No.6 Nov.2015.040~047
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Theoretical Basis and Realistic Logic
Zhao Yonghong(Ningbo University)
It is important to arr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modern state building. 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theory of people’s sovereignty from Marx and the thought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s its theoretical base,and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organic law of local governments.In practice,it is difficult to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ecause of imperfect system and restrict of social conditions.During the modernizing of state governance,it will be realized and get progressively closer to the ideal state of harmony and balance of local democracy and concentration by legalizing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the people’s congresses playing their role fully and the society having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democratic centralis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YJC810061)
■作者地址:赵永红,宁波大学法学院;浙江宁波315211。Email:zhaoyonghong@nbu.edu.cn。
■责任编辑:叶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