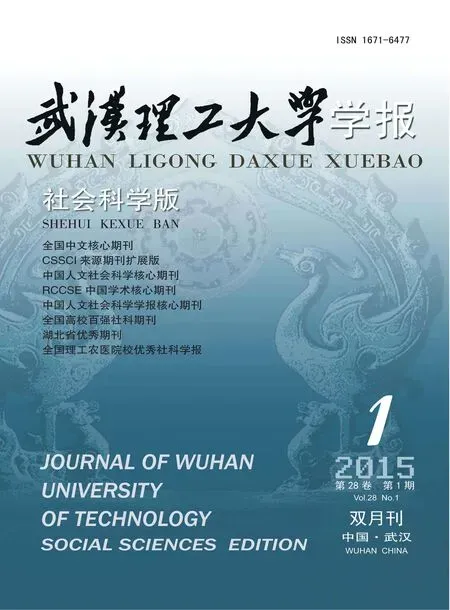集体意向面面观∗
柳海涛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2.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 400044)
集体意向面面观∗
柳海涛1,2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2.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 400044)
除了意向主义解释,集体意向在非意向论、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现象学中展现出了多幅面孔,它们对集体意向相互印证。在广泛的意义上,集体意向可被分为为四种类型:累积型集体意向、弱规范性集体意向、非规范性集体意向和静默式集体意向。集体意向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心理特征。
集体意向;集体行动;个体意向;实践
虽然集体意向是一个新问题,但已受到心灵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密切关注,并且逐渐延伸到了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集体意向有不同的表示形式,最早是芬兰哲学家托米拉采用“我们意向”(we-intention),后来,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哲学系的吉尔伯特采用“共同意向”(joint intention),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布莱特曼提出了“共享意向”(shared intention),塞尔直接用“集体意向”(collective intention)。它们虽然都蕴含着集体意向,但使用不同的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对集体意向的解释和基本态度有所不同。最近几年,不少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集体意向问题。当前,集体意向理论面临的困扰是在对集体行动的意向解释中,集体意向的本体论地位还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侧面给予集体意向一个全景式的论述,进而试图回答何谓集体意向。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对集体意向的意向主义解释,这是目前主要的观点和论证方式;第二部分从非意向主义、现象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四个侧面来描述集体意向,以期获得对集体意向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三部分从广泛的意义上把集体意向看作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心理特征,进而把集体意向分为四种类型,并尝试回答它的存在方式。
一、意向主义解释
托米拉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集体意向并对其进行系统论证的哲学家,自1988年至今,他连续发表了10多篇文章来讨论集体意向的相关问题。托米拉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集体意向:假设,一个集体的负责人在公告板上通知,计划下周六清扫停车场,愿意参加的人在通知下面签名。一旦集体成员在公告板上签名表示愿意参加清扫停车场的集体活动,就形成了集体意向。这个论证也被称作“公告板隐喻”。托米拉对集体意向的定义如下[]:
集体G中的任何一个成员A有“我们意向”实施集体行动X,当且仅当:
(1)A意图做X中他的份额(do his part);
(2)A相信X会实现,并相信G中有适当数量的成员为了实现X而会做X中他们各自的份额;
(3)A相信在G中,成员之间有一种相互(mutual)信念,即彼此相信为实现X而意图做其中各自的份额;
(4)(1)部分地是因为(2)和(3)。
托米拉把成员之间的相互信念作为形成集体意向的关键,这个定义不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向,集体中大部分成员具有合作意向就可以了。
吉尔伯特在论证集体意向时,引入了复合(plural)主体。她认为[2],集体行动的主体是“我们”。集体成员有集体意向做某事,当且仅当他们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作为“一个主体一样(as a body)”做某事。在吉尔伯特的整体主义论证中,集体意向的主体是“我们”,集体是集体行为的主体。集体有一个共同目标,每个成员都了解这个目标,并且承诺为共同目标紧密协作。但她没有解释复合主体如何具有自身的权利和条件去作为一个行动主体,也没有论及个体在集体中的地位问题。
现有的集体意向理论,一般都给出了产生集体意向的充分条件,但没有说清楚它的必要条件。因此,有人认为,集体意向理论主张的集体行动,它所执行的意向不是一种特殊的意向,而仅是说明了个体意向可以按照某种方式有资格共同意图做某事。所以,它们还没有在任何字面意义上表明意向是共有的[3]。
二、其他视域中的集体意向
(一)非意向主义
对集体意向的意向主义解释是以个体意向为基础的,通过个体意向间的某种关系才能形成集体意向。但它有两个问题:一是循环论证。在托米拉对“我们意向”的定义中,“做他的份额”是个体为实现集体目标做他自己的份额,在“做他的份额”中已经包涵着集体意向的观念,因为如果没有对集体目标的事先理解,个体就无从知道集体中“他的份额”。在吉尔伯特的论证中,共同承诺来源于个体明确表示的合作意向,共同承诺形成的同时集体意向也就产生了,然后再把集体意向归属于由共同承诺所构成的复合主体。二是例外情况。实际生活中会有一些特殊情形,我们知道家庭是常见的集体形式,但是婴儿、青春期子女的反叛行为、甚至家庭中的智障成员,他们无法表示自己的意愿,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他们属于这个集体。吉尔伯特的“共同意向”排除了集体中的非意向个体,它对集体意向的解释过强。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就出现了以目标为导向的非意向主义立场。
非意向主义不仅要解决例外情况,还要避免意向主义中的循环论证。其观点[4]是:一组个体形成一个集体,当且仅当这些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或利益而相互依赖,而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非意向主义看到了许多集体及其相关行为的产生并非是基于个体成员间明确的意识,很多时候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兴趣、目标等所实施的个体行动的结果,其间没有涉及到集体意向。在逻辑上看似乎是先有个体,之后才能通过个体意向组成集体。集体一旦形成,它就具备一定的自主性。置于其中的个体并不是时刻都要保持对集体的自觉,他在集体中仅仅是如此做而已(just do it)。无意向的集体也有可能是非意向主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但是,这种无意向是指没有强集体意向,至于是否隐含着潜在的弱集体意向,放在后面分析。
(二)发展心理学中的“假扮游戏”
假扮游戏(pretend play)是儿童早期发育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由于它具有先天性,因而仍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婴儿的假扮行为有阶段性,从第9个月时开始,逐渐从简单到复杂,从外显到内隐,24个月前后达到高峰。发展心理学中普遍认为人类的社会认知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在四岁之后形成的信念-愿望(believe-desire)结构,即所谓的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而在信念-愿望结构产生之前的假扮行为却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早期的假扮游戏背后已形成了初步的意向状态,12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理解基本的意向行动。假设一个成人使劲掰一个盒子,婴儿就确信他是在试图打开盒子。16个月的时候,婴儿可以用不同方式模仿同一种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还是偶然的。人具有生物适应性能力,这种能力在社会互动中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认知。婴儿在9个月前后,在与父母和家庭环境的互动中,首先形成了“共享性”能力,能够把他人看作是具有意向性的行动者,把自我和他人等同起来。随后,慢慢具备了视角性理解,能对同一事件用不同视角作出不同反应,也即视角转换的能力。最后,在12个月以后,开始运用语言符号,儿童学会规范性评价,可以从反思性的立场实施行为[5]。幼儿的假扮行为虽没有成人那样的概念认知结构,但有初步的意向结构。因为在假扮游戏中,幼儿不仅能实施非严肃的假扮动作,而且能够有所发挥,推论到其他假扮行为。这说明,幼儿在早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行动意向结构。早期的假扮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意向形式,并且它使人类认知独特化,从而区别于其他动物。在假扮游戏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学习,逐步使认知符号化,进而学会社会角色扮演,理解规则约束性的制度行为。因此,假扮行为蕴含着集体意向和制度现象的本质结构[6]。如果说“假扮行为”揭示了儿童早期形成集体意向的社会因素,那么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就为集体意向提供了神经生理学机制。
(三)镜像神经元
在神经科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猕猴在做一个指向目标的动作(如抓取香蕉)或者看到同伴做同样的动作时,在它的运动前区皮质(premotor cortex)会有相同的神经元被激活。也就是说,猕猴自己做一个动作时所激发的神经元,在看到另一只猕猴做类似的动作时,也同样会被激活,这些神经元就被称为“镜像神经元”。后续的研究证实,人在实施或观察同一个动作时,镜像神经元也有相似的活动。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理解他人内隐的体验和心灵提供了重要的神经学证据。当有机体面对他人有目的的行为时,有机体产生了一种“意图共鸣”的特殊现象状态。这种现象状态通过将他人的意向分解、形成观察者的意向来产生通晓其他个体的特殊品征[7]。
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手被割伤流血时,我们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就会发生反应,使我们自己仿佛被割伤了一样产生痛感。这虽然是幻象,但它承担着重要意义,借助它,我们可以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意图和内在心理状态。在共同经验幻象中,我们经验到了一种无法消除的接近感和一种在认知上的直接的身体等同感,这是我们通达他心的基础。在我们的自身经验中,我们知道存在着没有发展成为真实意愿,也不会产生真实行为的弱意向类型。我们发现自身无意识的活动,尤其是在对他人身体活动产生共同经验的情境下,类似于一种“预示性活动”[8]。吉尔伯特等人对集体意向过强的意向论解释,使它遗漏了以潜在形式存在的集体意向。对这种弱意向类型的把握,需要我们超越仅在理智上对他人意向行动的理解,不少情况下,我们是以默许或同感的方式参与其中,虽然这种隐性的共同意愿模式并没有产生真实的行为,但它预备了集体意向。
(四)现象学的“共情”
共情(empathy)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认知的关键部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它提供了神经机制说明。同时,共情也是现象学关注的重要论题。在现象学的视野里,共情是一种特殊的意向性形式,它通向交互主体性。我们对自身的体验是直接给予的,而对他人意识状态的觉知是推论的,呈现方式的不同使我们对他人内在状态的正确理解就成为一个偶然性的事件。所以,托米拉认为,在集体意向中,允许成员A相信其他成员会共同做某事的信念是可错的,甚至是幻觉。塞尔更是认为与外界缺乏互动的“缸中脑”也会具有集体意向,不管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也不管其他成员是有意识的人还是一具具行尸走肉。
心灵与身体的割裂不仅为唯我论留下了空间,也提供了一副扭曲的行为图景。我们的意图、情感等不仅是主观体验,它也表征在身体行为当中,并被他人看见。主体性并非远离世界和他人,正如梅洛-庞蒂[9]195所言,对于我自身而言,我总已经是一个陌生人,并且因而向他人敞开着。即,我是一个具身(embodied)的在世之在,我才能够与那些以同样方式存在着的他人相遇并理解他们。舍勒也反对把心灵看作是排他的、与身体和世界隔离的纯粹内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也不认为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论与自我内在体验的确定性之间存有差异,因为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向别人隐藏,只是以不同于向自身展现的方式向他人敞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隐秘的私人空间里,而是一个公共世界里,每个人自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因此,我们的活动渗透着对他人的指涉。我并不仅仅为我而存在,而是涉及了交互主体性,我的意向性亦是如此[9]213。
这些不同视域对集体意向的描述体现为两种路径:经验实证进路和形而上学进路。发展心理学反映了集体意向的社会性因素,镜像神经元揭示了集体意向的生物性因素,现象学则通过引入交互主体性呈现了我们对集体意向的内在体验。可见,集体意向具有社会性、生物性和现象性等多重特征,对它的进一步认识就需要深入分析它的不同类型和存在方式。
三、集体意向的类型和存在方式
从不同侧面和视域来看,集体意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有独特性,它的意向内容、规范性功能、满足条件、实现过程等都与个体意向迥然不同,它不能被个体意向还原或取消。若对集体意向的定义过强,反对者就可轻易地找出反例给以质疑,如集体中非意向个体的存在。笔者认为对集体意向的争议在于没有详细区分它的层次性,由强到弱,我们可以把集体意向分为四个类型:
一是累积型集体意向(强集体意向):集体中每个成员明确宣示自身意愿,达成承诺,为实现共同目标密切合作,吉尔伯特论证的就是这种类型。被称为累积型集体意向的原因是每个成员都有主动的承诺,累积一起就形成了集体意向。累积型集体意向有强的行动规范性。
二是弱规范性集体意向:它不要求每个成员都具有关于某个共同目标的意向,只要集体中的核心成员具有就可以了,核心成员起着主导作用,其他成员默认即可。这一类型可以解释集体中特定的非意向个体,它具有弱的规范性,甚至允许个别成员的反抗行为。因此,前面的非意向主义对集体的描述虽然没有累积型集体意向,但它仍然包涵着弱的集体意向。弱规范性集体意向可以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国家、社团、组织的解释。托米拉的“我们意向”属于此种类型的集体意向。
三是非规范性集体意向:它主要是指那些因某些特殊爱好或兴趣而组成的松散群体,如某歌星的粉丝团、音乐发烧友等。在这些群体中,成员们公开了自己的意向,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知识,但它对个体行动没有明显的约束性。
四是静默式集体意向:它存在于个体的知识体系中,但在群体中没有公开性的宣示,如我们知道吸烟的害处,但没有因此而组成一个戒烟组织;看到外面正下大雨,你递给了我一把伞;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的谈笑声停止了……诸如此类。静默式集体意向可归结为人的社会性,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合作者,我们的生活世界隐匿着这种集体意向。
把集体意向分为这四种类型,实际上把集体意向广义化了,它不仅指向集体行动,而且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心理特性,所以集体意向具有普遍意义。现有集体意向理论关注的是前两种类型,着重在认识论上对它进行认知分析,但集体意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规范性,对它的辩护更应从实践的规范性上着手。
对集体行动的解释有两种方式:“我们模式(we-mode)”和“我模式”(I-mode)。“我们模式”强调复数行动主体的本体论地位,它不能还原为单数主体;而“我模式”认为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向最终只能归结为个体行动和个体意向。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还原关系,而还原涉及层次上的不同,对这两种模式的概念分析往往会陷入两难。但实际生活中,“我们模式”和“我模式”经常顺利地无缝切换。也就是说,“我们模式”和“我模式”同时存在于行动者头脑中,根据具体实践不同,这两种意向形式互相转换。比如,在足球比赛中,后卫运球到前场,若他选择自己直接进攻,这时他的意向就是“我模式”的“我要单独进攻”;如果他观察同伴的站位后传球,他的意向就是“我们模式”的“我们要配合,然后进攻”。这两种意向形式是同时存在的,在他头脑中根据不同的实践要求互相切换。这实际上和塞尔的观点类似,就是集体意向和个体意向并行存在,只不过塞尔没有引入实践,他强调集体意向是人本能性的生物学能力。意向性是个体心灵的内在属性,它在根本上仅是个体的意向,无所谓集体性。然而,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是两种不同的行动类型,根本区别在于集体行动中的个体成员采取了集体的合作视角,他们因此而分享了共同知识,从而形成集体意向。所以,集体意向的存在不能脱离实践和个体心灵。
根据从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现象学等视角对集体意向的描述,以及集体意向与实践理性和个体心灵的关系,我们认为,虽然现有集体意向理论以个体意向为起点来论证集体意向,但在本体论、认识论上和概念分析的逻辑先后关系上,个体意向都不具备优于集体意向的先在性,集体意向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以实践为基底,个体意向和集体意向同时存在。也可以说是,以生活实践为背景,集体意向同一于个体意向。这正是集体意向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由集体意向的生物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多重特征决定的。
四、结 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现有集体意向理论的主要观点,它表现为在分析哲学的视野内对集体意向进行意向主义解释;然后从其他视角论述了集体意向展现出的多幅面孔;最后从广泛的意义上把集体意向细化为四种类型,把它看作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心理特征,集体意向的存在方式表现为在生活实践中同一于个体意向。由于集体意向是一个新问题,理论的缺陷和分歧在所难免,但它不仅对心灵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预见,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它的认识也必将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1]Raimo Tuomela.We-Intentions Revisited[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5,125:327-369.
[2]Margaret Gilbert.Shared Intention and Personal Intention[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9,144:167-187.
[3]J.David Velleman.How To Share An Intention[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7,57 (1):29-50.
[4]Elizabeth Cripps.Collectivities Without Intention[J].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2011,42(1):1-20.
[5]Micheal Tomasello,Hannes Rakoczy.What Makes Human Cognition Unique?From Individual to Shared to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J].Mind&Language,2003,18(2):121-147.
[6]Hannes Rakoczy.Pretence a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J].Mind&Language,2008,23(5): 499-517.
[7]维托利奥·加勒斯.从神经元到现象体验[J].张静,译.求是学刊,2008(5):6-10.
[8]D.洛马尔.镜像神经元与主体间性现象学[J].陈巍,译.世界哲学,2007(6):82-87.
[9]丹·扎哈维.主体性与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M].蔡文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文 格)
Collective Intention's Different Faces
LIU Hai-tao1,2
(1.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Shanxi,China;2.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Except for intentionalism,the collective intention has multiple aspects in different fields of non intentionalism.They ar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neuronal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These different aspects confirm each other.The collective inten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 a broad sense:summative,weak normative,non-normative and silent collective intention.Collective intention is people's inevitable character.It is identical with individual intention in practice.
collective intention;collective action;individual intention;practice
B712.6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1.011
2014-08-11
柳海涛(1977-),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心灵与认知哲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X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