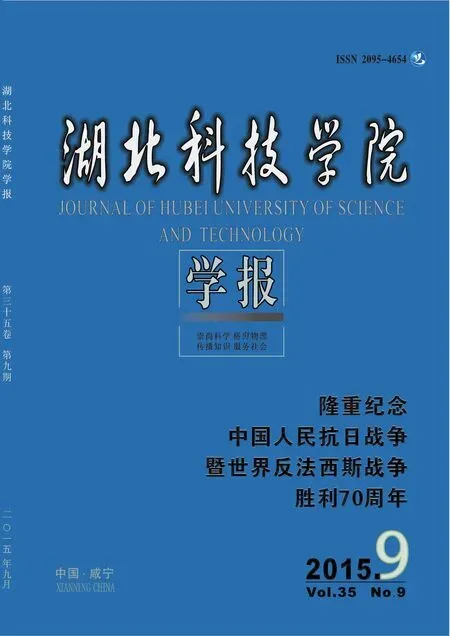我爱,我恨,我痛苦
——浅析《飘》之爱情叙事
成 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1)
我爱,我恨,我痛苦
——浅析《飘》之爱情叙事
成 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1)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飘》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其中生动的爱情故事和深刻的人物形象让人难以忘怀。本文运用诺思罗普·弗莱关于西方文学叙述结构的相关理论,追溯了男女主人公瑞德和思嘉的爱情所走过的四个阶段,指出爱情给人带来的痛苦。
爱;恨;痛苦;《飘》
伍尔夫曾用“我爱,我恨,我痛苦。”[1](P147)来概括《简·爱》的内容。而其实,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飘》中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飘》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深刻的人物心理,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讲述着令人牵肠挂肚的乱世爱情。“阅读着这样的故事,从长卷式的岁月中,看到沧海桑田的变迁,从十几岁的豆蔻年华,看到人物铅华殆尽,渐渐老去。难怪,很多人面对《乱世佳人》(《飘》),有阅读《红楼梦》的相似感慨,南方神话和战争荣光的破灭,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是更为沧桑的生命领悟。”[2](P124)书中人物的变化,让人深深感慨,生活是不易的,生命是沧桑的,爱情是痛苦的。
一、爱的历程
“弗莱认为西方文学的叙述结构,从总体上看,都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自然界的循环周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晨、午、晚、夜,或者是春、夏、秋、冬等等。与此相应,文学叙述的结构也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喜剧,即春天的叙述结构;浪漫故事,即夏天的叙述结构;悲剧,即秋天的叙述结构;反讽和讽刺,即冬天的叙述结构。”[3]而《飘》中的男女主人公瑞德与思嘉在爱情路上的辛苦历程正好契合了弗莱所提到的春、夏、秋、冬四个阶段。
1. 春
初到亚特兰大的白蝶姑妈家时,着黑孝服的思嘉觉得她丧失了穿漂亮衣服、寻欢作乐等所有的生活乐趣,是瑞德的出现为她带来轻松和快乐。喜剧拉开帷幕。“新喜剧一般表现一对年轻男女之间的风流艳事”。[3](P21)
在义卖会上,瑞德与她进行有趣的调侃,还作出顽皮的小男孩一样的表情,使她终于放声大笑,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在为医院筹款的舞会上,她在为要做墙角的花而黯然神伤,而瑞德竟然大大方方地出高价邀请她——正在服丧的韩查理的寡妇跳起舞来了,还紧紧地搂着她,令她激动万分。对她来说,他扮演着浪漫的偷闯封锁线的人的角色。在所有人都穷得叮当响的时候,足智多谋的他可以越过重重封锁,从异国他乡弄来许多令人心动的奢侈品。他给思嘉带来了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因守孝而着黑装的思嘉在对帽子爱不释手的同时又忍不住穿上多彩的衣服来搭配帽子,这就使她终于顺应了内心深处的呼唤,摆脱了虚伪的礼仪,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在义卖会之后的几个月中,瑞德一到县城就要登门拜访她,带她去坐马车兜风或参加舞会,还总要给她带点颇合心意的小礼物。希礼失踪时,他千方百计地动用自己的所有关系,成功地打听到他的下落,让她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2. 夏
时局动荡,然而却为瑞德和思嘉之间平添一份浪漫。
北方佬来了,到处杀人放火,所有的朋友都已逃离,南部的部队也在撤退。刚刚硬着头皮给媚兰接了生的思嘉守着媚兰和刚生的孩子,像只无头小鸡一样恐惧、无助。但一想到强壮、精明的瑞德,烦乱的心便立即平静下来,赶紧要普里西再去找他。他来了,带着一匹冒着生命危险才偷到的瘦马。她想回家。他正言厉色地告诉她不能回家,回家太危险,因为路上到处是北方佬和逃兵。但当看到吓坏了的她像小孩子一样哭着喊着要回家要妈妈时,他伸出了宽大的手掌,把她拥入怀中,轻轻地抚摩她的头发,声音也一改往日的嘲讽, “‘好了,好了,亲爱的,’他轻声说道,‘别哭了。你会回家的,我勇敢的小姑娘。你会回家的。别哭了。’”[4](P383)他的温柔给她无限的安慰,他强大的臂膀给她无限的安全感。战争结束后,他给她钱,使一贫如洗的她得以买下并经营锯木厂,开始起家;她每天要穿过危险的贫民窟,他只要在城里就会来陪她一起走,还一再告诫她要注意安全;俩人结婚后,他带她尽情吃喝玩乐,像宠孩子一样地宠着她。如果晚上她又做噩梦,他就会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把她楼住,用强健的肌肉贴着她,嚅嚅地抚慰她,对她微笑,用慈祥的眼睛看着她,并轻轻地抚平她散落的头发。
3. 秋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任何一个人是复杂的。像海一样深沉。” 思嘉也是复杂的,复杂得她有时候自己都看不懂自己。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她也开始爱上瑞德。但也许正因为两人之间的爱和在乎,却产生了太多的猜忌和痛苦,太多的阴差阳错。悲剧悄悄上演。
在锯木厂,希礼指责思嘉不该雇用囚犯干活,还把她的吝啬与残忍归咎于瑞德,认为她是近墨者黑。思嘉觉得这证明希礼爱自己,一回家就对瑞德声明要分房睡。但当她想起瑞德在晚上抚慰自己的宽大的手掌时,又默默地掉下了眼泪。
在思嘉因为和希礼拥抱在一起被人看到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瑞德对思嘉说了很多,关于他,她,还有卫希礼。之后,他强硬地把她抱起来,全身心地吻他。温柔的火浇遍全身。势不可挡的激情,他要了她。“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女性的渴望强奸源自于‘性感应部位对痛苦的渴望’,女性在性交中的角色是被动的,并从而具有自我虐待的性质,她的唯一的乐趣是承受痛苦。”[5](P218)她被征服了,然而却无比甜蜜,心醉神迷。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他已走,她看着凌乱的床,第一次像个新娘一样感到不安,因为要见他而感到激动。然而接下来的两天,她都没有见到他的踪影;而当他再次出现,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噢,你好。”[4](P950)思嘉觉得,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怎么能如此轻描淡写?她怀疑他又是去找妓女去了——而且是在对她,郝思嘉,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她感到莫大的耻辱。事实上,瑞德那天晚上的尝试对他自己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想看看思嘉到底爱不爱他,到底想不想要他,而他之后对思嘉的回避其实也是出于羞涩和不安;如果见面时思嘉能稍微主动一点,那他就会即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满腹狐疑的思嘉却对他冷言冷语,而他也觉得再没有解释的必要,两人之间再次展开唇枪舌剑。
瑞德带着他和思嘉的爱女邦妮出去了三个月。思嘉在怒气过后,又开始思念他了,而且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一见面,以为思嘉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瑞德又故意用嘲讽的语调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还故意问思嘉孩子是不是希礼的。气愤的思嘉伸手去抓他,却不小心掉下楼去,流产了。她病倒了。虽然想他,但她不敢说,她觉得他不想要她。而他呢,苦苦等候在门外,等着她对自己的呼唤,却没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吸烟,茶饭不思,衣冠不整,人也瘦了许多,脸上尽是痛苦,目光呆滞,甚至还发出了绝望的哽咽声。
4. 冬
瑞德完全变了,让人感到一种悲剧的反讽。“悲剧反讽的中心原则是,主人公不管遇到什么样不寻常的事都应该在结果上与他的性格不协调。”[1](P17)
思嘉生完病后的日子里,油嘴滑舌、玩世不恭的瑞德不再与她斗嘴、惹她生气,而是对她彬彬有礼,但同时又是漠不关心。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和温情都倾注在了女儿邦妮的身上,让思嘉看了都忍不住妒忌。瑞德成了一个良好市民,成了大家交口称赞的慈父,成了城里最受欢迎的人。他带邦妮尽情玩乐,还请人来指导她练习骑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邦妮在一次骑马越障时发生了意外,年仅四岁的她走向了死亡。瑞德几乎失去理智,而思嘉却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指责他把孩子杀了。满心悲凉的瑞德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呆在妓院里,还说妓院是避难的天堂,而他和思嘉的房子则是地狱。他和她互相折磨,就像用锋利的刀子切割彼此。瑞德在慢慢走向崩溃,以前机敏能干的他变得呆板迟钝,以前幽默风趣的他变得忧郁寡言,以前高大威猛的他变得垂头丧气,以前衣冠楚楚的他变得邋里邋遢。他如此绝望,以致当暮然回首的思嘉突然明白瑞德为她所付出的一切并向他表白自己的爱的时候,他却已经麻木。他的爱枯竭了。他就要远走。
“反讽将武断任性、牺牲者的不幸、被偶然性或被命运所捉弄、以及罪不当罚等感觉从造成悲剧的情境中剥离出去。如果存在一个原因足以挑选他去遭受灾难,那也是一个不充分的原因,这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它只会引起更多的反对。”[3](P17)瑞德的变化令人感慨万千,一个浑身上下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男人竟然成了一个自我贬斥的可怜虫。而究其根源,却只能归于其对妻子、对女儿的挚爱——这是多么令人不堪的原因啊!这就让人感到一种“对人类生活的不可避免性的反讽。”[3](P18)
二、结语
通过运用诺思罗普·弗莱关于西方文学叙述结构的相关理论,本文追溯了男女主人公瑞德和思嘉的爱情所走过的四个阶段。漫漫爱情路,瑞德和思嘉在享受了春的惊喜、夏的浪漫之后,还是不得不面对秋的萧瑟和冬的绝望。王国维曾有言:“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可见,有人生则有欲望,有欲望则有痛苦。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一种欲望。有人生则有爱情,有爱情则有痛苦。
我爱,我恨,我痛苦。
[1] 黄梅. 双重迷宫:外国文化文学随笔[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琼. 文本、文质、语境:英美文学探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 批评的剖析 论文四篇(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4][美]米切尔(Mitchell, M.). 飘(Gone with the Wind)[M]. 李美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5] 王宇. 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095-4654(2015)09-0082-03
2015-07-12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