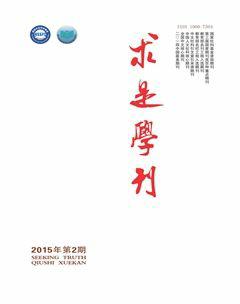宋元明清“富民社会”说论要
林文勋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如果将宋元明清时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称之为“富民社会”。自中唐特别是宋代“富民”阶层崛起以后,该阶层即构成经济社会的核心,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并对唐宋以来租佃契约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发展以及国家基层控制方式的转变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士绅社会”,实际上也是“富民”阶层崛起后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结果。
一、“至富敌至贵”:“富民”阶层的崛起
在宋元明清的文献中,“富民”又称“富室”、“富家”、“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某些情况下还可称“大姓”、“右族”、“望族”、“豪族”、“兼并之家”等。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了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作为一个在社会经济分化中产生的新兴阶层,其显著特征是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
早在中唐,富民的影响已备受时人关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全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竟于供送。朝士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1]又据唐人李冗的《独异志》记载:“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2](P45)这段史料中提到的“元宝”,就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天下富商王元宝。唐玄宗“至富敌至贵”之语,标志着其时财富力量的作用已显著增强,成为与政治力量同等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这两股力量共同规定着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实为一重大转折。
入宋以后,随着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富民”这个群体进一步壮大。北宋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3] (《栾城三集》卷8,《诗病五事》)可见当时“富民”已经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实为一个崛起的新的社会阶层。元代,由于蒙元统治治法疏阔,富民阶层继续承袭唐宋以来的发展之势,得以赓续和壮大。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明人于慎行说:“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4](卷12,《赋币》)清人吴履云也说,元代“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僻处海上,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而宫室用度,往往逾制。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摄服,称为‘野皇帝”[5](卷7)。
明代初年影响较大的富民大姓,大多是发迹于宋,壮大于元,沿续于明,特别是江南富民仍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洪武三年(1370),户部官员向朱元璋报告:“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6](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自明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众多的富家大户更是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正嘉以降,江南富室尤多,积银常至数十万两者”[7](卷358,《钱钞部·钱谷论》),以至“今宗藩之最巨者,不过以财自娱,如江南一富室而已”[8](卷160,《应诏陈言疏》)。正因为如此,时人王世贞曾指出:“盖东南者,国根本也。富民者,东南所恃以雄者也。”[8](卷75,《延祥上区华氏役田记》)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富户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这一变化,既是富民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扩大了富民阶层的社会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傅衣凌先生曾撰有《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指出明代江南出现了大批的市民。若从富民阶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市民”,还不具备近代市民阶层的特征。傅先生所说的“市民”,基本上都是本文所说的富民。清代,富民阶层仍是社会上最具有影响的阶层。乾隆时期的昭梿在其《啸亭续录》中有云:“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9](卷2,《本朝富民之多》)由于富民阶层拥有的巨大财富实力,“里党咸称为素封之家”[10](卷3)。
二、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
富民阶层一经崛起,迅速成为经济社会的核心。这具体表现为,它长期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
先看“中间层”的作用。南宋中叶叶适就对富民阶层的重要性作过全面阐述:“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具体而言,对“上”来说,“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此即富民既提供土地给贫民耕种而使贫民得以生存,同时又为国家提供赋税;对“下”来说,“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11](《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亦即富民在底层社会起到了一种核心的作用,离开富民,社会经济关系很难正常运行。
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指出:“从11至13世纪,由于新的势力在起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遂渐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12](P37)事实上商人只是富民中的一小部分,这个新出现的中间层并非只是商人,而是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这个阶层上通官府,下联百姓。它既代表百姓,代表乡村利益,与国家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但又有妥协合作的一面,从而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乡村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再看“稳定层”的作用。从宋代以来,历代均有大批朝野人士强调“富民”的重要作用。如王夫之就指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13](《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14](卷2)并进一步强调:如果一味要抑兼并,“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15](卷12)。明末,“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礼部侍郎钱士升激烈反对,他说:“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于圣明之世乎?”[16](卷251,《钱士升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富民在为国家提供税源、以富安贫、灾荒救济、维护乡村秩序等各方面都发挥了“稳定层”的作用。故而魏源有富民乃“一方之元气”之说,认为“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17](卷2,《治篇十四》),反对侵害富民的财产。即“富民”阶层的赓续安危是影响王朝盛衰存亡的关键变量。蒙思明先生更将南宋的灭亡归因于富民阶层的离心和怨叛:“(自公田法后)南宋政府与豪富阶级发生利益冲突而相乖离;于是元兵所至,诸郡望风而降;绝无豪士、义民起而拒抗,如元末之义军风起云涌者;是政府不得豪富阶级之奥援,亦南宋速亡之一因也。”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宋百有余年之统治,其内政之主要问题,即为对付境内之豪富阶层;初因富室之作梗而经界不行,终因富室之离异而国以速灭;南宋富室之影响政治有如此之大者。”[18](P9)
最后看“动力层”的作用。“富民”阶层极大地推动了宋以来乡村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在生产领域,如土地垦殖、水利工程的兴修、农业的精耕细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中,富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领域,富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借贷和灾荒赈济之中,同时大办私塾和书院,并延师讲学、藏书撰书和培养子弟进取功名,使乡村文化教育呈现勃勃发展之势。这不仅提高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水准,而且使乡村社会始终能够与外部世界保持较好的联系与沟通。
三、“以良民治良民”:“富民”阶层与社会关系
从社会经济关系来看,“富民”阶层推动了租佃契约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葛金芳指出,宋代租佃契约关系之所以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因为在唐宋之际地权关系和阶级构成的变动中产生了封建租佃经济形成的三大前提,即:地主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和合法地位,农民阶级的主体构成完成了由中古自耕农向契约佃农的过渡,超经济强制的松弛达到多数佃农争得迁徙与退佃自由的程度。[19](P1-P8)此言甚是。但笔者认为,租佃契约关系在这一时期能够最终确立起来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的崛起也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富民阶层只拥有财富而没有政治特权,他不能抑良为贱,采取超经济强制的手段来强制小农从事生产,而只能采取经济手段即租佃关系对小农进行剥削,即由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并交纳地租。而随着租佃富民阶层的进一步壮大,这种租佃契约关系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富民阶层成为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的占有者,这是租佃契约关系最终能够确立起来的基础。
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来看,“富民”阶层推动了唐宋以来国家基层控制方式的转变。唐宋之际,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其因亦在于富民阶层的崛起和发展。宋代以降,富民阶层凭借其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不仅成为乡村经济关系的核心,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在乡村中确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并事实上形成了对乡村事务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有效地治理乡村,就不得不依靠富民阶层。所以,宋代的衙前、里正,基本上都是由上三等户充任,南宋推行都保制,上三等户仍是应役的主体。明清两代曾先后推行粮长制、里甲制和保甲制,但不论乡村控制方式如何变化与调整,富民阶层都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依靠对象。洪武四年(1371)九月,明王朝在江南财赋之区行粮长之制,“乃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朱元璋对朝臣说:“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6](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这也就是说,随着富民阶层参与到乡村控制之中,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已由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
四、“士绅社会”:“富民社会”的最后阶段
中外学者常把明清社会称为“士绅社会”,我以为士绅社会即从富民社会发展而来,是富民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何谓“士绅”?明末清初的颜光衷说:“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20](颜光衷:《官鉴》)清代《钦颁州县事宜·待士绅》也说:“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21](《待绅士》)唐力行先生指出:“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22](P4,《本书序》)此说甚确。笔者以为,“士绅”虽拥有一定的政治特权,但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与“富民”阶层的特征是完全一样的。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当时人认为不肖子弟败家的主要途径是:“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虫,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23](卷3,《不肖子三变》)“三虫”之说真实地反映了唐宋社会富民家庭衰败的三部曲,也道出了富民家庭的财富与文化根基,说明富民家庭维持其家业不败,一是靠财富,二是靠文化教育。日本学者小山正明已经注意到明清乡绅来自于形势户、粮长层,也就是来自“富民”阶层,他说:“明末的乡绅阶层是继宋至明中期的统治阶层形势户、粮长层之后兴起的新统治阶层,其背景在于科举制度的社会机能发生了变化,即明以后举人、监生、生员成了终身资格,与官僚同样享有免除徭役特权(优免特权),构成了一个社会阶层。”[24](P457)
为什么“士绅”会来自“富民”阶层?这主要源自“富民”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旦崛起,他们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之后,必然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其主要途径和方式:一是科举入仕,一是加强与官僚交往甚至联姻。南宋中叶叶适就曾针对禁止富裕工商业者入仕的问题抨击道:“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决也。”[25](卷19,《国语·齐语》)胡寄窗先生认为,叶适“在十三世纪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固然是为时过早,超越了时代所许可的范围”[26](P184)。其实,这不是超越时代的呼声,而恰恰是富民阶层壮大后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反映。明清时期,富民对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更为迫切。人们熟知的“三言二拍”中有大量反映富民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事例。正因为富民入仕之多,甚至出现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27](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岁寿序》)的局面。
正是在追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富民阶层开始了一个士绅化的过程。所谓“士绅化”,就是一部分富民逐渐获得了政治特权,或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清人沈垚曾言:“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27](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岁寿序》)富民通过发展文化教育获取政治权力成为宋以后社会的共同特征。这样一来,在富民阶层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士绅。
士绅虽然没有富民人数多,但由于他们除了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外,还拥有政治特权,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们往往被很多学者视为“地方精英”。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士绅来自于富民,只是富民中的一部分,是富民决定着士绅阶层的特征和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我们如何定义明清社会,“士绅社会”本质上还是唐宋以来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富民社会”。
纵观历史的发展,任何一个阶层,一旦取得政治特权并形成一定的垄断性之后,必然走向反面。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在清中期以后,特别是清末社会,士绅由于拥有特权并形成某种政治垄断,逐渐从社会的发展层、稳定层、动力层变成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士绅阶层必然消亡。“士绅社会”的出现,反映了富民阶层与“士”和“官”的成功对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旦富民通过科举制度成为正式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便暂时成为了“官”而脱离了“民”的范畴。因此,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如同门阀社会是汉唐豪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其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最后阶段,我们认为,“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参 考 文 献
[1]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李冗:《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苏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于慎行:《谷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清道光八年(1828)醉沤居抄本.
[6] 《明太祖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84.
[7] 《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
[8]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 《毗陵胡氏宗谱》,清光绪三十年(1904)乐善堂活字本.
[11] 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3] 王夫之:《黄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14]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 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魏源:《魏源全集·古微堂内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
[18]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 葛金芳:《中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前提——兼论唐宋之际地权关系和阶级构成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0] 陈宏谋:《从政遗规》,谢文艺斋刊本.
[21] 田文镜、李卫:《钦颁州县事宜》,同治十二年(1873)羊城书局重刊本.
[22]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3] 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11.
[24] 檀上宽:《明清乡绅论》,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25]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
[26]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7] 沈垚:《落帆楼文集》,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