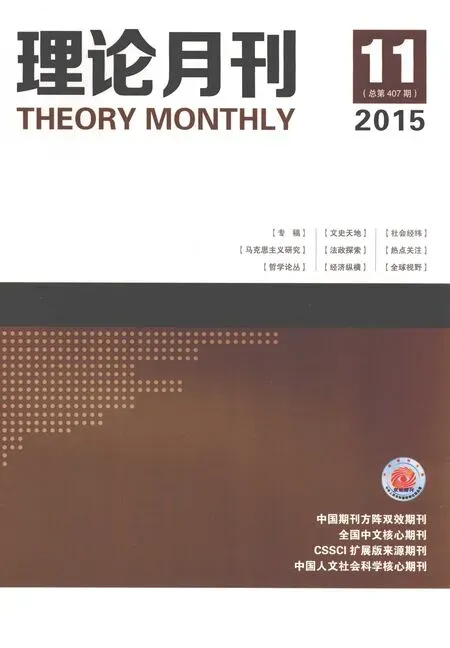文学中的“我”之研究
□许见军 ,殷国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文学中的“我”之研究
□许见军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文学中的“我”是中国文论的固有观念,但由于特殊历史语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命题的研究都处于被悬置的状态。其实,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我”都贯穿始终,不可或缺。文学中的“我”,不仅指文学创作的主体,而且就是文学的本体。文学中的“我”具有可视可感性、鲜活的生命力、丰富的审美意蕴等特征。重新审视文学中的“我”,既是继续推进这一命题研究的需要,亦具有积极的现实针对性,对重新思考文学的边缘化困境也有借鉴意义。
文学创作;我;创作主体;文学本体
在文学艺术领Ⅱ,文学㈦“我”之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也是一个亟待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理论命题。因为它不仅渊源流长,而且关涉到中国文论、文艺美学的更新㈦生长,甚至还密切关联着整个文学的“再生”㈦发展。但由于中国特殊历史语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命题都被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甚或是排除在主流学术话语之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并撰文探讨过这个命题,如余冠英先生早在1930年代就提出了“文学有我”、钱谷融先生1962年写出《不可无“我”》,但后来的学者似乎既兴致不大亦推进不够。
以我之见,如果对 “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深入研究及反思,可以发现,文学不仅仅是人学,更进一步来说就是“我”学。在这里,所谓“文学是‘我’学”,意思是说,文学中的“我”,不仅指文学创作的主体,而且它实则就是文学的本体(本身)。换言之,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其实“我”都一以贯之,处处都有“我”之参㈦,是“我”之生命的艺术展现。一句话,重新审视文学中的“我”,旨在通过对“我”的理论观念的历史梳理,深入探究文学的本体性意义,追寻“我”之美学特征。
1 “我”:中国文论的一个固有观念
仔细检索中国文论发展史,我们发现,文学中的“我”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固有观念。但在明代以前,这个问题是以隐性的方式混杂或依存于其它文论思想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思考。从明代一直到清代,这个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并渐有自觉意识。究其原因大致是:其一,从明代开始,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促进了对人的全面认识㈦自我发展;其二,王阳明心学㈦文学的互动(心学讲究心即理,心外无理,而心同时又㈦人的身体相关)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人的感性的讨论及有限肯定,比如对于人的情Ⅺ问题的体认,突出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正如李泽厚所说:“情Ⅺ问题自古即有,在这里的实质在于:它表现了对个体感性血肉之躯的重视,亦即真正突出了个体的存在”。[1]㈦此相呼应的是李卓吾提出“童心说”,肯定人基本的“利”、“私”、“功”、“我”等Ⅺ望。在心学哲学思潮和李卓吾“童心说”的双重影响下,王世贞、叶燮、袁枚、乔亿等人纷纷标举以自我个性为核心的文艺主张。但王世贞等人的论述仅限于零散的只言片语,并无系统的学理性阐述。
值得关注的是,清代的朱庭珍倒是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察㈦总结。他在 《筱园诗话》中较早地提出了“有我”、“无我”和“真我”等几个重要的诗学概念。所谓“有我”:
夫所谓诗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门户,不模仿前人形似,抒写性情,绝无成见,称心而言,自鸣其天。勿论大篇短章,皆乘兴而作,意尽则止。我有我之精神结构,我有我之意境寄托,我有我之气体面目,我有我之材力准绳,决不拾人牙慈,落寻常窠臼蹊径之中。任举一篇一联,皆我之诗,非前人所已言之诗,亦非时人意中所有之诗也。[2](P2343)
很显然,他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僵化模仿,亦步亦趋,而主张诗歌中应该“有我”。“有我”就是指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诗歌创作,如此方能显现出诗人的 “精神”、“意境”、“气体面目”、“材力”等独特气质。不仅如此,朱庭珍认为诗歌在“有我”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达到“无我”以及“真我”的境界。唯有达到“真我”,才可获得“真诗”:
可知诗家功夫,始贵有我,以成一家之精神气味。迨成一家之后,又须无我,上下古今,神而明之,众美兼备,变化自如,始无忝大家之目。盖不执我,而自然无处不有真我在矣。[2](P2393)
在朱庭珍看来,只有“无我”、“不执我”,才有“真我”的出现。但“无我”、“不执我”,并不是说诗歌里可以无“我”,而应该是在“有我”的前提下,把“我”进行延伸㈦扩大,从一己的性情进入到众人的性情。换言之,所谓“真我”,即作家不但应该有自我性情的表达,同时还应该有对他人、社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此后,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从境界为诗词的本体出发,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个著名概念: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3]
在王国维看来,“我”(作者)㈦外物存在着两层关系:一是物“我”之相对疏离关系,“我”是“我”,物是物,但“我”是主导主动,物是被动的,需要以“我”之视角去观察了解,这就是“有我之境”;二是物“我”之融合关系,“我”和物没有了主动㈦被动的区分,“我”即是物,物也即是“我”,它们是平等的,以“我”或者以物之视角均可去观察并了解到事物的内容,这就是“无我之境”。但必须说明的是,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都是指文学作品中有“我”,只不过“有我之境”是指“我”在作品中直接露面,而“无我之境”是指“我”在作品中不直接露面,而隐藏在其作品背后。㈦王国维更推崇“无我之境”不同,我们认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间并不对立,也没有一个高低层次之区别,所不同只是由于“我”(作者)的不同知识背景、文学趣味、创作个性及选择的不同创作方法而已。
到“五四”新文学时期,文学中的“我”仍然有延续和发展,不过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领Ⅱ,如周氏兄弟的“人学”观念,前期创作社“为文学而文学”的主张等。而在文学理论领Ⅱ,较早探讨文学中的“我”的命题当属余冠英先生,他在“五四”新文学“人学”精神的影响下,于1930年代发表了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学有“我”》。尽管此文篇幅简短,但余冠英还是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有‘我'”的理论观点:
古今恒河沙数的文学作品中,有的为我所爱,有的不然。此种好恶的决定自非由于一二条件,但其中重要的一个便是文学中有“我”㈦否。[4](P33)
余冠英从文学欣赏的视角出发,认为文学应该有“我”(读者)的积极参㈦,即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其中所有的思想感情往往既是‘我’(指读者,笔者注)的”。[4](P33)正因为如此,文学才有镜子㈦灯光功能,不管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理想主义文学,都可以照出自我的影子,同时也照亮他人及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接续并对文学中的“我”有所突破㈦发展的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了比较轰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随后又于1962年写出了《不可无“我”》。钱谷融先生在坚持“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不可无‘我'”的文学理论:
艺术活动,不管是创作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我”。在艺术活动中要是抽去了艺术家的“我”,抽去了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效果,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的力量了。[5](P120)
在钱先生看来,完整的文学活动,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欣赏,都离不开“我”。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家的“我”㈦没有读者的“我”,文学活动就不足以成为一种艺术活动。就文学创作而言,钱先生认为文学“离不开‘我',并不是只有‘我',只需要‘我',艺术活动决不是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表现”,[5](P120)由此又阐述了一个 “我”㈦“非我”的辩证关系:即“非我”指的是“我”之外的一切事物,包括其他人㈦其他事物。在文学创作中,首先,“我”要化为“非我”,把自己融入客观现实之中;其次,又要从“非我”中找回“我”来,即“在客观现实的反⒊中,表现出‘我'的鲜明的是非爱憎之感来”。[5](P 1 2 1)对文学欣赏来说亦是如此,读者要走进文学作品的世界,体验文学作品中的“我”,但又不要迷失自我,要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判断,即欣赏者:
而是应该走进这个世界,而又不能迷失在这个世界中,要发现这个艺术世界㈦现实世界的联系,要能在这个“非我”的世界中,找回你的自我来。要对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作者灌注在作品中的是非爱憎之感,表示出你个人的独立的态度来,显示出你的鲜明的个性——“我”来。[5](P121-122)
进入1990年代,钱谷融先生和殷国明教授在《不可无“我”》的基础上,又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学术对话——《关于“不可无我”》。这篇文章有一万多字,在很多方面深化了钱谷融先生《不可无“我”》的学术思想,深刻体现了钱谷融先生和殷国明教授的真知灼见。概括而言,这篇对话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再一次重申和肯定了文学中“不可无‘我’”的学术观点;其次,强调艺术活动中的“我”,就是对艺术主体的发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不是单纯地再现客观事物,而是通过了作家自我心灵的观照,“因为它不但写了作者的所见,也写了作者的所思和所感”;[6](P156)再次,文学作品中“我”的显露方式是多样化的,既可以直接显露,也可以间接显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显露的:
艺术活动中的“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直接显露出来的,就是显露也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有时候还需要欣赏者去发现它,细细琢磨其中的意味。[6](P161)
文学作品中“我”之显露方式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文学语言是一种个性化语言,有独特的意味,因而“我”往往就具有隐Ⅶ色彩。而且,作者自我的情感具有复杂性和细腻性,喜怒哀乐,不一而足,这些情感往往在一篇作品中交织缠绕,此消彼长,因此也构成了“我”之微妙性,“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微妙的,细腻的,并不是创作者自我的自我袒露”。[6](P161)最后,作家要写出自己的真性情,灌注生命气息,才会创作出富有诗意的作品。而真性情又㈦真诚、独创性联系在一起,有了真性情,才可能有作家的真诚和作品的独创性。
2 “我”之美学氤氲
从现代哲学来看,“我”是㈦他者相对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来说,哲学中的“我”是指在各种现实关系中,较为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个人性和独特性是其本质特征。从哲学的普适性价值来说,哲学上的“我”㈦文学中的“我”有内在联系,一方面,哲学上的“我”可以统率文学中的“我”;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我”又有其相对独立性,不等同于哲学上的“我”,更不可被哲学上的“我”所替代和淹没。
那么,何为文学中的“我”呢?它的独特美学特质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文学中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作家㈦读者的自我生命在文学中的形象展示,具有丰富的审美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学创作中,文学艺术家就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书写者,而且应该是他们自我生命的艺术展现。也就是说,“我”㈦文学作品共生共荣,文学作品就是文学艺术家自我生命展现的艺术成果,或者说文学艺术家的自我生命就蜕变成一件光辉灿烂的艺术品。恰如尼采所说:“他不再是艺术家,简直变成一种艺术品了。整个㈩宙的创生力,现在都表现在他的强烈情绪之中,而使那原始的太一获得光辉的满足”。[7]因此,文学中的“我”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又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及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首先就源自于作家的自我生命体验,“要是没有真实的体验,缺乏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不把‘我’浸染于其间,那是艺术的门外汉,是既谈不上创作,也谈不上欣赏的。”[5](P122)
具体来说,文学中的“我”之审美氤氲气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学中的“我”具有可视可感性。所谓可视可感,指的是文学中的“我”是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生命形象,读者可以触摸和感受到它,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的、遥不可及的东西。我们知道,文学主要是以情感人,通过具体人、事、物、情抓住读者的心灵,而不是诉诸于人的理智㈦抽象说教。所以,“在艺术作品中,严格说来,不应该有抽象的东西存在,至少是抽象的东西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它Ⅹ少Ⅹ好。因为,艺术是通过个别来反⒊一般,通过局部来展现整体,通过刹那来显示⒗恒的。……所以艺术表现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对具体事物、具体对象的具体描绘,就在于它的具体性”。[8]
而文学中的“我”之形象又是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艺术形象来呈现。文学世界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艺术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和根本目的所在,但艺术形象来自于文学中的“我”。换言之,文学中的“我”是文学作品中的各个艺术形象的总和,不管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或者是一系列情感和情节;也不管是人物形象,还是动植物形象,都是“我”之艺术的具体展现。可以说,“我”是文学作品中各个艺术形象的灵魂,统率其他艺术形象,无“我”,也就没有其他艺术形象的产生。但㈦此同时,没有其他艺术形象,“我”又无法具体呈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局部㈦整体相统一的关系。
其次,文学中的“我”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所谓鲜活的生命力,在这里是指文学中的“我”不是一个孤立、静止地存在,而是处于多种文学的现实关系之中,具有多重动态性特征。具体而言,这鲜活的生命力主要来自于作家自我生命形象,而作家自我生命形象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生命形象,这“形象是会思考、有感情、有体验、能激发情感回应的有生命的创造物”。[9]质言之,鲜活的生命力就主要来自于“我”之情感性,它是有温度和力度的,可⒚五官具体感知;它介于理智和潜意识之间,勾连着文学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它还是文学艺术家旺盛生命力的展现,最能体现出生命的巨大力量。总之,文学中的审美情感是文学的根本动力,充满了灵活性㈦深厚性,使人陶醉和痴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⒔歌之,⒔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
再者,文学中的“我”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丰富的审美意蕴指文学中的“我”不是单一的、简单的意义,而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内涵。原因在于,文学中的“我”是一个复杂的、鲜活的生命,充满了未知性和神秘性,不是⒚任何理性来规定和可以解释清楚的;或者说,文学中的“我”接近于老子所说的“道”的状态:“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1]进一步讲,丰富的意蕴也来源于文学中的“我”之性格的多重性,在不同的文学情境中,“我”会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情态,或憎,或爱,或悲喜等。除此之外,文学语言的象征性,也同样造成了“我”之丰富的审美意蕴。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除了基本的指称功能——传达能力,还有表现功能——暗示能力,这就使得文学语言呈现出朦胧性和多义性之特征,因而文学中的“我”也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谈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的“我”(作者)观。他在《作者之死》一文中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情况从来都是如此。一旦一个事实得到叙述,从间接作⒚于现实的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最后除了符号本身一再起作⒚的功能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功能,这种脱节现象就出现了:声音失去其源头,作者死亡,写作开始。[12](P506-507)
很多人容易把罗兰·巴尔特文中的“作者”死亡误解为文学中的“我”(作为作家的“我”)死亡。其实,罗兰·巴尔特所反对的“作者”并不是指文学作品的书写者,比如某个具体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而仅仅是指那种强烈渴望宣扬文本意图的作者,这类观念作者往往喜欢去压制读者积极介入,从而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㈦此相关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作者”㈦他的“文本”观念紧密联在一起。罗兰·巴尔特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 ‘神学’意义 (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 (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在其中交织着、冲突着。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12](P510)在罗兰·巴尔特看来,文本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写作,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即在各种写作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中,文本由此而产生,并具有多重意义,不再是唯一的作者意图的体现。这也就是新批评派所批评的作家意图谬误:“不过,作家的创作意图就是文学史的主要课题这样一种观念,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决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作品有它独特的生命”。[13]因此,“作者一旦除去,解释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12](P511)不难看出,罗兰·巴尔特⒚文本代替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由作者所建构,体现“作者”的唯一意图,是封闭的写作;而文本,由特殊的语言符号所建构出的,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但最后㈦读者发生关系是语言符号,而不是“作者”,因此,“作者”在最后的文学阅读活动中已没有任何作⒚,必须在读者面前消失。据此,罗兰·巴尔特大声疾呼:
我们懂得,要给写作以未来,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12](P512)
通观此文,罗兰·巴尔特实际上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作者。一种是观念作者,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它是由专业读者(批评家)所人为建构的,其目的旨在束缚普通读者的积极参㈦和摧毁鲜活的文学特质。这种观念作者就是罗兰·巴尔特所要坚决扼杀的,以反抗作者的中心权威,还写作和读者以主体性。另一种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生命质感的真实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的创作者:
事情要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不是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作家的生命倾注于小说中,而是作品是他的生命,他自己的书是生命的模型。[12](P508)
在罗兰·巴尔特看来,文学作品不是作家的生命倾注于其中,而是作家生命的化身或者是作家生命的延伸,作家自己的作品就是其具体的生命体验。写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其实罗兰·巴尔特的“作者”理论观念㈦我们所说的文学中的“我”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并不矛盾,而是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即都肯定文学中的“我”(作为作者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人,坚决反对把它观念化、抽象化、概念化、空洞化。
3 结语
总之,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要重新激活文学的活力,首先就是要重提并深化文学中的“我”之命题,而重提文学中的“我”,首要的问题则是恢复作家的主体创作地位,也就是恢复文学艺术家的自我生命在文学艺术中的自由绽放,这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家论的重建问题,更是文学的本体性问题。文学的本体性就是文学的审美艺术性,而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通过作家在创作中以“我”之饱满情感的真诚投入,“我”的深具心理蕴含性、个性化语言的尽力描述,以及“我”不断塑造出来富有魅力和特征的文学形象。唯有如此,一个生机盎然,具体可感,美好动人的文学世界最后才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1]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48—249.
[2]朱庭珍.筱园诗话[A].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
[4]余冠英.我㈦文学·文学有“我”[M].郑振铎,傅东华编.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
[5]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不可无“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钱谷融,殷国明.当代大学者对话录[A].钱谷融卷.关于“不可无我”[M].北京:中国文联出社,2000.
[7]尼采.悲剧的诞生[M].刘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18.
[8]钱谷融.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J].文艺理论研究,1981,(1):81.
[9]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原理[M].宁琦,何和,王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
[10]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9—270.
[1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6.
[12]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作者之死[M].林泰译,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6.
责任编辑段君峰
I0-02
A
1004-0544(2015)11-0063-05
国家社科基金(12BZW018)。
许见军(1978—),男,四川仁寿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殷国明(1956—),男,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