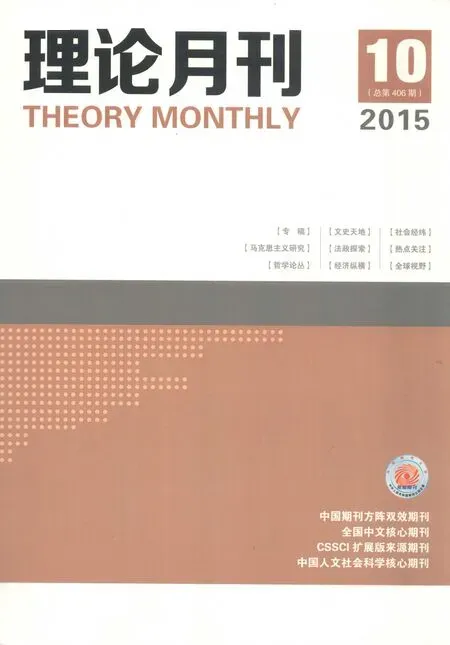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政治解读
□郭小香(北京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政治解读
□郭小香
(北京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总体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其标志性事件有:1899-1911年的新马孔教复兴运动、南洋大学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被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这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充满曲折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是既利用又限制,这既源于新加坡的政治考量也源于儒家文化对于新加坡发展促进作用的有限性。
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政治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时日已久,早在唐朝时就有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中国移民给新加坡带来了儒家文化。19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政府的自由港,新加坡的华人劳工迅速增加,儒家文化的传播也日益迅速。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对儒家文化开始了自觉主动的传播,但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可谓有起有伏,究其原因十分复杂,笔者试从政治维度对此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当前学术界对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一般持肯定态度,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则有夸大儒家文化对新加坡影响的倾向,笔者期望在从政治纬度对儒家文化传播分析的基础上能对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做出中肯的评价。
1 20世纪初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的高潮:1899-1911年的新马孔教复兴运动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最初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传承过程,这是因为早期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大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劳工苦力。到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和教育重要性的凸显,华人移民开始建立学校,19世纪中叶以后,“义学”和私塾大量涌现。学校的出现,使得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变成自觉有意识的主动传播,华人移民自觉传播儒家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1899年在新加坡、马来亚更是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史称新马孔教复兴运动,这也是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史上的第一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华人社会出现了明显分化:在左秉隆等清朝驻新加坡领事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认同和思慕中国的移民阶层;受英国殖民政府所推行的西方文化和教育政策影响形成了支持和倾向英国的海峡华人。海峡华人接受英文教育,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感情淡漠,不再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但和英国殖民政府关系密切,效忠英国并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林文庆等有识之士为了使在西化路上欲行欲远的海峡华人重返祖国精神家园,发起了孔教复兴运动。
这次孔教复兴运动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倡立孔庙和兴建学堂,设立文社学会、创办报纸、改编并出版儒学读本《千字文》、纪念孔子诞辰等。这次运动不仅有新加坡华人林文庆、邱菽园等有识之士的大力参与而且得到了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事实上后者还是此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在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并未设专门主管华人事务的机构,只是基于解决新加坡各种族之间矛盾纠纷的目的,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这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华人的管理非常松散,再加上其对华人权益的漠视并未被华人认同为其官方领导机构。而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历任领事尤其是左秉隆和黄遵宪积极兴办华校、发扬儒家文化,极大地激发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得到新加坡华人的拥戴和认可,从而被其看作心中的官方领导机构,这对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馆领导此次孔教复兴运动奠定了良好基础。1901年,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罗叔羹在建立孔庙的预备会议上大力呼吁与会者支持孔庙建立,并公布了官方通告;1902年,在代总领事吴寿珍的积极支持下,掀起了孔教复兴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成立了“创建孔庙学堂董事会”,并在短期内筹募到20多万元的创建资金。1900年康有为、孙中山相继来到新加坡,促使这股儒学热潮进一步发展。康有为在新加坡尤其是华人中积极传播尊孔保皇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成立了“中华孔教会”,一时祭祀孔子的活动纷纷开展。孙中山则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振兴华报,常设华校,高扬儒家文化大旗。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加入,使这场复兴运动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第一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从1899年开始持续到1911年结束,在此期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也曾跌入低潮,但总体上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发展。
2 20世纪中叶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低潮中的盛事:南阳大学的建立
由于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前者直接提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后者则激起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削弱了对儒学复兴的关注),1899-1911年的孔教复兴运动之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陷入长期缓慢状态。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政府基于内政外交的特殊形势及发展经济的需要对儒家文化也持打压态度,但1956年南洋大学(以下简称南大)的建立又掀起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继孔教复兴运动后的又一个高潮,可谓是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低潮中的一次盛事。在南大建立以前,新加坡已建立了完备的华文中小学教育体系,但新加坡却没有一所华文大学。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国与东南亚也处于隔离状态,因此新加坡的华校学生也不能像之前一样回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以前去中国留学的新加坡学生往往回国后担任中学教师,这就斩断了新加坡中等教育的重要师资来源,进而对新加坡中等教育的师资也构成了重大威胁。英国殖民政府则扶植并建立了系统的英文学校,对华文学校不管不问,故“新马华文教育至此已面临存亡断续的危机”,[1](P99-117)这使华文大学的建立成为亟需。在此情况下,新加坡华人开始积极筹办南洋大学,新加坡华人虽然热情高涨,但其建立过程极为艰辛曲折。英国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认定“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2](P95-128)不愿意承认南大学位。其还以新加坡是殖民地只能建立一所大学,而之前已建立了马来亚大学为借口,不批准南大的申请,南洋大学只得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请注册。南大的建立基金全部来自于民间筹款,上至富商下至舞女、三轮车夫均慷慨解囊,但却没有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任何帮助。南大的创立还遭到了马来族群的反对,如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肯以马来亚大学即将开设中文系为由反对南大的建立。不仅如此,南大还遭到了讲英语的华人社群的反对。讲英语的华人社群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完全西化,对汉语和中国的感情非常冷淡,他们坚决反对南大的建立。在新加坡华人(主要是讲华语的华人)的多方呼吁和积极努力下,1956年南洋大学终于得以建立,这对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南洋大学以华语为教学媒介,将儒家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它“是星马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因此南大的创立,使新加坡华文教育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在东南亚各国中,只有新加坡才能够提供由小学、中学而至大学的完整的华文教育,使万千青年有享受中华文化洗礼的机会,进而从事贯通东西的文化。”[3](P17)李光耀曾指出:“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4](P174)可以说南洋大学为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所凝聚了新加坡众多华人心血并被其寄予厚望的大学只存在了短短的25年。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建立,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但人民行动党政府并不支持南大的发展。语言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对南大发难的一个借口,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例外,1965年随着《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南大被迫实行改制。改制之后,南大成为政府控制下的一所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名存实亡。1980年,南洋大学终于在《丹顿爵士报告书》建议之下,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至此,“南大名为合并,实为关闭,奏完广陵散,一所最能代表民族精神的华文大学、中国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与晋朝名士稽康的古琴曲一样,成为人间绝响。”[2](P95-128)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儒家文化发展的新高潮:“朝野通倡儒学”
随着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外向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英语和西方文化越来越推崇,英语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西方文化也得以在新加坡迅速传播。随之年轻人的西化倾向日益严重,西方价值观对新加坡产生了严重冲击,产生了种种问题,如道德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吸毒泛滥等。为抵制西方文化的腐蚀,人民行动党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即第二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这次复兴运动使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此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学教育中设置了儒家伦理课程。儒家伦理课程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是在李光耀和吴庆瑞等新加坡领导人的支持下而设立的,如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亲自去美国纽约邀请著名的华裔儒家学者杜维明、熊介等到新加坡进行考察研究,这使其影响力迅速超出宗教知识课程的范围并扩大到社会层面。新加坡政府把儒家伦理教育的目标确立为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新加坡公民。为对儒家伦理课程提供学术支持,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该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曾多次主办高规格的儒学会议。在新加坡政府的号召下,新加坡的大众传播机构和民间社团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如新加坡图书馆建立了关于专门介绍孔子思想的中英文书籍的书橱,《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与运动相关的社论,国际儒学研究会、“亚洲研究会”、“中华总商会”等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这些社团积极开展儒学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儒学的影响。1985年,中文版的《儒家伦理》正式出版在全国中学得以普遍使用。1986年l月,英文版的《儒家伦理》也正式在全国中学应用推广。这次以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可谓轰轰烈烈,但随着儒家伦理课程的取消,此次运动也随之结束。宗教知识课程激起了教徒的传教热忱,因此宗教知识课程被迫结束,而1990年作为宗教知识课程组成部分的儒家伦理课程也随之结束。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列举了五项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毋庸置疑,“五大共同价值观”是以儒家思想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但这里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原本的儒家思想,而是根据新加坡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了现代性改造。显然,不管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还是共同价值观的提出,都是由政府社会设计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运动,这些目标不是只关乎市民文化或素质的,而是政治性的。
4 从政治维度来看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
纵观20世纪以来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史,新加坡政治态势的发展变化无疑是影响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命运就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需要。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第一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及结束就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和中国的政治力量的较量。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及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种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使其对儒家文化持敌视和打压态度。中国的政治力量则基于不同的目的对这场复兴运动持支持态度:清朝驻新加坡使馆是为了增强海峡华人对于祖国的感情与认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因为在国内的失败才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把新加坡当作其“避难所”和阵地。维新派对这次复兴运动的影响尤深,在某种意义上可将这次复兴运动视为回应康有为的维新运动而政治化了的孔教运动。
新加坡政府对于南洋大学的态度亦是有着诸多的政治考量。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宗教、种族多元的移民社会,文化多元和种族分层是政治骚动的根源,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文化整合的策略。文化整合策略主张各种文化平等发展,“人民行动党的政纲明确规定,不采用同化策略即不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普遍认同,而是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使不同的种族团体在政治上互相调整,保持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同时忠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5]另外,新加坡的地缘政治也是其采取文化整合策略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周边国家都普遍存在着种族紧张和暴力骚乱的状况,这些国家的国民以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教徒为主,尤其以马来人居多,新加坡如果以儒家文化对非华人采取同化政策,将难以在“马来海洋中”生存下去,而在国内也必将会招致其他种族尤其是马来人的抗议。因此,李光耀政府反对华族认同,严防出现“华人沙文主义”。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华人一词含有沙文主义的因素。新加坡还有许多组织使用新加坡华人或华侨的名词。用这种名称登记的组织意在保护华人的利益,阻止其他种族加入。这些名词对民族团结是有害的。”[6](P124)他还特别强调“有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是不能犯的,那就是我不能为了一时愚蠢,单独强调华族的最高利益,让人借以指责我们,在东南亚或亚非国家里,把我们新加坡完全孤立起来。切不可忘记,我们还是一个新生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密切注意着我们的言行动向。”[7](P140)新加坡政府压抑儒家文化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消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新加坡的影响,因为新加坡的华人认同将会加强新加坡华人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联系。同时,淡化新加坡的华人认同,还将有利于新加坡脱离“第三中国”的政治标签,并增强新加坡民众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李光耀曾宣称:“我们处于马来西亚人民的中心;尽管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华人,但我们不能避开我们的环境。一个复兴的中国己经不仅是东南亚各族人民仰慕的对象,而且也是恐惧的对象。”[6](P134)
新加坡独立以后,威权政治是影响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重要因素。独立之初,新加坡是一个多个种族、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各个种族、民族相互排斥和隔阂,缺乏凝聚力和民族缺乏认同感,为了维护新生国家,人民行动党不得不选择实行威权政治。人民行动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出色成绩及提供的高水平福利,尤其是大量提供公共住宅,取得了新加坡民众对其威权政治的支持。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公共住宅的依赖度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民众的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李光耀政府的“家长式”统治方法极为排斥和质疑,民众要求参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一时期,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受到严峻挑战,这使人民行动党积极寻求各种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人民行动党在对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强力控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软控制的手段。儒家文化所推崇家长制和服从观念能够从意识形态上淡化政治多元化,对威权政治起到了极好的维护和巩固作用。李光耀等人复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种证明人民行动党威权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引导的第二次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以及提出共同价值观都不过是借儒家文化复兴之名来为人民行动党的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罢了。
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导了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但也亲手结束了它,这看似前后矛盾的做法其实也是基于政治考量。第一个考量便是儒家文化与中国性的关系问题,由于儒家文化源于中国,这便使新加坡很多人担心推行儒家思想教育会引起中国精神的过于宣扬,并由此担心新加坡会被其他国家视为第三中国。其次,第二个考量是害怕儒家学说会对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产生消极影响。虽然新加坡实质上实行的是威权政治,但毕竟披着民主制度的外衣,而且新加坡的威权政治确实也蕴含有不少西方民主制度的因素。而人民行动党的核心人物李光耀也没有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的意思,只是认为过分强调民主,会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因此,人民行动党不能不顾忌儒家学说对于民主的一些消极作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对于儒家伦理课程社会上蕴藏着巨大的猜疑力量,这股猜疑力量主要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参与筹备儒家伦理课程的华裔学者杜维明对此感受深刻,他在回忆1982年初访新加坡的经历时指出:“在那疲于奔命的十几天,我直觉的感受是身陷重围:儒学传统受到英文源流和中文源流两类华裔知识分子的夹击。前者酷似英美自由主义学人,批评儒学是东方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雷同五四时代的知识精英,斥责儒家是封建遗毒乃至吃人的礼教。”[8]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害怕推广儒家伦理会增强华族认同导致华人沙文主义。归根结底,新加坡实行的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其威权政治亦含有西方民主政治的诸多因素,与封建专制统治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人民行动党政府决不可能允许儒家文化成为新加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其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既利用又限制。
5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影响之评价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对新加坡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体现在新加坡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结构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利用儒家文化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这是多元现代性的有力体现。多元现代性理论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点,提出西方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实践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各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和习惯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模式。多元现代性的代表人物艾森斯塔德认为:“理解现代世界事实上也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它看作一个现代性的文化纲领和文化样式以多样性的方式不断建构和重构的故事。”[9](P34)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个人主义、民主、立宪制、自由市场等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均来源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传统,很难与亚洲文化及其他非西方文化产生共鸣,其他文化也不一定要学习西方文化,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他还极力肯定新加坡政府倡导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反的儒教价值,认为这是保存新加坡自身文明特殊性的合理努力,甚至指出值得美国政府效法。
毋庸置疑,就新加坡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来说,儒家文化功不可没。但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不是儒家文化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在于新加坡将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进行了很好地融合。多元现代性不是强调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强调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与重构,“现代性”是各民族的底色,有了这一底色,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能焕发生机。由于新加坡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制度、自由市场、个人主义、法治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奠定了新加坡现代社会的基础。可以说,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新加坡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的竞争性与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勤奋、忠诚、集体主义等伦理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种完全融合的竞争体制。另外,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文化如马来文化和印度教文化对新加坡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文化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伦理和生活方式。就伦理层面的儒家文化,新加坡政府是持欢迎态度的。伦理层面的儒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上主张伦理本位。伦理本位的人际关系是以人情为核心的,以义务而不是权利为纽带,把个体视为依存者,强调人与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的相互的依赖关系。梁漱溟形象地描写了这一形态:“要在有与我情亲如一体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间尤相依以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念。——此即所谓‘亲人’,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10](P87)与西方新教伦理所形成的竞争模式相比,这是一种和谐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重视团体的力量,寻求一致的意见,没有个人权利观念,强调个人须以对他人尽责为美德,在相互依赖中得到社会和心理的安全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本位会激发人们参与到群体当中去,产生相互依赖的社会团体,使整个社会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能消除西方个人主义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的原子化状态。另外,儒家伦理强调义务、忠恕、自律、修身、尊重权威、社会和谐等理念对国民道德品质的提高和国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并能够增强国民对国家、政府的忠诚,进而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是新加坡一直要极力避免的,这是由其经济基础以及其西方传统决定的。每当儒家文化发展势头过猛,有变成新加坡政治意识形态危险的时候,新加坡当局就会采取打击政策。即使是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护自己建立的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打击政治多元化,使儒家文化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仍然是限制的基础上进行利用,未将其提升至统治地位。另外,儒家文化毕竟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其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也存在颇多冲突,比如重道德轻利益的价值观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家族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等等;这些非理性因素也限制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力。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是时代的产物,其兴衰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即它能否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需要及能多大程度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需要,以及人们能否客观地对其进行现代的审视和诠释,能否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已不是原初的儒家文化,而是结合现代性进行过滤与改造的现代化。如“忠”被阐释为忠于国家,具有国民意识;“礼义”被阐释为待人接物以礼相待、坦诚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心等等。显然,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八德是为了巩固新加坡民族国家的利益。正是新加坡对儒家文化的成功改造才使其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对新加坡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对我们今天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先进文化,是因为其具有较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极大的开放性,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想重焕生机,就必须进行自我修正,祛除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现代文明形成良好的融合与对接,这样才能与时俱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与源泉。
[1]黄金英.陈六使与南洋大学[A].王如明.陈六使-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C].新加坡:南大事业有限公司,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出版,1997.
[2]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A].李业霖.南洋大学史论集[C].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
[3]苏萤辉.中国文化在星马[A].程光裕,许云樵.中马中星文化论集[C].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
[4][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5]陈祖洲.从多元文化到综合文化——兼论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关系[J],南京大学学报,2004,(6).
[6][英]A·乔西.李光耀[M].安徽大学外语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7][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政论集·新加坡之路[M].新加坡:教授书局,1967.
[8]杜维明.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一九八八年儒学群英会纪实初版·序[C].台湾:正中书局,1997.
[9]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梁漱溟全集:第3卷[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友海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31
G122
A
1004-0544(2015)10-0177-0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15SHA002);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
郭小香(1981-),女,河南郑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