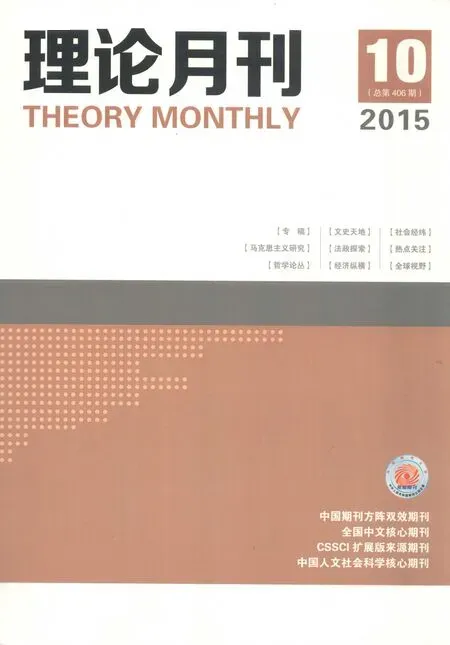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圈地思维
□黄仲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102)
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圈地思维
□黄仲山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102)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地域性,但这种地域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基于文化而不是现行的行政区划。近些年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形成一种圈地倾向,即争相将非遗资源圈定在各自的辖区,画地为牢。这种圈地思维一方面是狭隘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特性和传承、传播规律认识不清造成的,从文化全局乃至长远发展来看,它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产生了很大伤害。因此,各地应摒弃狭隘的地域意识,提高文化共享意识,加强沟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将非遗文化发扬光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圈地思维
2014年年初,韩国打算申报“暖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热议,普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暖炕现在似乎要成为别国的文化符号,这让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痛心疾首者有之,揶揄讽刺者有之,认真反思者也有之,人们很自然地将之前韩国“端午祭”申遗等种种所谓“抢文化”的举动联系起来,相关话题的焦点也集中在文化“争抢”上面。如果联系人们的思维方式来看,这种争抢意识来自一种典型的圈地思维,就是将非遗资源圈定在自己的地域内,不容他人分享。圈地思维其实是一种排他性的占有思维,把非遗文化当成了独占独享的资源,并试图通过种种手段维持这种独占性。实践表明,这种圈地思维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某种负面效应,对非遗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形成了障碍,需要结合问题出现的现实根源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理。
1
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一种活的历史话语,那么这种话语必然被打上特定的地域印迹,讲述着一个地方历史流传的特定习俗和风尚,和这个地方民众的文化生活血脉相连。因此客观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确实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有学者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地域性正是其多样性的一种表现。”[1]不同地域的风土、物产和人文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样态和文化品格,是地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样本。但另一方面,文化流传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很强的模糊性,在影响范围上并没有非常明显而确定的疆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属性划分参照的是行政地域而非文化地域,实际上,各级行政区划古今变化很大,将现代行政区划作为非遗地域划分的依据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不具有科学性。比如古徽州地区在现代区划中已横跨安徽、江西两省,在安徽省境内又包含多个县市,古徽州地区民居建筑和饮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属性就很难以现代行政区域进行划分,任何县市都不能单独代表这些曾流传整个区域的文化遗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就需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将这一地域的各方力量联合起来,从而使非遗的文化资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整合。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很难绕开现有行政区划条块管理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应完整的非遗文化常常遭到人为的切割,这种切割的动因就是各行政区的地方利益。因此从根源上说,正是当下非遗项目按条块进行划分和属地管理的普遍做法,使得各地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滋生了圈地思维,这种思维首先来自于各地的文化部门,在地方利益的博弈中不断地得到来自官方、民间各方势力的认可与鼓励,成为一种普遍的、常态化的惯性思维,贯穿体现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宣传推广的整个过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圈地思维的表现最为明显。现行非遗申报程序决定了现行行政区划恰恰成为非遗地域区分的依据,各级非遗名录体系收录非遗项目时,将所在地域作为重要属性。申遗方首先是代表着特定地域的实体,实际上就确定了非遗项目的地域属性,比如韩国向联合国申报“江陵端午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各级行政区文化机构纷纷建立区内非遗名录,并成为向更高级别非遗名录申报的组织者,自然将本地辖区作为非遗项目地域属性的重要参考。正如英国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所说:“在城市开发策略越来越乏味且标准化的时代,只有少数当地资源可以作为本地身份的‘独特’标识来展示。”实际上,“遗产在这些当地文化‘资源’的列表当中名列前茅。”[2]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一城一地的文化象征,从文化构建的逻辑来说,似乎只有将非遗项目尽可能完整地纳入本地管辖范围,才能使这种象征具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使构建起来的意义大厦具有更强的稳固性;从利益动机来说,只有非遗项目成为特定地域的专属文化象征,成为专属本地的文化资源,才能独占这种资源所获取的全部收益。这样,申遗在各地就成了圈定文化资源的必做功课,类似于抢注商标,将非遗资源据为己有,以求获取最大利益。一旦申遗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打上地域标签,地域属性得到认可,在后续的保护过程中自然会强化这种地域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圈地思维在行政干预下得以滋长,官方的认可与鼓励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圈地思维借“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名义堂而皇之地存留下来并被广泛接纳,这种被地方利益严密保护起来的狭隘思维很难得到真正的清理,往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实际障碍。国家、省市区县各种行政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也会成为利益主体,而这在申遗阶段就很大程度上被形塑、被鼓励乃至被确认的。一旦形成利益主体,就会产生资源独占的动机,极力排斥他者分享非遗资源。国内知识产权专家肖海教授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曾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地理标志保护模式”,[3]鼓励挂靠地方政府的协会或组织作为主体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的申报。将非遗打上地理标签是借鉴农产品等地理标识思路,但地理标志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体现,必然带有相当明显的排斥性,这实际上是将市场经济的强硬法则套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化形态上。尽管肖海教授也承认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局限于一定地域,建议这种地理标识保护不应影响其他地域“先权利”的行使,允许非商业合理使用,但这种变通并不能掩盖以地域和利益主体划分的排斥性思维倾向。因此,“地理标志保护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探索,对一些流传范围明确固定且具有较明显地域性的非遗项目进行保护试点,但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存在很大的疑问。这种保护模式试图明确保护的主体,但在赋予保护主体以责任的同时,也使其变成了利益攸关方,很难说这种利益诉求不会使保护变味,从而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存续和发展。
2
深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圈地思维出现的原因,首先要从非遗作为文化形态的根本特征来入手。如果人们对非遗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了解不够,以政治运作和资本运作方式来进行非遗文化的保护,就很容易产生圈地思维。文化圈地思维的逻辑来自领地占有观念和经济竞争法则,以保卫领土的思维来保护文化所属权,寸土必争;以经济营销的思路来维护文化资本收益权,锱铢必较。现在过分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资本,资本的独占性可使利益最大化,非遗文化圈地运动最大的动机也就是实现垄断性的资本收益。但是,非遗作为文化精神的载体,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性、功利性的经济资本。这种生硬的套用往往不得其要,而且对非遗文化本身是一种伤害。许多地方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违背了文化传承的规律,丧失文化传承社会效益的考量维度,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地方经济发展的附属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变成精神上的纽带而不是经济上的绷带,如果指望将文化牌打成清一色经济牌,结果却是为了过经济的河,却拆掉了文化的桥。
其次,圈地思维和非遗名录迷恋症和地方扭曲的政绩观念也有关系。不少地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将名录的收录情况以及所入名录的级别当成非遗保护唯一的价值体现,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为地方政府的 “政绩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此起彼伏的‘挖掘和保护’运动,以及对于入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这种政绩焦虑的集中体现。”[4]也许正是这种焦虑推动各地争相把文化遗产纳入自己的地域范围内,但这种并非真正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的 “申遗”狂欢会带来许多后遗症,造成许多地方申报积极,而后续保护乏力的局面。
再次,非遗圈地思维的产生还在于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的流传规律区分不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乎一国一地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因此弄清权属似乎很有必要,但问题是,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多点分布、多地开花的,不像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很具体的承载物,如建筑遗迹,文物艺术品等,较容易分清所属主体,能划定所在区域的边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的流传而不是以物的存留为核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这导致其中相当一部分非遗项目边界模糊,很难说谁能独占、独享。
非遗圈地思维产生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就保护主体来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认识存在盲点,即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仅仅是一种可带来经济回报的文化资本,而没有将其看成是提升当地文化底蕴和影响力的可共享的社会资源;二是价值存在扭曲,即只顾挖掘经济价值,而不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只为实现小范围内人们的功利目的,而不考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三是情感意志被狭隘利益所挟制,并非真正着眼于培养民众对非遗文化的感情,而是以利益切割不同地域的民众,使得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从非遗传承人的角度来说,狭隘的思维让他们过于关注其体制身份,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文化身份,往往难以从审美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对非遗文化的表现精益求精。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导致圈地思维长期顽固地存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在有些地方越走越窄,群众基础不断地被侵蚀,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也难以为继。
3
总体来说,圈地思维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许多衍生的问题,对于文化的传播是一种干扰因素。首先,它遮蔽了历史真相,解构了非遗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圈地思维功利性太强,地方利益的驱动干扰了历史的考证和研究工作,以至于非遗历史空间的构建往往是基于某种利益而不是历史事实,甚至为了需要可以生造历史。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群体的推动下,近些年某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历史研究已经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造成了“伪”专家大行其道,“伪”历史层出不穷。具体的表现是:(1)生造本来不存在的历史典故,作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资源;(2)将本来并不相关的历史片段生硬地组合在一起,张冠李戴,本属甲地的非遗历史被移植到了乙地;(3)将非遗历史按现代思维进行改造,以符合现代社会的市场需求;(4)无限夸大非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以增加非遗文化的历史厚度和重要性;(5)有意混淆非遗项目之间的历史界限,将非遗项目进行任意组合和拆分。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行为或许可以为地方带来短期利益,但终究是虚假的历史。急功近利的行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没有真正历史支撑的“伪”遗产也缺乏持久的生命力,长远来看不利于地域历史文化整体内蕴的构建,也让原本作为文化精神支撑的历史资源失去了坚实而可靠的认同基础,在民众中产生历史怀疑论和历史虚无感,将真正的历史文化精魂消解掉了。
其次,圈地思维造成了认知的混乱和传承的障碍。当下各地、各国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夺异常激烈,原本完整的、血脉相连的文化统一体被打上地域的标签,形成了人为的割裂,在传播中自说自话,自卖自夸,这就出现了一条街上“正宗王麻子剪刀”、“正版王麻子剪刀”、“嫡传王麻子剪刀”等招牌林立的局面,让人无所适从。这种商业投机主义产生的土壤就在于杂语化所造成的认知混乱,历史的水搅浑了,给“伪”遗产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真伪难辨,所谓保护就难以落实。圈地思维将非遗文化封闭起来,也给传承带来了困扰。古代许多传统工艺是家族谋生手段,吝惜而不外传似也无可非议,而现在许多人为满足毫无意义的文化占有欲,人为地设置传承障碍,将非遗文化的传承圈定在很小的圈子里,实为一种文化自戕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传承往往难以为继。
此外,圈地思维大行其道,降低了文化的品格。各地纷纷对本地非遗历史资源的过度开挖和解读,通过搜罗深挖,一些历史糟粕沉渣泛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夺战使得文化应有的价值因素被遮蔽,不少地方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整合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价值维度,为了圈占文化资源而罔顾社会道德观念和公序良俗,比如有些地方就抬出西门庆和潘金莲作为金字招牌,非要把文化搞得鬼气、邪气、市侩气十足,最终给人的感觉是乌烟瘴气,文化也因此变得有声无气。除此之外,圈地思维还加深了不同地区和国家人们的猜忌,以前常见争祖产闹得兄弟不和,现在则有争非遗导致各地相互拆台,国与国之间相互攻讦,失去了文化交流和沟通功能的要义。
4
“芝兰玉树,欲使其立于庭阶”,好东西都希望生在自己家里,似乎是人之常情,然而从目前来看,由政府牵头,学者发起,媒体推波助澜的非遗争夺战遮蔽了文化应有的包容性,不具有大气度和大胸怀,显得气量小,格局也小。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蕴的文化精神,其韧性和生命力往往就体现在流传的深度和广度上,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被接受并代代传承,说明它的包容精神和持久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与物质财富不同,作为“活态文化”,让它“活起来”才是真正有效的保存方式。另一方面,非遗文化资源的享用本身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沟通意识,非遗文化的流传将永远局于一隅;没有分享精神,非遗文化的价值将无法在更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现。其实,在现代社会,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对于那些穿越厚重历史而幸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生存和延续是最紧迫也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各地仍然固守门户之见和地域之分,宁愿将非遗制作成为本地博物馆里的死标本,而不愿将其放养于更广阔的江河湖海,这不仅戕害了历史流传的宝贵遗产,使得许多非遗项目失去了枯木逢春的历史机遇,而且也无益于地方文化的长远发展。地方文化部门应从文化出发,而不是从狭隘的地区利益出发,致力于将非遗项目推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其将非遗资源圈在那里发霉,半死不活,不如导水引流,让非遗文化流动起来,泽被千里。国内的一些都市如北京、广州、深圳由于文化资源以及人员的沟通往来比较频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相对开放,形成了较好的文化传播效果。北京近些年在非遗文化的传播传承上有意识地坚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将其他地方优秀的非遗文化请进来,并鼓励本地代表性非遗项目走出去,不仅为非遗项目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活跃了首都的文化氛围,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5]
事实上,在当下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空间正在被重构,不少非遗文化在地理空间中已经游移出原先所在的范围。高小康教授曾列举一例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广州越秀公园,不少市民自发组织客家山歌圩表演,此时,山歌圩的表演场地由传统客家聚居地如梅州、兴宁等地转换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中心,参与者已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乡民,而是当代都市市民。此外,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日益频繁,非遗传承人的迁移也将非遗文化带出其原生的地域范围,在异地开花结果。例如上世纪80年代,“贾氏点穴”传人陈荣钟在广东潮州开办治疗中心,2003年陈荣钟到深圳工作并培养传人,2014年,“贾氏点穴疗法”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项传统的医疗技艺由此成为深圳的非遗文化资源,得以在这座移民城市中发扬光大。[6]以上事例表明,传统的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已随着人员流动和文化传播的加速而流散到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因此,非遗文化传承、传播面对新的文化环境需要有新的开放性思维,不应拘泥固定的地域范围,这就需要重构我们传统的文化空间,包括非遗文化的保护格局,“重构传统文化空间以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存在,最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保存过去,而在于建设未来。”[7]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自古封闭的,千百年来向外传布,也接受外界的影响,文化的触须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历史遗存形态相互勾连,形成相互的认同感和代入感,真正地将非遗文化变成各地、各民族割不断的精神纽带。
文化日新在于开放的意识,文化传承也需开敞性的思维,处处心存沟壑不是文化大国应有的胸怀。古有“六尺巷”的典故来说明谦让的美德,然而将“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移植到非遗问题上却并不妥当,牌坊竖起来了,墙却还在那里,似乎应该改为“何妨拆墙通来往”更好一些。回到韩国申遗这个问题上来,首先应该明白,申遗并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与其在名头上打口水仗,不如切实加强自身的非遗文化建设。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国与国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应该相互合作,诚如非遗保护专家王文章先生所言:“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民族和国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大家一起承担责任是好事。”[8]2014 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两个项目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项遗产都是跨越国内多个省市,是沿线各地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从申遗到后续的保护,都得益于各地共同的努力,这为我们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圈地思维提供了绝佳的范例。因此,各方应摒弃“我有你就不能有”的圈地思维,尽可能加强沟通,互通有无,交流非遗保护经验,分享历史资料,尝试共同申报,共同开发,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1]董明惠.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J].中州学刊,2013,(9):91-94.
[2][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 [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3.
[3]肖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理标志保护模式[J].求索,2008,(2):53-55.
[4]吕俊彪,向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博弈[J].广西民族研究,2012,(1):169-174.
[5]黄仲山.2013年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A].北京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13-2014[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66.
[6]深圳贾氏点穴疗法上榜国家级“非遗”[N].深圳特区报,2014-12-05.
[7]高小康,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8]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358.
责任编辑段君峰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11
G123
A
1004-0544(2015)10-0061-00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X06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2014A228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2014A1962)阶段性成果。
黄仲山(1980—),男,安徽六安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