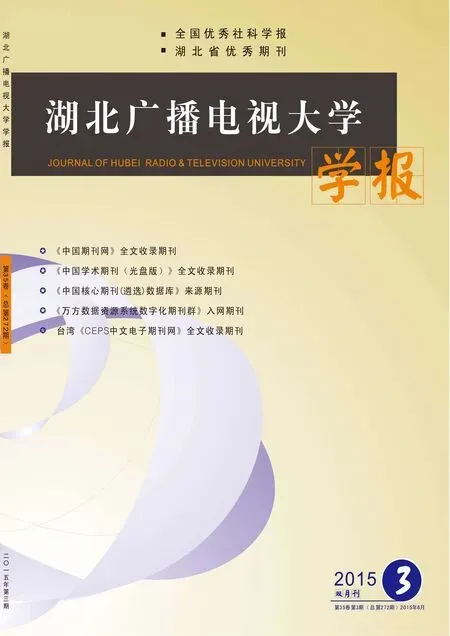纳博科夫的结构之谜
夏凌云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湖北 武汉430074)
一、前 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裔美国作家,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生平创作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他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最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同时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纳博科夫的一生颠沛流离,他的作品亦如他的经历,离奇曲折中透着诗意,另类创新中却不乏真实。他用神奇的笔触构筑了一个又一个纷繁而又典雅的谜宫,留给世人徜徉往返的无限空间。本文以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勾勒其作品中的结构,以此领悟其文学艺术的真谛。
二、线型结构
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贵族,由于政治原因,从1919年20岁起就开始了流亡生活,先后定居柏林和巴黎。1940年迁居美国,最终加入美国籍,晚年长住瑞士。纳博科夫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童年的快乐、少年的阳光、家庭生活的温暖成为他记忆中的天堂,也成为他早期作品的主题。纳博科夫一生创作了582篇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完成于离开俄国在欧洲流亡至迁居美国以前。纳博科夫用朴实的笔调把零散的生活片断归结到一个启承关系的结构中,人物和情节都集中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主线之上。这种单线型结构有两个特点:第一,围绕一两个主要人物展开情节描写。第二,作品只安排一条线索。《O小姐》(1939年)是对纳博科夫童年时代法语家庭女教师的回忆。稍晚时间发表的《初恋》(1948年)讲述作者童年时去欧洲度假,在海滨结识的一个可爱的女孩给他留下青涩却又美好回忆的故事。这些作品都忠实于生活的细节,情节单纯,线索明晰,没有任何技巧上的虚构,使得主题在完整的情节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中表现出众。
单线型结构只占据了纳博科夫小说结构中的微小一部分。早在1926年,纳博科夫的结构就有复杂化的趋势。过去与现在,想象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致使主人公无时无刻都意识到,这个世界里还存在另一个“我”,如影随形地跟着。因此,小说的线索开始复杂,两个“我”构成了复线型结构。
1926年创作的《玛丽》讲述的是:一个流亡柏林的俄国人“我”得知另一位流亡者的妻子即将从俄国到柏林,而那位流亡者的妻子正是“我”以前的女友玛丽。于是“我”灌醉了那位流亡者,去车站接玛丽,但“我”很快意识到玛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女友,于是在玛丽到达之前离开了车站。这是一部乡愁小说,在回忆与现实的双重结构中书写着失意。当主人公试图去捕捉回忆时,回忆始终不能成为现在的交集,更无法演变成现在的延续。写于1938年的《菲雅尔塔的春天》与《玛丽》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的主人公“我”也是在异乡的环境中邂逅了一个叫“尼娜”的女人,并由此回忆了与她的五次相遇。“我”与尼娜的五次交往仿佛是发生在与当下生活画面平行的另一个世界里。它并不破坏“我”与尼娜各自的现实存在,却又发生在两人之间挥之不去的生活中。当他们相遇,生活的节奏立即发生变化,所有生活的微粒都重新组合,他们便生活在另一个轻松的介质里。这样并行的复线型结构,反映了流亡者内心充满希冀却又矛盾痛苦的心理。
除了描写情感生活,纳博科夫也用侦探小说的模式进行创作,在复线型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元素:镜像关系。所谓镜像,就是指事物在镜子中映出的反像。创作于1936年的《绝望》写了一个经营失败的德国人赫尔曼,在布拉格遇到一个跟他长相十分相似的流浪汉费利克斯,他精心策划将后者杀害,并指使妻子报案以获取一笔保险费。赫尔曼最终被警察逮捕,神经错乱。纳博科夫的镜像关系首先体现在人物层面,即两人长相相似,另外更体现在文本的建构层面。《绝望》里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赫尔曼谋杀费利克斯的故事,另一个是赫尔曼为自己的谋杀自我评注的故事。在这样的复线型结构中,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相互兼容,相互指涉,镜像里生出无限的他者与自我,造成了文本结构的复义性,使得小说反映的生活内容得到充分展示,展现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孤独的处境,人物形象也刻画得丰满充分。
尽管纳博科夫的文本已经开始变得复杂化,但他仍然是一个对真实生活怀有温暖回忆的人,是一个不带任何面具的人,充满了主观情感和人道主义色彩。此时纳博科夫的结构和读者之间是可交流的,可感知的,也是无距离的。
三、辐射型结构
1919年纳博科夫带着伤痛离开了俄国,辗转来到欧洲。在此后的20年里,纳博科夫作品渲染了浓厚的流亡色彩。流亡人生对他在“世界”“现实”“时间”“意识”等方面的认识具有根本性改变,进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小说观。纳博科夫逐步告别乡愁主题,进而探索永恒纯粹的思辨性主题,如时间、空间等。
传统小说的叙述结构方式是把作品组成独立自足的整体,不管情节如何地颠来倒去、盘根错节,小说始终是建筑在一个相当完整、严密的故事结构之上。因此,人物的设置、命运的安排,都要限定在一定的视野范围内。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其他人物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主导情节线,这就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小说的时空容量。纳博科夫的小说没有遵从传统的叙述结构,叙述顺序没有依照单纯的物理时间的先后,他将结构的统一性瓦解,并无限发散。
耗费纳博科夫五年心血,于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描写了一段为常理所不容的畸恋。男主人公中年教授亨伯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十二岁的美国女孩洛丽塔,近乎病态的执迷最终把他引向毁灭而锒铛入狱。小说从亨伯特在狱中的忏悔散射出去,以主人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行为方式贯穿全文。
出版于1966年的《说吧,记忆》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出色的自传之一。纳博科夫用记忆的闪回与切入,带着读者走进了早年的人生经历。幸福的童年生活,幼年时的初恋,他的旅游,他的家庭教师,他对动植物所培养出来的独特的兴趣,对蝴蝶的挚爱,都在一一对应的时空里发生、发展,而记忆也就攀沿着翠绿的根,穿透障碍,巧妙地嵌入空间的窄缝,横亘出时间的长久。在所有这些真实的物理空间里,交替变更着一个个伤怀的故事。身处陌生境遇的纳博科夫在忧伤迷惘中徘徊挣扎,在融合与排斥中踯躅前行。
《透明物体》(1972年)记录了一名编辑胡夫·波森四次访问瑞士的情形。小说并不提供连贯的胡夫的行程,胡夫拜访作者R先生、父亲去世、与妻子相识、结婚、误杀妻子、自己死于火灾等情节没有先后联系,在无数的倒叙和插叙中将情节无限的悬置起来。结构上的空缺为读者的阅读留下了发挥想象的巨大空间。读者只有在通篇阅读结束后才会了解胡夫的家庭、职业、生理疾病及最终结局。插叙结构使得小说跳出了情节框架和线性时间的束缚,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颠覆了追溯过往的单向度时间模式。
纳博科夫的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对两个时间结构的协调控制能力。一方面,他紧紧把握物理时间,即钟表时间,用它来支配全书的框架和作品的叙述。物理时间的流向是单向度的,永远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依次线性演进。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采用心理时间,将物理时间之点重新排列,或交错、或重叠、或省略、或强化,这种块状放射性意识结构展示人物离奇复杂的感情和叙述的独特视角,捕捉瞬息万变的思维火花。尽管埋没主题的意象呈现为分散的碎片,但作者的“透视点”很集中,情节线索都以这一点发射出去,显示出无限的扩展性和巨大的凝聚力。叙述者穿透时空的界限,超然地观察和记录着人世间的林林总总。纳博科夫的结构不仅起着组织和联接的作用,而且还蕴藏着小说内容的奥秘。随着小说结构的变动,世界也跟着变化,由此便产生出对社会生活新的概括能力,创造出某种新的意义,增大了作品的容量,共同展示了作品的现代意识和精神结构。
四、螺旋型结构
“我的生命犹如玻璃球中的彩色螺旋”[1]266──纳博科夫曾这样比拟自己的一生。螺旋是圆形神灵化的体现,圆在断开后,表现出时间上与生俱来的螺旋性,螺旋因此有了生命。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纳博科夫的生活环境逐渐稳定下来,流亡的主题也从主轴退居到副线,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高超的创作技巧与多变的主题。在《说吧,记忆》,纳博科夫谈到了他的创作过程:“……我时刻准备牺牲形式的纯洁,以换取奇异的内容,使形式如同装着一个狂暴骚动的小鬼一般膨胀、进裂。”[1]281他在作品中讲究全篇的文体结构,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被共时性的空间叙述结构所代替。螺旋的精巧,贯以细节上的精雕细刻,文笔的艰深晦涩,叙述的另辟蹊径,以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终极追问成了纳博科夫独特的艺术风格。
《塞·奈特的真实生活》(1938年)叙述一名俄国流亡者通过为他将死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作家塞巴斯蒂安撰写传记,来驳斥塞的秘书所写的另一部歪曲事实的书。小说结尾,叙述者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与兄弟合为一体:“我成了塞巴斯蒂安,或者塞巴斯蒂安成了我,或者我们可能变成一个我们俩都不认识的人,我们俩也许是彼此谁也闹不清的某某人。”[2]从起点到终点,离奇的巧合,出人意料的重复,正是纳博科夫追求的一个目标:圆,螺旋的圆。螺旋的伸展扭转中变化层出不穷的空间,展现命运的重复细节和连续的图案。
1953年到1957年创作的《普宁》引起了美国读者广泛注意和欢迎。小说描写一个流亡于美国的俄国老教授铁莫菲·普宁的生活。普宁为人温厚而怪僻,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物格格不入,终日沉缅于故纸堆里,通过钻研俄罗斯文化和古典文学来逃避现实。《普宁》的结尾耐人寻味,在最后一章中透露出讲这个故事的人的身份:作品人物之一的“我”与普宁同时存在于小说的虚构空间中。“我”早在40年前就认识了普宁。最后邀请他到温代尔学院任俄文教授,但由于普宁孤僻性格终于使他忍受不了周围的一切,驾着那辆寒伧的小轿车走了。“我”去追赶却没有成功。普宁的车子“终于自由自在,加足马力冲上那条闪闪发光的公路。”[3]此时,虚幻的普宁结束了他异于常人的存在方式,化为另一种生命形态进入日常世界。至此,小说的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圆环,仿佛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小蛇。[4]如果说普宁是活跃于前台的具体形象,“我”则是故事中明察秋毫的全能叙述者。作品以“我”的视角观照着普宁,而“我”和普宁又都是统摄于作者的掌控之下。纳博科夫让叙述者在叙述层的不同界面上自由行动,在不同的艺术空间中淡入淡出。
1962年出版的《微暗的火》被人称为是纳博科夫小说中最具有试验性和最神秘莫测的一部小说,无论从形式还是结构上都是独具风格的。前一部分是999行诗,后一部分是繁琐的注解和索引。小说近似文字游戏,多层次的结构如迷宫一样,反映了作者在叙述艺术上的创新。小说写一个从赞布拉放逐出来的国王改名为金伯特在美国一家学府任教,他的邻居约翰·谢德教授是一个诗人,在完成伟大诗作《微暗的火》后被一名罪犯误杀。谢德去世后,金伯特从谢德夫人手中索取了诗稿,并通过对诗作的妄加揣测,讲述自己浪漫而危险的生活经历。《微暗的火》结构奇特、复杂,可以看做是一个幻想家幻想的产物。
诗名《微暗的火》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中对比日月光源那句话,意指太阳比喻生命力的源泉,月亮是一种反复无常而欺骗性的源泉,它那微暗的火只是反射之光。作者把谢德教授看作是太阳式的人物,而金波特则是月亮式的人物。谢德的诗作和金波特的注释是《微暗的火》中的两个不同的空间。谢德的生活以及诗作是建立于现实空间的,体现出纳博科夫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全部因素;金波特的注释则是建立在想象与虚构之上,他任意删改谢德的诗行,并借题发挥,讲述想象空间中的赞布拉王国的故事。所有故事都远离线性的时间而以混乱的碎片漂浮在文本之中,并以螺旋的结构相互绕合。著名评论家博伊德曾评价《微暗的火》“不仅以一个世界的价值出售给我们两个世界,而且还给了我们这两个世界结合的疯狂喜剧。”[5]
纳博科夫后阶段的作品晦涩难懂,复杂的结构实则是多层面的。第一层面是尘世的或传统的现实性,是文本的世界。第二层面则是理想的或主观的现实性。在创作中,纳博科夫认识到自身作为作家所具有的超越于所创造出来的文本世界的造物主般的地位,并有意识地将这一点贯穿于作品之中。塞巴斯蒂安借助潜意识,普宁依靠回忆,金波特假借文学,胡夫重温旧梦,都是通过想象超越尘世凡俗,在主观的空间里演示着现实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都是纳博科夫的作家意识借助人物的外化。同时,作家在所创造的世界中有着有限的意识,又为另一种更高等级的意识所限定和操纵,向着那绝对存在努力,这就是第三个层面。评论家D.B.约翰逊在《回退的世界》一书中,也谈到了纳博科夫创作中螺旋型等级结构模式。他总结说:“每个世界都是一个层次的意识,这意识又被包裹在一个更大的层次中,这更大的层次创造和包含了那更小的一个层次。”[6]纳博科夫的螺旋型结构可以总结如下:文本世界——创造文本的作家意识——创造作家的神灵意识——更高意识——最高等级的无限意识。纳博科夫将可见现实与精神现实结合在一起,叙述者在多层级中流连忘返,形成了多个相似的圆环结构,时而重合,时而分离,时而并行,时而缠结。虚幻的空间里上演的是世俗的悲欢离合,现实的丝带编织的却是五彩透明的梦。结构上的虚实、疏密、主次、浓淡、断续等辨证关系产生了似真似幻的错觉和更为宽广的螺旋往复的美感。
五、结 语
纳博科夫的小说,不论长短,感性或理性,情节都很简单,以精美的结构承载叙述。纳博科夫有一句名言: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7]其实,正是纳博科夫风格的独特和结构的精致才体现其巨大的想象力和深邃的思想。纳博科夫用魔幻的手法,艺术的创作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每部作品中都会有两个纳博科夫,一个置身“此在”,一个远离“此在”。前者属于具体一部作品;后者属于每部作品,更属于高居于所有这一切之上的那个纳博科夫。从根本上讲,纳博科夫是“非此在”写作的。他站在人类历史的终点,等候着另一个他。读者跟着连袂而行的两位纳博科夫,逡巡于他的小说世界,与他的角色打交道,同时又在一副俯视的眼光的注视下,在结构的迷宫中艰难但快乐地寻找着并不存在的出口。纳博科夫作品在结尾处时而悄然遁身,时而自行解构,时而巧妙复合,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可以参与其中。纳博科夫在亦真亦幻中为人们揭示彼岸的信息的特征,探索艺术哲理的真谛。
[1]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M].陈东飘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2]纳博科夫.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M].王家湘,席亚兵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318.
[3] 纳博科夫.普宁 [M].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204.
[4]CharlesNicol.“Pnin’s History”,FromCritical Essays on Vladimir Nabokov,Phyllis[M].A.Roth.G.K.Hall&Co.Boston:Massachusetts,1984:72.
[5]Brian Boyd.Vladimir 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rinceton[M].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427.
[6]Johnson,Donald Barton.World in Regression:Some Novelsof Vladimir Nabokov[M].Ann Arbor,Mich.:Ardis,1985:203.
[7]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译本序言 [M].申慧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