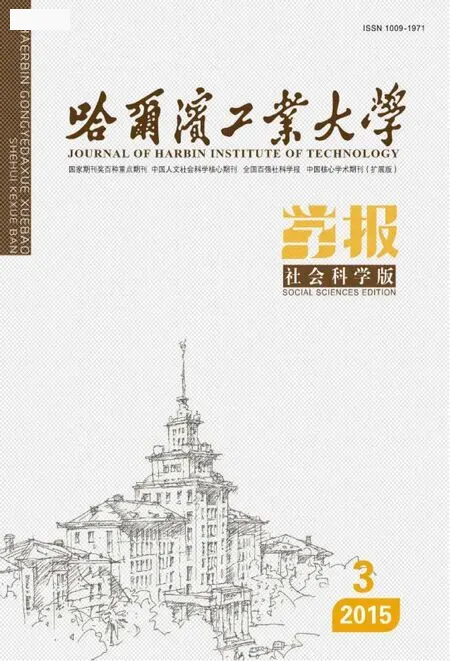从僧传与小说关系角度看《坛经》中的惠能传
王 芳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2)
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结构与手法来源之一就是史传,中国古代的史传也多有文学笔法。佛经、僧传作为宗教领域的典籍和历史传记,和佛教题材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之间的关系亦非常紧密。西方互文性理论文论家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1]。《坛经》诞生于唐代后期,有多个版本存世,且在版本演进过程中经过不同僧俗文人之手,宋代吏部侍郎郎简在契嵩本《六祖坛经》的序言中写道:“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2]177其所言“患其为俗所增损”,道出了《坛经》自最初版本诞生后经过不同的僧人和文人之手增删的事实。①①如张培锋先生曾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曹溪本《坛经》的编订者可能是陈俶,参见张培锋《〈六祖坛经〉与道教、道家关系考论》,《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坛经》的多个版本,可以说有多位作者参与其中,这就导致《坛经》中更明显地存在着先前和周围文化中的其他文本,也包括文学的文本,其中的惠能传部分,兼具僧传和小说两种属性。《坛经》的诞生和每一次相对较大的增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增订者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尤其受到当时传奇小说兴盛、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倾向增强等因素的较大影响,具体体现在谶言描写、其他神异情节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
一、《坛经》中谶语描写的文化与文学意味
契嵩本《坛经》在五祖弘忍传法于惠能,并嘱咐“汝须速去”之后,增加了这样的文字:
“能曰:‘向甚处去?’祖曰:‘逢怀则止,遇会则藏。’”[2]22
这样隐语式的预言,契嵩本中增加了不止这一处,如惠能为惠明说法后有这样几句后加入的话: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2]26-27
这一处与上文中弘忍指点惠能的话如出一辙。
此外,在契嵩本《六祖坛经》的“咐嘱品”中,惠能去世前召集弟子,在突然表示欲归新州之后,有这样的对话:
(弟子)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2]156-158
这几段隐语式的预言从形式和作用上都等同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中的谶言,它们在契嵩本之前的法海本、惠昕本中是所没有的。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继承了佛教运用偈语的传统,同时也明显有通俗小说的痕迹。谶言本不是小说用以作意好奇的专利,它本是古代神秘文化思维的产物,在政治和民间文化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进而才影响到小说创作。早在先秦时期,占卜性质的活动产生的语句如甲骨卜辞就可看做谶言的前身,后来这种卜辞之类的语句蒙上了政治的色彩,在形式上演变得更加精炼,才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谶语[3]。随着历史的发展,谶言逐渐成了古代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指涉政治扩散到指涉个人命运,由现实走入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的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长篇小说,都常用谶言来增加趣味、推动情节,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叙事特色。杨义在《中国叙事学》的“时间篇”中认为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预叙是强项,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能看到预叙的最初形态,而在叙事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左传》等史书就通过描写占卜等活动造成预言叙事,在客观上形成了叙事文学作品中较早的预叙。在后世的史传和小说中,预叙的出现频率非常高,譬如史传、僧传中对高人料事如神、预言必应的描写;再比如《说岳全传》、《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中“叙事元始”的应用,这写小说在开头部分就以带预言性的“元故事”、“后神话”来揭示后文将要讲述的情节[4]。在中国叙事文学中最常见的预叙手法就是使用谶言。
在佛教的发展历史上,谶语也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佛教文献中所说的“谶”与其他“谶”有区别也有联系。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篇引李复言:“潏水(李复)云:梵书有修多罗谶,言释氏之教兴废。”[5]王应麟认为由梵书中修多罗谶能够说明“则谶书其来远矣”。何焯对此作注:“东汉尚谶纬,此妖书所由乘之以兴。”[5]2188而全祖望认为:“此‘谶’字不可即指汉人谶纬之书,何氏亦因潏水而附会之。”[5]2188王应麟认为梵书中的“修多罗谶”能够说明中国谶书之渊源久远,何焯认为东汉时期谶纬的发达使佛教借机得以兴盛,而全祖望则认为李复所言“修多罗谶”之“谶”不同于汉代之谶。
综合这几家说法,可对佛经中的“谶”与中国历史上的谶言之关系做一番辨析——如果从谶言的广义内涵来说,带有预言性质的话语都可叫作“谶”,故佛书中修多罗之言佛教兴废之预言也可称为“谶”。而全祖望所言“汉人谶纬之书”是专指汉代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兴盛的谶纬之学,汉代谶纬包括当时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工具的谶言、谶谣之类,也包括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的纬书。王应麟因“梵书有修多罗谶”而认为“则谶书其来远矣”,似乎不当,汉朝兴盛的谶纬现象,原因似乎不能追溯至梵书,但是不管是印度的佛教经典,还是汉代兴盛的谶书纬书,都是古代神秘文化思维的产物。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作为外来宗教,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当时佛教一方面被动受到中国固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主动借鉴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和民间方术,以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而且佛教因本身有异域色彩,再加上教义堂奥,故在民众眼中难免有些神秘,就被大众看作中国民间方术一类事物,僧人也被看作方士、道士一类人,佛经便在当时谶纬之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被当成一种谶纬之书。①参见蒋逸征《超能与无能——从〈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看唐代的宗教文化风土》,载于《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2期。中国汉代的谶言与政治变动和民间方术有紧密的联系,而佛教追求超脱,不求干预政治,并禁止占卜、星象等方术,佛经中的预言被人与汉地的谶言混同,正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本土化甚至庸俗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可见,谶言具有跨越政治、宗教与文学的多重功用,《坛经》中的谶语也可从多重角度来解读。从其在文本中的思想功能来看,它们无疑增加了高僧的神秘性,使得高僧的能力契合佛家“六通”说法。尽管对佛教徒而言,这些有辅教、传教作用的描写,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但以世俗眼光看,它们毕竟有明显的虚构色彩,且从版本演进的角度来考察,多是后来的编纂者所增加,所以我们也需要从僧传与小说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谶言的增写。
《坛经》诞生于中唐时期,版本演进的阶段也基本在唐宋,这正是佛教题材小说和唐传奇文体走向成熟的时期。当时种种题材的传奇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多种多样,谶言描写不只是迎合大众猎奇心理,也是塑造异人形象、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安排人物命运、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从形式上看,小说作者笔下的谶言往往以字谜、韵语形式出现,形式整饬。如李公佐《谢小娥传》中,谢小娥梦见父亲向自己交代“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后又梦见丈夫言“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就是用隐语的形式设置了一个悬念,吸引读者带着“凶手是谁”的兴趣读下去。这种字谜式的隐语,尽管在古代政治斗争中的谶言与歌谣中就有了,但是到了唐代的传奇小说文本里,这类隐语主要起叙事作用、指涉个人命运走向。从逻辑上说,谢小娥梦中的父亲和丈夫也可以直接告知谢小娥凶手的名字,但作者偏卖了个关子,让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用字谜的形式道出凶手,此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谢小娥和故事外的读者都充满了疑问,作品本身也就带上了悬念。
《坛经》中几则后加入的谶言在形式上也很整饬的四言句式,语言较为通俗直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文中的功能是指涉人物的个人命运走向,而不是表达佛理,传奇小说中起预叙作用的字谜式谶言同样多指涉人物个人命运。谶言也在客观上起到一种提示作用,即暗示惠能已成为高僧,如第二条惠能启迪惠明后,指点惠明今后去处,言“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是弘忍嘱咐惠能“逢淮则止,遇会则藏”的翻版,惠能对惠明的传法、指示,客观上标志着惠能已成为一名大师。此外,这些谶言的增加,对读者而言有提升悬念和趣味的阅读感受,是不言而喻的。但《坛经》惠能传部分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其运用谶言作为叙事手段,与小说才去此手段的效果不尽相同。《坛经》不着意于描写谶言应验的那一酣畅淋漓的时刻,而是更注重惠能说出预言的过程,以此来神化惠能。如《坛经》中写到惠能圆寂,尽管给出了“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这则谶语,也说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但后文对于惠能身后其法门传承仅用寥寥数语带过,也并没有写到他去世多年后张净满受朝鲜僧人金大悲指使盗取首级不成的情节,读者要了解这一来龙去脉,还需参考其他文献,因此这一预叙只能算是“外预叙”。对于通俗小说来说,不论长短,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始有终、相对完整的文本,读者在其中感受到的悬念,必然要在该文本内部得到解答。而《坛经》惠能传奇作为宗教文本,是整个宗教历史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在惠能传奇中谶言的增加给读者增加了悬念、趣味,但是读者只有联系起整个宗教历史体系中的其他文本,才能完成《坛经》惠能传奇的阅读。故在这一层面上,《坛经》文本的演进,不但受到先前文化文本和周围文化文本的潜在影响,也与“后来”的文本做了联结。
二、《坛经》中的其他神异描写与惠能形象的世俗化倾向
除了谶言的运用,《坛经》惠能传部分也有其他的神异描写,如惠能振锡出泉、遇刺而刀枪不入、以及圆寂时的奇景异象等。从这些神异描写中可以看出古代史传与小说相互交融、彼此互见的形态。对此我们需要联系唐代的其他佛教题材传奇及笔记小说。
《太平广记》卷八十七至卷九十八收录关于异僧的小说、笔记多篇,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以出自于《高僧传》等佛教史的僧传,另一类是出自各种笔记小说集、传奇小说集的作意好奇之文。前者是传记文学,有纪实性,后者是小说,重在虚构。有趣的是,编纂者却把这些性质不同的作品按题材放在一处。其实细分起来,尽管《高僧传》一类僧传中也会加入神异性的描写,并非只有平易如实的描述,而传奇小说中的僧人形象也不都是虚构的,很多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僧人,但是僧传毕竟与作意好奇之小说有一定的区别——僧传往往篇幅较长,历史容量大,详细记载传主生平,说明传主佛教思想,尽管会有夸张、虚幻的神异描写,但并不占太大篇幅,作用主要是为达到“自神其教”的宗教目的,如《康僧会》《支遁》等篇。而笔记、传奇小说的叙述重点就是僧人的奇言异行,往往只写具体的一个或数个神奇的事迹,并不着意于叙述僧人生平与思想,也较少涉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其他事件。例如《太平广记》卷九十七所收录的出自《西京记》的《秀禅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爇,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瘗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6]645
通过文中提到的“洛都天宫寺”、“汴州陈留人”、“天宫寺”及死后有“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等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这则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大通禅师神秀为原型,或者说就是一则关于神秀的轶事。但这则故事并不着意于介绍秀禅师的生平与思想,而是通过记述两件“未卜先知”的小事来刻画一个料事如神的高僧形象,令读者啧啧称奇,尽管也简要介绍了秀禅师的来历,但也只是像其他杂传类传奇小说一样增加真实感,因此文中的秀禅师不完全是历史上的神秀,而是故事中的一个形象。
如果说这则《秀禅师》中所描述的高僧预言尚可被解释为出自阅历丰富的远见,神异色彩并不浓郁,那么《太平广记》卷九十四所收录的出自《原化记》的《华严和尚》,就是一则明显地以真实人物为主人公,但情节曲折离奇的志怪小说了: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怒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6]624
华严和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此文中是作为一个高人形象出现的,文中另有性颇褊躁的僧徒和青涩胆怯的小沙弥两个形象,再加上情节曲折离奇,这篇文字无疑是有趣的小说。对佛教信徒来说,这样的作品也有传教辅教之作用,但对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人物由和尚改换为道士,也毫不影响阅读乐趣。
综上所述,僧传与僧人题材的笔记、传奇之间既有显而易见的区别,又有微妙的联系:僧传尽量写真人真事,但所写的是作传者眼中的“真实”,它吸收民间传说中的神异成分,和笔记、传奇同样有夸诞、玄想的色彩;而笔记、传奇尽管着重于虚构、猎奇,却也会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为主人公或原型,以一些手段营造真实的氛围,所以它们同僧传一样有真实的成分。中国古代的僧传与僧人题材小说就是这样在彼此交融的形态中各自存在着,《坛经》惠能传部分因此能兼有传记与小说两种属性,是深深契合这一文化现象的。
既然惠能传这一部分具有小说的属性,文中部分事迹是后人所增加、润色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坛经》中惠能的形象,也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的惠能,而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人物形象。参与塑造这一“形象”的作者们,无论身份是僧是俗,无论出发点是否是“自神其教”,都在客观上使这一文本有了与世俗叙事文学、广阔大文化背景的紧密联系。惠能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就有当时文化环境的烙印,这具体体现在惠能的部分神异事迹和不识文字两点上。
契嵩编订的版本中,《顿渐品第八》增加的张行昌行刺情节是之前版本中没有的: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警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2]127
这段因南北宗分化而导致佛门弟子矛盾激化至雇凶行刺的情节写得颇有任侠小说风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惠能不但能预知有人来行刺,还在“行昌挥刃者三”的情况下“舒颈就之”、“悉无所损”,可谓玄之又玄。以宗教视角看,既能“心通”,又有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正说明惠能大师已经成佛。然而,这类对于高僧成佛之后神通能力的描绘也是出于一种庸俗化的想象。“金刚不坏身”据《大宝积经》卷五二解释为:“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坚固之身,超于三界最胜之身。”[7]“法身”是佛教“三身”之一,从本质上说它是指遍及法界的真理,本来并不是指某一人或身有刀枪不入的坚固身体。《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三《报恩品》:“法身无形离诸相。”[8]又如《大方等无想经》卷五《37增长健度》:“法身无像不可睹见。”[9]正是因离诸相、不可睹见的真理,方能如金刚般不坏。但“金刚不坏身”这一说法又无法不令普通民众想象为具体的人身,这种经过了通俗、直观的“误解”之后的“金刚不坏身”在中国的各种文学作品中被用作典故,甚至佛门弟子也不再深究,而是按照世俗化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佛教术语。《高僧传》卷四所载汉地第一位西行求经的僧人朱士行就有一副在圆寂后依然不怕烈火的“金刚不坏身”:“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阇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众咸惊异,乃咒曰,若真得道,法当毁败。应声碎散。因敛骨起塔焉。”[10]146自《高僧传》有这一记载,后世不断有类似的夸张传说载于书册,《坛经》中惠能大师以脖颈就刀刃而毫发无损,也是其中一例。
《坛经》中早年的惠能大师被塑造成一位目不识丁的樵夫,但惠能是否真不识字,今人有不同说法。饶宗颐《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一文中谈及惠能的文化素养,从家庭背景、母亲的出身和成为高僧后新州故宅被赐额为国恩寺等史实说明,惠能文化素养并不低,出家前也并非一贫如洗[11]。那么为什么惠能的形象在《坛经》等书中一贫如洗、目不识丁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佛教否定性思维在叙事文学中具象化的结果。方立天《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中提道:“佛教追求的超越现实的人生理想境界,或者是彼岸佛国世界,或者是排除一切烦恼、欲望、妄念的主体内在本性的纯正呈现。这就需要运用否定思维以否定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体悟人空或一切皆空的佛理。”①方立天:《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载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3期。佛教的这种否定性思维在佛教题材的小说里被形象化为颇有意味的矛盾性僧人形象②参见曾礼军《〈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载于《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如牛肃《纪闻》中《法将》一篇中的“襄阳客僧”:
长安有讲涅盘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籍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狘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迳持酒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门下,以手擘狘襄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盘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盘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6]629
唐代有不少这类酒肉和尚的记载和文学形象,释道宣《感通记》写初唐僧人法琳也是一例。这些人物的作为从表面看是破戒了,但实际上往往通达了佛家真谛。佛教戒律规定僧人不得食肉饮酒,但却有人又把这一戒律做了一番否定,以说明对于真正的通达悟道者而言,饮酒食肉也无非是空。《坛经》的结撰者用同样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塑造了不识字的惠能形象——高僧本该广阅经卷以参透佛理,但以禅宗“不立文字”的思维来看,既然真正的佛法是以心传心,那么立言传法的方式便不是最上乘,一个不识字的高僧形象才能最生动直观地说明禅门心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否定并不只是出于宗教思维,也是叙事文学创作思维的体现。文学具有天然的否定性思维,因为文学具有虚构的特性,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修辞性,往往拒绝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所以任何一位参与到文学文本结撰过程中的主体,都会用各种否定固有事物、固有思维的方式来使自己的创作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文学的否定性思维以及宗教的否定性思维,都可以说明《坛经》等书中“文盲高僧”惠能这一形象形成的深层原因。
小 结
纵观各个版本中的《六祖坛经》惠能传记部分,可以看出,这一文本自诞生起,在不断的版本演进中,一直体现出与世俗文化思维和通俗叙事文学的密切联系,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属性。中国古代众多高僧传记在事迹描述有很多相似性,也多经历了版本的演变,故这一观点也可为分析其他类似文本作为参照。
[1]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5:44.
[2]郭朋.坛经对勘[M].济南:齐鲁书社,1981.
[3]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8-14.
[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1-157.
[5]乐宝群,田松青,吕宗力.困学纪闻[M].校点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唐]菩提流志编译.大宝积经:第二册[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04:367.
[8]大正新修大藏经,CBETA,T03,no.159,p.305,b3.
[9]大正新修大藏经,CBETA,T12,no.387,p.1103,a28.
[10][梁]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146.
[11]《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编辑委员会.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G]//卷五:宗教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31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