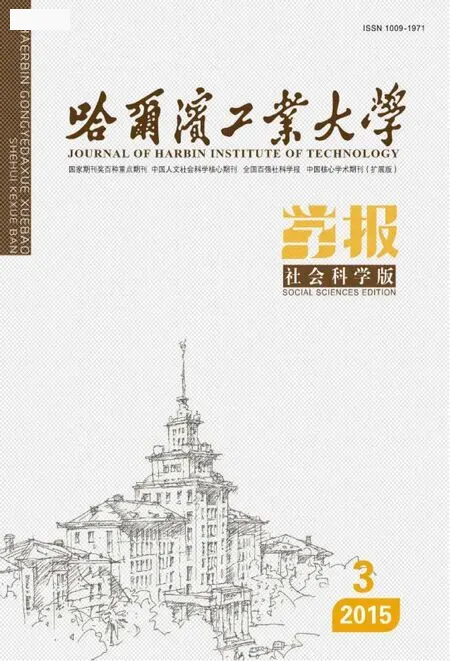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李舜臣
(江西师范大学 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南昌330022)
中国佛教向来是一种“国家佛教”,教权始终运行于政权体制之中,它的发展常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依托于佛寺的僧侣的文学创作、心性情感,与特定时期的佛教政策自然亦密切关联。此种情势,在大批诗文僧被广泛纳入到政教网络中的洪武朝,显得尤为突出。很多诗文僧的声誉、命运沉浮,与明太祖均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洪武朝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本文拟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考察洪武朝诗文僧的命运和创作心态,力图呈现出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
一、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学界关于洪武朝实施的佛教政策,已有相当成熟的认识。释见晔认为经历了“管制、怀柔、隔离”三个阶段[1],周齐以为“基本上是恩威并举,宽严并施”[2],何孝荣认为是“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3],任宜敏则以“尊崇、整顿与控制”[4]概括之。诸家的表述、内涵不尽相同,但皆认识到洪武朝佛教政策的“两面性”和“阶段性”:以洪武十四年(1381)僧录司的建立为标志,前期以怀柔为主,后期则以管束为主。这样的认识,显然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明太祖的佛缘,始于他十七岁时入皇觉寺当小沙弥的经历。这段经历,虽未使他认清佛教之本质①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四载有明太祖《御制龙兴寺碑》,自云:“于教茫然。”又,“明太祖文集”卷八《谕僧》中云:“朕不知法。”,但对他登基后采取的佛教政策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和尚”的身份似乎有损“真命天子”的威严,因为这是史上绝无之先例,所以他对“秃”、“和尚”之类的字眼颇觉反感;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以及彭玉莹等人借“明教”起义之事,又使他深谙佛教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对于巩固皇权的特殊作用。因此,定鼎之后,太祖屡次强调佛教“阴翊王度”、“佐王纲而理道”的功用,尝说:“佛之有经者犹国著令,佛有戒如国有律,此皆导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恶。”[5]又特撰《三教合一论》,以弥合儒、释、道,使之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明太祖还积极地将此种思想付诸实践,频繁地征召僧人以预佛事,甚至采取“儒化”僧人的措施。洪武八年冬,“诏天下凡寄迹佛老而有志于圣贤之学者入国子学,俾习知天理民彝,然后授之以政焉”[6]。僧人入国子监习儒家圣贤之学,这在历朝都是极罕见之事。基于此一背景,那些儒释兼修、诗禅两得的“复合型”僧人,大多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例如,“博通今古,儒术深明”的季潭宗泐,太祖令其“育须发以官之”,宗泐婉谢后,又亲撰《免官说》一文 赐之(《赐宗泐免官说》)[7]170-171。又如,“禅学之暇,发为文辞,抑扬顿挫,开阖变化”的来复见心,太祖尝诏侍臣取其诗览之,褒美弗置[8]。再如,“喜为儒者博贯该通之学”的独庵道衍,被太祖命事燕王藩邸,诵经祈福[9]669。明太祖将此种僧人称为“儒僧”,撰《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等文,鼓励他们积极入仕。洪武年间,即有不少儒僧被擢拔入仕。例如,释愿证(李大猷),太祖览其所著,赞曰:“论议甚高,其铁中铮铮者乎!”遂召见,敕吏部除以翰林官职。又有郭传,尝“寄迹浮屠”,以宋濂荐,进其文,太祖擢为翰林应举,升起居注迁考功丞[10]927上。洪武九年,钟山寺僧吴印“有文学”,太祖亲选命蓄发拜官[10]928下。这些儒僧在朝中还不止是“小摆设”,太祖对他们“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至有儒者李仕鲁、陈汶辉辈因疏言而被处死[11]。
陈玉女认为,明太祖“拔儒僧入仕”之举,实是他元末以来“礼贤”策略的延续[12]4。这既是历史情势的必然,更是基于他对佛教的认识。显然,明太祖看重的只是佛教的社会功能,纯是出于政教伦常的价值判断,而非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我们检视他的相关诗文,不难发现,他既鲜有深入阐发佛教义理的文字,亦无僧人圆融、清净心境之流露。此种因着外力而非出于真信仰的宗教观,决定了明太祖只能游移于佛门之外;随着外在情势的变迁,其态度必定会发生急剧的转变。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竟多达六十四名僧人卷陷其中。明太祖似乎又听见了元末民众借宗教名号揭竿而起的呐喊,因此,调整佛教政策势在必行。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四日,开设僧录司,目的即是整饬丛林。次年,又将佛教严格区分为禅、讲、教,各司其责。至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又相继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周知板册》《榜示僧教条例》《清教录》等,明令禁止不得僧人“潜在民间”,禅、讲、教三宗“各承宗派,集众为寺”[10]936上。几年之中,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僧人的行为被限制在寺院之中,这不仅切断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而且也分化了佛教内部强大的力量。
此种政策,释见晔概括为一种“隔离政策”和“山林佛教”,其用意是使僧人远离世俗尘嚣,入深山崇谷苦修。明太祖曾说:“僧本侣影,空山俦灯,松底吟清,风翫皓月,扪已探渊。”(《钟山僧妙云》)[7]175又说:“(僧人)当深入危山,结卢以静性,使神游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怀,景张佛教。”[13]明太祖改变原初的佛教政策,无疑是出于政局调整的考虑。不过,若是从佛教自身发展的角度评估,明太祖的此种政策导向,亦利弊参半。自元末以来,丛林风气窳败,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十分明显,他鼓励僧人走入山林静修,从某种角度而言亦维护佛门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然而,明太祖并未仅停留这一层面,他利用“胡党”案,捕杀僧人,制造酷烈的“文字狱”,使洪武后期的丛林噤若寒蝉,僧人的心境乃至命运,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二、明初诗文僧参与国家层面的佛教活动
洪武初期,明太祖倡导“擢拔儒僧入仕”,很多稍具影响的诗文僧均积极响应征召,参与各种国家层面的佛教活动。具体来说,可分以下几方面予以论述。
(一)参与佛事、法会
洪武建极,明太祖为祈求神佑和安顿战争中死难亡灵,数诏东南高僧广演法会。洪武元年(1368),“以为折抱毁鼓之初,而殁于王事者无答焉,遂蒲车四出,征天下高行沙门”,楚石梵琦等人即被征请至蒋山说法[14]。洪武三年(1371)秋,太祖又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说”,征天下有道僧三十余员,能诗者有梦堂昙噩、楚石梵琦、九皋妙声、来复见心、竺隐弘道、季潭宗泐、至仁行中等人,赴南京天界寺。洪武五年(1372),太祖设无遮法会(又称广荐法会),超度亡灵,各地僧人三千馀人云集天界禅寺。由西白万金主持,宗泐季潭、来复见心、夷简同庵、天渊清浚、天镜原瀞等能诗者参与其中,尤其是宗泐季潭、来复见心凭借法会之演法,赢得了太祖的宠信。
李圣华曾根据《古今禅藻集》《明诗综》《明史》等史料,将明初诗僧应征及事迹,汇成表格,其中洪武朝有21人[15]。但实际遗漏还不在少数。仅据《列朝诗集小传》,就可补入一云大同、行中至仁、万峰时蔚、天真惟则四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被征的诗文僧,多数有着密切的法缘。例如,觉原慧昙、宗泐季潭、清远怀渭、懒庵廷俊、克新仲铭等,均为元代笑隐大䜣门人;而西白万金,楚石梵琦、愚庵智及、独庵道衍、梦堂昙噩、至仁行中等,则元叟行端弟子或再传弟子,特别是洪武三年春的征诏,三十余员尊宿中,“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16]。这两系僧人,分属临济宗居简系与之善系,历来与统治者关系最为密切,有着积极入世的传统。
(二)奉旨出使
明太祖为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及域外的关系,数次选派僧人奉旨出使,以招谕、安抚故元僧俗首领。他曾派遣克新仲铭等三人奉旨出使西藏招谕吐番,并图其山川地形以归。克新自号雪庐、江左外史,江西鄱阳人,俗姓余,著有《雪庐南询稿》《雪庐集》等。
洪武三年,太祖“择有志沙门,通诚佛国”,觉原慧昙应诏,从行者二十余人,“道经高昌、素叶诸国,诸国俱尊礼之”,甚至“膝行求法”。次年九月,慧昙因病,示寂于省合剌国(今斯里兰卡)。太祖闻之嘉惜不已:“中原有僧,万国之光。”
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二月,朱太祖以佛经有遗佚,又遣季潭宗泐领徒三十余人至西域求经。宗泐一行历时五载,“往返十有四万程,皓首还朝”,不仅求得《庄严》《宝王》《文殊》等经书,还带回来了觉原慧昙的遗衣,一时名振他邦,声闻朝阙。
(三)整理佛经
朱元璋为了更好地管制丛林,统一思想,洪武五年(1372)命四方名德沙门,集于蒋山点校藏经,随即开雕,刊行了历史上所谓的“南藏”。洪武二十四年,又陆续刻录中土诸宗典籍,三十一年竣工,版存于金陵城南天禧寺,惜经版于永乐六年被大火吞噬。
洪武十年(1377),又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弘道笺释之。次年七月,三经相继注成。明太祖在西华楼亲自接受了宗泐、如玘的进献,阅之大悦,评之曰:“此经之注,诚为精确,可流布海内,使学者讲习焉。”并撰御制序文于前,命锲梓于京师天界寺,颁行全国。
(四)担任僧官
僧录司的僧官均有特定职责,例如,左讲经如玘、右讲经守仁,“接纳各方施主,发明经教”;左阐教来复“简束诸山僧行,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置立文簿,明白稽考,并掌天界寺一应钱粮产业及各方布施财物”[10]932上。同时,他们还要参与朝廷的一些重要活动。例如,洪武十八年九月,太祖命蜀王朱椿阅武于中都,闲暇之余,召儒臣李叔荆、苏伯衡及名僧来复辈,与之讲道论文,殆无虚日。
总之,明初有影响的诗文僧基本都被朱元璋纳入彀中,出入掖庭,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诗文僧与政治的关系,似乎从未有过如此之密切。
三、明太祖的涉佛诗歌及其与僧侣之唱和
明太祖于万几之暇,亦喜吟咏。《全明诗》辑录其诗153首,涉佛诗歌约20余首。太祖的涉佛诗,多为赞佛、游寺、示僧等题材,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与僧人的倡和之作。此类诗歌现存有《赓僧韵》《赓僧锡杖歌》《赓玘太朴韵》《山居律诗十二首赐灵谷寺左觉义清浚》等,但肯定遗佚不少。例如,洪武五年,太祖敕宝金璧峰“施摩伽斛食,以赈幽冥,宠赉优渥,赐诗十二韵,有‘玄关尽悟、已成正觉’之言”[10]925下;但这12首诗,今未见任何文献记载。
季潭宗泐是明太祖最为宠信的诗文僧。太祖尝称他为“泐翁”,又将他与宋濂相比,称宋濂为“宋和尚”,称宗泐为“泐秀才”。今存文献中,尚未见到明太祖写给宗泐之诗,但《释氏稽古略续集》说他曾御和宗泐诗145首,解缙亦曾云:“故天下之士为诗,鲜有得上意者。有诗僧宗泐尝进所精思而刻苦以为最得意之作百余篇,高皇一览,不竟日尽和其韵,雄深阔伟,下视泐韵,大明之于爝火也。盖如泐者之不足以当圣意,圣凡度量相越固如是耶?”[17]太祖所和宗泐诗作数量之多,恐怕刘基、宋濂辈都难以企及。遗憾的是,原诗、和诗今俱未见存,倒是宗泐《全室外集》有23首题“钦和御制”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这首:
奉诏归来第一禅,礼官引拜玉阶前。恩光更觉今朝重,圣量都忘旧日愆。凤阁钟声催晓旭,龙池柳色弄晴烟。有怀报效惭无地,智水频浇道种田。[18]
据释心泰云:“(宗泐)后因长官奏事,获谴,同往凤阳槎峰建寺,三年讫工,敕赐圆通之额。十九年秋趣归天界,引见赐诗,有‘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①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见《全室和尚语录》,抄本,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学界关于宗泐的塔铭、语录,征引者极罕,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近见卞东波《明初诗僧季潭的版本及其作品在日本的流传》(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第333-365页。)根据用韵情况,宗泐之诗当即钦和此诗而作,内中表达了他对明太祖“宽宥”的感激和竭忠报恩之意。宗泐不仅唱和颇称意于太祖,且诗思敏捷,诗艺颇高。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十八载,洪武十五年六月,马皇后崩,九月葬于钟山孝陵,时风雨雷雹,“帝甚不果”,召宗泐至,曰:“太后将就葬,尔其宣偈焉。”宗泐随即应曰:“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帝甚悦,顷忽朗霁,遂启輀,诏赐泐白金百两。”[19]296这一记载颇具神异色彩,却很好地表现了宗泐敏捷的诗才。他随即吟出的诗偈,不仅抹去了太祖的烦忧,亦巧妙地赞颂了马皇后的佛德。
清浚,字天渊,别号随庵,浙江台州黄岩人(今浙江省黄岩县)。洪武五年参加了蒋山普度大会,授为僧录司左觉义。宋濂尝极称其诗才,以为“未必下于秘演、浩初,其隐伏东海之滨未能大显者,以世无柳仪曹与欧阳少师也”[20]。《金陵梵刹志》卷一载有明太祖《山居诗十二首赐灵谷寺左觉义清浚》,而《列朝诗集》闰集卷二则存有清浚的两首和诗。我们各择一两首,以分析他们君臣唱和的旨趣:
侣影山间兴趣幽,竹鸡声断悟禅由。山房夜月明心镜,水国宵灯照衲头。崖柿熟甜须九月,溪芹味美必三秋。忘尘思入重嵬迥,道备咸称释氏流[21]。(明太祖)
分别移取0、0.10、0.30、0.50、1.0、3.0、5.0、10.0mL Ga、In、Tl、Cd、Ge混合标准溶液于100mL容量瓶中,用2% HNO3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标准系列溶液中Ga、In、Tl、Cd、Ge的质量浓度依次均为0、1.00、3.00、5.00、10.0、30.0、50.0、100.0ng/mL。采取三通阀在线添加的方式加入内标混合溶液,在选定的仪器工作条件下进行测定并绘制校准曲线。
老来一钵住岩幽,尘境无心得自由。空里每看花满眼,镜中渐觉雪盈头。吟余月照千峰夜,定起云生万壑秋。身世已知浑是梦,百年光景水东流。[9]679(天渊清浚)
清浚任灵谷寺主持,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故此组唱和诗必作于此年之后。这时期,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已从擢拔僧人入仕而转为倡导山林佛教,这组《山居诗》,反复出现的“侣影山间”、“忘尘”等语词,即是鼓励僧人忘却尘俗,走入山林;而清浚诗中主要表达了老来回归山林之况味,既有身世若梦之慨叹,亦有禅悦之风致,明显是对太祖佛教政策的积极回应。
山居诗本是佛教诗歌的特殊题材,僧人们借此表达参禅悟道的体验和山居生活的状态。明太祖所作《山居诗》除了表达对山居生活的向往之外,还是其佛教政策的诗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明初附和太祖《山居诗》的不止清浚一人。宗泐亦有《钦和御制山居诗赐灵谷寺住持》11首,竺隐弘道有《和御制山居诗》3首。祁伟曾指出佛教山居诗肇始于唐代的寒山和贯休,至明代山居诗“蔚为大观”,已经成为僧人写作的“一种习惯,或者传统”[23]。此种现象出现的缘由,十分复杂,但明太祖提倡“山林佛教”及其首唱《山居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明太祖与僧侣的诗歌唱和,固然不似解缙所云“大明之于爝火也”,但也不至于说它“不具有任何艺术平等的意义,更没有任何艺术的自由可言”[24]43。事实上,明太祖与僧侣的诗歌唱和,深刻地影响到明初方外诗坛的创造取向,使大批僧人都参与到歌赞新朝的合声之中。譬如宗泐《全室外集》卷一所收皆为应制奉和之诗,因此,徐一夔《全室外集序》评曰:“其诗不沦于空寂,推叙功德,则发扬蹈厉,可以荐郊庙,褒赞节义。”[25]又如,夷庵同简在洪武五年的钟山法会上,“以应制篇章宣说第一义谛,声韵鸿朗,宣公红楼之作,方斯蔑如矣。”[9]679明初另一诗僧止庵德祥更说:“诗岂吾事耶?资黼黻焉耳!”[26]尤可代表明初诗僧的创作取向。
“颂圣诗”,是明诗的第一波创作高潮,宋濂、刘基等开国功臣,自是引领此种创作风气的人物;而高启、张羽等吴中文人亦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加入到盛世铙歌之中。此外,那些缁衣释子,则辅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之佛曲,使明初诗坛众响毕奏,缵圣绩而开来世。
四、明初诗文僧的命运与畏祸心态
洪武前期,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主要以尊崇、怀柔为主,较少见到僧人受到责罚;但洪武中期后,太祖调整了佛教导向,以整顿、抑制为主,僧人的遭际和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分化。陈玉女《洪武年间儒僧受聘事例表》举证了慧昙“以污罪、诈欺流放西域”、愿证“郁郁而逝”、守仁“以诗触上怒,幸免于死”、德祥“以《西园诗》忤上”、宗泐“坐胡党案,但免于死”、来复“坐胡党,凌迟死”诸事,进而认为洪武朝“能够平安无事、寿终正寝的入仕儒僧几无一人”[12]8-9。这一看法未免略显绝对。其实,洪武年间的儒僧能善终者仍不在少数,有的甚至还得到了极高的礼遇。例如,如玘太朴病故于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太祖御制特撰《祭如玘文》;竺隐弘道,洪武二十四年告老,赐驿驰归,明年秋,跏趺而逝,世寿七十八岁;天渊清浚辞官后,命住灵谷寺,太祖御制诗十三首赐之。其坐化后,太祖以“恁礼部与祭祀”[10]938下。
同时,陈玉女所列举数位遇害的儒僧亦有必要略作辨析。例如,守仁“以诗触上怒”、德祥以“以《西园诗》忤上”,事见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七:
仁一尝题翡翠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祥止庵有《夏日西园》诗云:“新筑西园小草堂,熟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晓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二诗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谓德祥曰:“汝诗‘熟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密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兴礼乐?‘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遂皆弃市。[19]293
兹事又载于吴之鲸《武林梵刹志》、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陈师《禅寄笔谈》卷六。但对于这两桩“文字狱”,钱谦益则力辨之:“德祥,字麟洲,钱塘人。……《西园》诗今载集中,不知所忤上者何语?野史流传不足信也。祥公有题倪云林、周履道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则知公生元季,至永乐中尚在也。”[9]678明太祖对诗歌谬释,实难以考辨,问题在于“皆罪之而不善终”,是不符合实情的。钱谦益考证出德祥至永乐间仍在,所谓“弃市”事,实不足为信;而守仁在洪武二十四年主天禧,后示寂于寺,亦为善终。
宗泐与来复获罪之事,亦当仔细辨析。关于这两人获罪的缘由,相关僧传资料,例如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南宋元明僧宝传·泐季潭小传》、《南宋元明僧宝传·复见心小传》均语焉不详,倒是钱谦益所撰《跋清教录》二文最为详细:
《清教录》条例,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以智聪为首。宗泐、来复,皆智聪供出逮问者也。宗泐往西天取经,其自招与智聪原招迥异。宗泐之自招,以为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从之。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脏钞奏遣之西行也。果尔,则宗泐之罪自应与惟庸同科。圣祖何以特从宽政,着做散僧耶?岂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知其非妄语抵谩者,故终得免死耶?汪广洋贬死海南在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二年”为“十二年”误,见《明实录》),去惟庸之诛才一月耳,智聪招辞惟庸于十一年,已云:如今汪丞相无了,中书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则智聪之招,未可尽信也。闻《清教录》刻成,圣祖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今从南京礼部库中钞得,内阁书籍中亦无之。
按《清教录》复见心招辞:“本丰城县西王氏子,祝发行脚,至天界寺除僧录司左觉义,钦发凤阳府槎芽山圆通院修寺住。”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获胡党僧智聪供称胡丞相谋举事,随泐季潭长老及复见心等往来胡府,复见心坐凌迟死,时年七十三岁。泐季潭钦蒙免死,着做散僧。野史称复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不根甚矣。田汝成《西湖志余》载见心临刑道其师诉笑隐语,上逮笑隐而释之,尤为传会。笑隐入灭于至正四年,而为之弟子者宗泐也,来复未尝师笑隐。野史之传讹,可笑如此。”[27]
《清教录》,是洪武二十四年山西捕获释智聪后,明太祖颁布诏令。依钱谦益的跋文看,《清教录》颁布后,即“不令广布”,明代很少有人亲见之。从钱氏所述看,《清教录》所载内容,或许就是清除尝与胡惟庸“爰书交结”之僧徒,是“胡党狱”在丛林的演绎。钱谦益虽力辨智聪招辞之诬,欲洗清宗泐、来复之冤,但两人因“胡党案”而获难,却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宗泐和来复同坐“胡党案”,可最终命运并不相同。宗泐最终侥幸逃过一劫,而来复却被凌迟至死。此种原因,钱谦益推论是“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而最根本的原因,或为两人性格层面的差异。释明河就说:“国初高僧师(宗泐)与复见心齐名,见心疏放,师谨密,故其得祸为尤轻。噫,亦幸耳!”[28]蔡晶晶曾就宗泐和来复两人的性格差异,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所举一事尤能说明问题。李默《孤树裒谈》卷二载,来复“长髯数尺”,太祖怪之曰:“汝不欲仕我而为僧,吾亦任汝,然留须亦有说乎?”来复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同样对待蓄发及出仕的问题,宗泐则显得更为谨慎,洪武八年,明太祖曾命宗泐蓄发为官,宗泐先是听其令,可待头发长了后,他才再三推免,太祖不仅未迁怒他,反而撰写《宗泐免官说》,予以旌表[24]39。可见,来复见心之所以最终“凌迟至死”,“胡党案”或只是诱因而已,最根本还在于他个人狂放的性格,不见容于明太祖。《南宋元明僧宝传·天界金禅师》中亦记载:“初高帝诏选名宿,辅导诸藩。而蜀王椿,师事见心复,复名溢都中。金叹曰:‘复公其不免耳!’复果罹难而终。”[29]正是来复一开始就不拘小节,万金西白才有此一谶言。因此,我们在探讨明太祖对待儒僧态度,还应考虑僧人的品行问题。
尽管我们努力辨清明初诗文僧的最终命运,但是,洪武中后期酷烈的政治对丛林的影响,仍是不争之史事。钱谦益《列朝诗集》载曰:
惟则,自天真,吴兴费氏子。……师有《七幸序》曰:“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八月二十九日晚朝,上命凡天下僧人,但清理册文上有名籍者,不问度牒已给未给,皆要他俗家余丁一人充军。比时在京,钦闻上命,进偈七章,其七曰:‘天街密雨却烦嚣,百稼臻成春气饶。乞宥沙弥疏戒检,袈裟道在祝神尧。’或讥之曰:‘无事请死而已。’上览偈,罢军事不果。”[22]304
惟则天真进偈以“乞宥沙弥”,虽最终被明太祖所采纳,但其中所载:“或讥之曰:‘无事请死而已”,尤可见出太祖酷烈的“文字狱”确使丛林噤若寒蝉。此种“畏祸”的心态,亦深刻地体现在诗文僧的创作中。明人徐伯龄《蟫精隽》卷九“诗有警策”记载:
国初高僧宗泐季潭有《偶成》诗云:“人事天时不可常,才逢炎暑又逢凉。芭蕉似解知秋早,蟋蟀如能识夜长。向日高台还走鹿,只今沧海已成桑。殷勤说与权豪客,鸟尽良弓合自藏。”警策之意深矣,可谓明哲保身、知几之君子乎![30]
《偶成》诗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宗泐在明初酷烈的政治情势下的心态。宗泐示寂前尝遗言:“人之生灭,如海一沤;沤生沤灭,复归于水。何处非寂灭之地也。”言毕乃唤侍者曰:“这个聻。”侍者茫然。师曰:“苦!”[31]这一“苦”字,不仅是宗泐对人生况味的体察,更表现了明初酷烈的政治情势下僧人普遍的生存状况。
[1]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J].台北:东方宗教研究,1994,(4).
[2]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
[3]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J].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7,(4).
[4]任宜敏.中国佛教史·明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5]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十·诵经论[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6.
[6]钱宰.临安集·卷四·知止斋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5.
[7]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十五[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宋濂.灵隐大师复公文集序[G]//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417.
[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卷二[M].钱陆璨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69.
[10]释大闻,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927上.
[11]张廷玉.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陈汶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88-3989.
[12]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13]明太祖.明太祖文集·卷八·谕僧纯一敕[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0.
[14]危素.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G]//楚石梵琦.佛日普照慧辩楚石禅师语录·卷二十.卍新纂续藏经本.
[15]李圣华.从方外到方内,味趋大全:明初诗僧述论[J].贵阳:贵州社会科学,2012,(2).
[16]释自融撰,释性磊补辑.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楚石愚庵梦堂三禅师[G]//卍新纂续藏经:第79册,No1562.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30.
[17]解缙.文毅集·卷七·顾太常谨中诗集序[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80.
[18]释宗泐.全室外集·卷一[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89-790.
[19]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十八[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8册:296.
[20]宋濂.送天渊禅师浚公还四明序[G]//罗月霞.宋濂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504.
[21]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御和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3册:568.
[22]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16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祁伟.佛教山居诗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162.
[24]蔡晶晶.元末明初诗僧群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
[25]释宗泐.全室外集·卷首[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87.
[26]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二僧诗累[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2册:684.
[27]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42.
[28]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四[G]//卍新纂续藏经:第77册,No1524.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72.
[29]释自融撰,释性磊补辑.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天界金禅师[G]//卍新纂续藏经:第137册,No1501.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35.
[30]徐伯龄.蟫精隽·卷九[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2.
[31]释心泰.前天界禅寺住山全室大禅师塔铭[G]//释宗泐.全室和尚语录·卷首.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