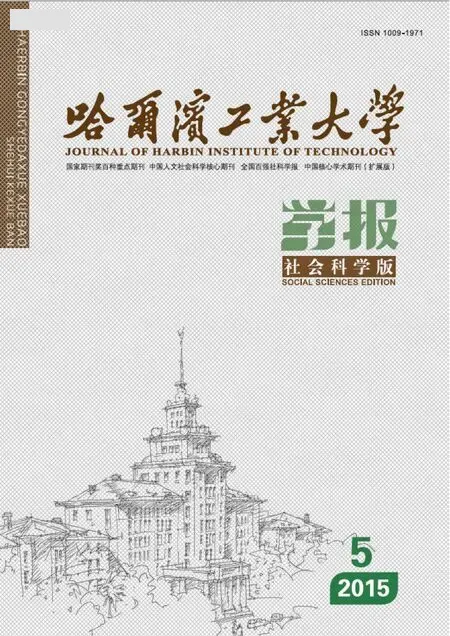探问生命:幸福本质的历史探寻与当代诠释
于文思,颜宏赫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东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长春 130024)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探问生命:幸福本质的历史探寻与当代诠释
于文思1,颜宏赫2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东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长春 130024)
摘要:幸福的本质是以个人体验为主、以社群关系为体现的一种文化定位,它强调个体对生活的认知。因而,自我建构的特征也就成为对幸福本质的诠释方式之核心。中国与西方两种哲学传统奠定了两种自我建构的方式,也就出现了对幸福的两种诠释。在自我存在的本源层面,中西方对幸福的认知差异在于承担责任或展现自我;在自我精神提升层面,幸福本质的差异来自个体相对于社会的位置与归属;在自我建构的时间指向层面,幸福本质的差异来自中西方时间观的指向是此刻或未来。
关键词:幸福本质;自我建构;民族文化心理
收稿日期:2015-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及健全人格培育研究”(BBA120020)
作者简介:于文思(1987-),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欧美文学研究;颜宏赫(1992-),男,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幸福感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志码: A
文章编号:编号: 1009-1971(2015)05-0069-05
Abstract:The nature of the happiness is a kind of cultural location i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cognitive of the personal life. So the self-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appiness. There are two ways of the self-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trad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at produced two way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appiness. At the level of self-being, the difference of understanding happi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es in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or showing oneself. At the level of spirit, the difference of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originates from one's self-position and affiliation in the society. At the level of tempo, the difference of happi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ime is directed at present or future.
对幸福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心理学的热点之一,亦是心理学对于如何培养民族健康心态、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尝试。对幸福本质的追求更是探寻生命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文化因其思想形成过程的不同,而对其民族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文化会赋予心理以含义。幸福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定位,它以民族文化心理为依托,侧重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与体验,并表现在个人行为与社群关系之中,最终形成一种多维、立体的认知模式。因此,自我建构模式成为诠释幸福在某一民族文化中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东西方文化,幸福都是个体善与社会善的融合:它既有形而上的哲思,亦是形而下的存在状态;既包含了个体心理品格建构与终极信仰的完善,也包括了社会道德规范与社会价值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幸福的根源是“自我”与“社会”的链接关系,是自我建构的不同表达。因此,以“自我建构”的视角探索幸福的本质,可产生三个维度:自我存在的本源意义、自我人格的提升空间、自我建构的时间取向。这三个维度以递进的方式将自我在幸福本质中的意义逐层揭示出来。当今,幸福的本质被多元文化价值观所误读甚至背离其初衷,这是自我建构能力丧失的表征之一。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入手,以自我建构的途径来探究中西思想中对幸福本质的诠释,提出幸福本质具有塑形性、超越性、时间性三重意义,也望借此能重塑当代幸福本质的价值意义。
一、自我存在的本源意义:幸福的塑形性
自我建构的首要部分是对自我本源的审视与对自我意义的完善。无论是社会取向自我还是个人取向自我的内涵,都对“自我”有着明确的要求。社会取向自我具有“扮演性”,其自我是依附于社会角色而存在,关键词是“适应”。它强调自我建构应符合、顺应环境,要求个人扮演好社会角色,认同社会价值与道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扮演”的成功程度决定了个体建构的完整度。而个人取向自我则具有“表演性”,其自我指向个体的偏好、内在本性而存在,关键词是“彰显”。它重视个体的内在潜能与偏好,要求个体进行充分的自我表达,并以自我强化与自我成长为终极目标。“表演”的个性化程度决定自我实现的完整度。
扮演性与表演性虽然都暗含了“演”的含义,但一个侧重装扮,一个则偏重表现。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演”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表现,是自我与社群互动关系的表征,也是自我完善的终极意义之一:形成自我与社会的良性生态关系。扮演性暗示了个体要良好地融入社会角色中,其本质是“承担”,指向是“和谐”;表演性暗示了个体要尽己所能地强化、彰显自我,其本质是“展现”,指向是“满足”。无论“和谐”或是“满足”,个体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都是完善性的,这种完善趋向于幸福,就是人在自我建构中对幸福本质的诠释。在“自我存在”这一维度中,幸福具有“塑形性”,其内涵对个体本源也起到一定的塑造作用。
幸福与本体的关系是幸福问题进入社会学视野的基石。幸福问题在国人对自身生存状况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热烈关注中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就国人而言,对幸福感的关注源于主体性从无到有的一种精神追求,从外在的“有福”拓展为内心的“幸福”。在中国,个体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并不强,很多人并不知道幸福的存在状态,甚至没有将幸福纳入思考议题。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较少去思考自己生活是否幸福,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独立、清晰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一情况自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发生转变。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文化问题的对撞更多体现在自我观念上。丛晓波等人的研究显示,与父辈及同龄的日本大学生相比,中国青少年的社会行动更为自我,更少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与周围环境的制约[1]212。中国人传统的自我观正在西方文化的融合下发生转变。因此,探寻中西两种幸福感的根源,就与两种文化中的自我观密不可分。
西方哲学对幸福本质的探寻建立在对“人之本质”的理解之上,人在体验幸福时重新审视自我的行为被纳入研究范畴。对幸福的思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全面展开,由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影响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启蒙时期对幸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人的本性,直至现代则更为关注“异化”之下失落的自我建构与幸福内涵。幸福本质的诠释每一步都伴着对人之本质的追问。
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思想中建构自我的根源之一。理性主义中的个体内涵强调以“人的目的”为出发点,崇尚人的理性力量,高扬人的道德品性,相信人类具有权衡能力和辨别能力。理性主义自我建构的核心是让人具有“善”的德行。善是幸福的本质价值之一,同时也是理性与德行达成融合的层面。个体在建构自我时以知识、理性来充实自己,在理性中为自己定位,并以此诠释幸福。
苏格拉底认为人只有具备道德的知识,才能做善事,因此知识是获得幸福的关键。道德依赖知识,知识成为德行存在的必要条件。进而苏格拉底认为,道德是人探寻幸福的起点以及对幸福本质的评判标准。道德关乎理性,因而培养人的理性能力成为苏格拉底诠释幸福的条件,即让人们发现善、了解善、过有道德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合乎德性的行为是爱德行的人快乐”[2]。自我以知识与理性建构的人格结构通过对善的追求不断提升自我存在的意义,以此作为个体主义文化探寻幸福本质的第一步。即使在理性层面上,个人的情感与态度依然是行为引导的要素,被幸福的意义要求去实现独立、完满的个体。而我国国民对幸福的追求是从无自我意识到有自我意识的转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包含“幸福”这一概念。“福”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里面提到“人有五福”,这里的“福”指的是一种个人生命境遇的良好状态。中国文化中的自我建构建立在这种对“福”的追求中,其目的是让个人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基本上都认同“和谐”是幸福的终极状态,即都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中体现的。儒家学说强调人际和谐对个人生命境遇的塑造,将人际和谐提升至生命状态的首位。道家学说中的自我认知来自外部环境,认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人生命境遇的最高追求。而释家对和谐的解释更倾向于个体内心环境的塑造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自我建构的本源意义方面,中西方哲学都提到了“善”与“道德”对幸福内涵的意义。区别在于: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对善与道德的要求是人与自我、外界的和谐关系,因此幸福的本质则是这种和谐关系达到一个良性模式所引发的生命境遇。而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分支更强调道德来自知识对于个体人格塑造的提升,将知识列为幸福的本质意义。
二、自我人格的提升空间:幸福的超越性
“人的存在意义”是自我建构的根基,也是幸福感的必要来源。然而人格的发展完善需要提升空间,这也是督促人不断追求幸福的前行动力。这一提升空间的作用力来自两方面:个体接纳社会的态度与个体自我反思的程度,前者又通过后者得以表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发展,当今社会对物质欲的需求也随之提升,人被物化、机械化等异化表征愈发明显。精神迷失,与社会、自然等外在的对立使得人的自我建构呈现出缺陷、偏执的模式,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很难拥有真正的意义。因此,自我人格的不断提升成为探寻幸福本质的第二个维度。
历史上的幸福感在空间结构中以社会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呈现。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个体对幸福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对于国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幸福感来自家庭纽带,个体自我意识依存于寻缘关系,并将自我精神保持在亲情中。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幸福感则与自我的社会角色相连,以社会成就衡量自我价值。这种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幸福感原则使幸福感评价呈多元化趋势。在传统与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博弈中,各种价值观对自我精神空间的提升各有利弊,而人在选择的过程中,也要选择多元文化中最为切近自身的。
社会取向自我对精神空间的提升以个人的自我反省与社会反馈为标准,具有反思性,依靠自我批评及承诺进行自我改善,并以得到社会认可为最终目的。因此,社会取向自我对产生幸福感的行为判定标准是依据他人的适应程度,也源于压抑个体的愿望和要求。个人取向自我提升精神空间的途径主要是自我能力的不断强化与对本性的持续开掘,它具有提升性,依靠自我强化与自我成长来获取自尊。个人取向社会对幸福感的判定是个体内在本性的发挥程度,也源于个体自尊的建构度。
在自我精神空间提升这一层面上,社会取向自我与个人取向自我对幸福本质的理解是“殊途同归”的。二者分别以“压抑”和“彰显”为输出手段,实则均以提升自我内在修养为目标,实现自我人格建构中对幸福的解读。“在个体主义弥漫的西方文化中,幸福感具有个人负责和直接追求的特点”[1]212,对自我的要求侧重于个人表达,在哲学层面走向感性主义。而中国文化对角色责任和辩证均衡的偏好使个体以“平衡”为建构自我的终极目标。“平衡”对幸福感的塑造是使人追求内心的平和宁静与道德规范。幸福在自我提升层面具有超越性。
自我与本性的追寻与提升是自古希腊起哲人们就为幸福所灌注的内涵之一。德谟克利特认为,享受感官的肉体的快乐时,更要想到精神的灵魂的快乐和幸福。应当在追求肉体、感官快乐与灵魂、精神快乐中寻求某种和谐与一致,以“节制”与“适度”为行为准则方能满足各种愿望的要求[3]118。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伊壁鸠鲁同样认为幸福就是人生最高的善: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3]368。生命有限而欲求无止境,幸福依赖美德以节制。
17世纪的斯宾诺莎提出具有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就是至善与幸福。他从人性自保理论出发,提出每个人都为生存而自保,这是出于其本性的必然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4],出于自己本性去判别善恶并以自己意愿去寻求利益。同时期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则将“趋乐避苦”的快乐主义原则发扬光大。他认为,外界对个体造成的感官刺激是人类苦乐感形成的重要原因。洛克重视快乐对本性的释放,他认为幸福就是快乐,“极度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的快乐”[5]。
18世纪的康德对经验主义的幸福本质进行了反思,他承认人的本性对自身建构的影响,感性世界中的人需要幸福,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理性是自我精神提升的必要条件,人虽有追求感性满足的欲望,但其本质是理性的。由于理性能够为自己确立行为准则,道德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道德法则成为确定幸福的必要标准。康德认为,道德的标准是行为的意图,善良意志是判断事物能否给人带来幸福的首要条件。进而康德提出至善论,至善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德性和幸福是被人思想为必然结合在那对我们来说有实践作用的至善里面的。”[6]道德与节制是自我精神层面塑造的必要因素,也是个体主义诠释幸福的手段。在理性与感性的综合层面来看,自我建构的精神提升空间产生了幸福内涵中的超越性。
中国传统哲学对幸福超越性的理解集中于“超越物质的个人道德标准”,它亦以压抑自身情感为特点。与西方幸福观中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不同,儒释道三家都认为追求内心层面的愉悦平和是幸福,而这一幸福是通过降低物质欲望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体精神空间层面所诠释的幸福是以个体对社会的影响与对欲望的压制共同塑造的。
儒家依据的幸福观是“义以为上”,其中的“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本身就有内在的至上感,赋予人们超功利性、崇高性与导向性。道家认为满足欲望不仅不是幸福更是一种罪过:“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而佛家更是认为欲望是到达幸福的业障,要通过“戒、定、慧”三种方法进行消除。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诠释更多来自社会需求与超功利性。儒家反复强调个体之于社会的价值,暗示了个人情感的意义在社会价值面前可以被忽略。儒释道三家均强调个人建构的道德属性要以压抑欲望来完成,从道德高度重新定义了幸福与个体建构之间的关系。
中西方对幸福内涵探索的分野主要在于是否认同感官幸福作为道德幸福的基础。社会取向自我几乎完全否定感官层面的幸福享受,只看重道德教化的作用,着重个体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与“大我”的培养,中西方文化对个体价值诉求的区别实质上是对个体意义的独立性是否有所承认。
三、自我建构的时间指向:幸福感的时间性
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动物,个体建构也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因此中西文化对幸福的诠释在时间维度上同样有所差异。在时间层面,中西方文化对幸福的认知来源都是宗教性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将原始的宗教祭祀转化得更为隐蔽。西方文化的时间观是线性的,它以基督教时间观为基础,终极目的是追求永恒的幸福,却始终关注现世与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是圆形的,它以传统儒家的时间观为基础,糅合释道两家的轮回观念,形成了带有未来指向的现世幸福体认。西方文化以永恒幸福为终极目标,其时间取向却是当前性的;而中国文化虽以当下幸福为终极目的,其时间取向却是未来性的。
西方的时间观始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盛行。这一时期对幸福的思考转化为以人神关系为基础的人性善恶问题。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对此问题有过着重论述。奥古斯丁认为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当前的纵情肉欲、热衷于名利和欲望并非幸福而是痛苦,而排除这些纷扰的方法就是向上帝忏悔、依附上帝。他把上帝作为真正幸福的前提,“天主即是真理”[7],幸福就是时间指向未来的快乐。由此,奥古斯丁将幸福界定为对上帝的信仰,从而将真正的幸福变为永恒的信仰追求。而要做到信仰上帝就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即要做到信仰、仁爱、希望、节制、审慎、公正和坚毅。这样,永恒而在尘世不可追求的幸福又以现世形态回归于每个人的生活。
托马斯·阿奎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尘世幸福和天堂幸福,他认为人生应以天堂幸福为最终目的,因此其终极意义也是未来性的。“幸福可以界说为一切欲望的终极目的,幸福是人的最完善的境界,同时也是所有的人都想达到的善的顶峰”[8]66,真正的幸福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完满的、永恒的美德。“人在尘世的生活之后还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的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8]67阿奎那提出的永恒幸福成为西方世界的时间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是皈依于信仰的,然而这种信仰又是以尘世幸福的满足为前提的。因而西方思想中,个体以不断满足现世目标来追求未来的永恒性作为对幸福的诠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是圆形的,它结合了儒释道三家的观点,虽然着重于现世幸福,却在观念中流露出对未来幸福与轮回的期盼,并且这种期盼并不带有终极意义上的永恒性。在甲骨文中,“福”字从示部,是双手捧酒樽于祭台上之像。祭祀带有对未来祈福、期盼美好之意,也暗示了中国人的幸福观具有未来取向。儒家对个体幸福感的要求是基于当下而包含未来的。佛家主张个人在修行的同时也要普渡众生的烦恼,即使在自己悟道后,也要帮助别人解脱,才是真正的幸福。个体时间在齐平甚至超越社会时间的状态下具有更为超功利性的道德水准,也就达到了自我完善的境界。个体在现世环境中建构自身其最终指向是未来,而未来则是为下一个现世做准备。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文化中的时间观是拒绝个体性的,它同样是社会取向的,个体时间被放置在社会时间中才能获得拥有幸福的可能。
社会取向的自我与个体取向的自我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了各自的不同取向。中国文化的时间观面向社会,将个体时间置于社会时间之中,只有具有社会意义的时间才具有道德性,也就才能成为建构幸福感的条件。西方文化的时间观面向自我,注重自我道德的完善,个体幸福感只与个体成就有关。就本质而言,社会取向自我需要一个未来指向的时间维度,使个体在一个封闭时间内感受到推动力,也就是将个体与社会在时间层面同构。个体取向自我则要依靠指向当下的时间维度,使个体在开放的时间中不致因最终目标过于渺茫而产生虚无感,因此个体时间是社会时间的基础单位,社会时间由个体时间构成。幸福本质在这两种时间维度中分别是社会性的和个人性的。
结论
人在任何层面上的追求都是对幸福的追求,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诠释幸福的方式,当利用幸福本质对人生加以指导时,就必须要符合其文化对幸福的理解。自我是感知幸福最直接的载体,因而自我建构是诠释幸福本质重要的途径之一。以往对幸福内涵的文化研究往往偏重于中西文化的相同之处,而较少关注差异性,因此以自我建构为脉络对中西方思想史关于幸福的探究做一对比,是对幸福本源意义与产生方式的一次实践。中西方对幸福理解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自我”认知的差异。在中西比较中,反思本土思想中幸福的独特意义,对幸福本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的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上的诸多幸福观也纷至沓来。“何为幸福”,“怎样才能幸福”也成为国民当下的热门话题。这样的中西比较,在思想脉络上纵览幸福的意义,也为更加本土化的幸福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丛晓波.何以幸福:论幸福感的社会文化前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4,(2).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学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
[3]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2.
[5]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91.
[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64.
[7][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2.
[8][古罗马]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Inquiry into Life: Historical Expl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YU Wen-si1,YAN Hong-he2
(1.College of Libera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2.Pepartment of Soci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Key words: nature of happiness; self-construction;na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责任编辑:唐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