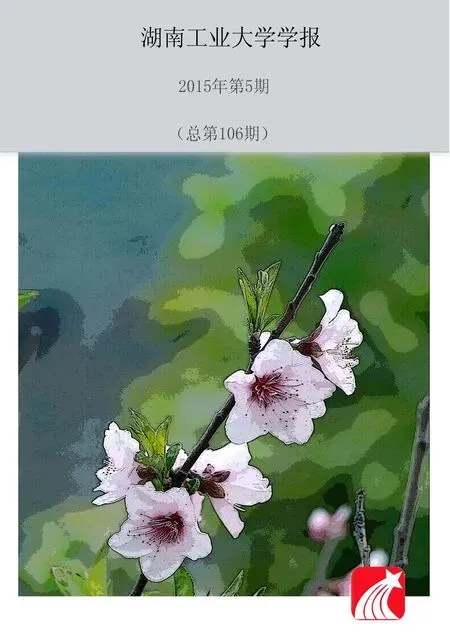“现代”进程中的民间狂欢——沈从文《长河》中的民间诙谐式叙事
陈 婵(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现代”进程中的民间狂欢
——沈从文《长河》中的民间诙谐式叙事
陈 婵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沈从文的小说《长河》描写了20世纪30、40年代湘西地区受到“现代”意识形态入侵而产生的种种变化。大量民间诙谐语言的运用,反讽叙述手法的使用以及怪诞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整个小说文本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狂欢式风格,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颠覆。《长河》中的民间诙谐式叙事表现了作者对平等而自在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对自由和淳朴人性美的歌颂,以及与追求秩序、规范、权威和物质的“现代”进程的抗衡。
[关键词]《长河》;民间狂欢;民间诙谐语言;反讽叙事;怪诞形象
沈从文的《长河》描写了20世纪30、40年代湘西地区“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所谓的“常”乃是湘西民间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准则进行着的淳朴生活,和生活在其中的乡下人的善良、质朴、天真和自信,而“变”则是边地湘西受到“现代”意识形态的入侵而产生的种种变化。
《长河》中“现代”在湘西的进程表现为以描写省里派来的委员和治安队长不断巧取豪夺来表现代表着强权和等级的政治权力对乡间控制的加强;以儿子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后,“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2]14来表现现代文化资本对传统父亲权威的瓦解显示知识权力对乡间生活的渗透。还有“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1]即一种追求物质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确立;以及以“新生活”为代表的“现代化”运动将乡间生活纳入理性化、文明化轨道的过程。“‘新生活’运动是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文化复兴运动’,核心是恢复‘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的目标。”[3]126这种政治权力干预下的理性化运动,带有改造、革新、扫除和破坏的特点。“‘现代’的野心,是要占领和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三十年代湘西的情形,不过是‘现代’过程刚刚开始的情形。”[3]125
面对淳朴而充满活力的湘西的变化,沈从文“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1]而这种“牧歌式的谐趣”恰恰表现了带有狂欢节性质的民间文化的特质,成为“现代”进程中民间自由独立和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这种对抗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民间狂欢书写来实现。
《长河》中描绘的湘西虽然危机四伏,但仍然按照它特有的方式运转,乡下人面对忧患仍然保持一份镇定从容,他们以狂欢式的生活方式抵御“现代”进程的侵袭,用民间狂欢话语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嘲讽和笑谑。
“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更替和更新的节日。”[4]139小说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集体狂欢的广场:赶场和社戏。
能体现乡间活力和生机的是熙熙攘攘的赶场集会。“三八逢场,附近三五十里乡下人,都趁机来交换有无,携带了猪、羊、牛、狗和家禽野兽,石臼和木碓,到场上来寻找主顾。……到时候走路来的,驾小木船和大毛竹编就的筏子来的,无不集合在一处。……耕牛和猪羊与农村经济不可分,因为本身是一生物,时常叫叫咬咬,做生意时又要嚷嚷骂骂,加上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吃食棚子里去喝酒挂红,交易因而特别热闹。……若当春夏之交,还有开磨坊的人,牵了黑色大叫骡,开油坊的人,牵了火赤色的大黄牯牛,在场坪一角,搭个小小棚子,用布单围好;竭诚恭候乡下人牵了家中骒马母牛来交合接种。孩子从布幕间偷瞧西洋景时,乡保甲长多忽然从幕中钻出大声吆喝加以驱逐。当事的主持此事时,竟似乎比大城市‘文明结婚’的媒人牧师还谨慎庄严。”[2]40赶场为民众提供一个集体狂欢的场所,这里,人畜混杂,热闹喧嚣。走路的、架木船和撑竹筏的汇聚到一起,消除了等级尊卑。骂人话和盟神发誓充满民间诙谐,冲击着平日的禁忌和规范,荡漾着狂欢节式的欢乐气氛。象征生命诞生的鄙俗化、肉体化的活动被推崇。牲畜交配变得神圣庄严,民间忌讳也可被颠覆。节日狂欢式的生活,是一种“暂时进入人人共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的大众第二生活形式。”[3]125这是“常”态中的民众狂欢节,是在“现代”的脚步逼近的背景下,乡间民众维持生活的完整性和生命的新鲜活力的重要场所。
社戏是民间狂欢的有代表性的空间场所。看社戏是一种群体性活动。“是一乡中公众庄严的集会,包含了虔诚与快乐”“到开锣那天,本村子里和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换了浆洗过的新衣服,荷包中板带中装满零用钱,赶到萝卜溪伏波宫看大戏,一面看戏一面就掏钱买各种零食吃。……妇女们……必到把入晚最后一幕杂戏看完,把荷包中零用钱化完,方又扛起那条凳子回家。有的来时还带了饭箩和针线,有的又带了香烛纸张顺便敬神还愿。小孩子和老妇人,尤其把这几天当成一个大节日。”[2]164-165观看社戏成为民众尽情狂欢、释放被压抑欲望的途径。这是“变”态下的民间狂欢。此时的乡间在现代进程中正悄悄发生变化,其中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侵袭日见明显。在观看社戏前设定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安排官商要人坐在首位,由他们钦点剧目。但在社戏休息期间,主角由高高在上的官商转为民众。脸上带着化妆颜料的戏子跻身在小食摊子上,与观众一同喝酒。“顽皮孩子且乘隙爬上戏台,争夺马鞭仔玩,或到台后去看下装的旦角,说两句无伤大雅的笑话。多数观众都在消化食物,或就田坎边排泄已消化过的东西。妇女们把扣双凤桃梅大花鞋的两脚,搁在高台子踏板上,口中嘘嘘的吃辣子羊肉面,或一面剥葵花子,一面谈论做梦绩麻琐碎事情。”[2]166台上和台下、艺术和生活的界线被打破。随着整个节日中的剧目由正剧“武松打虎”转向趣剧“王大娘补缸”,再到最后一出杂戏,由“三个穿红裤子的小花脸,在台上不住翻跟斗,说浑话”[2]167,节日娱乐的对象渐渐转移为民众,社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狂欢节。民间狂欢节恢复了本质,并起着颠覆和净化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乡村的朴野而近乎原始的私人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与新生活的普遍化、规范化和模式化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
狂欢式的生活不仅表现在节日和风俗的描绘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长河》中关于民间生活的描写符合狂欢节的特殊本性,即:“是生活本身在狂欢节上的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回复为生活本身。”[4]138
在日常的、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壁垒所分割,沈从文笔下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人们之间一切等级壁垒、规范和禁令暂时消除,长顺和会长与水手、修船匠喝酒、攀交情,人与人的交往坦诚而热情。这是一种自由的摆脱了日常礼节规范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际交往。在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中,人们之间打破了一切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接触。
在乡间,除了在节日和社戏中人们可以释放生命的原始活力、颠覆等级和规范外,狂欢的场所还可以是野地和河边。镇上烧窑的刘聋子和野娘儿们在坳上树林里撒野,夜泊河岸的水手一靠岸就“和妇人口对口做点糊涂事”[2]104、赌钱、烧荤烟、唱曲。
沈从文忧心忡忡地审视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湘西民间的进攻,始终站在民间的立场构想狂欢节式的湘西边地生活,以抵御渐渐压来的以“现代”为名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和他不久前写的小说《边城》不同,后者用几乎纯净的牧歌笔调,描绘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而在《长河》中,他没有回避现实,而是真实再现了乡间的各种变化和“‘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5],这里,他充分展示了他所熟悉的湘西的民间狂欢文化,通过表现民间诙谐语言、运用反讽叙述和创造怪诞形象,表现民间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抗衡。
《长河》中描写了大量恣肆泼辣、无所顾忌的民间语言,这些是官方话语定义的放肆、粗俗甚至下流的“脏话”,而沈从文称之为“野话”。他笔下的“野话”充满雄强的生命力,也散发着民间的诙谐,这些带有笑谑性的语言具有创造狂欢节的自由气氛的作用。
沈从文来自湘西民间,从小处在民间诙谐文化的渲染中。调皮逗趣的凤凰民歌以及包含大量讽刺手法的酬谢傩神的笑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这些遭到官方排斥的“低级”、非标准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极大的兴趣。20年代中期,他创作了一些中国式狂言滑稽戏,如《鸭子》《过年》《野店》。这些笑剧“台词非常生动,甚至猥亵下流,滑稽诙谐,辱骂对方,大量使用当地双关俏皮话。演员在一旁向观众展示传统民间戏曲风味,揭露对方是个卑鄙无耻的无赖或傻瓜,让观众也感到对方已经陷入绝境”,[6]表现了民间特有的机智和幽默。40年代完成的《长河》,也穿插了风趣而带有性暗示的山歌,机智逗趣的对话,表现了民间富有野性生命力和对官方智慧和官方“真理”片面严肃性的快活讽拟,构想狂欢节式的民间节日想象。
“诙谐是通往狂欢之路,诙谐的原则是狂欢节仪式的组织原则,没有诙谐就没有狂欢意识所需要的快感。”[7]民间诙谐在《长河》中随处可见。在广场式的乡间野地,乡下人围绕关于城里人以及官吏们各种题目的对话、讨论和争论以及对官方滑稽的赞词构成特有的民间诙谐。委员变成一个会法术的人,拿着土囊(土壤)炼猪油、熬膏药。军队都是上云南打瓜精的。水手引用谚语打趣基督教会:“耶稣爱我白白脸,我爱耶稣大洋钱”[2]99。老水手过城门和士兵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这些民间诙谐话语消解了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教条主义、权威观念和片面严肃性。
而新生活运动在乡间话语场遭遇到的一系列的误解和嘲讽,反映出民间和官方话语的错位,产生了一种诙谐的效果。代表理性和文明的新生活运动在乡间要么被理解为杀人拉人、派捐征税的暴力革命,要么被代表民间立场的长顺揭露其悖谬处,而嘲讽一番:“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要向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起赶场?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浇菜用不用大粪?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哪里来卫生丸子?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乡下人一出城到河边,傍吊脚楼撒尿,也就管不着了。”[2]56-57船主口中的“新生活”更像一场闹剧:“大街上人走路都挺起胸脯,好像见人就要打架神气,学生也厉害,放学天都拿了木棍子在街上站岗,十来丈远一个,对人说:走左边,走左边,——大家向左边走,不是左倾了吗?”[2]100代表现代理性的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一切在乡间话语场显得滑稽、荒谬而不屑一顾。民间百姓的理解完全凭着直觉经验,却有着预见的智慧和能力。
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互讽性叙述。治安队长想讹诈长顺一船桔子运到常德卖掉捞笔横财。而长顺则表现得木讷呆憨,以退为进。队长的小聪明表现出愚蠢,而乡下人的愚蠢又包含了智慧。聪明和愚蠢、恭顺和执拗、强悍和懦弱在人物身上互为同体,形成强烈的互讽效果。
面对纯真的夭夭,治安队长夸夸其谈地打官腔、炫耀白金手表和其贪婪好色的本性相互映照,产生了集严肃与鄙俗于一体的高度反讽效果。敲诈碰壁后的队长同夭夭讲理、论法,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出理和非理、法和非法双重悖谬的滑稽。他在夭夭面前又是唱歌又是炫耀,而夭夭则觉得他唱的说的都不大高明,有点傻像。美和丑、低俗和高尚在这里消失了界线,互为反讽。会长笑“队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革命军人”[2]129,称颂与谩骂汇集于一体。淳朴的小贩认为桔子不值钱而准备白送,而差人以为他嫌钱少,骂他刁狡。这里,文明和野蛮、慷慨和小气、诚实和虚伪在不同话语场的错位定义,引起反讽的效果。
互讽“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如‘车轮’)、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讽拟和滑稽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4]141深谙民间笑谑文化的沈从文将民间特有的讽拟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使得文本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颠覆了官方话语定义下的种种“正统”概念,对贪婪、虚伪、愚蠢的官吏予以嘲笑和戏谑。
民间笑谑文化中,小丑和傻瓜是典型的人物。沈从文通过民间的视角将高高在上、故作严肃的官员们鄙俗化、丑角化,从而产生了怪诞的效果。《长河》中委员、治安队长及其师爷的言行类似小丑的表演,其装腔作势、忸怩作态等等,就其本质而言,是民间笑剧中画着假面的小丑的衍生物。
治安队长的师爷讹骗长顺不成,自觉没趣,“学戏文上丑角毛延寿神气,三尾子似的甩甩后衣角”,悻悻而归。出了桔园,师爷“只想像到肥狗肉焖在砂锅里时的色香味种种,眼睛不看路,打了个岔,一脚踏进路旁一个土拨鼠穴里去,身向前摔了一跤,做了个‘狗吃屎’姿态,还亏得两手捞住了路旁一把芭茅草,不至于摔下河坎掉到水里去。到爬起身时,两手都被茅草割破了,虎口边血只是流。”[2]113这一场景和笑剧中的丑角非常神似,其狼狈下场,正是民间立场上的道德惩罚。
老水手把官吏比作肥胖臃肿、保守稳健的鹌鹑,而他眼中的委员“就像是个又多事又无知识的城里人,下乡来虽使得一般乡下人有些敬畏,事实上一切所作所为都十分可笑。坐了三丁拐轿子各处乡村里串去,搅得个鸡犬不宁,闹够了,想回省去时,就把人家母鸡腊肉带去做路菜。”[2148]路人描述的委员长更加不伦不类:“委员司令坐在大白马上,把手那么叉着对民众说话,(摹仿官长声调)诸位同胞,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姊妹,我是‘新生活’。我是司令官。我要奋斗……”[2]26,这些怪诞变形的漫画式描写,消解了官方的严肃性和权威感,产生了怪诞效果。“怪诞风格充满了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一切在正常的世界上是可怕和吓人的东西,在狂欢节的世界上都变成欢快的‘滑稽怪物’。”[4]176在民间文化语境中的丑角形象那里,可怕与可笑之间的界线消失了。严肃的当权者被鄙俗化、渺小化,失去应有的权威,呈现去势的态势。
“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8]自觉站在民间立场的沈从文创作《长河》的目的是为了匡正人们对湘西人民的误解,揭露官方对湘西的迫害。从更深一层讲,沈从文对现代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湘西充满了忧虑。而《长河》中呈现的民间狂欢节式的书写,形成对以现代/官方意识形态权威的颠覆,表现了长顺、老水手等为代表的民间百姓对官方不卑屈的自尊和独立,以及面对现代进程侵袭的从容镇定。从更高层面来说,小说中狂欢节式的民间书写表现了沈从文一贯的理想:向往平等和自在的人际关系;歌颂自由、淳朴的人性美,以及与追求秩序、规范、权威和物质的现代进程的抗衡。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9,235,239.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7卷[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社,1982.
[3]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巴赫金.巴赫金集[M].张 杰,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凌 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65.
[6]金介甫.沈从文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119.
[7]王春辉.巴赫金“狂欢诗学”浅析[J].齐鲁学刊,2004 (5):159-160.
[8]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白春仁,晓 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
责任编辑:黄声波
Folk Carnival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on
——On the Folk Humorous Narration of Shen Congwen’s Changhe
CHEN C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Shen Congwen’s novel Changhe describes the changes of west Hunan areas in 1930s and 1940s brought by“modern ideology”.Lots of folk humorous language and ironic narration are used and many weird folk images are moulded in the book,which gives the whole novel a distinct folk carnival style and subverts the official ideology.Through the folk humorous narration,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yearn for the equal and democratic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his praise for the free and honest humanity and his struggle agaist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which pursuing the order,norms,authority and material.
Key words:Changhe;folk carnival;folk humorous language;ironic narration;weird image
作者简介:陈 婵(1974-),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讲师,博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文科院中文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5-10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15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80-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25